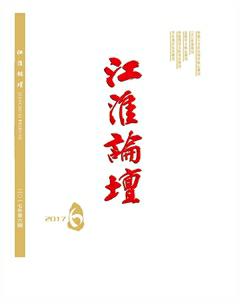基于博弈論視角的高校教師行為分析及對策研究
管春英+田軼+楊彥


摘要:將高校教師的行為界定為教學和科研方面的行為,通過構建靜態博弈模型,分析高校教師在教學和科研領域的投入數量來探討教師的行為取向。結果顯示,由于科研成果的顯性和教學成果的隱性,呈現出資源向科研領域集中、教學領域資源分配不足的狀況,從而解釋了我國高校普遍存在的“重科研、輕教學”的現象。為了減輕抑或消除教師行為偏差對教學的危害,高等學校有必要建立比較完善的激勵機制,需要建立起高校和教師的溝通機制、表達機制、認同機制和協作機制,矯正高校教師的行為偏差,將科研和教學更好地結合起來,促進高校的發展。
關鍵詞:高等學校;高校教師;教學行為;科研行為;合作博弈
中圖分類號:G46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862X(2017)06-0117-005
高等教育在我國國民教育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高校教師質量是決定高校質量和聲譽的最重要因素。[1]隨著“雙一流”建設的提速,高等學校對于高層次人才的競爭日趨激烈,紛紛采取各具特色的激勵機制吸引、培養和留住人才。由于高等學校本身及其人力資源情況的特殊性,高校與高校教師群體、高校與高校教師個體以及教師個體之間存在較為明顯的利益沖突。高校教師在教學和科研領域表現出來的行為,不僅對高校管理產生影響,同時影響到高校的發展,最終影響到高校的聲譽。通過對高校教師在教學和科研領域的行為分析,探究高校建立利益相關方參與的合作博弈機制,促進高校合理分配資源,充分調動教師的積極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一、高校教師行為的審視和博弈的內涵
高校教師不僅是知識的傳播者,也是科技進步的參與者,更是社會進步的推動者。古今中外對教師行為非常關注。在古代中國,教師行為集中體現在“傳道授業解惑”之中,由于受當時社會環境和社會價值導向的限制,教師只能將主要精力放在教學領域,“全心全意”為教學服務,“科學研究”只是業余愛好。在歐洲,文藝復興帶來了思想的開放,探究未知世界成為多數教師的興趣所在,根本不存在所謂的科研壓力。但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變遷,高校教師行為的內涵不斷發生變化,政府、社會、學生和高校本身對教師的要求越來越高。在現實生活中,科研給高校教師帶來越來越大壓力的同時,也帶來實實在在的物質和非物質利益。最近幾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位居第二位,僅次于美國,在科技領域跟隨者的邊際效應不斷遞減,發達國家在高科技領域對中國的封鎖變本加厲,社會對創新的需求越來越緊迫,對高素質勞動力的培養要求越來越高,高等學校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引領作用日益凸顯。在高校“雙一流”建設中,高校教師在教學和科研領域所表現出來的種種行為,是高校管理層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本文基于博弈論視角,就高校教師在教學和科研領域表現出來的行為進行分析。
博弈論思想在我國《孫子兵法》中早已有之,著名的田忌賽馬包含著博弈論智慧。現代博弈論最早由馮·諾依曼于1928年提出。1944年,馮·諾依曼和摩根斯坦將兩人博弈推廣到n人博弈,在經濟學領域的規范應用取得了豐碩成果,從而奠定了博弈論的基礎和理論體系。1950—1951年,約翰·福布斯·納什利用不動點定理證明了均衡點的存在,為博弈論的一般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經過萊因哈德·澤爾騰和約翰·海薩尼的推動,博弈論已發展成為一門較完善的學科,在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和教育學等領域的應用日益廣泛。博弈均衡是指使博弈參與各方實現各自認為的最大效用,即實現各方對博弈結果的滿意,但各方實際得到的效用和滿意程度是不相同的。在博弈均衡中,所有參與者在現有條件下都沒有意愿改變自己策略的這樣一種相對靜止的狀態。在博弈過程中,博弈各方的關系不僅體現一種利益上的競爭,更體現出參與各方的合作關系。博弈實質上是由動態的競爭(討價還價)到相對靜態的合作“博弈均衡”的一個變動過程,所以博弈均衡不僅是競爭的需要,也是利益相關方發展的內在要求。
博弈論在教育學研究中應用得越來越多,學者從不同視角利用博弈論對高校教師行為進行分析。張素雅和田友誼針對高校教師的利益沖突、從教行為等方面展開博弈分析,這些分析主要是定性描述,缺乏定量分析,而且對高校教師的教學和科研行為缺乏系統性的博弈分析。[2]而在現實生活中,高校教師作為特殊的知識型群體,是高校人力資源的主體架構,在知識傳授和知識生產中起著主導作用,其行為方式及產生的效果蘊含在高校整體利益中,二者具有統一性。[3]同時,高校教師群體又作為特殊的個體性存在,有自身的利益訴求,與高校既存在著利益的合作,又存在著利益的沖突,教師的行為表現與高校期望值存在偏差。王保星基于教育理論視角,總結了國外高校在教學和科研方面的做法,在教師聘任、發展和評價體系方面重塑“教學和科研相結合”的教育價值,對教師在教學和科研的行為做出引導。[4]這些教學和科研激勵機制是高等學校單方面的意思表示,有待于博弈中參與方的認同。但在集體行動中,每個參與方是從自身利益價值最大化的角度進行博弈,常常出現“囚徒困境”的局面。因此,高校制定的提升高等學校整體利益和教師個人利益的各種激勵機制需要在博弈分析的基礎上進行深入的研究。
由于教育資源的有限性,高等學校在整體利益上追求較少的資源投入獲取最大的利益,即不斷提升教育教學質量,獲取優質的生源,獲得更多的科研經費,不斷擴大自身的社會知名度等,而這些利益的獲取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賴于高素質的教師隊伍,高校教師隊伍質量的提升關系到高等學校的整體利益。李斐從高校管理視角,分析高校資源分配錯位,導致教師行為與高校發展目標存在矛盾,影響到教學和科研協調融合發展。[5]而張駿從行為經濟學視角,在高校資源受限的條件下,分析了高校教師的非理性行為。[6]對于高校教師來說,作為理性的個體,教師也有自身的利益訴求,高校教師憑借自身的腦力和體力投入,在從事教學、科研工作中也期望獲取利益。這種利益訴求可能與高校發展目標存在沖突。現實生活中出現的“重科研、輕教學”的現象就是這一沖突在高校的普遍反映。高校教師激勵的主要目標就是通過制度與措施的設計,激勵教師將個體的最大努力方向與高等學校的發展方向所表現的整體利益相一致,在實現教師所希冀目標的同時,實現高等學校整體利益的最大化。但如何協調兩者利益之間的沖突,實現“共贏”的局面,這是我國高等學校“雙一流”建設中急需探討和解決的問題。本文從博弈論視角,深度分析高校教師在教學和科研方面的行為,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建議。endprint
二、高校教師行為的博弈分析
作為一個理性的經濟人,對于高校和高校教師來說,都會追求自身利益價值最大化(效用最大化),這種利益價值既可以是物質層面的,也可以是非物質層面的。在一定時期內,外部資源是固定的,如何分配這些資源,高校和教師都會根據自身的利益訴求進行分配,在滿足自身利益價值最大化的情況下在教學和科研領域分配資源。對于高等學校來說,可以調動的資源包括資金、教學和科研設施以及獎勵等。對于高校教師來說,可以調動的資源包括資金、時間和精力,我們將這些資源統稱為投入。高校的利益價值主要體現在高校的排名、畢業生質量和高校的美譽度等領域,而高校教師的利益價值體現在經濟利益和各種榮譽層面,我們將這些利益價值統稱為產出或收入。我們將產出看成是投入的函數,設定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無論是高等學校還是高校教師,其行為所產生的后果都可以通過一定的投入或付出表達出來,在此我們借鑒張維迎的靜態博弈分析法[7],求解納什均衡。用U代表高等學校,T代表高等學校的教師,R代表科研領域,E代表教學領域,RU代表高等學校在科研領域的投入,RT代表高校教師在科研領域的投入,EU代表高等學校在教學方面的投入,ET代表高校教師在教學方面的投入。假設高等學校和高校教師支出的收益函數分別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通過對3種均衡解的分析,考慮資源的稀缺性和經濟人假設,由于科研成果的顯性和教學成果的隱性,教師對科研的重視帶來的收益要大于教學帶來的收益,教師對待教學和科研會出現不同的行為,由此帶來“重科研,輕教學”的現象在我國高等學校不同程度的顯現,即高等學校的集體理性與教師的個人理性不一致。如何平衡教學和科研,提高高等教育教學質量,需要高等學校和教師的共同參與,建立一種激勵相容機制。[9]
三、高校教師行為的協調性對策
通過高校教師行為的博弈分析,能夠清晰地描繪出目前高校教師激勵面臨的困境,教師在教學領域激勵行為不足的固有問題依然存在,亟須建立起博弈各方的溝通機制、表達機制、認同機制和協作機制,從而糾正教師的行為偏差,為“雙一流”建設提供可靠的師資力量。
(一)建立高校教師激勵機制中博弈各方的溝通機制
高校教師激勵機制過程中應避免非協作博弈行為的出現,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要建立起高校教師激勵機制中博弈各方的溝通機制,實現博弈各方對于信息的充分掌握,從而促使博弈各方能夠做出“理性”的判斷。
高校作為激勵政策制定與出臺的博弈方,需要重點把握博弈中的兩個前置性約束原則。[8]其一,激勵相容約束原則。由于高等學校對于教師的努力程度難以實現完全程度的檢測和測量,而僅能從教師的工作成果中予以反映,因而,高等學校除了通過制度設計來激勵和監督教師外,還應該注重在激勵政策制定的過程中如何將教師個體利益與高等學校整體利益相統一,實現“激勵相容”。其二,參與約束原則。即要實現教師從與高等學校訂立合同中所獲取的最大效益,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的最大效益。市場經濟的發展,促進了社會分工日益細化以及對知識需求,市場可以給高校教師這類知識型員工所提供的發展空間和機會越來越多,高等學校的教師激勵政策應當注重教師個體需求的滿足,在滿足基本的物質生活的基礎上,要探索教師個體的更高層次的需求激勵,包括職稱晉升、職務任免、個人榮譽等個人職業發展方面的激勵措施。在此基礎上,高等學校在教師激勵機制設計中應建立與廣大教師的溝通機制,在制度設計中引入廣大教師參與方式,充分發揮和利用教職工代表大會制度,通過學校教職工代表大會向廣大教師宣傳制度設計的出發點和受益面,積極做好基層教職工中的宣傳、解釋工作,并廣泛聽取學校教師的意見和建議,根據廣大教職工的意見和建議及時調整激勵政策,從而使高校教師激勵政策在制定與實施過程中博弈各方信息的對稱,增強博弈各方的期望效益。
(二)建立高校教師激勵機制中博弈各方的表達機制
高校教師激勵機制的建立離不開教師這一重要博弈方的廣泛參與,不斷健全教師利益訴求的表達機制,而這一機制建立的前提則是打破教師與高等學校之間的從屬關系,切實改變高等學校現有的師資管理體制,使高校教師能夠擁有平等的博弈地位。
由于高等學校與教師在傳統的博弈中具有主從地位,使得高等學校在教師激勵政策制定過程中掌握主動性,在較大程度上降低了教師參與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因而建立高校教師激勵機制中高校教師的表達機制,需要給予高校教師平等的博弈地位。[10]高等學校應當加強工會、教職工代表大會等組織機構在教職工利益訴求表達中的重要作用,以群體的約束力實現高等學校與教師群體在博弈過程中的平等地位。一方面,不斷鼓勵教師勇于表達自身的利益訴求,在教師激勵政策的制定、論證、實施等過程中敢于聽取教職工中的不同聲音,敞開渠道聽取廣大教師的意見和建議;另一方面,通過高校師資管理體系由權力支配型向制度規范型轉變,在不斷的對話協商中提升教師群體的“主人翁”地位,自覺尋找教師個體利益與學校整體利益的契合點,從而有效地實現高校教師激勵機制中博弈各方的“均衡博弈”。
(三)建立高校教師激勵機制中博弈各方的認同機制
高校教師激勵機制的有效建立有賴于博弈各方的目標認同,在一個博弈環境中,博弈各方作為理性個體參與其中,但各方理性的出發點往往是個體的利益,因而容易產生“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的對抗。[11]
這種均衡的實現,需要提高博弈各方的理性認知水平。為此,作為高等學校而言,應當明確設定自身的發展路線與發展目標,形成全校教職工都能夠接受并認同的“共同愿景”,并以此作為行動指南,不斷激發高校教師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并通過目標引導方式,將教師個體的利益統一到高等學校的整體利益中,從而實現教師個體利益與高校整體利益的發展方向相一致,形成合力,促進高等學校的長遠發展;對于高校教師而言,應當提升自身的歷史感和使命感,進一步明確“教書育人”的職業理想,自覺增強自身對職業的認同感和敬畏感,使高校教師在博弈中能夠正視自身的局部利益、短期利益,正確看待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之間的關系,從而主動投身于教學科研工作中,不斷提升自身的綜合實力,積極做好人才培養、科學創造以及服務社會等工作。endprint
(四)建立高校教師激勵機制中博弈各方的協作機制
高校教師激勵機制的建立中應加強博弈各方的協作機制,緩解教育資源投入的有限性與教師個體逐利行為之間的矛盾,在激勵制度建設中注重教師之間的利益協調分配制度設計,避免陷入 “零和博弈”困境。
建立高校教師激勵機制中博弈各方的協作機制,首先應當正確認識教育資源投入的有限性,這里有限性是一個相對概念,即以高等學校作為一個相對靜止的參照物,它每年的教育資源投入是有限的,但高等教育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隨著學校師資素質的不斷提高,教育教學質量的提升,以及社會知名度的擴大,學校所獲取的資源將不斷增加。[12]因而,加強高等學校教師激勵機制中博弈各方的協作機制,需要在激勵中使高校教師能夠深刻認識到個人的努力水平與學校的整體發展呈正相關,從長遠看,也與自身獲得的個人利益目標相一致。其次,要注重教師激勵過程中不恰當的利益差距問題。我國古代便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問題,高校教師作為特殊的利益群體,不僅會對個體利益在縱向上進行比較,還會對比其他教師所獲得的利益。如果付出相同努力水平的教師所獲得的利益存在差距,甚至是較大差距,那么,學校教師會在利益分配中存在嚴重的不公平感,最終導致高校教師對高等學校的激勵措施失去信心,也會使教師群體中出現分化,影響高等學校整體的激勵效用。[13]為此,高等學校應當建立起合理的激勵制度和科學的分配制度,在激勵分配制度設計中既要突出對優秀教職員工的獎勵,拉開他們與其他教師的利益差距。同時又要兼顧教師群體內部的利益差距,“在教師之間保持一種合理和動態的利益差距,堅持促進多數教師和褒揚個別優秀教師相結合或并重的策略”,只有均衡高校教師的利益分配差距,才能促進教師之間消除“零和博弈”,走向“合作博弈”。
參考文獻:
[1]孔令帥,趙蕓.美國高校新教師發展的問題與策略[J].外國教育研究,2016,43(5):28-41.
[2]張素雅,田友誼.教育變革中教師利益的沖突與協調——基于博弈論的視角[J].教育理論與實踐,2014,34(16):27-30.
[3]朱鳴雄.利益非一致性的經濟學分析[J].財經研究,2003,29(4):61-66.
[4]王保星.從“結合”走向“疏離”:大學“教學”與“科研”關系的歷史解讀[J].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刊,2011,(1):128-136.
[5]李斐.論我國高校教學與科研關系的演變與協調發展[J].高校教育管理,2015,9(1):1-5.
[6]張駿.基于行為經濟學視角的高校教師激勵措施研究[J].中國成人教育,2017,(10):32-36.
[7]張維迎.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
[8]蒲勇健,李攀藝.高校教師科研激勵機制:終身教職制度的經濟學分析[J].科技進步與對策,2006,23(4):151-153.
[9]代應,宋寒,李海燕.基于模糊層次分析的高校人才培養質量評價[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1): 127-131.
[10]鐘春玲,楊曉翔.基于期望理論的高校教師教學激勵機制優化研究[J].福建醫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13(3):51-55.
[11]丁浩,王美田.高校教師激勵的困境分析及治理路徑選擇[J].高校教育管理,2012,(1):39-43.
[12]畢憲順,楊嶺.法治視野下高校學術權力運行的規制[J].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4):113-121.
[13]易高峰.省域內高校學科論文的國際學術影響力研究[J].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4):112-116.
(責任編輯 明 篤)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