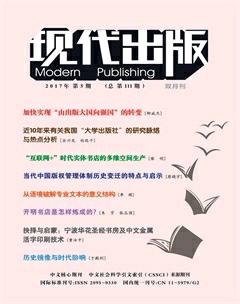我的課堂我做主
作為象牙塔里的“知識守望者”,筆者在地方本科院校新聞傳播學領域從教恰滿三年。這三年中,從一名出版學的博士畢業生到“什么課都可以拿來講”的教書機器,我教過多門新聞傳播領域的專業基礎課,但唯獨與自己的“老本行”出版學“完美”地擦肩而過。偶然的一次課堂互動,讓我有了在講臺上重新講述出版學的沖動。這次教學體驗讓我仿若在漫夜里找到一個有光的罅隙。正如《舊約·創世記》所言:“神說,要有光,于是有了光。”轉變了教學思維之后,從教心態隨之而轉,我決定去尋找這罅隙之后的光源所在。
“出版學是一個怎樣的專業?”這個問題對于非出版學的本科畢業生來說,恐怕未必是了了分明的。在有些同學看來,“新聞出版”是個被合并使用的偏義復詞,“出版”只是“新聞”付諸傳播的最后一環,為了押韻而存在的陪襯。學生對于“出版”一詞的熟稔和他們對這個行業以及相應的知識理論的無知所形成的強烈反差令我反思。
從教第一年,我曾在《媒介經營與管理》課程的期末安排新聞學、廣告學、廣播電視學三個專業的本科生分別組建卜7人次的團隊,開展“媒體公司模擬運營”的課內實驗。在所有團隊中有個“單兵作戰”—人組的同學提出的策劃案是“開辦一家出版社”,甚至連社址和注冊資金都列出來了。我開始以為該同學對于出版系統的“無知”當屬個案,只是反問他是否做過市場調查,知不知道現有多少家出版社?誰料想,這位同學以及其他近百位學生,表示并不知曉,甚至不少同學認為:“最起碼上千家”。再問:出版社和圖書出版公司有什么區別?答案五花八門,最響亮的聲潮涌向耳畔:“出版社是出雜志的,圖書出版公司是出書的”。
我在講臺上聽得膽戰心驚,一方面嗅悔自己過于信奉教材所提挈的大綱體系,在理論教學環節一板一眼地按照虛化而空泛的大媒介觀講述媒介市場、媒介受眾、媒介組織、媒介財務、媒介規制等“萬金油”式的知識點;一方面在案例教學專題方面只是單純以講故事的方式講述諸如“劉波與誠成文化”這類典型的媒介經營管理案例,卻并沒有特別針對案例背后的媒介機構特點進行點評或是原理的清理。以致讓他們有了這種“學理論就是為了考場用,上課聽故事才更來勁”的分裂式思維,理論與實務“兩張皮”,油與水互不相侵。在這樣一個“段子手”型教師備受追捧的教學時尚下,教師的個人魅力、教學風格對于調動學生的學習熱情可以說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怎樣扭轉學生們“講故事的時候才會抬起頭”的現狀,我想以后不妨試試將計就計,“以故事為餌”。
慶幸的是,距離學期末還有兩次課的機會可以彌補。我在接下來的課程里給大家集中講解了出版社、圖書出版公司以及新書書店、獨立書店等一些出版界構成的基本原理。課下不少同學向我追問并反饋,表示他們非常希望聽到更多這樣的“新鮮事兒”,這是他們在其他課程中聞所未聞的。
吸取了教訓,在第二次講授《媒介經營與管理》課程時(該年份所涉專業在此前基礎上又增添了網絡與新媒體方向),我有意識地按照媒介機構的類別展開專題,一改之前的“泛媒介”講述思路,希望從較為具體的層次為學生搭建媒介機構的系統知識并梳理不同媒介機構的運作模式,盡量做到“由故事引發興趣,但務必將視線拉回理論的譜系”。其中“出版經營與管理”的專題作為傳統媒體經營的代表被放在了課程的開篇部分。后來,這竟成了學生們最愛聽的部分。從學生們的課堂表現以及課后反饋,我感受到這一調整或許有某種內在的合理性。對于廣播電視、網絡新媒體、廣告公司,學生們已從其他專業課程中學有所獲,而出版行業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新大陸”。
我在出版經營與管理專題里帶領大家從讀每一本書的“準生證”——版權頁開始,講述一本書是如何歷經“十月懷胎”得以問世的;并以當年的熱詞“IP劇”為線索為大家梳理整個版權鏈條的源流和價值實現,讓他們知曉“出版”并非是他們刻板印象中那樣一個“老掉牙”的傳統專業;我還告訴大家如何以出版社的線索去尋找專業性圖書,如何在茫茫書海里有技巧、有效率而非撞大運般邂逅到你最鐘意的那份共鳴;在獨立書店的專題里,我為大家展示了所在城市的文藝范兒書店,同學們課下很快就按圖索驥,并在近距離感受這份“獨立”之精神品質的同時,對我所講的“無論是買一杯咖啡,還是一本書,都是一種支持”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有位同學在我沒講這個專題之前就曾偶然闖進過城市里這樣的別致空間,但他當時并不知道這種書店是以“獨立”堅守并著稱的。課程結束的時候他告訴我,當他明白這種獨立的存在不僅僅是出于商業性之后,他每一次再去到這樣的小店,每拿起那里的經過店主人二次汰選的書籍,都有種別樣的珍重情愫。兩年之后,這位同學考取了省內一所高校的研究生,讀上了他所向往的編輯出版專業。
雖然這樣的故事聽起來像是生硬而蹩腳的“插入廣告”,但對于真實的個體案例而言,這既不是勵志的雞湯,也不是逃避就業的避風港,而是在經過四年系統的專業教育之后,對自己興趣方向的一次細化和微調。據我觀察,這樣的興趣導向型案例,在我們這類壓根沒有開設過出版學課程的高校并不常見,盡管編輯出版學位列本科專業的二級學科,但在大多數新聞傳播院系的學科基礎課程中或因師資結構或因辦學特色所限而并沒有設置相關的教學內容,也并不是每位老師都在課程設置里或自覺或如我般偶然地加入關于出版學專業的知識體系,這也有可能意味著,除非學生在實習實踐的訓練環節里有所接觸,否則很難有機會對出版專業有一個大致的認識,更奢談興趣。
反觀我所教的這三個專業本科生在整個大學期問的課程設置,除去大一期間諸如新聞學概論、傳播學概論、廣告學概論之類的共修課,在完成專業分流之后就開始了各自的專業基礎課程學習。整個課程設置里不僅全然不見“出版”的字眼,而且在各個專業基礎課程中也少有足以容納或輻射出版學意涵的課程體系。這對于新聞傳播學科的學生來說無疑是個認知的短板,我通過課下與學生的隨機談話得知,他們拿到畢業證之前必須獲得社會實踐的分數,所以每一個人都有過前往報社、電視臺、電臺、網站、廣告類新媒體公司的實習經歷,但唯獨沒有一個人去過出版社。這一方面是因為出版單位門檻高,無論是招聘員工還是實習生,均要求研究生學歷以上,(個人認為所謂的“門檻高”的背后,倘或是因為這類工作的價值創造更多依附于個體的知識水平、資源人脈,而并不需要很多諸如“實習生”這樣的廉價勞動力去跑腿或幫工);另一方面也是囿于區域性出版資源的分布不均,地方高校的學生只得面對僧多粥少的現實。
這就是我在一線教學崗位工作中所感受到的,學生們對于出版行業的“驚人無知以及濃厚興趣”。如果說這種“興趣”里有私心,我想在此與諸位分享一位曾旁聽我這門課的傳媒經濟學研究生對我的傾訴,她認為自己畢業后最理想的去向就是出版社,原因是“如果去那些本科生都能進去的單位,那豈不是白讀了這個研究生?”雖然直白,但似乎恰恰隱晦地暗示了當前不同媒體機構對于學歷的“隱形門檻”。
我并沒有做過精確的調查,有多大比例的出版專業研究生是憑借著校內社團、校外實踐或是參加工作的緣由接觸并認識到這個專業,然后在這種“行先于知,由行致知”的驅動力下和出版專業結下不解之緣。但通過三年來的一線教學觀察,我幾乎每年都能聽到一兩個這樣的故事——或是因為自發的興趣指引,或是偶然的機緣,走向出版學專業的研究生道路。用一位考研被調劑到出版專業的我們的畢業生的話,“沒想到出版專業這么有趣”,我在一次學術會議上與她偶遇時,她對自己當年被調劑專業的慶幸溢于言表。并不否認,也許這種所謂的“有趣”可能只是源白初涉另一個“圍城”的短暫新鮮感,然而,這種“陌生化”的印象也從另一層面暗示了出版學專業與同屬二級學科的其他專業在知識體系構成上的顯著差異,以及“新聞
信息”生產規律與“知識
內容”生產規律的本質差別。
反觀我們當下的新聞與傳播學專業本科目錄,編輯出版學專業前有新聞學、傳播學這樣早已納入西方主流知識體系、有著成熟建制的傳統學科;后有如網絡與新媒體、數字出版這樣聽起來更加“時髦”的新設專業。編輯出版學雖然歷史不短,可謂中國特色的“傳播學”,但其學理根基卻非常薄弱,缺乏學科共識與規范。單從教材來看,雖然也陸續出版了幾本名之為《出版學概論》的書籍,但在教學使用上仍舊缺乏共同認識,難免陷入“自說自話”的尷尬。學界內部尚未制定出標準或范本,又憑何奢談在新聞傳播學本科生中間普遍推廣并設立諸如《出版學概論》這樣的課程呢?
在當前課程范式改革、翻轉課堂等概念不斷涌向大學校園的同時,教師的“主觀能動性”得到了空前的放大,倘若由不同老師來上同一門課,學生們的反響很有可能就是“這是同一門課嗎?”“我的課堂我做主”這一趨勢似乎令課程之問的內涵和外延漸趨模糊了,雖然有課程體系的固攝,但難免有交叉和重復之處,作為教齡尚淺的“青椒”,上述不成熟的“教學實驗”,只能不斷地拿學生當“小白鼠”,期問種種不如法處,有愧疚也有遺感。然而,我所清醒的是,總算是在課程與課程之間“活動的板塊”處真的發現了罅隙,并盡可能地修修補補以令其嚙合地更加圓融一些。然而,如我般“仰望星空”的井底之蛙,更深切的祈盼或許在于,那些光源能夠“自上而下”地令學生們“醍醐灌頂”,而并非是從這些“罅隙”而來。
(李瑞,河南財經政法大學文化傳播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