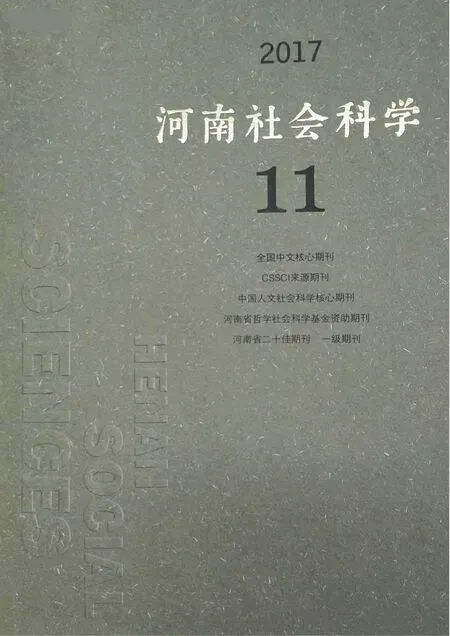當前中國國際貿易特點與全球定位
王佃利,孫海云
(山東大學 管理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0)
當前中國國際貿易特點與全球定位
王佃利1,孫海云2
(山東大學 管理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0)
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參與國際化分工是各個國家發展的必然趨勢。全球價值鏈分工是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的表現形式。通過介紹全球價值鏈體系,闡述中國國際貿易的新特點,表明在經濟發展的同時,貿易壁壘同樣是阻礙經濟發展的障礙,為提高國際競爭力需強化產業升級,增強綜合經濟實力。依據中國在全球價值鏈分工視角中的全球定位,結合中國大國情形的實際情況,根據勞動力、市場、資源等比較優勢與技術提高、產業優化后的后發優勢相結合的原則,對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進行重新定位,提出技術密集型產業是今后發展的關鍵。要充分利用比較優勢與后發優勢,不斷提高中國的綜合競爭力。
全球價值鏈分工;國際貿易;中國;綜合競爭力;全球定位
一、引言
伴隨著科技的進步,世界經濟正步入全球化發展階段。國際貿易以一種全新的模式引領各個國家的經濟發展[1]。全球價值鏈與國際貿易息息相關,全球價值鏈的分工影響著國際貿易的發展方向。在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國際貿易活動中,中國的國際貿易以其特有的豐富資源、獨特區域,在經濟全球化發展中占有一定優勢[2]。發揮勞動密集型產業優勢是中國發展初期的有利優勢,而隨著科技的進步,技術型產業日益崛起,重視科技進步、吸引外資企業是實現經濟發展的有效途徑。
全球價值鏈分工指一種產品生產過程是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分工生產完成的,包括連接生產、銷售、回收處理等過程的全球性網絡組織,該組織涉及原材料的采購、運輸,產品加工、分銷,最終到消費、回收等環節,是在知識經濟背景下實現經濟全球化的表現形式之一[3]。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實質是全球多個價值環節的鏈接,而非單一價值鏈創造價值。由于全球價值鏈存在價值等級劃分,因此并不意味著每一個環節都能創造同等重要的價值。價值鏈分工包含生產同一商品存在多道工序、不同環節、不同技術組裝零件以及不同增值能力等,將優質資源綜合利用實現資源利用的最大化,充分提取各個地區的優勢構成網絡組織進而形成全球價值鏈[4]。從空間角度而言,全球價值鏈分工存在一定的特定性,將特定組織與具有競爭力的優秀企業聯合起來,利用多國的優質資源形成整個生產供應系統,實現不同價值等級的不同區位選擇。
二、當前中國國際貿易特點
(一)貿易投資一體化——以外商投資企業占主導地位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全球性的資源配置表現出極強的活力。以跨國公司為主導按照全球價值鏈分工的方式推動新型產業迅速發展成為主流[5]。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對外貿易不斷發展,跨國公司作為一種新元素促進了中國對外貿易迅猛發展。
截至2016年年底,我國跨國公司貿易額達23524.88億美元。伴隨著外商投資規模的逐漸擴大,貿易效應增長顯著,特別是外商直接投資的外貿出口額急劇增長。
隨著外商投資額的不斷增加,我國進出口總額不斷增加,外貿進出口總額比例不斷上漲,從而促進我國外貿規模的進一步擴大。我國對外貿易額由2000年的4742.6億美元增長到2016年的52521.2億美元,2016年外商投資企業對外貿易額首次超過國內企業,成為出口貿易的第一力量。經驗表明,外商投資企業數量與進出口額度成正比,隨著外商投資企業數量的增加,我國進出口總額隨之增加。外商利用中國豐富的各種資源,來料加工產業迅速發展,憑借貿易創造效應與市場擴張模式,推動企業經濟效率的增長,有效帶動了國內經濟的迅速發展。
(二)國際貿易拉動經濟增長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我國經濟呈現不斷上升趨勢。雖然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時,各國經濟持續衰退[6],而我國仍然保持超過8%的經濟增長率,由此說明,我國雄厚的經濟基礎。當前我國對外貿易優勢主要表現在制造業方面,隨著技術的引進,科技產品數量增加,如汽車、電子、機械等,成熟的技術支持形成勞動密集型產業,進一步促進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7]。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立之后,中國多元化的經濟發展形式促進各個貿易國相互合作,中國積極參與國際貿易新體系建設,從多個角度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實現貿易共贏、實現貿易多元化國際貿易有效帶動了國內經濟增長[8]。
(三)貿易結構向服務貿易與技術貿易方向發展
實現我國“后發優勢”主要依靠研發能力的提高,進而提升我國的綜合國際競爭力[9]。2016年,國務院將成都列為西部首個國家級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城市。此后成都高鐵設計出口、國航發動機維修相關信息、文化服務都獲得較高收入,其中高鐵服務總收益人民幣780億元、國航維修服務超過3億美元,大大推動了西部地區的服務貿易全面發展。運用新技術、新模式,建立公眾開發者的眾包平臺是2016年成都市發展服務貿易的重點[10]。自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服務貿易得以迅速發展。在2001—2017年間,中國的專利服務、咨詢服務、計算機服務等的出口額增長了3倍、2.2倍、4倍。隨著海外市場的不斷開發,運輸、旅游等傳統服務貿易發展更加迅猛。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1年到2017年的數據得到我國服務貿易額度的走勢圖,如圖1所示。
由圖1可知,自2001年起,我國加入WTO以來,服務貿易呈現持續上漲態勢,年增長率達到19.88%,超過全球平均水平,實現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生產加工制造業大大帶動了交通、租賃等服務行業的發展,居民收入的增加帶動醫療、教育、旅游等傳統消費型服務業的發展。可見與國際市場的接軌是推動中國發展的強大動力。

圖1 2001—2017年中國服務貿易走勢圖 (單位:億美元)
(四)國際貿易壁壘愈演愈烈
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進出口貿易國家,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同樣遭到多國貿易保護主義的反傾銷、反補貼等措施,是遭受貿易摩擦的最大受害者,其涉及的制造業、新興產業遭到的創傷很大,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到來,中國的國際貿易摩擦仍然存在。
1.國際貿易摩擦強度不斷增大
截至2016年年底,海關統計資料顯示,我國的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達到24.33萬億元人民幣,其中出口總額為13.84萬億元,進口總額達到10.49萬億元。在與貿易伙伴的雙邊貿易中,新興起的國家勁頭加強,但主要還是針對歐美、東南亞等國家聯盟[11]。如此巨大的貿易交易量必然存在眾多的貿易摩擦。截至2016年年底,中國共遭遇來自27個國家(地區)發起的119起貿易救濟調查案,其中反傾銷的91起,反補貼的19起,保障措施9起,總計涉及金額達到143.4億美元,跟上年相比,案件數量與涉及金額同比分別上升36.8%、76%。2016年我國遭遇的貿易摩擦數量刷新了紀錄。多半經濟案件針對中國的鋼鐵產品,包括21個國家發起對中國的鋼鐵立案調查,涉及金額78.95億美元。貿易摩擦的背后反映的是“搶飯碗”的問題,由此反映出中國產業重合以及面臨的雙重摩擦問題。
2.貿易摩擦涉及的產業領域增多
2016年針對我國鋼鐵行業的調查49起,涉及金額78.95億美元,由此數據可知,中國的貿易摩擦主要體現在生產制造業上[12],如輕工、紡織等產業。我國優勢日益減弱,高精端產業的匱乏導致我國的競爭力有所下降,特別是東南亞等地的發展導致我國紡織等行業出口進程緩慢。在產業結構升級的當代,光伏、機電等產業領域受發達國家產業結構重合的影響,遭受新的貿易壁壘越來越多。同時,電子信息等新興產業也是貿易摩擦的多發領域,比如新一代移動通信、新型的顯示器材、軟件開發等領域,最具代表性的有中國臺灣的富士康、烽火科技以及長飛光纜等企業。隨著產業結構的升級轉化,全球價值鏈分工日益明顯,新興產業在發展對外貿易的同時,更加注重產業優化。但由于受發達國家的扼制,我國新興產業進出口貿易摩擦不斷增加。美國曾經一度限制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隨著新興產業的不斷發展,美國對中國的責難轉向新興產業以及高精端產品的制造領域。由此可見,隨著產業升級,我國遭遇到的貿易摩擦也不斷增多。
3.根據貿易摩擦針對性的救濟措施增多
針對目前我國遭受到的貿易摩擦特點,我國相應地采取反傾銷調查、反補貼調查、反規避調查等貿易救濟措施。近年,在WTO內部,歐美國家展開對中國產品的反傾銷、反補貼調查,例如2016年美國對中國采取13項反傾銷措施,中國將美國告上世貿組織,最終專家組審查報告裁定,中方勝訴,支持中國主要的訴訟請求,美國的13項反傾銷措施違反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由此,中國在反傾銷案方面積累了諸多經驗。其次,自貿區談判也成為減少貿易摩擦的重要手段。中國在自貿區談判方面做了相當多的努力,90%以上的商品實現了零關稅,從而大大減少貿易摩擦的產生。近年,技術性貿易壁壘呈上升趨勢,主要涉及《技術性貿易壁壘協定》以及《實施衛生與動物衛生措施協定》,眾多發達國家以保衛本國居民健康為借口制定眾多貿易壁壘,限制進口商品保護本國企業。歐盟技術性貿易壁壘是該特征的典型案例,歐盟出臺的“歐盟REACH法規新規”就屬于典型的技術性貿易壁壘措施,中國等國家的產品面臨技術標準這一重要難題。
4.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摩擦增多
伴隨著新興起的發展中國家的崛起,貿易格局悄然發生變化。與發達國家的貿易往來已經無法滿足中國面對當今國際貿易的形勢及內需,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得到了中國發展雙邊貿易的關注,“金磚五國”是典型的發展中國家保持貿易往來的典范,新興發展中國家成為中國發展對外貿易的重要貿易伙伴[13]。隨著貿易往來的增加,貿易摩擦必然產生。例如中國與印度的貿易摩擦成為當今我國對外貿易關注的重點。自2008年金融危機開始,印度對我國發起的反傾銷措施多達12起,2010年印度對我國的鋼鐵、機電、建材、食品化工等領域均發起反傾銷措施。與此同時,阿根廷與巴西等發展中國家對我國的貿易壁壘日益增加。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雙向夾擊下,中國的貿易轉型局面不容樂觀。
三、全球價值鏈分工視角下中國國際貿易全球定位
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下,中國產業國際競爭力挑戰與機遇并存。隨著國際生產體系的轉變,決定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獲利的條件不能再依賴于進出口,應取決于參與國際分工的層次,對價值鏈的控制能力等因素,由此必須將中國的國際分工模式重新定位以帶動產業結構不斷升級,促進國際貿易的全面發展。
(一)定位原則
1.中國參與國際分工的模式單一
在改革開放大門打開之前,中國的經濟發展主要依賴于重工業,由此產生資源配置不均,資源利用效率低下,環境污染嚴重等問題[14]。在改革開放之后,中國摒棄了傳統的以破壞環境為代價的重工業,從發展對外貿易角度出發,優先發展出口產業,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發揮我國的資源優勢發展對外經濟貿易。伴隨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2001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更大程度上融入世界經濟及國際分工的層次中來。隨著外商投資企業大批擁入,依靠我國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地區資源優勢,生產加工貿易得到迅速發展,中國在國際貿易格局中逐漸站穩腳跟,在發展的同時,產業競爭力得到了明顯提高。毋庸置疑,國際資本流動對一國經濟而言猶如雙刃劍,在促進經濟蓬勃發展的同時也加大了經濟波動的風險[15]。隨著跨國公司的不斷建立,依賴于廉價勞動力使我國處于劣勢地位,貿易條件隨之惡化,進而推動產業升級。
2.單一模式轉變的必然性
對中國參與國際分工的模式進行重新定位,以提升產業結構、提高國際競爭力。是否繼續堅持比較優勢是當前發展模式討論的重點[16]。有人認為摒棄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的比較優勢,追逐本身并不擅長的技術密集型產業不是明智之舉,由此產生的后果是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經濟發展緩慢。在經濟全球化的當下應堅持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依靠國內優勢提高國際競爭力。另有人提出應考慮國家經濟安全與比較利益,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重點發展資本投資產業,利用好后發優勢,培養創新型人才提升國際競爭力。以勞動密集產業為主要出口對象的貿易結構已經不能滿足國家貿易發展需要,貿易條件的局限性必然導致發展空間的縮小,因此,發展資本、技術型產業才是當前我國產業提升的有效途徑。
通過兩種不同觀點的比較,說明在全球價值鏈分工的視角下,中國的國際貿易發展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較優勢發展模式的缺點在于過于突出一定要素成本,把優勢要素等同于產業優勢來看待,忽視了其他發展產業的因素,如果按照比較優勢發展貿易必將導致與發達國家的貧富差距更加擴大。以后發優勢發展產業對于中國現實國情而言存在局限性,我國處于發展中國家行列,技術、資本等還不能與發達國家相提并論,因此不能光追求趕超而忽略現實。
(二)定位原則的相關理論
中國產業要發展必須從本國的實際出發,正確看待中國當下所處的國情,可以利用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及后發優勢來發展產業,從確定在全球價值鏈的位置出發,依據中國的大國背景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順利發展。
1.將大國優勢作為發展的重點
按照經濟學范式“大國情”與“小國情”的情形,針對我國的實際情況而言,我國屬于大國情形,指的是按照產品的供給能力及消費能力來判斷的,按照對產品進出口情況能否影響市場價格決定國情發展。中國的特點實屬大國國情,在國土面積、人口規模上看是必然的。眾多發展中的小國,根據經濟制度、技術水平等方面來發展并提高國際競爭力。我國的大國情形必對周邊小國造成一定影響,使得我國在發展產業升級時考慮得更多。
(1)生產力轉移優勢。大國情形存在經濟發展不均衡情況,人均分布不均衡、資源配置不均衡,地區政策差異等都會引起區域經濟發展不均衡情況。我國的國內發展主要表現在由城市發展帶動農村發展,由東部經濟發展迅速地區帶動中西部經濟發展較慢地區。根據比較優勢的理論分析,在大國情形下經濟發展不均衡是產業升級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各地區的技術水平、勞動力資源、資本等要素差異較大導致產業結構升級過程較為復雜,但有利于推動各個地區生產力的推進。根據各個地區生產力資源優勢進行合理配置,實現地區經濟均衡合理發展。發達地區的生產能力較強,可將生產要素向欠發達地區推進,縮小地區發展差距滿足市場需求實現全國經濟均衡發展目標進而提高國家的總體競爭力。
(2)多層次參與分工優勢。依據各地區資源與生產力狀況,按照比較優勢選擇適合地區發展的分工結構。從分工結構可劃分為勞動、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有利于擺脫單一型分工體系,實現地區合作共贏。在全球價值鏈分工的背景下,根據大國情形不同地區的產業差異依據自身比較優勢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為各地區參與國際分工創造了機會和空間,同時擴大了中國產業在國際市場格局中的份額,提高了綜合競爭力。
(3)市場及規模經濟優勢。隨著市場經濟時代的到來,市場購買力可以影響市場規模。作為大國情形的中國,市場規模大,自然市場需求層次比較繁多。根據我國人口總數可知市場規模巨大,然而經濟發展的不均衡導致人均收入差異較大,對市場需求的層次不同。世界各國通信企業、航空制造業都享有中國市場的發展便利,為其提供一定的市場滿足需求。有專家表示,中國市場規模巨大有利于低收入地區發展規模化經濟,實現工業發展的多樣性。市場規模優勢可以促進規模經濟的有效運行,但是規模經濟與市場規模并沒有絕對效應,經濟發展還要依靠生產力的提高及經濟制度的決策。
(4)加強后發優勢。根據中國國情,資源豐富、勞動力資源充足為后發優勢提供了條件,可有效地整合資源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大國情形的主要特征可以為經濟發展提供有力幫助。這些后發優勢可以有效地吸引外資、技術利用中國廉價勞動力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不僅滿足人們的就業需求,還可以使傳統產業得到提升。大力培養自主創新型人才,利用科技知識實現對新興產業的創新發展。
2.比較、后發優勢與競爭優勢并舉
(1)后發優勢是比較優勢演進的動力。比較優勢是經過長期演進形成的,在當代世界競爭中,傳統比較優勢在完全競爭化的環境下不存在經濟規模效應、不存在產品質量好壞、不存在價格的高低,因此競爭優勢與比較優勢是同樣概念[17]。然而,在當代國際競爭格局中,規模經濟、產品質量及附加值是參與競爭所考慮的必要因素,由于勞動密集型產業是通過比較優勢的勞動力資源來發展的,與競爭優勢是不同的,比較優勢不等同于競爭優勢,因此擁有比較優勢的企業并不代表也具有競爭優勢,只能說潛在的比較優勢經過努力可以轉化為競爭優勢,這需要一個復雜的演進過程,同時應考慮自身企業的實際生產經營狀況是否滿足實現生成生產新要素的條件,只有提高競爭能力,才能形成競爭優勢。
(2)比較優勢是后發優勢的基礎。“追趕假說”是由艾布拉莫威茨(Abramovitz)提出的,他指出:一個國家的初級經濟發展水平與這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是成反比的。有此項假說可知,每個發展中國家必將超越發達國家,但是,世界發展的當下,當今的實際發展情況并非如此。當今社會,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但艾布拉莫威茨也提出“潛在”與“實際”的差別,“追趕假說”只是潛在而不是實際情況,實際差距是現實存在的,一方面由于科技的差距,后起國家的科技水平與發達國家還存在一定差距;另一方面,社會能力有限,教育、科技、政治、制度等多方面影響,導致經濟發展緩慢,現實差距拉大。
后發優勢既是優勢又是劣勢,關鍵在于怎樣利用人的能力轉換成創造社會的能力,對于后發國家而言,社會能力是經過后天努力形成的,是以經濟基礎為根本發展起來的。相對而言,比較優勢是通過對外開放的初始狀態形成的。運用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為積累資本、培養人才、提高技術水平提供可靠條件。在知識帶動經濟的時代,后發優勢是通過學習和積累形成的,通過對所學進行創新改造形成后發優勢。相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比較優勢是通過為勞動者創造學習機會培養學習能力掌握先進技術實現對本土的改造。因此,后發國家是通過學習發達國家的模式,積累經驗形成的創新過程。企業通過對先進技術的學習運用,生產高科技產品,使資源得到充分利用,加快經濟發展。
(3)比較優勢與后發優勢最終形成競爭優勢。在當代競爭形勢下,優勢利用是參與國際競爭的有效途徑。通過對比較優勢與后發優勢的有效利用形成競爭優勢,實現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完全競爭條件下,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相對統一,是傳統優勢在國際競爭中占有不可抗拒的地位。而當下不完全競爭環境下,比較優勢是相對獨立的,競爭優勢是通過后發優勢推動比較優勢形成的,在二者相互作用下形成一個國家特有的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競爭優勢。一個國家需要發展經濟必然離不開科技知識,而這些知識的獲取恰恰是通過學習積累發達國家的優勢得來的,形成后發優勢,結合本國比較優勢形成強大的競爭優勢,在充分發揮生產能力、創造能力的基礎上實現綜合競爭力的提高。
(三)基于優勢組合的重新定位
1.比較優勢成為我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理論基礎
(1)比較優勢是全球價值鏈分工理論的基礎。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資源集中化是實現價值鏈分工的首要環節,降低成本、獲取利益是價值鏈分工的目的。從價值鏈分工角度來看,各個環節對于生產要素的不同需求為各個國家的比較優勢提供基礎條件。在相互分工、相互合作的前提下,國際共同合作完成生產的全部環節。我國根據自身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參與世界市場的貿易往來,利用資源優勢及比較優勢實現競爭優勢。
(2)現實國情決定基礎地位。按照當下我國國情來看,在未來的發展階段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將比較優勢作為我國發展國際貿易的基礎,勞動要素是比較優勢的重要因素。隨著科技水平的顯著提高,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呈現“質高價廉量大”的趨勢,性價比提升使得比較優勢的特點更加突出。勞動密集型產業使得勞動力就業問題得到解決,我國參與國際分工的方式主要依靠勞動力不會改變。假如不從我國國情出發,忽略勞動力與資源要素,將技術密集型產業放在發展的首位必將付出高昂的代價,使得經濟發展放緩,扭曲中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因此從國家實情出發,走中低端路線才是我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合理途徑。
(3)比較優勢動態化是參與國際分工的原則。當前國際競爭激烈,保持動態化是比較優勢推動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的有效模式。如果我國參與國際分工的演進模式靜止不變,在一段時間內可以獲得經濟利益,但完全依賴于外資企業是不利于我國參與國際分工形式的,造成低水平的分工模式,使得我國的發展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然而比較優勢動態化可以擴大我國勞動力的效應,擴大貿易規模,優化貿易結構,在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原則上發揮比較優勢,培育、創新比較優勢,使其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得到升級。
(4)我國勞動力比較優勢的全新定位。從我國國情來看,廉價、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是我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比較優勢。但從實際生產的角度而言,生產效率低、資源浪費、品牌質量差、營銷手段落后等問題大大降低了勞動力的優勢地位。從我國國情出發,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依然是我國參與國際分工的基礎,通過降低勞動力成本實現與技術、資本及知識產權相結合的優勢。由于我國在經濟發展初始階段經過積累優勢資源實現了與其他非優勢資源的結合,提高了綜合生產效率。利用先進新技術實現產品創新,提高產品質量,增加產品種類以提高單位產品價格,增加收益,有效防止單一商品價格惡化,影響產業結構對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市場優勢。
2.后發優勢成為我國在價值鏈分工中提升的必然因素
(1)后發優勢是提升我國實現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優勢原則。在當今全球價值鏈分工中,對于發達國家而言傳統產業的地位已經形成,發達國家處于全球價值鏈分工最高位置,發展中國家依附于發達國家,趕不上發達國家的經濟地位。在比較優勢的原則下根據我國具體情況是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必然趨勢。在追求比較優勢的前提下同樣重視非勞動資源的后發優勢,通過后發優勢與比較優勢統一結合才能實現技術進步、產業升級,使高新技術產業迅速發展,提高科技產品質量,為市場提供高精端產品,同時令國家的國際貿易地位得到提高。地位提高有利于更大強度地吸引外資,利用有限資源創造無限價值,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滿足人們的生活需求,加快我國向發達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的地位攀升。
(2)全球價值鏈分工為后發優勢發揮提供便利。伴隨著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產生,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貿易往來日益增多,跨國公司作為國際自由流動的生產要素可幫助發展中國家克服經濟發展中出現的資金鏈斷裂、人才稀少、制度不合理、市場雜亂等諸多問題,成為后起國家發揮比較優勢的有利平臺。根據我國國情,以后發優勢深入發展知識產業,抓住后發優勢帶來的優勢,吸取先進技術用于加工貿易,推進產業結構傳導型優勢,對于改善我國國際競爭力具有重要作用。
3.大國情形下發展比較優勢與后發優勢相結合
(1)大國情形下發展比較優勢與后發優勢相結合。我國作為參與國際分工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參與分工的目的符合自身發展目標及競爭態勢。經濟規模擴大導致參與國際競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在較長時間內帶動全國經濟的發展。由此可知,我國作為大國國情的發展中國家有必要占領更多的市場份額,從發達國家學習先進的科技,培育新產品,發展新型產業,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我國在國際競爭中占有優勢,發揮大國資源優勢,發展內外資源相結合的優勢,構建完整的經濟發展體系。在全球貧富差距拉大的情形下,大的國家為了自身發展愿意讓小的國家依附于自己,保證大國對小國經濟的掌控。而作為大國的中國卻與之意愿相反,中國不走依附路線,不會做發達國家的經濟附庸,保持產業發展的自主權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根本;充分利用局部資源、發揮后發優勢來取得國際分工中的經濟利益;在當前國際環境下,擁有自身比較優勢是參與國際競爭的關鍵。因此,我國必須加強科技教育,培養科技人才,完善創新產業結構,實現國際分工中比較優勢與后發優勢的結合。
(2)我國工業化發展的特殊要求。工業文明時代的到來,使得我國步入工業化階段,當前的工業中級階段是落后于發達國家的階段。作為后發優勢的新型工業化應運而生,實現了自然資源向經濟資源的轉換,有效促進產業升級。對于后起國家而言,產業結構的轉變一般經歷資源型向技術型的轉化。我國的工業化特征,一是處于初級階段,勞動密集型產業占主導地位,憑借勞動力低成本優勢吸引外資。二是我國產業向信息化推進,技術型產品數量增加,向技術密集型產品行列邁進。由此可見,發揮比較優勢積累資金,發揮后發優勢積累資源,實現中國向新型工業化的邁進。
(3)大國優勢是發展的強大后盾。我國擁有豐富的資源、大型市場需求、廉價勞動力等優勢,吸引跨國公司“駛入”中國。充分利用跨國公司帶來的先進生產技術,發揮我國比較優勢及后發優勢,提高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促進國際貿易額增加。掌握關鍵技術是發展大國經濟的關鍵,對構建創新型企業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總之,全球價值鏈分工是實現經濟全球化的有效路徑。通過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實現我國國際貿易的發展,是我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方式。我國國際貿易特點呈現多樣性:外商投資企業占主導地位;參與國際貿易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方面;服務貿易與技術貿易是今后發展國際貿易的主要方向;國際貿易壁壘愈演愈烈。對我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國際地位進行重新確定,主要從我國大國情形出發,根據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結構的優勢進行闡述,在掌握科學技術、提高技術產品質量、完善產業升級等方面的后發優勢相結合,產生競爭優勢,實現比較優勢的動態演變及升級,提高我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國際地位。
[1]楊繼軍,范從來.“中國制造”對全球經濟“大穩健”的影響——基于價值鏈的實證檢驗[J].中國社會科學,2015,(10):92—113+205—206.
[2]尹偉華.全球價值鏈視角下中日制造業國際競爭力的比較分析[J].國際經貿探索,2016,(6):58—70.
[3]Jhawar A,Garg S K,Khera S N.Improving Logistics Performance through Investmentsand Policy Intervention:A CausalLoop Model[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d Quality Management,2017,(3):363—391.
[4]杜傳忠,張麗.中國工業制成品出口的國內技術復雜度測算及其動態變遷——基于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的視角[J].中國工業經濟,2013,(12):52—64.
[5]林建勇,洪俊杰.全球貿易發展的趨勢與特點——兼論中國外貿發展新策略[J].現代管理科學,2016,(10):73—75.
[6]Martel A,Klibi W.Supply Chains:Issues and Opportunities[M].Designing Value-Creating Supply Chain Networks.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6.
[7]Mangan J,Lalwani C,Lalwani C L.Global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M].John Wiley&Sons,2016.
[8]張躍勝.基于區域分工與合作的生態補償機制設計[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學報),2016,(3):67-72.
[9]王原雪,張二震.全球價值鏈視角下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及中國的策略[J].南京社會科學,2016,(8):10—17.
[10]盧福財,羅瑞榮.全球價值鏈分工條件下產業高度與人力資源的關系——以中國第二產業為例[J].中國工業經濟,2010,(8):76—86.
[11]Lu Y,Sun S L,Chen Y.Global Value Chain Embeddedness and Latecomer's Productivity:Examining the Springboard Perspective[R].2016.
[12]李佳.論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對公共利益條款的解釋——以對專利權主張實體的管制為落腳點[J].河南社會科學,2016,(2):64—69.
[13]李曉華.國際產業分工格局與中國分工地位發展趨勢[J].國際經貿探索,2015,(6):4—17.
[14]李宏艷,王嵐.全球價值鏈視角下的貿易利益:研究進展述評[J].國際貿易問題,2015,(5):103—114.
[15]鄭璇.新興市場國家國際資本流動突然中斷的形成機理研究——基于信息不對稱的視角[J].理論與改革,2015,(6):81—84.
[16]王俊,楊恬恬.全球價值鏈、附加值貿易與中美貿易利益測度[J].上海經濟研究,2015,(7):115—128.
[17]Sturgeon T,Kawakami M.Global value chains in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was the crisis a window of opportunity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R].Global Value Chains in a Postcrisis World,Washington,DC:The World Bank,2010.
Features and Global Positioning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Trade
WangDianli,Sun Haiyun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inexorable trend of national development.The global value chain division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The present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new features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trade by introducing the global value chain system.It also demonstrates that trade barrier blocks economic development.In order to improveinternationalcompetitiveness,itisnecessarytostrengthen industrialupgradingand enhance comprehensive economic strength.According to the actual condition of China,the present author relocates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and propos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intensive industry is key to future development.
Global Value Chain Division;International Trade;China;Overall Competitiveness;Global Positioning
F81
A
1007-905X(2017)11-0032-07
2017-06-05
山東大學自主創新團隊項目(IFYT12104)
1.王佃利,男,山東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城市管理、區域治理、社會政策研究;2.孫海云,女,山東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公共政策、區域治理、城市管理研究。
編輯 凌 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