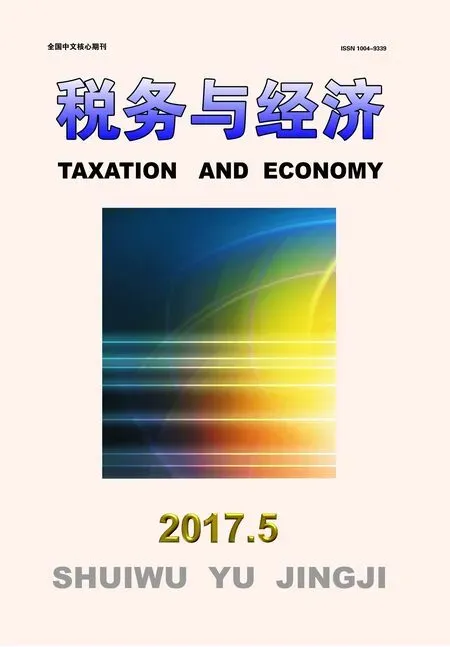“穩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動因
袁 茵,趙 玲
(1.吉林大學 哲學社會學院,吉林 長春 130112; 2.吉林財經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吉林 長春 130117)
可持續發展意涵下的穩態經濟,是建立在生態環境承載力基礎上,與自然界的凈化能力和再生能力相適應,以經濟的穩妥發展、健康發展、綠色發展和有質量的發展為本質要求的經濟發展模式。發展穩態經濟,就需要構建一種新的經濟發展范式,摒棄對經濟增長的無限制追求,采用一種更綠色、更環保、更健康的生產生活方式來應對全球生態危機的挑戰。
一、穩態經濟源于生態的極限性
20世紀興起的宏觀經濟學關注并追求經濟增長,表現出對人口以及經濟增長指數的盲目崇拜,把自然界看作是一個自發提供給人類經濟資源的慷慨捐助者,認為自然界資源支撐經濟發展的能力是無限的,這導致了人們對經濟增長的片面追求和樂觀預測。在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的經濟增長理論中,表現出極大的對經濟增長的盲目熱衷和對生態環境及倫理道德的冷漠與傲慢,無視經濟生產活動中的資源稀缺性。環境資源經濟學家認識到經濟的超常增長可能帶來生態問題,強調特定資源是有限的,告誡人們不能迷戀經濟增長而對自然資源進行盲目掠奪。但是,他們僅僅認識到特定資源是有限的、稀缺的,而沒有認識到資源的稀缺性是普遍存在的,即所有的自然資源都是稀缺的。這種稀缺性是相對于人類需求的滿足而言的,是相對稀缺,而不是絕對稀缺。因為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能夠找到新資源來替代舊資源,資源最終不是稀缺的。但作為生態經濟學代表人物的戴利則提出了自然資源的絕對稀缺和穩態經濟的概念。他認為,企望為人類社會的經濟增長找到永恒資源是一種普羅米修斯式的頑念,在自然界有限的資源和生態凈化能力條件下,過分執拗于經濟增長的理念,將會加速把人類推向生態危機的邊緣,只有穩態經濟才能夠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在正視自然極限和追求穩態增長的原則下,穩態經濟學作為傳統增長經濟學的反叛,試圖破解傳統宏觀增長經濟學在生態物理、倫理道德和經濟發展方面遭遇的諸多問題,并為人類在資源有限的地球上如何幸福地生活提供一個穩態經濟學的解決方案。
“穩態”的概念最初來自于19世紀英國哲學家、經濟學家約翰·穆勒的經濟思想。他認為,財富的增長并不是可以一直持續下去而沒有限度,因為在所謂進步狀態的盡頭便是靜止狀態,財富的增長只不過是延緩了靜止狀態的來臨,人類社會每向前邁進一步,都意味著向靜止的狀態臨近了一步。1971年,羅馬尼亞經濟學家尼古拉斯·喬治斯庫—羅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在《熵定律與經濟過程》(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中第一次將物理學原理運用到經濟運行的規律中。他認為,經濟發展過程會受到熵定律的限制,人類總是在夢想可以通過廢棄物的循環利用來實現經濟持續增長和避免環境破壞,但是,“被重復利用的東西中的熵都降低了,而我們必須使用額外更多的低熵。免費的重復利用是沒有的,就像沒有不生產廢物的工業。”[1]9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能量在轉化的過程中不可能全部被利用,每一次轉化所產生的無效能量即“熵”,世界上的所有物質與循環都依賴外部能源的參與,在此過程中都會產生熵,不存在任何沒有損壞的重復使用。在他看來,經濟過程就是一個有價值的自然資源轉化為無價值的廢物的過程,即由低熵向高熵轉化的過程,而經濟增長所面臨的最大瓶頸就是低熵的稀缺。
正是基于現實生活中對資源的稀缺,一味地追求經濟增長指數必然會帶來對自然資源的瘋狂掠奪與破壞,自然資源越是匱乏,經濟發展越是無力,于是就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的境地。因此,為解決人類共同面對的生態環境問題,迫切需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由原來的粗放型增長向集約型增長轉變,由過去的強調經濟指數的增長轉變為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構建穩態經濟發展模式。
二、穩態經濟體現發展的可持續性
“發展”一詞最初來自于生物學,是指生物體在進化變異過程中所形成的細胞重組現象,后來逐漸引申到哲學社會科學中。發展蘊含著變化。自然是整個世界賴以存在的根基,它為地球上的每個生命個體提供必需的生命給養,維持生命物種的存在,正是由于有了自然界的依托,才使人類獲得了生存的可能。生存是發展的前提和基礎,沒有生存就談不上發展,因而發展同樣依賴于客觀的自然環境,依賴于具體的自然物質資源的供給。“生態學中基本的守恒概念是承載能力的思想,也就是某個區域年復一年在不造成環境惡化的情況下——即不相應降低其承載力——能夠支撐原始物種的數量。超越這一承載力,哪怕是很短的一段時間,也將造成一系列環境惡化的過程(如土地侵蝕),這個過程是正反饋(失控的反饋)所控制的。為此,超過承載力,哪怕只是短暫的一會兒,也是一種最嚴重的錯誤。”[1]96生態系統的再生和吸收能力決定了規模的最大值,但這種最大規模并非最佳規模。將生態系統考慮在內的經濟發展的最佳規模說明,一個既定的經濟發展規模決定了它的自然資源擁有量以及相對應的環境承載力。“經濟可持續發展必須滿足以下雙重條件,即在不過分損害環境之生產能力的前提下充分地利用物質資源,將廢棄物排放量限制在環境吸收能力許可的范圍內。”[1]173
穩態經濟是一種體現整體性的,綜合了物質的、社會的和道德內容的經濟發展范式,關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不平等、人口增長和物質能量消耗的約束,提倡正義的、可持續的、公眾廣泛參與和共享的經濟。這需要穩態發展而非無限增長。穩態不是目的,它本身作為一種手段,是為了達到經濟的正義、可持續、參與和共享以及整個自然生態系統應具有的穩態特征而構建的一種制約機制。穩態經濟代表的是一種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水平,根本的主旨是在有限的自然生態中人類如何更好地生活下去。“主流經濟學對去增長和穩態經濟的一大批判依據是,隨著科學技術發展,經濟效率會提高,未來人們能更好地將經濟增長與環境沖擊相分離,而以更低的物質和能源輸入獲得更高的經濟產出。然而,歷史事實顯示,當某種資源的利用效率因技術進步而提高時,這種資源的消耗率反而趨于上升。”[1]301這就是說,單純依靠技術進步不足以解決資源和環境問題,必須同時對無止境的增長及消費需求進行約束。在穩態經濟的視野中,自然界物質能量的存量和流量是有限的,經濟發展可以契合自然界自身的演化規律實現自我更新,經濟生活中物質的數量方面停止增長不會妨礙社會進步,甚至可以說,這種經濟發展的生態限制和倫理約束能夠使經濟擺脫目前這種自我毀滅式的增長模式,為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開啟新的道路。
三、穩態經濟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性
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的現代化進程在帶來巨大物質財富和經濟福祉的同時,也帶來了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的問題,使人類的生存以及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面臨著極為嚴峻的挑戰。現代宏觀經濟學盲目追求經濟增長,忽略了生態物理、道德倫理對經濟的根本制約。以穩態經濟學為代表的生態經濟學賦予了經濟學一個全新的研究視域,也被看作是“經濟學正在出現范式變化的一個信號”。[2]穩態經濟學從生態學、倫理學和經濟學的角度來綜合考察經濟的正當性問題,涉及生態學意義上經濟發展是如何可能的以及倫理學意義上人們應該擁有什么的問題。厘清這兩個問題,對于生態文明建設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建設生態文明的規則、制度和體系,需要轉變傳統的經濟增長理念和方式,建立一種生態經濟范式,實現對自然資源的合理配置,以確保作為人類經濟社會發展基石的地球生態系統的完整性。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在社會生產中人與人之間所形成的關系會反作用于人與自然的關系。特別是由于發展的不均衡性而帶來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在貧困的地方,人們為了生存而過度地使用自然資源,從而導致自然資源的嚴重損毀;而越是無節制地開發自然資源,就越會給經濟發展帶來掣肘。如此惡性循環會直接威脅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倡導穩態經濟,是對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它強調自然界存在一個不可彌補和逾越的稀缺限制,在自然的可承載能力上證明了增長經濟在生物物理規律上的不可能性,并對無限增長的經濟觀進行了倫理道德批判。它嘗試解決這樣一個帶有根本意義的問題:在有限的地球上人們該如何幸福地生活。[3]
穩態經濟學代表了生態文明的應有內涵。把握穩態經濟的經濟學范式革命,對于中國建設生態文明和實現綠色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中國未來必須從傳統工業文明走向生態文明的綠色發展。當前制約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因素開始從人力資本轉變為自然資本,如何有效地在市場經濟發展中對自然資源進行合理配置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應有之義。在穩態經濟學的視域下,建設生態文明需要的自然資本,既包括自然資源的供給力,也包括自然界對污染和廢物的凈化力和承載力,還包括自然界給人類提供的生態服務產品。在中國建設生態文明的進程中,必須遏制經濟增長對自然界的征服、壓榨和破壞,建立以自然資源普遍稀缺為基礎理念的生態經濟觀,實現經濟發展質量和生態環境保護的和諧共贏。
在穩態經濟學看來,物質財富增長是經濟發展初期的重要特征,而代表社會福利的分配公正和人的精神滿足才是經濟發展的根本目標。進入到一定階段,經濟增長是要停止的,而經濟發展是能夠實現可持續的。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和美麗中國建設的目標是實現生產發展、生態良好和人民幸福,實現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可見,穩態經濟學的理論與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理念有相通之處。
[1][美]赫爾曼·E.戴利,肯尼思·N.湯森.珍惜地球——經濟學、生態學、倫理學[M].馬杰,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
[2]王悠然.構建“去增長”的穩態經濟[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10-10(A03).
[3]張永慶.從人的存在方式看可持續發展的哲學基礎[J].北京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