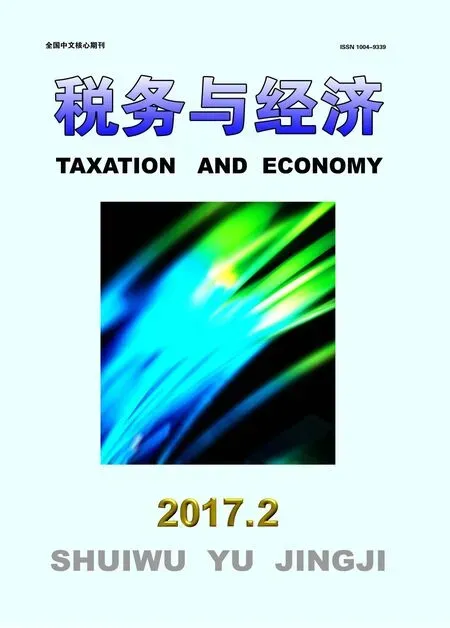生物燃料產業擴張:從全球性變化到全球性治理
薛 狄
(東北師范大學 經濟學院,吉林 長春 130117)
當今世界各國政府均認同生物燃料是一種有潛力的化石燃料替代選擇,其產業發展與減緩氣候變化、繁榮農村經濟、緩解全球和國家能源安全的聯系已促使許多國家在該領域紛紛展開行動。但是,產量和貿易的迅速膨脹引起了許多環境和社會經濟問題的爭論。因此,探討生物燃料產業發展的本質,探尋治理途徑時不我待。
一、生物燃料產業擴張:一種新的全球性變化
全球生物燃料生產從2000年到2009年已經翻了20倍[1],生產國也從最初的巴西一枝獨秀擴展至美國、歐盟、中國等主要農業國,儼然成為了新能源產業中最具潛力、最重要的化石能源替代產品。盡管這番蓬勃景象很大程度上歸功于生產效率的提高,但原料作物種植擴張也“功不可沒”,有越來越多的作物應用于該產業生產。生物燃料產業擴張帶來了以下巨大影響。
(一)由生物燃料產業擴張引起的生態變化
生物燃料對環境的影響是復雜的。生物燃料替代化石燃料、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是其快速擴張的根本動力。但是,仍要對生物燃料整個生命周期排放做出全面評估。比如,原料作物的生產使用化肥、殺蟲劑,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同時消耗化石燃料。機器化大生產帶來更多甲烷氣體,而甲烷對全球變暖的作用遠遠大于二氧化碳。另外,土地使用目的的轉變可能導致大量的溫室氣體排放。因此,關于排放平衡必須考慮產業的整個生命周期。單一種植原料作物還會帶來生物多樣性喪失、土壤質量下降、對水資源質量造成沖擊;即使大多數作物可依靠降雨生長,但是當提高生產率成為優先選擇時,灌溉則會成為首選。而且,生物燃料生產有外來物種侵害原有生態的風險。
(二)由生物燃料產業擴張引起的社會經濟變化
生物燃料產業對農村經濟的影響體現在包括國家、區域和全球的各個層面。國家對該產業利潤的保證使大量投資涌入種植業,尤其是以農業為主要支撐的發展中國家。這就促使農民成為農業工人,喪失了對土地的傳統控制權。雖然產業擴張確實增加了農村人口就業機會,但是勞動條件卻不盡人意,勞動安全難以保證。除了對農村本地的影響,生物燃料生產也打亂了糧食生產和供應格局。因為主要糧食作物既可供人食用也可成為生產原料,由此全球糧食價格隨需求大增而屢創新高。生產者雖可從中獲利,但那些農村和城市的低收入者無法負擔基本食物費用,惡化了全球糧食安全狀態。
(三)由生物燃料產業擴張引起的南北關系變化
相對于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可獲土地數量較高、原料價格較低、勞動力成本低廉,被認為最有潛力生產生物燃料。但生物燃料的主要消費者卻是發達國家,即便全球產量不斷提高也無法滿足發達國家的消費目標,進口需求應運而生。于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簽訂了許多相關貿易協定。這種供求關系的發生本應帶來全球雙贏局面,但是發展中國家生產大規模擴張卻給自身帶來了巨大挑戰,包括森林退化、土地沖突、傳統耕種方式的遺失等等。發展中國家是該產業發展負面影響的主要承受者,卻沒有充分機會參與全球治理議程。即使參與,也只是該國的一些大企業,而不是生活受到實際影響的大多數人,這無疑增加了北方對南方國家的控制力。
二、生物燃料治理框架現狀與評價
(一)生物燃料治理現狀
目前各個國家、區域及國際組織已出現了應對生物燃料影響并促進其可持續發展的政策和治理結構。
1.國家生物燃料治理議程:以主要生產國為例
隨著氣候變化成為全球環境議程中的重大問題,許多國家構建了可再生能源戰略,其中就包括生物燃料。使用生物燃料不僅能替代化石燃料和提高能源安全性,更重要的是還可以擴大農產品的出路和收益。在此促動下,各國普遍采用的政策是頒布燃料混合國家命令、稅收豁免、對農民或生產者直接支付、對進口產品適用關稅壁壘。除此之外,主要生產國美國和巴西面對產業的負面影響也采取了有限的政策調整。美國的玉米業已飽受詬病,尤其是玉米乙醇生產:減排水平低;超大型農業公司的控制使小生產經營者無利可圖;由于美國是世界玉米的主要供應者,對生物燃料的加大投入引起全球大宗食品的價格動蕩。即便是這樣,美國仍然一再提高生物燃料使用比例,要求到2017年生物燃料替代汽油消費達到20%,對加工商提供每加侖0.51美元的補貼,對進口燃料乙醇適用每加侖0.54美元的進口關稅。[2]雖然新能源計劃提倡木質纖維素乙醇技術的發展,但是美國近期對生物燃料的需求增長仍不可避免地從傳統生產中獲得。巴西是世界第二大生物燃料生產國。甘蔗的乙醇轉化率比玉米乙醇高。但種植園的迅猛擴張對亞馬遜森林造成了負面影響;甘蔗乙醇的生產對水需求量較大;單一種植擴張也帶來了嚴重的土地沖突。但巴西政府仍決定每年新建25個甘蔗乙醇生產廠。[3]盡管計劃逐年有所微調,但傳統大型甘蔗生產仍然占據主要地位。由此可見,可持續關注在美巴兩國并不是最優先考慮的事項。但是生物燃料凈進口國和地區卻對生產的可持續性進行了更為積極的應對,主要體現在歐盟及成員國。
2.區域生物燃料治理議程
歐盟生物燃料治理分為成員國個別要求和歐盟共同要求。就成員國而言,英國和荷蘭生物燃料標準最為典型,因此從英、荷、歐三個角度分析區域治理工具。 生物燃料可持續性爭議包括減緩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保護,水、土壤、空氣保護,土地所有權保護,勞工標準,社會經濟發展和糧食安全7個方面。關于減緩氣候變化,三者要求類似:首先都禁止將高碳封存土地用于原料作物的種植。英國要求溫室氣體減排至少為40%,每年增加5%,但性質是建議式的。荷蘭規定了最低30%的強制減排,到2017年逐步增加到80%~90%。歐盟強制性要求將最低減排量提高到35%。關于生物多樣性,荷蘭和歐盟都禁止將具有高生物多樣性區域用于生物燃料生產。英國禁止生產毀損以上區域即允許合法生產。荷蘭要求要遠離高生物多樣性區域5公里以上。關于水、土壤和空氣保護,三者具有區別。英國要求沒有土壤退化、污染、水資源耗盡或空氣污染。荷蘭要求實行最佳保護實踐;遵守《斯德哥爾摩農藥使用公約》或國內法;禁止生產焚燒。歐盟除了就國家保護措施進行年度報告外,無具體要求。關于土地所有權,英國要求對土地權和當地社會關系沒有負面影響。荷蘭要求在土地原始使用者同意下謹慎使用土地;尊重原主人傳統制度。歐盟僅要求進行年度報告。關于勞工標準,英國要求對勞工權利和工作關系沒有負面影響。荷蘭要求遵守《普遍人權宣言》和關于跨國公司及社會政策的國際勞工原則。歐盟除了就《國際勞工公約》的國家授權和執行進行年度報告外,沒有具體的要求。關于社會經濟發展,英國和歐盟僅要求就此履行年度報告義務。荷蘭要求生物燃料生產必須利于當地繁榮;要求就生產影響當地人口和利于當地經濟發展進行報告。關于糧食安全,英國僅要求檢測對糧食價格的間接影響。荷蘭和歐盟除了就土地使用改變形式、土地和糧食價格影響進行報告外沒有具體要求。只有滿足上述標準的產品才能計入歐盟2020年運輸領域可再生能源10%的強制性目標,進而才會獲得市場準入好處和稅收豁免、直接支付等利益。歐盟在證明產品是否符合標準的問題上采取靈活做法,即權力下放到歐委會認可的自愿性生物燃料認證制度,認可時效為五年。可見,就世界最大的生物燃料進口市場的準入而言,得到具有資格的認證制度的認證是關鍵。截至2011年7月,有2BSvs、Bonsucro、Greenergy、ISCC、RBSA、RSB、RTRS七個生物燃料認證制度得到了歐委會的認可,此外還有18個認證機會等待歐委會的批準。[4]
3.國際生物燃料治理議程
與生物燃料相關的國際協定在各個領域早已出現,例如氣候、能源領域。雖然目前尚無專門針對全球生物燃料挑戰的國際協定,但國際社會已開始展開努力。首先,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聯合國糧農組織(FAO)、聯合國能源機制(UN-Energy Interagency)在其報告和研究中均已提出生物燃料問題。但是,它們的行動大多僅局限于分析和建議,并沒有就其各自的領域達成國際協定。國際能源署(IEA)以及經合組織(OECD)發揮了更為積極的作用,通過IEA生物能源部的第40工作組為生物燃料貿易認證構建了可持續性標準。其次,新近建立的論壇和伙伴關系開始在生物燃料全球可持續發展議程中嶄露頭角。最為典型的就是2005年發起的全球可再生能源伙伴關系。該制度目的是促進可再生能源的繼續發展和商業化,支持更廣泛的、符合成本效益的生物質和生物能源發展,尤其對發展中國家。生物燃料國際貿易大幅增加,2007年巴西、美國、中國、歐委會等建立了國際生物燃料論壇。最后,專門針對生物燃料可持續性問題成立的新的國際倡議,采取利益攸關方組成圓桌會議的形式,討論和構建可持續性環境和社會經濟標準。但覆蓋產品范圍各有不同,例如責任大豆圓桌會議以及意圖進行普遍適用的可持續生物燃料圓桌會議(RSB)。
(二)對目前治理框架的評價
如前所述,美國和巴西對生物燃料的治理舉足輕重,但目前二者發展議程中似乎并沒有將治理作為優先考慮的問題。
隨著全球生物燃料貿易的擴大,作為主要進口者的歐盟國家的生物燃料治理議程對市場準入和不同可持續性產品的競爭力的影響在逐步提高,甚至成為了全球治理生物燃料的風向標。但是,從歐盟和成員國的可持續性標準來看,主要局限于對生態環境的要求,而對于諸如當地經濟發展、公平正義以及糧食安全等與發展中國家緊密相關的社會經濟問題則關注不夠;間接土地使用轉化問題也被忽略,甚至不存在報告制度。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標準既適用于外國生產者也適用于歐盟國家,但制定決策時卻沒有主要供應國——發展中國家的參與,亦即發展中國家的訴求和關注沒有得到體現。
雖然國際治理議程給參與性帶來了一些新的變化,但也有其自身弱點:首先,不同國際生物燃料治理議程仍局限在自己業務范圍內處理環境和社會經濟影響。國家合作多集中于研究和技術發展,而不是應對擴張帶來的更為嚴重的糧食安全問題。其次,通過給當地提供能源生產和供給的方式來促進當地發展的生物燃料發展的替代模式幾乎被這些治理議程所忽略,即它們主要以生物燃料貿易為預設前提而展開談判。再次,有些國際議程如IEA、OECD具有明顯的發達國家傾向,以它們的能源需求為優先考慮,因而主要關注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為導向的生產,而不是發展中國家的當地需求。而全球生物能源伙伴關系也代表主要國家團體利益。甚至像RSB由多利益有關方組成的圓桌會議也不對稱地給來自工業部門和發達國家的參與者更多的關注和投票權。21位RSB發起委員中僅有5位來自發展中國家,而這5位代表中有3位代表了像巴西的甘蔗聯盟這樣的工業團體利益。很明顯,利益受到重要影響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無法充分表達意見。最后,現有的國際行動沒有形成多層次、協調統一、相互支持、相互影響的治理方式。許多國際倡議或國際行動十分分散,僅關注自身覆蓋的領域,且其框架下的國家行動仍被符合本國利益的議程所主導。這種情形實際導致生物燃料問題仍然是“無治理領域”。試想有各自利益的國家和企業一旦發生紛爭,將如何公正、合理地解決爭議?
三、新多邊生物燃料產業治理框架愿景
(一)建立新多邊生物燃料產業治理框架的緣由
無論從國內還是國際層面,目前生物燃料治理制度都無法滿足治理需求,迫切需要建立新多邊治理框架:第一,該產業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均具有重要的全球要素和關聯。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燃料就是由《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促動的。化石燃料的可用竭性是一個全球性難題;而動蕩的國際關系又是國家追求能源安全的巨大障礙;生物燃料農業尤其在發展中國家又是由發達國家的消費目標促發的出口繁榮所驅動的。以上每個環節都具有“全球烙印”。第二,生物燃料生產帶來的環境影響是無法依靠個別國家得以解決的。該產業對氣候變化、水等自然資源的需求以及對土地使用改變的累積作用均具有明顯的全球關聯。第三,個別國家解決生物燃料擴張帶來的社會經濟影響能力有限,比如對農產品市場和全球糧食安全的影響。第四,生物燃料的爭論從一開始就具有南北關系的特性,是以一方的主要社會、政治和環境利益為代價而使另一方獲利的問題。第五,關于生物燃料生產存在許多相互沖突的觀點和看法,因此不僅需要有效的治理框架,更需要體現公平性、合法性、責任性、代表性的統一治理制度。
以上各個方面均體現了建立全球性生物燃料治理框架的必要,而這里的全球性并不意味著所有國家都就此進行談判,但至少是一個與現有治理框架不同且能夠反映生物燃料產業核心問題的視角,能通過多邊平臺包括國家和非國家參與者構建的負責而合法的方式進行治理和調控。那么,這種新多邊治理框架究竟應該具備怎樣的條件和內核呢?
(二)新多邊生物燃料產業治理框架的建構
1.多邊生物燃料產業治理框架應具備的基本特征:多部門、多層次和多參與者治理
首先,生物燃料產業治理需要多部門協調。生物燃料產業發展不僅是一種能源戰略,它和糧食、農業、貿易、氣候和生態保護等多方面都具有重大關聯,而這些領域都有各自的政策制度。因此氣候談判、可再生能源議程、全球貿易和農業發展、保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戰略均涉及到生物燃料問題。以上不同領域的各自政策必須避免沖突、尋求協調,這就需要多部門協調來應對生物燃料產業治理。其次,生物燃料產業治理需要多層次協調。如果沒有國家、當地政府以及當地生產者的協助,多邊框架很難達成,這也是目前國際相關治理制度的欠缺。這種協調既要體現在國際政策的成功執行上,比如認證計劃的實施,也要體現在不同層面的規制活動上。第三,不同參與者和平行決策體系間的協調也是必要的。這會減少重復勞動、避免政策沖突。
2.新多邊生物燃料產業治理框架的制度設計:趨利避害
雖然需要進一步協調不同產業部門、參與者和治理層次,但是何種制度設計才能最有效地發揮功能卻是一個大問題。從實現的可能性出發,有兩種路徑可以選擇:
第一種路徑是在某一類寬泛的領域建設治理制度,能源和農業領域可供選擇。在能源領域探討生物燃料產業治理制度的優勢是能夠很容易地將該問題并入可再生能源政策;能夠讓業界對照其他生物能源對液態生物燃料做出評估。弱點是由于目前與能源相關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制度本身就十分分散,加之聯合國相關機制治理權力也十分有限,新建立的國際可再生能源機構(IRENA)固然令人欣慰,但是像巴西、中國等主要生產國尚未加入,因此治理很難從全球能源制度中獲得有益的制度支持;加之,如果國家將生物燃料單純看作是國家能源安全問題,由于其敏感性,將會使多邊談判變得異常艱難;最后,由于生物燃料是由許多作物提煉而來,因此對農業部門的影響也舉足輕重,將其作為能源問題處理自然會導致對糧食安全、農村地區和土地政策的影響關注不夠。在農業領域處理生物燃料問題最大的優勢是可以借助FAO現有的各種制度,可使業界更加關注糧食和農村發展問題,也會從國際農業協定中最終獲利。但是國際農業貿易談判頻頻陷入僵局,這必將阻礙該產業的可持續發展,也會割裂生物燃料與可再生能源政策的聯系。
第二種不同的制度設計路徑就是將生物燃料作為獨立的焦點問題進行制度設計,而此種方式根據所設計的制度框架以生物燃料產業問題的一個方面還是多個方面為治理對象分為單一框架和復合型平行框架。不論是單一政策框架還是復合政策框架同樣各具優缺點。在有效性方面,復合型平行框架更有利于不同政策工具的創新、彼此競爭和實踐檢驗;在公平性和權力分配方面,復合型平行框架更易于禁止權力集中,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會增加發展中國家在決策中的影響力。缺點就是遵守和執行成本較高。而單一框架由于設定的制度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局限性,因此遵守和執行成本較低;所設定的單一規則更容易和像WTO這樣的現有國際規則協調一致;也更易于吸收眾多參與者的集中關注并利用他們可提供的資源。缺點是過分支持某類參與者的風險較高;靈活性和調節性較差;由于會吸引更多的參與者,因此達成一致意見就更為困難。
綜上,新多邊生物燃料產業治理框架是一個開放性議題,需要把握住合理合法內核,比較各種選擇路徑的優缺點,在實踐中逐步探索。
[1]Patrick Lamers. International Bioenergy Trade-A Review of Past Developments in the Liquid Biofuel Market[J].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2011,(11):2673.
[2]USA. H.R.2419: Food, Conservation, and Energy Act of 2008[EB/OL].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xpd?bill=h110-2419, 2012-5-1.
[3]Alcides Faria. Macro Effects in Brazil the Impacts of Agroenergy Crops in Four Areas of the Country[EB/OL].http://www.riosvivos.org.br/arquivos/site_noticias_543305119.pdf, 2012-6-10.
[4]Thomas Vogelpohl. The Institutional Sustainability of Public-private Governance Arrangements-the Case of EU Biofuels Sustainability Regulation[R].The Lund Conference on Earth System Governance, Berlin 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