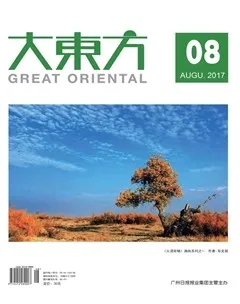淺析明清時期山東運河水源管理的影響
摘要:明清時期,漕運為國家要政,而山東運河的水源管理為漕運要害。明清兩代為解決山東運河水源問題,采取了行政管理和工程管等多項措施。同時此亦對該區域農業生態和社會生活產生了深遠影響。運河用水與農業用水的時空一致性,濟運優先造成了傷農害農的結果。然則,民眾以對官方信拜的金龍四大王表現冷漠作為回應。明清時期山東運河水源管理問題是人、社會與自然關系問題的集中表現和反映。
關鍵詞:明清;山東運河水源管理;農業生態;信仰崇拜;影響
一、對農業生態的影響
京杭運河的開通帶動了區域內商品經濟的發展,山東運河區域的臨清、濟寧、張秋等都是運河“運”來的城鎮。然而運河對農業生態的影響則是弊端大于優利,山東運河用水與該地區農業用水具有超強的時空一致性,漕運與農業生態的矛盾的最大沖突點就是水源問題。
(1)與農爭水。山東地區屬溫帶季風性氣候,雨熱同期,降水多集中在夏秋季節,冬春季節則干旱少雨。漕運之際,亦是農田待溉之時。在漕運用水與農業用水的沖突之間,明清朝廷選擇濟運保漕用水優先,民眾不得隨意取水灌溉農田。從上文官方對泉、河、湖(水柜)的律令制度的嚴格管理中充分體現了政府的傷農保運政策。康熙六十年(1721年)四月,康熙帝發布諭令:“山東運河,全賴眾泉灌注微山諸湖,以濟漕運。今山東多開稻田,截湖水上流之泉,以資灌溉,上流既截,湖中自然水淺,安能濟運?……地方官未知水之源流,一任民間截水灌田,以為愛恤百姓,不知漕運實因此而誤也。若不許民間偷截泉水,則湖水易足,自能濟運矣”。由此可見,統治者把保漕濟運視為全局要政,其作用要遠遠大于百姓灌田之需。然而“民以食為天,斷不能視田禾之枯槁,置之不問”,灌溉旱田亦是現實,鑒于此,清廷在很多運段制定了水量分配制度。如衛河濟運,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定“每年至五月初一日起,將閘板封貯,盡啟渠口,毋致旁泄,俟漕船過竣,再行分泄,以資民田”。康熙三十年(1691年)規定,雨水充足時,每年三月初一至五月十五日用竹絡裝石阻塞渠閘,使大流濟運,余水灌田。若雨水不足時,“止令三日放水濟漕,一日塞口灌田,以后聽民便用”,此即“官三民一”之制。后來,又改為“官二民一”:“五月以后,民間插秧需水,二日濟運,一日灌田,按期互相啟閉。六七月間,聽民自便。”道光年間又先后規定了“官八民二”、“官七民二”的分水比例。
(2)水裕沉田。夏秋之際,降水充足年份,運河水位漲溢,朝廷為防止潰運河堤壩,遂泄水于水柜,甚至直接泄入洼地民田之中,造成水澇災害。微山湖為濟運重要水柜,湖中設有水樁,以測水位。按照定制,收蓄湖水一丈二尺,即足夠漕運用水之需。但因漕運為國計要政,法治嚴苛,管漕官員往往超多蓄水,害怕運道缺水而受懲處。這樣就造成微山湖水位過高,湖面擴大,水患頻發,淹沒周邊農田。
南陽湖區還出現了“沉糧地”的特殊歷史現象,“沉糧地”即被水淹沒的產糧田地。清張伯行在所著《居濟一得》中提到:“濟寧南鄉一帶,地勢洼下,邇來疊罹水患,有地不盡耕種,縣罄吁嗟,哀鴻甚憫,皆因楊家壩開通放水,不入馬場(湖)濟運,而徑由運河轉至南陽湖,南陽一湖不能容納,遂漫入南鄉一帶,是以民田受淹。”原本產糧田地被水淹沒成為“水深難涸地”,無法耕種。身處“沉糧地”的農民深受洪澇之災,陷入無田而有稅的困境。對于微山湖蓄水過多,濟漕運而害農田的情形,清代思想家魏源對此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山東微山諸湖為濟運水柜,例蓄水丈有一尺,后加至丈有四尺,河員唯恐誤運,復例外蓄至丈有六七尺,于是環湖諸州縣盡為澤國。而逾旱需水之年,則又盡括七十二泉源,涓滴不容灌溉。是以山東之水,惟許害民,不許利民,旱則益旱,澇則益澇,人事實然,天則何咎?”
(3)土壤鹽堿。山東運河流域內的土地質量并非優良,一旱一澇,交替頻仍,土地的鹽堿化較為嚴重,而運河沿岸尤甚。山東運河水量季節較大,降水豐沛時節,運河水量較為充足,運河沿岸地下鹽堿物質隨水毛細上升,浸漬至地表。雨季過后,運河水位和地下水位均大幅度降低,地表水分亦旋即蒸發,但鹽堿物質全部留在了地表,造成了鹽堿化土壤。加之土壤春干夏燥,這樣就降低了土壤肥力,不適宜作物的種植,致使農作物減產,甚至絕收。
二、對信仰崇拜的影響
山東運河水源管理對該區域的社會生活產生了深遠影響,就該區域的民間信仰崇拜而言受其影響亦甚。如從對漕神(運河神)——金龍四大王的信仰崇拜就能看出運河水源管理對民間信仰的影響。在山東運河區域,民間對金龍四大王的信仰崇拜要遠遜于土地神與龍王,土地廟與龍王廟遍及運河區域,而金龍四大王僅寥寥數座。金龍四大王的信仰崇拜的形成方式是由上及下,由官方及民間的,信奉人群主要是官方特別是管漕人員和往來于運河之上的商人,而非基層民眾。這就與普遍的信仰崇拜的形成方式恰恰相反。因為金龍四大王主要澤佑的是安瀾黃運兩河,保障漕運通暢。而漕運與沿線民眾的農業生產無益,為濟運保漕,朝廷嚴管運河區域水源,嚴禁灌田,奪民之水,旱澇傷農。山東運河沿岸民眾還是“靠天吃飯”,期盼風調雨順、五谷豐登。實現這一愿望民眾只能向天神求雨,祈求有直接關系的土地神和龍王爺更加妥當。金龍四大王信仰缺乏雨澤廣大民眾的神威,難以形成上與下的互動,官方與民間的共鳴,所以沿岸民眾信仰土地神之類,而非崇拜運河之神。隨著漕運的衰敗,金龍四大王的信仰崇拜也更會淡出民眾的生活,只得留下殘碑黃卷的寥寥記載。
因氣候、地形等原因,官方對運河水源的管理與農業生態產生了激烈沖突,進而影響了區域的信仰崇拜。在以農為本、以農立國的國策之下,局部地區農業生產與漕運相比,顯得是那么微不足道,反而商品經濟的發展獨樹一幟,臨清、濟寧等商業重鎮興盛,與“重農抑商”的觀念產生了巨大反差。
(作者單位:聊城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