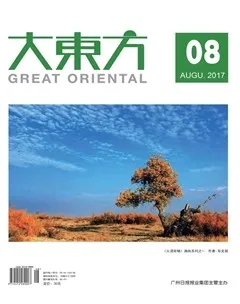論野生鳥類的刑法保護與立法完善
摘要:當前,城市化進程的發展使得鳥類的棲息地不斷被壓縮,部分邊遠地區對于鳥類保護的意識也較為薄弱,盜獵猖獗,形勢嚴峻,嚴重影響了鳥類的生存空間。人類的生活與鳥類的保護不斷發生激烈碰撞,破壞了生態系統的平衡,使其更加脆弱,因而通過法律上的完善來建立保護鳥類的相關制度已迫在眉睫。本文欲通過深圳男子出售鸚鵡而獲刑為例,試圖闡述我國現今刑法在鳥類保護上的薄弱環節,并由此提出建設性意見以期有益于司法實踐,從而更好地處理人與鳥類的關系,達到和諧共生狀態,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關鍵字:鳥類 ; 刑法保護; 立法完善;
一、案例引入
2017年3月30日,深圳市寶安區人民法院一審以犯“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判處王鵬有期徒刑5年,并處罰金3000元。究其案件的經過,原來王鵬在2014年4月拾到了一只鸚鵡,以為是別人飼養丟失的,就帶回家飼養。5月,王鵬又從網上購買一只雌性鸚鵡與之配對,沒想到鸚鵡繁殖能力極強,在短短一年時間內,家中已超過50只。2016年4月初,王鵬將其中6只鸚鵡,以約3000元的價格出售給朋友謝田福。事后的調查結果表明,6只鸚鵡中,除4只為玄鳳鸚鵡外,有2只為小太陽鸚鵡,學名綠頰錐尾鸚鵡,被列為《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Ⅱ中,屬于受保護物種,因此事發,深圳市公安局森林分局于2016年5月18日14時,以涉嫌“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及其制品罪”,將王鵬刑事拘留。
二、我國刑法對于野生鳥類的保護現狀
《刑法》在分則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第六節“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第三百四十一條,規定了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罪,非法狩獵罪三個罪名,在分則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第二節“走私罪”第一百五十一條規定了走私珍貴動物、珍貴動物制品罪。保護對象上主要是針對“珍貴、瀕危野生動物”非法狩獵罪與走私罪的對象是一般野生動物。整體規定較為分散單一,而且處刑較重,不能很好的對野生鳥類資源保護起到保護作用。
在有關司法解釋方面,則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其他相配套的還有一些部門法以及地方條例與辦法。
總的來看,我國有關法律法規對于野生鳥類的相關保護規定無法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部分法規出臺時間距今年限已有數十年甚至幾十年之久,并不能很好適應當下對于野生鳥類的保護現狀,就拿動物保護名錄來說,是在1989年1月14日通過實施,距今已有28年,中間只有一次調整是將麝(所有種)由二級改為一級,在如此長的時間里有很多鳥類可能由于獵捕已由正常種群變為瀕危物種,而部分種群由于得到很好的保護,種群數量已經得到恢復。部分法規的配套規定也并不完整,很多地方甚至相互沖突,導致具體適用中產生各種疑難問題。比如對于“情節嚴重”的認定,如果是同時獵捕、殺害、收購、運輸、出售不同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的話,需要“其中兩種以上分別達到附表所列‘情節嚴重’數量標準一半以上的”,這樣就造成一種情況如果恰好某個人所獵捕的野生鳥類絕對數目很多但一共加起來卻達不到?,那么就只能按低一檔法定刑處罰,即使他實際侵害的法益很大,同時,“獵捕、收購野生動物的數量帶有相當程度的隨機性,這勢必會導致民眾對非法獵捕、收購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的何為嚴重產生認識模糊而陷入刑法的恐懼當中”。而且在刑法方面以前的重刑主義思想依舊反映出來,對于野生鳥類的犯罪單罪即可判至15年,在刑罰方面遠遠高于同時代的其他國家。此外,對于保護鳥類相關的國際條約,雖然國際上已經有了不少規范條約,但我國批準加入的卻較少,與各國的交流合作并不充分。
三、對于野生鳥類保護的問題分析
(1)野生鳥類的生態重要性。鳥類在整個生態系統中處于一個獨特的地位,其種類繁多,分布極廣,不同于其他大型動物,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都有可能接觸。同時,它們具有極高的生態價值,在保護人類的經濟利益和維護人類健康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所發揮的巨大生態效益也是難以估計的。一只燕子一個夏天能吃掉蚊子、蒼蠅等各種害蟲60萬~100萬只;一只貓頭鷹一個夏天就能消滅1000只田鼠,相當于保護了1噸糧食;一只啄木鳥每年能啄食50萬條寄生在樹皮中的害蟲;群棲的一千只紫翅椋鳥,在繁殖期間可以消滅20噸蝗蟲;就連常被抓來觀賞的灰喜鵲、杜鵑等也是食蟲“能手”。以往人類依賴于農藥來消滅害蟲,但往往由此引發的副作用更大于其治蟲能力,還給生態帶來破壞,而鳥類則就是天然的生態滅蟲劑,其一定種群的存在構成了生態鏈條的一個重要環節,不可人為打破。隨著文明社會的到來,人們也越來越注重到對其生存環境給予保護,鳥類的健康生存也是檢驗一個社會文明和諧的重要一方面。
(2)野生鳥類的法律討論的重要意義。野生鳥類是屬于野生動物資源的一部分,由于其天然的移動特征,不會固定于某一個地方,它可流動于人類社會的各個地方,各個角落,與人類的接觸高于其他動物,這也解釋了為何屢屢有上述案例類似情況的出現,像河南大學生掏鳥案也是與其相似。不同于其他野生哺乳類動物,爬行類動物,兩棲類動物,野生鳥類的保護品種及數量也是遠遠多于其他國家所保護的野生動物,而現實中人們又往往對法律所保護的鳥類品種與保護程度了解甚少,由此造成的結果便是普通群眾忽視了對野生鳥類的一些行為會帶來刑罰的后果,降低了警惕性,也更使得對于鳥類的保護相比其他動物如大熊貓、雪豹、金絲猴等物種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破壞鳥類資源也是對于環境權的一種侵犯,環境權是一種自然權利,“環境權是環境法律關系的主體享有的在不受一定程度污染和破壞的環境里生存和在一定程度上利用環境資源的權利,而野生動物資源是自然環境的有機組成部分”,野生鳥類也構成了整個自然體系不可或缺的一環,維護野生鳥類資源即是維護這種環境權。
(3)野生鳥類的刑法保護分析。就上述判決來說,只是我國在保護野生鳥類方面問題的一個縮影,此判決一出引發了社會公眾的極大反響,因為該判決超出了人們的合理預期。就一般人看來,王鵬的行為不僅沒有對小太陽鸚鵡種群造成破壞,而且還幫助其繁衍了后代,客觀上增加了種群的數量,理應不該受到刑法上頂格刑法的判決,認為該判決有失妥當。但站在法律人的角度來看,王鵬客觀上實施了出售的行為,主觀上不知道這是國家保護動物并不能免除其責任,受到刑罰裁判是于法有據,只是在在具體分析上出現不同聲音。這就出現了法理與情理的沖突碰撞,普通大眾發表看法是出于內心的一種態度認知,看待事情是否合乎情理,而法官判案看是否違反了法律規定,需要在法理與情理之間找到合理的契合點,實現合情合法,達到最大的社會效益。就此案來說,主要爭論點有四個:①王鵬飼養的鸚鵡是否符合野生動物的定義;②王鵬的行為是否侵犯了刑法所保護的法益;③王鵬的主觀方面能否認定為故意;④剩余住處查獲的45只鸚鵡能否認定為是待出售(即是否認定為未遂)。就第一個問題來說,存在著肯定說與否定說兩種觀點,但在司法解釋的第一條里對其進行了定義: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條第一款規定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包括列入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的國家一、二級保護野生動物、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一、附錄二的野生動物以及馴養繁殖的上述物種。法官也是據此對王鵬所售鸚鵡認定為符合刑法所規定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但對此筆者認為也有兩個問題:①王鵬其后繁殖的鸚鵡客觀上來說是屬于變異種,并不是純種小太陽鸚鵡,對于變異種是否還符合保護名錄上的鸚鵡有待討論;②法律規定了馴養繁殖的也屬保護范圍有擴大處罰之嫌,這樣會造成一種情況,很多人假如不知道自己所養的鳥類種類,而進行養育繁殖,本想擴大其數量卻使得自己刑罰加重,這是有悖于情理。另外,“對于純粹人工馴養或培育的動物,原則上不應納入本類犯罪對象之列”,因為,法律規定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保護野生動物資源,而獵捕,殺害純人工馴養培育的鳥類一般情況下是無法破壞既有的生態環境。對于第二個問題,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條所保護的法益應是野生動物的種群完整性,違法性的實質是對于法益的侵害及其危險,沒有造成法益侵害及其危險的行為,即使違反了社會倫理秩序,缺乏社會相當性,或者違反了某種行為規則,也不能成為刑法的處罰對象。王鵬的行為主要有兩個,飼養行為與出售行為,其飼養行為不僅完好的保護了首只小太陽鸚鵡,而且還通過繁殖將其種群擴大了,是和保護該種群的立法宗旨相契合的,對于法益是沒有侵害的;而出售行為則違反了對于野生動物禁止出售的規定,雖然王鵬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但該行為客觀上是為刑法所不許,具有違法性。針對第三個問題,王鵬在出售鸚鵡時只是認識到可能賣的屬于野生動物,并不知道是屬于國家保護物種,即并不具有明知的故意,但王鵬是否具有應知的故意和條件呢?這需要結合主客觀的情況來判定,既要考慮行為人自身的認識能力,又要考慮案件當時的具體情況,并參考社會一般人在當時能否認識等,綜合分析,做出判斷。王鵬在飼養鸚鵡時并沒有以出售的故意來飼養,后來出售也是鸚鵡太多照顧不來而臨時起意,再結合所賣出的價錢6只3000元,平均每只500元,是符合市場上流通買賣的普通鸚鵡的價位,可見其本身對于鸚鵡的品種也沒有具體的認知,所以王鵬既沒有明知的故意也沒有應知的可能,在主觀上是不具有有責性的。對于第四個問題,結合第三項,王鵬賣6只也是臨時起意,其他45只并沒有足夠的證據與條件可認為是待出售的鸚鵡而認定為未遂,即使王鵬是想出售,也沒有出售的行為(找好買家,商量價款等行為),至多可認為是屬于預備,因此,法院在此的判決也是有待考量。
結合以上案例的分析,可見我國刑法上對于野生鳥類的保護存在與社會環境脫節的問題,行為人出售鳥類并不能像出售其他野生動物如老虎,亞洲象,金絲猴那樣,能十分清楚的認識到自己行為的違法性,大多數情況下由于社會宣傳的不到位,會在無意中就觸碰刑法的底線,這對刑法是社會最后一道保護線的地位不符。刑法在運行中應當避免過多的對社會進行干預,很多領域也不適合刑法來介入,日本學者平野龍一指出:“只有在其他手段如習慣的、道德的制裁即地域社會的非正式的控制或民事的規制不充分時, 才能發動刑法。只有在其他社會統制手段不充分時, 或者其他社會統制手段(如私刑)過于強烈有代之刑罰的必要時, 才可以動用刑法”,刑法在社會中要保留一定的謙抑性,對于野生鳥類資源需結合案件實際情況來做出保護,司法中也不應一刀切的進行刑罰,這并不能激勵人們去保護鳥類,這樣判決一出,以后人們看到野生受傷的鳥類可能也不敢去救助不敢去接觸,違背了刑法條款制定的初衷。
四、域外一些國家的法律實踐
由于不同國度的文化環境,宗教觀念,道德認知的不同,對于鳥類的保護就有了不同的立法實踐,西歐國家的法律里普遍突出“動物福利”的特點,1965年生效的《瑞典刑法典》第十六章《對公共秩序的犯罪》第13 條規定,虐待、使過度勞累、忽視或以其他方式,故意或重大過失不正當地使動物遭受痛苦的,以殘酷對待動物罪處罰金或2 年以下監禁。而《芬蘭刑法典》在第17章《侵害公共秩序的犯罪》第14條有“侵犯動物福利”規定,行為人故意或有重大過失地采用暴力、加重負擔、不提供必需的照料或食物,或者其他違反《動物福利法案》的方式,殘酷地對待動物,或者對動物施加不必要的疼痛或痛苦的,以侵犯動物福利罪論處,處以罰金或者2年以下的監禁。在1962 年美國法學會擬制的《模范刑法典》中規定了“傷害動物罪”, 是指行為人故意地或者輕率地使任何動物遭到殘酷的虐待,或者使任何由他監管的動物遭到殘忍的忽視,或者殺死、傷害他人的動物而沒有得到主人的許可。⑧在1994年《法國刑法典》第五卷《其他重罪與輕罪》全一章《對動物的嚴重虐待或殘忍行動》規定的動物犯罪, 有兩個法條。第511 -1條第1 款規定,在并不必要的情況下,對家養、馴養或捕獲的動物實行嚴重虐待或施以殘忍行為的,處6個月監禁并科5萬法郎罰金。⑨加拿大刑法第445條規定,故意給動物造成不必要的痛苦折磨或傷害可被判最高一萬加幣的罰款,情節嚴重者還面臨長達5年的監禁。
從各國的法律規定來看,對于動物的保護普遍突出反應以下幾方面:①保護范圍較廣,對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動物進行虐待就可構成犯罪;②刑罰方面,大多以罰金為主,自由刑的較少,且刑期較低;③突出體現“動物福利”的思想,該思想力圖使得動物在一種康樂的狀態下生存,實現動物的各種應有天性與應得的權利。
五、對于野生鳥類資源的立法建議與完善
(1)增設刑法專章關于破壞環境保護類的罪。將對破壞環境保護的行為提升為單獨一章的重要性高度,將破壞野生鳥類資源的行為置于該章之下,增設專節。眾所周知,目前還存在許多由于不懂法,不知法,而無意中就觸犯刑法鋃鐺入獄的情形,將對于鳥類的保護設為專節,可以極大程度上增強人們對于野生鳥類保護的法條理解與認可,從而避免不小心一伸手就觸碰刑法的紅線。
(2)建立區別之上的統一管理體制,將對野生鳥類的保護與處刑區別于其他類別的動物。由于野生鳥類的特殊性,其與人類接觸的緊密性與分布的廣泛性和人們對于鳥類的非熟識性的矛盾不斷地引發人們對于法律設定處刑的質疑。同時,刑法上籠統對于野生的瀕危、珍稀物種予以保護,而不區別種類,有違動物的生存規律,野生動物中還分有哺乳類、爬行類、兩棲類、昆蟲類等物種,都具有各自的生活特性與生存規律,刑法應予區別化保護,只有根據鳥類的自身特點與規律來進行精細化的保護才可實現刑法所最終想要實現的刑法保護的目標。
(3)突出罰金刑,減少自由刑的運用。首先,我國對于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的態度一直就是處以重刑,但這絲毫無法阻擋各地偷獵盛行,重刑之下反而增加了其價值,使許多人敢于鋌而走險,“過分依賴重刑來懲治犯罪實際上是一種“高成本,低收益”的犯罪治理模式”,⑩由此,重刑是無法根本解決問題;其次,由于犯罪的隱蔽性,大多數破壞鳥類資源的行為無法被發現,只能憑借公安機關慢慢發現偵破或群眾舉報,刑法的重刑之策無法很好的落實下去,人們也不會對于有著畏懼心理;最后,鳥類資源的破壞行為無非就是為了逐利,而加大罰金刑的力度則起到增加犯罪成本的目的,這樣的話,盜獵者們(或其他破壞行為人)在做出行為之前就會衡量取舍。
(4)擴大保護范圍,將一些普通野生鳥類也納入保護范圍。野生鳥類品種繁多,在普通群眾尚無法一一識別的情況,最好對于野生鳥類予以普遍性的保護,如此可以更長久更持續的維護野生鳥類的種群完整。當然,在保護方式上是要區別于那些珍貴、瀕危的動物,以避免處刑的泛泛化,過猶不及的情況。現行狹窄的保護范圍會讓人想到“不屬于保護范圍的野生動物是否意味著沒有生存權”,只有普遍保護才可形成整個生態共生狀態。
(5)不斷滲透動物福利的思想,與社會道德想契合。現實中,人們會對于公開虐殺、虐打動物的行為深惡痛絕,但在法律上卻對其無所奈何,這種維護動物生存權的道德觀理應得到刑法的認可,從法律上禁止這類行為,對于野生鳥類也應如此,維護其基本的生存權。其實,在新修改的“野生動物保護法”里第26條已經隱約反映了動物福利的思想,“不得破壞野外種群資源,并根據野生動物習性確保其具有必要的活動空間和生息繁衍、衛生健康條件,具備與其繁育目的、種類、發展規模相適應的場所、設施、技術,符合有關技術標準和防疫要求,不得虐待野生動物。”刑法上也要跟進一步,通過立法不斷在社會上確立動物福利的思想,更加全面的對鳥類進行保護。
(6)綜合發揮社會合力共同維護野生鳥類資源。首先,應當加大對于野生鳥類保護的宣傳,尤其在邊緣山區,擴大宣傳。當前,人們對于野生鳥類的關注不夠,認識也不夠,對于哪些是國家所保護的哪些不是也無法很好的區分,導致經常發生群眾所無法接受的判決,保護思想宣傳到位了,鳥類的種群方可不被破壞。其次,不斷強化行政機關的監督管理作用,刑法是維護鳥類資源的最好一道防線,在此之前,相應行政機關林業部門等應在社會中出現其努力保護的身影,行政監管的缺失會造成更大的資源破壞,監管到位了,也便不需要刑法的最終制裁。最后,完善相應的配套規定,很多相關保護條文與規定早已出臺多年,已經跟不上現今社會的運行規律與鳥類的種群狀態,像“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就是典型,出臺年限距今久遠,急需做出調整,應當跟上國際步伐,像IUCN(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就是每年公布一次瀕危物種名錄,即使每年都更新達不到條件,也應每隔3年或5年更新一次名錄,從而對一些物種及時跟進保護。此外,16年新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陸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第九條“任何單位和個人發現受傷、病弱、饑餓、受困、迷途的國家和地方重點保護野生動物時,應當及時報告當地野生動物行政主管部門,由其采取救護措施;也可以就近送具備救護條件的單位救護。”雖然規定了明確的發現處理規定,但現實中很少有人會意識到送往救助站,發現了就會帶回去自己先養著,這就無意識中又違反了規定,另外,在一些偏遠山區地方,也不具備能及時救助的條件,因此,法律上應當確認由發現者臨時帶回家救助的合法性。
參考文獻
[1]陳福牛.野生動物刑法保護之完善—以河南大學生“抓鳥案”為例[J].法制與社會,2016,6.
[2]吳獻萍.論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J].中山大學學報論叢,2004年第24卷第4期.
[3]彭文華.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疑難問題研究[J].法商研究,2015,(06).
[4]張明楷.《刑法學》(第五版)[ M] .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10頁.
[5]趙秉志.刑法總論問題探索[ 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54.
[6]陳琴譯.瑞典刑法典[ 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30.
[7]肖怡譯.芬蘭刑法典[ 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60,136 -138.
[8]儲槐植.美國刑法·第三版[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19,201.
[9]羅結珍譯.法國刑法典[ M] .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5.189 -196, 224 -226.
[10]王志祥、韓雪.我國刑法典的輕罪化改造[J].蘇州大學學報.2015(1).
[11]詹長英.試論完善我國野生動物保護法刑事立法的有關條款[J],野生動物雜志,2007,28(5).
作者簡介:趙華陽(1994-),男,湖北襄陽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碩教育中心2016級碩士研究生。
(作者單位:湖北武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法碩教育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