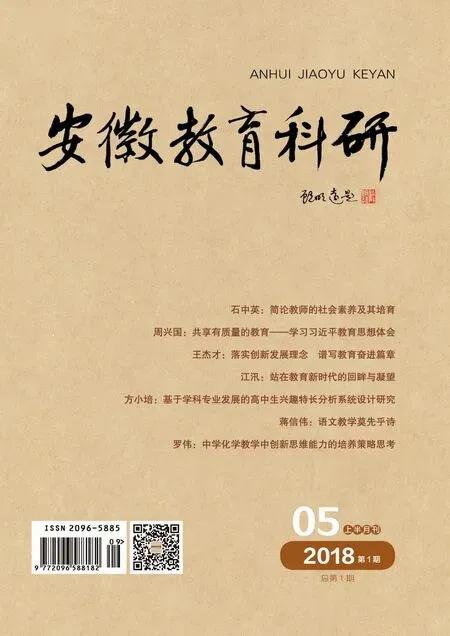語文教學莫先乎“詩”
蔣信偉
(合肥市第一中學 安徽合肥 230601)
一個值得反思的現象是,語文老師對詩歌教學越來越望而生畏了。隨之,詩歌教學也在格式化、程式化、技術化的任務完成中走向可悲的放逐。但《中國詩詞大會》的收視率、“叫座率”,似乎在告訴人們:這個時代詩歌沒有走向終結,如果說要走向終結的話,只能是人們那被物欲堵塞、蒙蔽的內心世界。
詩歌是青春世界的最好代言。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學生寫詩是一種風尚,“文藝范”背后折射出的是青春思考與時代激情的交匯與碰撞。而當下,寫詩對中學生來說似乎已經成為一種奢望,詩歌也接不上他們生活的地氣。對此,語文教師何為?
人教版語文高中必修教材第一課是什么?為什么要把這篇課文放在高中語文教學的第一課?《沁園春·長沙》這首詞以青春的激情,生動地詮釋了以天下為己任、改造舊世界、創造新天地的“少年精神”。以擔當與創造為核心的少年精神,與這首詞磅礴激昂的氣勢水乳交融,進而產生的引人向上的力量,足以表達中學生自我修煉的青春宣言。
唐朝為什么會成為詩的朝代,唐詩的主旋律為什么會彰顯獨特的少年精神?從根本上說,乃是李唐一族的文化基因重組,以致在情感動能、生活勢能上把文化包容、文明諧和的氣度、胸襟和力量空前地展現出來。反觀當下的“恰同學少年”又是一種怎樣的精神樣態,他們凝聚不起時代的精神定力,被冠之以某某一族,我們的教育似乎罪莫大焉。
子曰:“小子何莫學乎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當詩歌不能走進中學生時,何來的興觀群怨?子曰可以超越時代,成為經典的獨白。但師說也可以貼近學生,成為心靈的對話。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的語文老師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工作要做,就是把學生的心拉過來,拉到屬于詩的世界中,拉到本來屬于他們的青春話語中。語文老師不要有任何功利的顧慮,一個被詩歌浸潤、滋養的學生,他的語文素養必然是優秀的;一個沉潛、耕耘在詩歌教學中的語文老師,他的教學素養一定是卓越的。
詩歌教學最能展示教師的才情。不可否認,詩歌因其抒情的含蓄蘊藉對教學的藝術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抒情作品雖然內容十分豐富,但卻仿佛沒有內容似的——正像音樂作品用甜美的感覺震撼我們的整個身心一樣,但它的內容是講不出的,因為這內容是根本無法翻譯成人類語言的。這說明了為什么常常不但可以把一部讀過的長詩或戲劇的內容講給別人聽,甚至還可以多多少少用自己的復述來對別人發生作用,卻絕對無法掌握一首抒情作品的內容。是的,它是無法復述、無法說明的,只能讓讀者自己去感覺”。對于詩歌來說,教學本質上是一種藝術的詮釋、審美的感知和心靈的凈化,而這種要求也絕非一般老師所能達到的。
曾經有一個中學在招考語文教師時,要求極其簡化,沒有撰寫教學設計、無生上課、現場答辯等環節,只是要求應聘教師朗誦一首詩。簡化但絕不簡單,審視一位老師對詩歌的停頓、節奏、重音以及起伏變化的處理,不僅可以了解其對文本把握、理解與處理的能力,更能夠發現其是否具有語文教師的才情。
為何才情對語文教師、語文教學尤為重要?才情,顧名思義,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教學者的才華,這是語文教師的能力和稟賦;二是教學者的激情特質,此為語文教師的情感特質。值得關注的是,“才”與“情”二者并非獨立的內在要素,而是互相激涌、彼此點燃的關聯因素。也就是說,“才”為“情”蓄勢,“情”為“才”張本。從受眾的角度來說,“才”具有強大的客體塑造自我的可能性,“情”具有極強的客體實現自我塑造的主動性,可能性與主動性的相互結合,才能使語文學科的核心素養培育真正落地生根。
詩歌是一種才情高度凝聚的文學樣式,詩歌教學更是一種涵養學生才情的教學藝術。在詩歌的課堂里,詩人的才情、教師的才情以及學生的才情三者相互引發、激蕩,構成一種基于心性的情力推進環,形成一種“相忘于江湖”的文化情境。以徐志摩的《再別康橋》為例,詩人對離別的心的感悟與美的呈現,教師對文本的心靈解讀與情境演繹,學生對自我的鏡像代入與詩思撥動,把“康橋”作為三者際會的邂逅之地和對話的想象空間,以及由此而蔚為心力的發力場和融合地,煥發出超越庸常的巨大力量。
為什么我們的學生越來越不喜歡語文了?縱然訴苦萬千,恐怕庸常也難辭其咎。語文的庸常,大致有三個層面。一是課程層面,表現為必修模塊之間缺乏明顯的難度梯度,雖在教學要求上有一定的層次性,但就高考而言,先上任何一個模塊,似乎也無甚不可。另外,由于教學時間的限制,基本上要求進入高三年級就必須進入復習教學,這一限制,使得選修模塊的教學時間極為有限,也就造成基于興趣的語文選修往往會走過場。梯度的缺乏和時間的限制,使語文教學在走向平面化、考試化中喪失了體系化的特色和個性化的亮色。
二是教師層面,職業倦怠日趨消磨了教師的激情,不少教師缺乏深入鉆研的內在動力,缺少課堂對話的從容心態,缺失人文自信的精神風骨,以庸常為常態,只能換取學生的慵懶和不屑。
三是教學層面,過于突出以考法為核心的語文教學,在考點與考點之間迷茫游走,在考試與練習之中穿插前行,把文本魅力與人性溫度拋到九霄云外,卻驚呼“教師用心在教,學生真心不學”!
語文教學莫先乎詩。常見一位語文教學名師,學生在早讀時,他也在窗外“早讀”。手里捧著一本厚厚的《唐詩宋詞鑒賞》,或昂首目天,或閉目含玩,時而放聲誦讀,時而掩卷沉思,只見品到妙處時,禁不住擊節稱贊。常笑其“上課時如同打了雞血,狀態好比氣球漲滿了氣”。連學生常感枯燥的作文課,他都能上得“活蹦亂跳”,激情四射!
顯然,他的語文課超出了庸常,而這種“超出”的本質是語文教師學科氣質與修養的內外兼修,從而形成“超越自我、出乎本然”的境界。語文老師要超越庸常,就必須具備一定的境界,有一種近乎純粹的定力和修養。
清華大學原校長梅貽琦曾提出“從游”這一生動的比喻,以老師為大魚,學生為小魚,認為“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從游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然而,現在的語文教學所做的事,往往卻是“有為而不成”。我們過于注重從方法論的角度殫精竭慮地去調動學生學習語文的興趣,“小魚”卻“尾隨不遠”,就徑自散漫各自游去。
可見,“大魚”能夠“前導小魚”,不能只靠方法,關鍵還在于“大魚”自身的“濡染力”及其創造的“觀摩境”。回到詩歌教學的問題上,教師的“濡染力”和教學的“觀摩境”是以詩歌為原點構成的力與場的關系,也是以生活為視角構成的情與意的關系。也正是因為詩歌的情性力度最大、情感溫度最高,才能使得教學的磁場最強、學生的意愿最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