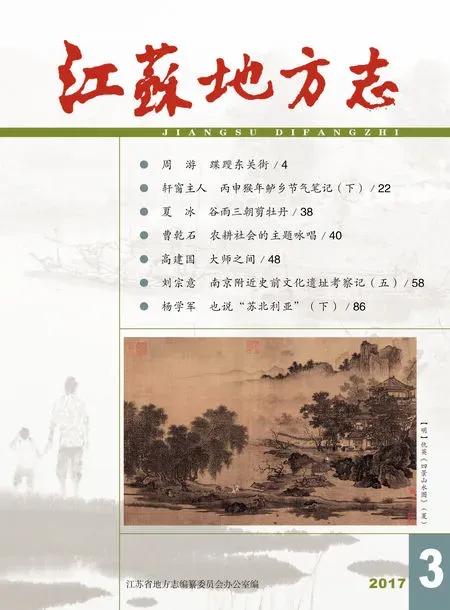百年三里橋
◎ 宋羽
百年三里橋
◎ 宋羽

吳橋上遠(yuǎn)眺無錫老城區(qū)
去無錫,不可不看看穿城而過的古運河;看古運河,則不可不走走一百年前無錫老城北門外最繁華的三里橋。
今天的三里橋地區(qū)大約從無錫勝利門往北,從北大街附近的吳橋開始,沿著運河過三里橋,直至蓮蓉橋。和數(shù)百年前一樣,運河的水悠然地從一座座橋下流過,在無錫城北分開一道岔,一支匯入梁溪河,一支順著惠山東麓流淌,兩支水流在南長街的盡頭匯合,繼續(xù)逶迤南下。千余年來,古運河就沿著這樣的脈絡(luò)與古城相依相伴,像一段割舍不了的情緣,至今仍相互訴說著綿綿不絕的衷情。
三名四橋
“三名四橋”的說法在三里橋一帶由來已久,在這片水網(wǎng)交織的秀美之地,橋是必不可少的點綴,由北往南共坐落著四座橋,它們的名字分別是吳橋、三里橋和蓮蓉橋。明明是四座橋,卻只起了三個名字,這讓許多初來無錫的人想不出個所以然來。
原來,這四座橋中的“三里橋”是個“雙胞胎”,為了便于區(qū)分,老無錫人習(xí)慣上把靠近吳橋的喚作“新三里橋”,另一座稍遠(yuǎn)一些的喚作“老三里橋”,兩座橋仿佛一對孿生兄弟,隔著運河水相互對望。時光像一本大書,一頁頁翻過,兩座橋的面容也漸漸變得滄桑起來。曾幾何時,新三里橋的高度與跨度在無錫人眼中是極其引人注目的,而今,這樣的光芒早已黯淡,若不留心尋找,很容易就與這座大橋擦肩而過了。
還是老三里橋名氣更大一些,因為距離老無錫城的北門大約三里路,樸實的無錫百姓就給它取了這個平實而又生動的名字。據(jù)說,老三里橋旁曾有一座木質(zhì)樓房,名叫“芙蓉樓”,這座三層木樓占地三開間,是當(dāng)年老北門運河水畔最高大最精美的建筑。每到炎炎夏日,水邊荷花盛開,紅似胭脂,綠如翡翠,坐在芙蓉樓上,在習(xí)習(xí)涼風(fēng)中賞荷品茗,聽采蓮姑娘唱起水淋淋的漁歌,這是多么愜意自在的生活!
今天的城市已很少能找到這般貼近大自然的景象了,縱然是河網(wǎng)密布的江南,城市的河道里也難見到別樣紅的大片荷花了。可是在1400年前的唐朝,無錫北門一帶荷香遍野,所以北門也被人們稱為“蓮蓉門”。如此清新的名字,讓那堅硬的城磚也變得柔軟和多情了起來,仿佛淡雅的青花瓷瓶上的寫意荷塘,氤氳著水與墨相互交融時幻化出的韻律,淡淡的詩情畫意搖曳在江南的風(fēng)中,讓人覺得這樣的城門天生就是該進入畫中的。芙蓉門,它的命運似乎與城防無關(guān),只為這美景而存在。
“美人遙盼木蘭舟,一夜相思隔春水。”北門外的運河水,滿載著一池胭脂霞色,將小小的無錫城裝點得脈脈含情。
也許是因為十里荷塘曼妙景致的緣故吧,老三里橋南邊就有一座蓮蓉橋。今天的蓮蓉橋是一座現(xiàn)代化的斜拉索大橋,如長虹臥波連接著運河兩岸四通八達(dá)的立交橋,唯有傍晚時分,霞光將挺拔的橋梁映襯出淡淡的羞色時,人們才能從泠泠的波光中想象出當(dāng)年荷香縈繞的美景。
今日的通衢大道,昔日是無錫城北最繁華的通商貿(mào)易之地,看看蓮蓉大橋周邊的老地名——竹場巷,一個半世紀(jì)前,這里的竹器經(jīng)營異常紅火;笆斗弄,匯聚著一批制作笆斗的手工作坊;布巷弄,顧名思義是絲綢布料的集散地;麻餅沿河,念著名字就能嗅得到當(dāng)年濃濃的芝麻香;還有芋頭沿河、桃棗沿河……這些生動的名字勾勒出的是一幅安寧祥和的生活畫卷,一縷縷煙火氣將紅塵中的日子渲染得那么親切。
就在老三里橋和蓮蓉橋之間,還有一座赫赫有名的米市。位于江南地區(qū)中心位置的無錫一直以來就是糧食運輸?shù)闹匾⒌兀┖歼\河貫穿無錫全境,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南等省的糧船南來北往都要從無錫經(jīng)過。據(jù)記載,乾隆年間,無錫的糧食吞吐量達(dá)到八百萬石,到清朝末年,從北塘大街到老三里橋,不足一公里長的河畔已分布著大小糧行80多家,糧食儲存量為東南各省市之冠。那時候,還只是常州府下屬縣城的無錫,就已經(jīng)和長沙、蕪湖、九江等江南重城并稱為全國四大米市了。可以想見,當(dāng)年的運河水上,川流不息的定是長長的船隊,河岸的碼頭上,米行老板、搬運工人、纖夫、車夫的身影絡(luò)繹不絕,京腔、吳語、江淮話、閩浙方言交織在一起,將這片彈丸之地渲染得五光十色。
城市總會在歲月的變遷中改變著面容,今天的古運河已經(jīng)遠(yuǎn)離了交通要道的位置,河面偶有船只經(jīng)過,顯得那么孤單冷清。許多繁華的老街巷已經(jīng)隨著舊城改造消失了最后一絲痕跡,唯有老人們蒼白的記憶里,還能尋覓到那些斷斷續(xù)續(xù)的故事。
風(fēng)月吳橋
水是江南的脈絡(luò),也是無錫生命的源泉,運河如同一根血管,為無錫源源不斷地輸送著生命的力量。河水悠悠,生生不息,運河與無錫,注定了世代的血脈相連。
當(dāng)運河流過江南,富庶的小城便洋溢著自足的笑聲,船從窗前過,水在身邊流,沾衣欲濕的杏花細(xì)雨,驚鴻一瞥的春閨紅顏,為市井的繁華增添了幾許情意和遐想。風(fēng)牽著水的手,像飄動的衣袂,行走出一條無形的曲線,流暢而灑脫。彎彎的水,彎彎的路,彎彎的橋,水中倒映著彎彎的月,在彎彎的眉眼間唱出一曲彎彎的思念。
吳橋,就在這彎彎的風(fēng)月里安詳?shù)囟冗^了百年時光。
遠(yuǎn)處是錫惠二山黛青色的山影,近處是古運河畔初綠的楊柳,吳橋可謂盡覽一方山水空蒙的風(fēng)光。
吳橋是無錫最早的鋼鐵桁架結(jié)構(gòu)的公路大橋,曾是溝通惠山古鎮(zhèn)至火車站的交通要道。100年前,當(dāng)吳橋的鋼鐵骨架出現(xiàn)在水墨畫一樣的惠山腳下時,粗獷的身軀定為這無限溫柔的風(fēng)月增添了一抹剛勁之氣。那時候的江南,遍布小橋、流水、人家,鋼鐵鑄就的橋梁居然與陰柔的景致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實在是一件讓人嘖嘖稱奇的事情。
說到吳橋,就不能不提及一個名叫吳子敬的人。
吳子敬,祖籍安徽黟縣,是民國初年江南地區(qū)著名的民族工商業(yè)家,他在江浙一帶創(chuàng)辦的民族實業(yè)成為近代中國民族資本積累的基石。吳子敬年輕時,因為家中貧困,獨自來到上海南翔的布莊學(xué)生意,也做過英國怡和洋行絲棧的職員,憑著聰明好學(xué)的勁頭,他很快熟悉了絲廠業(yè)務(wù),先后和朋友合資創(chuàng)辦了協(xié)和絲廠、協(xié)安絲廠、吳翁絲廠,經(jīng)過十多年苦心經(jīng)營,積累了40余萬兩白銀的資本。1909年,吳子敬和無錫民資實業(yè)家何夢連、祝大椿在惠山浜開辦源康絲廠,從此與無錫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
吳子敬每年都要來無錫收購蠶繭,每次都會在無錫逗留數(shù)月之久。據(jù)說,當(dāng)時有一個名叫桂林的名妓,懂詩書畫藝,舉手投足頗有大家閨秀風(fēng)范,讓吳子敬傾心不已,然而桂林只把吳子敬看做風(fēng)流商人,并無真情。后來,吳子敬提出要為桂林贖身,沒想到桂林已經(jīng)戀上了一個白面書生,藏著不肯見他。一日,滿腹愁緒的吳子敬與鄉(xiāng)紳薛南溟乘坐畫舫游覽湖光山色,薛南溟見好友郁郁寡歡,于是通過無錫朋友幫忙,找到了桂林。在畫舫上,薛南溟和朋友對桂林說:“嬉笑風(fēng)塵終非長久之計,風(fēng)塵女子,有幾個得以善終?吳先生對你一片真情,替你贖身是拯救你于水火,那書生不過念著魚水之歡,一旦私蓄用盡,定然棄你而去。等到你風(fēng)韻不再,想再遇到吳先生這樣的人,恐怕為時已晚。”
一句話說得桂林如夢方醒,愿意跟隨吳子敬從良。吳子敬對無錫士紳也是感激不已,決心為鄉(xiāng)鄰們做一些實事以表謝意。當(dāng)他得知惠山浜一帶水流湍急,經(jīng)常有渡船被風(fēng)浪打翻的情況后,立刻與當(dāng)時的無錫市公所總董事薛南溟、副總董事錢鏡生商議,雇工修建一座現(xiàn)代化大橋。
吳子敬慷慨地出資27000兩白銀,于1916年的春天開始造橋。大橋的樣式仿造上海外白渡橋,長78米,寬7.2米,在當(dāng)時是頗為壯觀的。大橋建成后,兩岸物資和百姓的往來更加方便了。時至今日,盡管大橋已經(jīng)經(jīng)過了三次大規(guī)模改造,新的橋梁已不再是昔日的模樣,但一如既往的是車水馬龍的繁忙。
遺憾的是,大橋尚未竣工,吳子敬就在上海患病去世了。為了紀(jì)念這位多情的工商業(yè)家的功績,無錫士紳們給大橋起名為“吳橋”。薛南溟還為好友主持召開了追悼會,將吳子敬的牌位迎入惠山腳下的尊賢祠和丞德祠內(nèi),與列代鄉(xiāng)賢一起,供后人瞻仰。
“樵客耕夫官塘苦喚斜陽渡,星移物換口碑不沒惠人名。”這是無錫百姓為吳子敬撰寫的挽聯(lián)。吳子敬,吳橋,一段流傳在吳地市井的風(fēng)月佳話,像是天然的巧合,又像是冥冥中注定的因緣。
絕版的“江尖”
清朝無錫籍詩人杜漢階著有《逸軒詩草》,詩中寫道:“惠山泉酒久馳名,酒店齊開遍四城。最是江尖風(fēng)景好,紅闌綠柳遠(yuǎn)山橫。”江尖,自古就是無錫古運河上飽覽山水風(fēng)光的好去處,不論是布衣還是鴻儒,人們總愿意在某個閑暇的午后,悄悄逃離紅塵的束縛,來到江尖小憩半晌。或遙看惠山點點春色,或靜候清茗漸透涼意,或吟詩,或垂釣,或?qū)模蚺收劊磺锌扇朐娨嗫扇氘嫞靡慌捎迫蛔缘玫膱D景。
江尖,沐浴著運河水,看似不在紅塵中,卻未跳出三界外。
“尖”是江南吳地方言,在別的地方是極少見到用“尖”來稱呼水中小島的。在無錫北門外,零星分布著五座尖,分別是南尖、北尖、小尖、雙河尖和江尖,這些尖尖的小島仿佛睡夢中不小心跌落到凡間的星辰,在平靜的水面濺起一圈圈漣漪,歡快的水珠在明媚的陽光中凝結(jié)成一顆顆珍珠,又被溫柔的風(fēng)吹散開來,彌漫成朦朧的霧靄,氤氳出一個濕漉漉、清凌凌的江南。
從風(fēng)水學(xué)角度看,江尖占據(jù)了無錫城絕版的位置。古人認(rèn)為,兩條水流交匯的地方是“吉穴”,若背后還有高山可靠,那就絕對是風(fēng)水寶地了。江尖恰位于無錫北門外古運河中段,西北部就是風(fēng)景秀麗的錫惠二山;三角形的小島恰如一只翩躚于水面的燕子,頭部迎著水流,展翅飛起。河水在江尖分成兩股,一支流向蓮蓉橋,一支流向惠山,兩股水流在老無錫城南門外的跨塘橋附近匯合,沿著千年古河道,滋潤著江南的萬畝良田。
和蓮蓉橋的水域一樣,江尖一帶在古代也是茂密的荷塘,荷塘與江南仿佛天然的伴侶,江南的亭臺水榭、小橋人家若沒有田田荷花點綴,將會失去多少玲瓏的顏色。明代以前,北門外的運河水域非常遼闊,像一片湖,煙波浩渺,景色宜人,荷花盛開時更是美不勝收,因此,江尖在古代被稱為“芙蓉尖”。無錫名門秦氏的后裔秦銘光在《錫山風(fēng)土竹枝詞》中描繪道:“芙蓉尖渚枕湖清,近市鳑魚此著名。等是民老今昔感,安知頳尾不金睛。”有青山綠水,有芙蓉秀色,更有鮮美的魚蝦,真可謂是物華天寶之地了。
詩中寫到的鳑魚就是生活在江南一帶的鳑鲏魚,這是一種沿河群居的淡水魚,約半寸來長,身體扁平而小巧。鳑鲏魚總是與河蚌相生相伴,它們把魚卵產(chǎn)在河蚌體內(nèi),利用蚌的呼吸所產(chǎn)生的水流來提供養(yǎng)分,當(dāng)魚兒孵化成形,便從蚌殼中游出。有趣的是,河蚌也將卵附著在鳑鲏魚身上,二者就這樣默契地合作著。
據(jù)說鳑鲏魚鮮香無比,尤其是金眼鳑鲏,素來是難得一見的珍品。戲劇理論家周貽白也寫過一首《竹枝詞》——“芙蓉尖上晚秋色,隔岸樓臺沸管弦。金眼鳑魚紅色鯉,網(wǎng)頭潑剌乘時鮮。”金鳑,紅鯉,既有口腹之歡,又能賞心悅目,這樣的生活真是活色生香。
鳑鲏魚可紅燒,可清蒸,也可熬湯,尤其讓無錫人鐘愛的是椒鹽鳑鲏。將魚瀝干水分,放在油鍋中炸成金黃色,撈起后再復(fù)炸一次,等油漸干,灑上蔥末、椒鹽,松軟酥脆,滿腹都是濃郁的香氣。十多年前,老無錫人都說:“鳑鲏比河豚還肥,比刀魚還鮮,比銀魚還嫩。”
我之所以要說“十多年前”,是因為現(xiàn)在已經(jīng)尋覓不到鳑鲏魚的蹤跡了。城市的發(fā)展總會給人們留下太多遺憾,由于過度捕撈,以及多次河道改造,鳑鲏魚生存環(huán)境開始惡化,漸漸淡出了百姓的生活,最終凝固成一座城市與自然曾經(jīng)和諧相處的回憶。
江尖所記錄的關(guān)于無錫的記憶,除了鮮美的鳑鲏魚,還有繁華的陶市、米市。
作為近代中國民族工商業(yè)的發(fā)祥地之一,無錫自古就有著經(jīng)商互市的傳統(tǒng),交易,讓這里的百姓變得靈動而聰慧,也讓太湖畔的這座小城擺脫了地域的束縛,成為中國著名的工商業(yè)之都。
清朝末年,由于北門外運河水道寬闊,便于大型船只航行,許多商船便就近展開水上貿(mào)易,江尖也就成了絕佳的貿(mào)易市場。大大小小的碼頭遍布沿岸,商船和民船成排,到處是桅桿和跳板,籮筐、扁擔(dān)橫七豎八地堆在岸邊,等著運送貨物。一時間,小小的江尖被南來北往的人們擠得水泄不通。當(dāng)時的無錫百姓上江尖,要么從北塘大街乘坐擺渡過河,要么走過三里橋一帶的布巷弄,過長安橋,穿過橫浜里,再到尖上。所以無錫曾有一句民諺,叫做“江尖渚上團團轉(zhuǎn)”,甚是生動有趣。過去每年的三月廿八,三里橋一帶都要舉行盛大的香會,人山人海,比過農(nóng)歷年還隆重;到了端午節(jié),從江尖到吳橋,一條條嶄新的龍舟穿梭而過,熱鬧非凡。
今天的江尖已經(jīng)改造為一座水上休閑公園,茂密的樹木掩映著江南風(fēng)格的回廊、馬頭墻,演繹出江南水鄉(xiāng)特有的風(fēng)韻。江尖公園最引人注目的還是造型各異的雕塑,在公園中央,坐落著一組米缸雕塑群,大大小小的米缸堆在一起,足有兩米多高。原來,昔日的米市就是用這樣的缸來儲藏和運載糧食的,米市的繁榮使得對米缸的需求量大大增加,迅速帶動了制陶業(yè)的發(fā)展。當(dāng)時比較有實力的缸店老板,會在店鋪前把缸堆得高高的,以顯示其富有。這看似散亂堆砌的米缸造型的雕塑,恰恰是無錫商業(yè)繁榮的生動寫照。
其實,江尖這個名字也來源于米缸。在無錫方言里,“缸”和“江”同音,而缸店又被習(xí)慣叫做“缸棧”,所以這里曾經(jīng)也叫“缸棧渚”。渚與尖同義,棧與尖同音,諸多巧合碰撞在一起,終于誕生了“江尖”這個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名字。
江尖,承載著無錫好幾個世紀(jì)的記憶,這份絲絲縷縷的牽掛,編織出絕版的美麗。
運河上的江尖,周遭縈繞著樸實的煙火氣息,卻又如伊人遺世獨立,靜坐水中央。它的故事,來自紅塵,來自市井百姓的生活,而故事中的美,已悄悄定格在了那一幅幅泛黃的畫卷里。
兩水回環(huán)只通舟
乾隆皇帝愛作詩,據(jù)說一生寫了3萬余首詩,只可惜這位愛新覺羅家族的皇帝幾乎沒有一首詩能成為膾炙人口的佳作,說他是附庸風(fēng)雅怕也不為過。
江南的美景、美食、美人總吸引著風(fēng)流天子的腳步,對紫禁城內(nèi)的帝王來說,江南是一種充滿誘惑的文化意向,它代表著浪漫、詩意、優(yōu)美和情調(diào)。乾隆皇帝一生六下江南,僅在無錫一帶就寫下了不少詩句。盡管讀來平平,并沒有什么出彩的地方,但畢竟是御筆親書,對無錫來說,也是一項不可多得的殊榮了吧。
下面這首詩也是乾隆皇帝的大作——
兩水回環(huán)抱一舟,不通車馬只通舟。
到來俯視原無地,攀徙遙吟恰有樓。
含雨濕云篇似重,隔湖煙嶼望如浮。
惠山翠色迎眉睫,慢濾沾衣作勝游。
這首詩名叫《黃埠墩》,所描繪的是吳橋以南的古運河水面上一座小巧玲瓏的島嶼。在皇帝看來,這座小島出沒于水波煙云之間,若有若無,若隱若現(xiàn),更兼山色含黛,水波粼粼,真如海市蜃樓的仙境一般。
運河水道曾與無錫城北的古芙蓉湖相連,由于明代當(dāng)?shù)毓賳T治理湖水,芙蓉湖水域逐漸縮小,隱藏于水下的高地就露出了水面,形成了一座座島嶼。在江南方言里,大一些的島嶼叫做“尖”,小一些的叫做“墩”,黃埠墩就是這樣一座美麗的小島。
黃埠墩實在袖珍得很,整個小島只有220平方米,比一座農(nóng)家小院大不了多少。島上建有一座精致的樓宇,飛檐翹角,層巒疊嶂,雖然小巧,卻不乏氣宇軒昂的大氣。樓宇被一圈圍墻環(huán)抱著,院內(nèi)遍植花木,枝繁葉茂,鳥語花香,儼然浮在水上的一戶江南人家,讓觀者浮想聯(lián)翩,心馳神往。
據(jù)說,無錫古運河中曾潛藏著一條蛟龍,一天夜半時分,三里橋米市附近忽然狂風(fēng)大作,剎那間白浪滔天,大雨傾盆,天地間一片混沌。第二天早晨,驚魂未定的人們發(fā)現(xiàn)停泊在河邊的船只全部傾覆,貨物蕩然無存。人們懷疑是蛟龍所為,便在這片水域中間筑了一座土墩,把圓形的土墩視作龍珠獻(xiàn)給蛟龍,蛟龍受到百姓的這份安撫后,從此再也沒有作亂過。直到今天,無錫的老人們還能興致勃勃地告訴你,江尖是龍頭,小尖是龍身,龍尾則是西水墩。長江中下游一帶,每到夏季汛期,水位都會驟漲,可無論運河水怎么漲,黃埠墩這顆龍珠始終沒有被水淹沒過,成了無錫城中一處奇景。
其實,黃埠墩的真正締造者是被譽為“戰(zhàn)國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當(dāng)時江南一帶屬于楚國的疆域,丞相春申君被分封到江南吳地,為治理芙蓉湖水患,他相中了水中的這座小島,并在這里扎營落腳。春申君名黃歇,這座小島也就被命名為黃埠墩了。
黃埠墩四面環(huán)水,南來北往的船只從小島兩側(cè)翩躚而過,水流沿著島嶼的輪廓描繪出一道道優(yōu)美的弧線,仿佛一幅古代丹青,盡顯明凈秀美之氣。
黃埠墩雖小,卻總有令世人矚目的大人物前來光顧。1276年,偏安江南西子湖畔的南宋王朝步入了生命的盡頭。這一年正月,一隊蒙古士兵羈押著一個瘦弱的文人經(jīng)過無錫,文人面容憔悴,但眼神中卻閃爍著不屈的光芒,如炬的目光中透露出憂思與憤慨。那個飄搖著冷雨的夜晚,士兵們把船只停靠在黃埠墩,也把一首悲壯的詩留給了這座小島。
“金山冉冉波濤雨,錫水茫茫草木春。二十年前曾去路,三千里外作行人。英雄未死心先碎,父老相從鼻欲辛。夜讀程嬰存國事,一回惆悵一沾巾。”這個滿腹愁緒的文人就是文天祥。狀元出身的他官居宰相,組織軍民抵抗蒙古鐵蹄入侵,兵敗后被敵軍俘虜,沿京杭大運河北上押往元大都(今北京)。后來,無錫人為了紀(jì)念這位舍生取義的愛國英雄,在黃埠墩上建了一座正氣樓,將文天祥的詩句鑄成石碑,立在樓旁。
關(guān)于在黃埠墩上歇過腳的人,當(dāng)?shù)赜小岸鄱嘁磺嗵臁敝f,“二帝”即清朝的康熙、乾隆兩個皇帝,“二相”即戰(zhàn)國的楚相春申君和南宋宰相文天祥,“一青天”就是被民間譽為“海青天”的海瑞。當(dāng)年擔(dān)任應(yīng)天府(今南京)府尹的海瑞到無錫游玩時也被黃埠墩的美景吸引,登臨小島后,為環(huán)翠樓題寫了匾額“環(huán)玩臨水第一樓”。
時過境遷,這些曾在黃埠墩發(fā)生過的故事都已遠(yuǎn)去,朦朧成了星光下淡淡的霧靄。黃埠墩就像一座戲臺,一幕幕或喜慶或悲壯的傳奇在這里登臺,又在這里謝幕。墩,依然是千年前的墩;水,依然是千年前的水,變遷的是歲月的痕跡,不變的是這一方山水所包容的氣韻,以及——江南的無限風(fēng)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