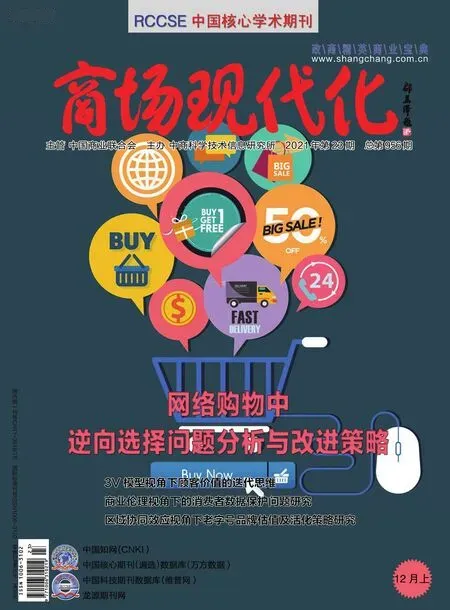資本形成能力與經(jīng)濟增長相關性研究
駱世廣+張宇楷
摘 要:資本形成能力是區(qū)域經(jīng)濟發(fā)展的重要推動力,本文基于資本形成能力視角,從資本形成能力的來源結(jié)構(gòu)、傳導模式兩個環(huán)節(jié)實證分析了資本形成能力與經(jīng)濟增長的關聯(lián)差異。結(jié)果表明與區(qū)域經(jīng)濟發(fā)展關聯(lián)性較強的資本依次是外國直接投資、銀行貸款、財政資本,資本市場的作用仍待提升;最后提出促進與區(qū)域經(jīng)濟發(fā)展相適配的資本形成能力發(fā)展的建議。
關鍵詞:資本形成能力;經(jīng)濟增長;相關性;資本來源結(jié)構(gòu)
一、引言
資本對于經(jīng)濟增長的重要作用,無論是古典經(jīng)濟增長理論,還是新古典經(jīng)濟增長理論、新經(jīng)濟增長理論等,都有重要論述。然而,隨著經(jīng)濟發(fā)展階段的變化、經(jīng)濟一體化的推進、新技術(shù)革命出現(xiàn)的新特點、人口結(jié)構(gòu)的變遷等因素,資本之于經(jīng)濟發(fā)展的作用機制并非一成不變,甚至出現(xiàn)了連續(xù)性變化,區(qū)域差異也愈發(fā)明顯(趙昌文,2004);資本形成能力與經(jīng)濟增長的相關性機理需要不斷檢驗(李揚,張曉晶,2015;王定祥,李伶俐,冉光和,2009)。由于影響經(jīng)濟增長的因素除了資本之外,還有技術(shù)創(chuàng)新、勞動力、土地等,眾多因素中單獨研究資本的作用機制,必須將其他因素的作用剔除掉,如果上述其他因素的作用顯著,則不利于對資本形成能力作用的分析。基于此,我們選擇廣州和深圳這兩個城市作為研究樣本,原因之一在于這兩個城市同是我國華南地區(qū)經(jīng)濟最發(fā)達的城市,同時也是我國資本、創(chuàng)新集聚的主要城市,具有相似的區(qū)位特征、相近的發(fā)展路徑和同脈的文化(蔣玉濤,鄭海濤,2013;姜巍,2004);原因二也是近年來引起關注的是,這兩個城市近年來的發(fā)展呈現(xiàn)出不同的局面,深圳大有全面超過廣州之勢:總量上,兩地GDP已非常接近;結(jié)構(gòu)上,廣深兩地的第三產(chǎn)業(yè)占GDP比重均超過50%,但自2013年起,深圳的現(xiàn)代服務業(yè)在第三產(chǎn)業(yè)的比重超過60%,廣州第三產(chǎn)業(yè)則以傳統(tǒng)服務業(yè)為主;產(chǎn)業(yè)升級方面,2015年深圳新興產(chǎn)業(yè)增加值是7003.48億元,是廣州的三倍;趨勢上,2013年,廣州新登記企業(yè)戶數(shù)為154575戶,同期深圳為167220戶,旗鼓相當;2015年,廣州新登記企業(yè)戶數(shù)是205887,深圳則為299925,多于廣州近10萬家,深圳的資本聚集能力已遠遠領先于廣州。
因此,理清兩地經(jīng)濟發(fā)展的差異及導致差異的資本形成能力層面原因,有重要實踐意義。本文從資本形成的來源結(jié)構(gòu)層面研究資本形成能力與區(qū)域經(jīng)濟發(fā)展關系及資本形成能力的傳導效應。
二、區(qū)域資本形成能力及其比較
廣州深圳兩地資本形成的主要途徑是類似的,具體包括民間資本、財政性資本、銀行貸款、外商直接投資、上市公司權(quán)益融資等。全文數(shù)據(jù)根據(jù)廣東省統(tǒng)計年鑒(2000-2015)、廣州市國民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統(tǒng)計公報(2010-2015)、深圳市國民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統(tǒng)計公報(2010-2015),廣州統(tǒng)計信息網(wǎng)等整理而成,由于篇幅所限,詳細數(shù)據(jù)對比略。
1.廣深人均可支配收入較高,民間資本形成潛力都比較大
2000年至2015年間,深圳的城鎮(zhèn)居民可支配收入都比廣州的城鎮(zhèn)居民可支配收入高,但是廣州城鎮(zhèn)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增幅為9.02%,比深圳的平均增幅5.47%大。2015年,廣州城鎮(zhèn)居民可支配收入為46734.60元,實際增長為2.06%,農(nóng)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9323.10元,實際增長9.40%;深圳城鎮(zhèn)居民可支配收入為44633.00元,實際增長9.00%。由于深圳農(nóng)村居民占比極低,因此從居民可支配收入角度看,深圳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略高于廣州;居民可支配收入是資本形成能力的微觀表現(xiàn),但單憑此還難以直接定資本形成能力強弱,儲蓄率、消費水平對資本形成能力也有一定影響。不過儲蓄率整體下滑、互聯(lián)網(wǎng)經(jīng)濟拉底城市間消費水平的差距已成趨勢,在此背景下居民可支配收入對資本形成總量的影響不容忽視。
2.廣深兩地財政收入相當,自身積累能力較強
廣州、深圳兩地從2000年到2014年,財政收入增長了近10倍,且兩地相當。在支出方面,廣州略高于深圳;廣州財政支出從2000年的258.6億元,2014年增加到2525.38億元,15年間增加了9.8倍;深圳財政支出從2000年的225.04億元,2014年增加到2166.14億元,15年間增加了9.6倍;廣州略高于深圳。具體在公共財政收入上,在2015年,由于股市、樓市的帶動,深圳財政收入大幅增長。數(shù)據(jù)顯示,2015年,來源于深圳的公共財政收入達到7240億元,比上年增長30.2%,其中中央級收入實現(xiàn)4512億元,增長29.7%;深圳市地方級收入實現(xiàn)2728億元,增長31%,為近8年以來新高。分行業(yè)看,去年深圳稅收規(guī)模占比前四大行業(yè)是制造業(yè)、金融業(yè)、房地產(chǎn)業(yè)和批發(fā)零售業(yè),合計占整體稅收的比重達到71.6%。金融業(yè)等現(xiàn)代服務業(yè)貢獻較為突出,金融業(yè)稅收實現(xiàn)980億元,超常規(guī)增長60%以上。廣州稍顯囊中羞澀,廣州2015年公共預算收入僅為1349.1億元,僅為深圳的一半左右,當然這與廣州的財政收入要上繳省級和中央兩級財政,而深圳只與中央分成有關。
3.廣州利用外資數(shù)量相比于深圳處于下滑狀態(tài)
2000年,廣州利用外資28.89億美元,領先深圳10億美元;而到了2014年,廣州利用外資卻落后于深圳近7億美元。表明在吸引外資上,深圳更具有優(yōu)勢。
4.深圳在資本市場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廣州難以比擬
深圳證券交易所使得深圳企業(yè)在資本市場相比于廣州具有無可比擬的優(yōu)勢,因此,在上市公司權(quán)益融資方面,廣州落后于深圳,有時甚至遠遠落后于深圳。資本市場發(fā)展的區(qū)域不平衡性,即使在經(jīng)濟相對發(fā)達的珠三角地區(qū),仍然是凸顯的。如何在已有資本市場發(fā)展格局下提升直接融資比重,引領產(chǎn)業(yè)發(fā)展,需要多層次資本市場的輔助。
三、資本形成能力與區(qū)域經(jīng)濟關系的實證分析
從表1及表2可知:
(1)模型擬合優(yōu)度較高,資本形成來源與GDP增長關系顯著。以廣深兩地的GDP為被解釋變量,在0.05的顯著水平下,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對地區(qū)GDP影響較大,彈性系數(shù)分別為2.16和1.86且皆表現(xiàn)為顯著,即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1%,GDP分別增長2.16%和1.86%,可見廣州經(jīng)濟與外資的關聯(lián)度較深圳稍高。endprint
(2)另外,廣深兩地的上市公司權(quán)益融資產(chǎn)出彈性分別0.39和0.41,即深圳在上市公司融資方面的投入度和效率比廣州稍高;最后,相比兩地的財政支出和銀行貸款產(chǎn)出彈性,廣州高于深圳,說明廣州對財政的依賴性大于深圳。對廣州而言,繼續(xù)發(fā)揮財政資本對經(jīng)濟增長的有力作用的基礎上,通過促進金融發(fā)展,來優(yōu)化資本形成的結(jié)構(gòu)。
2.形成能力對第三產(chǎn)業(yè)產(chǎn)值的貢獻
從表3與表4可知,第三產(chǎn)業(yè)在廣深兩地的發(fā)展中皆處于較好態(tài)勢。
兩地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對第三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貢獻相對最大,兩者之間的相關度最高。外資與兩地經(jīng)濟的深度嚙合性基本顯現(xiàn)。財政支出、貸款余額與第三產(chǎn)業(yè)產(chǎn)值的擬合優(yōu)度相當高,產(chǎn)出彈性上廣州高于深圳,這是廣州近年來經(jīng)濟轉(zhuǎn)型的成果。盡管如此,前文所述,深圳的第三產(chǎn)業(yè)發(fā)展含金量更高,說明深圳民間資本的投資績效作用凸顯。
3.資本形成能力對高新技術(shù)產(chǎn)品產(chǎn)值的貢獻
從表5和表6可知,這部分模型的總體擬合效果稍低于前面的模型,但皆于區(qū)間[0.74,0.96]中,資本形成能力與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具有較強關聯(lián)。
高新技術(shù)產(chǎn)品產(chǎn)值受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較大,每增加1%的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兩地的高新技術(shù)產(chǎn)品產(chǎn)值分別增加2.96%和2.36%,產(chǎn)出效率較高;但擬合優(yōu)度低于其他類型資本,說明民間資本、財政資本、銀行貸款對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逐步展現(xiàn)較高的投資動能。從兩地財政資本、銀行貸款對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的產(chǎn)出彈性均大于1,相比較它們對三大產(chǎn)業(yè)的貢獻度而言,有了顯著提升。資本流轉(zhuǎn)呈現(xiàn)出新趨勢,但通過資本市場直接融資對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的貢獻仍較低,可能與大量高新技術(shù)企業(yè)所處發(fā)展階段有關。不過,有效發(fā)揮資本市場對高新技術(shù)企業(yè)的支持,尤其是提升科技型中小微企業(yè)金融獲得性,是亟待從政策層面重視的。
四、結(jié)論
本文立足于廣深兩地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評價,分析資本形成能力在區(qū)域經(jīng)濟發(fā)展中的作用,并利用實證方法確認兩者之間的作用機理,在此基礎上我們提出適配區(qū)域經(jīng)濟發(fā)展的資本形成模式和傳導路線。
1.繼續(xù)發(fā)揮財政資本對經(jīng)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同時加快資本市場建設
深圳具有證券交易所這一得天獨厚的條件,資本市場比廣州發(fā)達,因此深圳經(jīng)濟發(fā)展受資本市場支持力度比廣州大。廣州經(jīng)濟發(fā)展對財政的支持仍然比較依賴,這也并非一無是處,從供給端進行資本形成能力的結(jié)構(gòu)優(yōu)化與動能疏導還是比較容易操作的。但廣州金融發(fā)展結(jié)構(gòu)性失衡,金融市場金融服務盡管發(fā)展很快,但尚不能與新常態(tài)下的經(jīng)濟發(fā)展相適應;尤其是普惠性金融發(fā)展緩慢,創(chuàng)業(yè)金融仍停留在理論探討階段。廣州應抓住金融科技創(chuàng)新的契機,借助于大數(shù)據(jù)、人工智能技術(shù)改進金融服務模式,提升金融服務效率。
2.推行以公平為主導的長效發(fā)展機制
深圳投資效率較高,源于資本形成能力與第一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是負相關;而廣州的銀行資本、財政資本與第一產(chǎn)業(yè)產(chǎn)值呈現(xiàn)高度相關,并對其具有正向支持作用。這提示廣州在促進經(jīng)濟發(fā)展過程中,產(chǎn)業(yè)政策的實施應該謹慎。選擇性政策若不精準則極易導致產(chǎn)能過剩,政府重心應轉(zhuǎn)移到解決金融資源的傾斜問題,避免將金融資源錯配到產(chǎn)能過剩的產(chǎn)業(yè)中。系列針對科技型中小微企業(yè)的科技金融政策,秉承“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的傳統(tǒng)發(fā)展模式,并沒有起到預想的作用。在效率優(yōu)先下,公平往往是兼顧不到的;部分中小微企業(yè)會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去滿足預設條件而套取政策補助。由于政策性優(yōu)待具有典型的時間節(jié)點約束,更加加劇了部分中小微企業(yè)難以將主要精力投入到公司未來發(fā)展息息相關技術(shù)創(chuàng)新上。
政策的同質(zhì)化導致政策實施效果的必然不同,而差異化政策又不能精準化,政府控制金融有效供給不足,且供給結(jié)構(gòu)跟不上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的變遷;國企無法律授權(quán)不可為,中小微企業(yè)無法律約束皆可為,這種雙重標準是追求公平的速成之路。國企強勢,體量大,回旋空間小,則應嚴約束;廣大中小微企業(yè)處于弱勢,體量小,回旋空間大,則寬約束,通過這個過程,充分釋放微觀主體的活力。
3.資本形成能力的傳導要優(yōu)先考慮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
資本形成能力近年來呈現(xiàn)出新的趨勢,但總體上資本形成能力對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的貢獻度仍然處于低位。共享經(jīng)濟、長尾經(jīng)濟、零成本經(jīng)濟不斷涌現(xiàn),大數(shù)據(jù)、云計算、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物聯(lián)網(wǎng)、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shù)與經(jīng)濟、產(chǎn)業(yè)、科技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斷催生新業(yè)態(tài)、新產(chǎn)品和新模式的未來新形勢;這些新特征都要求決策部門能夠及時的掌握,并從資本供給端采取騎墻策略,即針對當前金融覆蓋性不太好的種子期、成長期科技型中小微企業(yè)的資金需求問題,政府應當直接發(fā)揮財政資金的支撐作用。而針對那些目前仍然能夠從金融機構(gòu)獲取金融資源的、而發(fā)展動力與創(chuàng)新驅(qū)動不一致的,政府減少或不再實施類似稅收返還或補貼的資助。
參考文獻:
[1]趙昌文.中國西部地區(qū)資本形成能力與經(jīng)濟增長相關性及其與東、中部地區(qū)的比較[J].中國經(jīng)濟問題,2004(05):64-72.
[2]蔣玉濤,鄭海濤.創(chuàng)新型城市建設路徑及模式比較研究--以廣州、深圳為例[J].科技管理研究,2013(14):24-30.
[3]姜巍.廣州、深圳經(jīng)濟增長因素實證比較分析[J].廣東外語外貿(mào)大學學報,2004,15(1):57-60.
[4]李揚,張曉晶.“新常態(tài)”:經(jīng)濟發(fā)展的邏輯與前景[J].經(jīng)濟研究,2015(5):4-19.
[5]王定祥,李伶俐,冉光和.金融資本形成與經(jīng)濟增長[J].經(jīng)濟研究,2009(9):39-51.
作者簡介:駱世廣(1981.01- ),男,河南信陽人,碩士,廣東金融學院副教授,(廣州)區(qū)域金融政策重點研究基地研究員,研究方向:科技金融、金融數(shù)據(jù)挖掘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