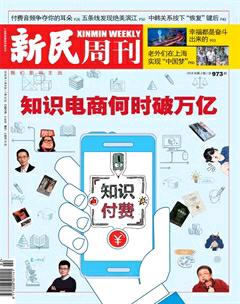解秘爆款:冰面上的狂熱
吳遇利
不久前,咪蒙團隊宣布進軍知識付費領域。三年后加薪不超過50%可申請全額退款,看似戲謔的豪言仍在試圖證明知識付費的未來。在這個行業內部,已經誕生了不少爆款,究竟是少數“頭領玩家”的紅利,還是每個人都可能挖出這一桶金?
從“星火”到“燎原”
在當今知識付費的含義中,“知識”的外延已經被大大拓寬,涵蓋了一切技能、信息、經驗等等,知識付費也可以被看做是信息付費。知識共享從免費走向付費,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知識付費的原始形態涵蓋了很多行業,例如出版、教育等等。在互聯網普及之后,這些業態都以積極的姿態進入了互聯網領域并衍生出了新的知識付費模式,例如出版業的電子書業務,教育行業的在線教育等。而在當時,我們現在所講的狹義的“知識付費”平臺,還處于混沌狀態之中:平臺設計不合理、支付手段繁瑣、缺乏行業知名人士的帶動以及國內用戶不習慣為虛擬商品埋單等等。其中較為突出的兩個知識共享平臺知乎和果殼,都蟄伏于專業領域之中,對內容和用戶進行深耕,逐漸塑造了一定的“知識共同體”的意識。

伴隨著微信和微博兩大知識分享平臺上“打賞”功能的上線,有眾多不同領域的內容和作者通過知識的分享獲取了酬勞。用戶在閱讀完喜歡的內容之后,可以點擊文章末尾的“打賞”鍵,向文章作者支付自定義數量的賞金以示鼓勵。雖然依靠“打賞”賺取的收入微薄,遠不及廣告為作者帶來的盈利,但是“打賞”功能卻在潛移默化之中培養起了用戶為虛擬產品埋單的習慣。
2014年《羅輯思維》推出付費會員制度,半天之內5500個會員名額一售而空,這可以說是互聯網形式的知識分享首次得到了大眾市場的認可。

2015年3月,果殼推出了線下一對一的咨詢應用“在行”,同年5月,《羅輯思維》團隊上線了知識分享平臺“得到”。作為同期上線的兩個知識付費平臺,“得到”顯然比“在行”受到了跟多用戶的關注和追隨。例如2016年6月5日,“得到”推出的爆款產品《李翔商業內參》上線,短短10天之內就收獲了4萬訂閱量。在今年3月,羅振宇向外界公布了“得到”客戶端的運營數據:總用戶529萬,日活躍用戶42萬,訂閱總人數79萬,產品訂閱總數130萬,盈利或超2億元。而在2017年11月,“得到”App大咖專欄《薛兆豐的北大經濟學課》總訂閱人數突破20萬,創下同類知識服務產品付費用戶數最高紀錄,被稱作“全球最大的經濟學課堂”。
在隨后的“知識付費元年”2016年中,各類知識付費平臺紛紛上線。
知乎于2016年4月推出其第一個知識付費產品“值乎”,在知乎原有的問答模式下,改進了一對一咨詢場景,以語音為主的回答,可以被所有人付費收聽,費用被回答者和提問者平分;緊接著知乎又在5月推出實時問答產品“知乎Live”,回答者創建一個Live并設定價格,此Live會出現在關注者的信息流之中,用戶點擊并付款后即可進入都群內,通過語音分享信息。“知乎Live”是知乎的核心產品,上線約半年之后,已經有超過200萬的參與人次。

就在知乎推出“知乎Live”僅僅一天之后,果殼緊隨其后上線了“分答”,早期以付費語音問答為主,答主用1分鐘的時間來解答問題,未付費用戶可以花1元錢來“偷聽”回答,利用了答主以及用戶非常碎片化的時間。
2016年6月,喜馬拉雅FM開始涉水付費訂閱,推出《好好說話》,依靠著《奇葩說》的影響力,《好好說話》在上線首日銷售額就突破了500萬。截至2016年底,喜馬拉雅FM付費營收占比高達50%,目前有超過2000位知識網紅和上萬節付費課程,覆蓋了商業、外語、親子、情感、讀書、脫口秀等諸多品類。
2017年,伴隨著用戶需求提升、市場下沉和產業鏈的脫產,知識付費形成“風口”。3月份,國內知名社區平臺豆瓣退出了“豆瓣時間”,邀請學界名家、青年新秀、行業大人推出付費專欄。首期專欄為北島主編的音頻節目——《醒來——北島和朋友們的詩歌課》,該節目由北島親自策劃編選,并邀請 16 位詩人、譯者朋友一起在豆瓣打造這堂特殊的“詩歌課”,該課程共有51 首中外經典現代詩, 102 堂大師級的詩歌課,上線5天銷售過百萬。
爆款因何誕生
雖然這些知識付費爆款產品以及平臺一直受到褒貶不一的評價和質疑,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它們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成功的。逐一分析這些目前成功的知識付費平臺和產品,它們之所以能夠受到眾多用戶的簇擁都是有原因的。
從產品本身來說,首先,由于規模效應對成本的稀釋,知識付費產品的價格都相對低廉。在以專業生產內容為主的平臺上,例如前文所提到的《醒來——北島和朋友們的詩歌課》,16位詩人的102節詩歌課程,售價僅為128元。而問答類的產品,價格則更為低廉,例如果殼的“分答”上,可以花1元錢“偷聽”答主的回答。
其次,以音頻為主的知識付費產品,為用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性。正如羅振宇所言:“音頻是非常好的載體,它可以用伴隨性的方式完成信息交付。”相比于文字或視頻,音頻媒介已經走了很多年的下坡路。但是其實音頻媒介的價值在于場景,無論是在通勤路上、在廚房中又或是睡覺前,音頻剛好填補了移動碎片場景的需求。2017年3月羅振宇宣布《羅輯思維》視頻節目停播,轉戰“得到”的音頻領域,也實踐了他對于音頻內容的看好。得到等知識付費平臺都并不是以音頻起家,但他們卻依靠音頻內容收獲了大量的付費用戶,這也為困境之中的蜻蜓FM、喜馬拉雅FM和荔枝FM等音頻內容平臺指明了新的出路。音頻內容平臺也都紛紛上線了知識付費產品,喜馬拉雅FM依靠著自身在音頻內容方面多年的積淀和用戶積累,已經成功晉級為中國最大的知識付費平臺。
最后,名人效應對產品的加持作用也不容小覷。“互聯網時代,要用人的方式形成自己的族群,只要有人愛你,你就會有成就。人將成為未來商業的渠道,比如我只看我信任的人讀的書,去我信任的人推薦的參觀,買我信任的人推薦的車子等等。”羅振宇如是說。縱觀各個爆款知識付費產品,業界名人、明星、網紅等等都是平臺的吸睛法寶。李笑來的得到專欄《通往財富自由之路》,憑借這他本人的巨大爭議和“一夜巨富”的光環,也收獲了高達17萬的訂閱人數,專欄的一年訂閱費用是199元,僅此專欄,一年的營業額就達到了3000多萬。《李翔商業內參》不僅憑借擁有12年媒體經驗的資深媒體人李翔的名氣鋪下了路線,馬云、雷軍、柳傳志等諸多大咖的背書更是讓《李翔商業內參》備受關注。
再比如蜻蜓FM與高曉松聯合出品的付費音頻節目《矮大緊指北》,僅僅上線一個月,就有超過10萬的訂閱用戶,而其中與高曉松淵源最深的北京用戶占到了總訂閱量的1/5。從每集節目后面幾百條跟帖看來,大部分用戶都是為了高曉松而訂閱此節目,正是這樣的名人效應將主播和用戶進行了深度綁定。例如,前段時間推出節目《文青手冊22:王菲》,因恰逢王菲與馬云合唱的電影《功守道》主題曲《風清揚》發布,關注度和話題性較高,于是他們就盡量促成這檔節目,取得很好的反響。
不僅是PGC專業內容依靠名人效應賺的盆滿缽滿,問答領域中的名人效應也不容忽視,王思聰在“微博問答”平臺上,憑借著給網友僅4個字的答復“熟能生巧”,坐收約8萬元,可謂“一字千金”,“微博問答”平臺也可在幾乎零投入的前提下拿到近2萬元的平臺服務費。
除去產品本身的各方面優勢之外,知識付費平臺的興起和爆款產品的誕生,都與外部條件的成熟息息相關。
一方面,知識付費的發展得益于相關技術的進步。智能手機的普及、移動通信技術的發展,為消費者增加了新的媒介,以《薛兆豐的北大經濟學課》為例,如果把課堂搬到現實環境中,需要三個國家體育場(鳥巢)才能容納所有訂閱用戶同時上課。不僅如此,智能手機和移動通信技術也增加了碎片化時間的消費場景。碎片化時間一直存在,但是曾經由于技術限制,知識付費產品幾乎不可能近入這一領域,但是伴隨著技術的發展,知識付費產品在用戶有限的時間中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目前的知識付費平臺,全都擁有手機App,手機早已取代電腦成為最主要的終端,有些平臺例如“得到”甚至都沒有開發用于電腦的使用端口。另外,作為一種付費產品,知識付費還受到另一個重要的技術的影響,那就是支付手段。近年來,以支付寶、微信支付等為代表的支付手段的大幅升級,也是知識付費能夠風起云涌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用戶的變化為知識付費提供了極其重要的要素——需求。“有需求,并且有為需求付費的意愿,這就是市場真正的起點。”正如羅振宇所言,消費者的需求,是真正成就知識付費風口的起點。曾經由于經濟狀況的限制,多數中國人只愿意為實物埋單,而信息和體驗類的消費一直難成氣候,但是這一狀況正在慢慢發生著變化。據英國經濟學人智庫所發布的《中國消費者2030年面貌前瞻》顯示:以收入水平來衡量,中國將在2030年成為中產階級國家。伴隨著中產階級崛起的正是我國大眾消費升級的需求,而知識經濟和體驗消費,正是這一波消費升級浪潮中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另外也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消費能力正在日漸增長的中青年群體,從小就接受者“活到老學到老”的終身教育觀念,這一觀念也讓他們愿意為學校之外的知識埋單。
盛名之下,是否暗流涌動?
羅永浩和Papi醬兩位知名網紅知識付費項目的接連折戟,給發展得熱火朝天的知識付費產業潑了盆冷水;《羅振宇的騙局》雖然是一篇舊文,但也時不時會出現在微信朋友圈中。知識付費這一商業模式從其誕生就伴隨著唱衰的聲音。有人說線上學習沒有效率,也有人說碎片化學習“損害智商”,更有親歷者現身說法,表示花了許多錢卻沒有讓他升職加薪等等。除了用戶的體驗問題之外,知識付費也確實面臨著更大的問題,線上版權嚴重缺乏保護,各大平臺的爆款產品,幾乎全都可以從閑魚、淘寶等平臺購買到盜版;平臺內容的同質化程度較高,且缺乏有效的篩選機制,相較于一般的內容變現,知識的效果更為長期,且用戶很難在付費之前對內容進行完整的了解,目前多數用戶只依靠“名人光環”對內容進行選擇,但隨著知識付費內容不斷增多,內容篩選問題將越發尖銳;《中國分享經濟發展報告2017》還指出了目前只是付費內容泛娛樂化的問題:“少數知識付費平臺發揮明星效應,通過滿足用戶的獵奇心理提升平臺活躍度,背離了知識分享的初衷,對眾多擁有知識盈余的專業人士產生了擠出效應,甚至出現高質量用戶逃離現象。”
縱然有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但這并不能證明知識付費本身的商業邏輯有誤,從我們梳理的問題中不難發現,最大的困擾來自于操作層面,是某些平臺急功近利、某些主播急于圈錢,是在風口上太過躁動的人帶來了巨大的問題。但是另一方面,知識付費也要適當降溫才能夠實現可持續的發展。用一時之力打造幾個爆款產品,并不能帶來長遠的發展,平臺必須建立從內容開發、主講人、宣傳到用戶體驗和用戶反饋等等一系列健全的體系,形成一個有機的生態系統,才能沉淀到更多核心用戶,實現平臺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