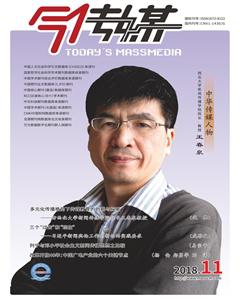淺析賈樟柯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的美學(xué)特征
李玉茜
摘要:《公共場(chǎng)所》是賈樟柯一部三十分鐘的純紀(jì)錄片,這部紀(jì)錄片呈現(xiàn)出了賈樟柯在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中更加清晰的美學(xué)特征。本文將從影像呈現(xiàn)、空間美學(xué)、背景聲寫實(shí)三個(gè)角度進(jìn)行研究。
關(guān)鍵詞:影像呈現(xiàn);空間美學(xué);背景聲寫實(shí)
中圖分類號(hào):J952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672 - 8122( 2018)
11 - 0110 - 03
《公共場(chǎng)所》是賈樟柯應(yīng)韓國(guó)全州電影節(jié)“三人三色”計(jì)劃所拍攝的記錄短片。當(dāng)時(shí)三人三色是全世界唯一一個(gè)數(shù)字電影節(jié),每年從全球選三個(gè)導(dǎo)演,每個(gè)導(dǎo)演拍一個(gè)30分鐘的作品,然后組成一個(gè)片子。賈樟柯參與那年的主題是“空間”,《公共場(chǎng)所》應(yīng)運(yùn)誕生,并獲得了2001年第13屆法國(guó)馬賽國(guó)際紀(jì)錄片電影節(jié)最佳影片。《公共場(chǎng)所》并沒(méi)有一個(gè)完整而具體的故事,只是單純記錄了各種空間里真實(shí)的生活狀態(tài),又通過(guò)這種狀態(tài)賦予了空間新的內(nèi)涵,產(chǎn)生了一種暖昧和美學(xué)的韻味。
一、影像呈現(xiàn)
《公共場(chǎng)所》把鏡頭對(duì)準(zhǔn)了郊區(qū)小火車站深夜的候車室、礦區(qū)黃昏時(shí)分的汽車站、一輛不知開往什么方向的公共汽車、一個(gè)廢棄公共汽車改造成的小餐館、以及長(zhǎng)途汽車站的候車室,它兼具臺(tái)球廳、舞廳等多種功能……。鏡頭就架在某個(gè)地方,展示空間里來(lái)來(lái)往往的人,火車站深夜等待的男子、汽車站邊耐心拉拉鏈的老人、公共汽車上牙疼的孩子或者候車室里伴著歌聲的交誼舞,都是一種或熟悉或陌生的生活狀態(tài)。
(一)“攫取生活碎片式”的美學(xué)呈現(xiàn)
賈樟柯在《公共場(chǎng)所》里呈現(xiàn)出了不同于傳統(tǒng)意義上的紀(jì)錄片美學(xué),他采用的是一種攫取生活碎片的方式。不局限于跟蹤某一個(gè)人或某一件事,而是截取生活碎片里的某一個(gè)場(chǎng)景下某一種狀態(tài)。《公共場(chǎng)所》沒(méi)有劇本就是單純的拍攝,最后再截取,整個(gè)片子本身甚至是凌亂的,散漫的,不同的段落記錄不同的內(nèi)容,其間的過(guò)渡有時(shí)候也比較生硬。但生活碎片的方式卻給了紀(jì)錄片更多的選擇余地和更多的內(nèi)涵多義性,展現(xiàn)了一種廣泛狀況下的生活百態(tài)。
生活碎片式的紀(jì)錄使得紀(jì)錄片別具一格,但難得的是把這些碎片能找到同一個(gè)主題表達(dá),達(dá)到“形散神不散”。《公共場(chǎng)所》做到了,并獲得了第13屆馬賽國(guó)際紀(jì)錄片電影節(jié)最佳影片。評(píng)審團(tuán)認(rèn)為此片在緩慢的近于靜止的狀態(tài)中讓人不知身處何時(shí)、何地,再次表現(xiàn)出賈樟柯神秘的時(shí)間處理。而大會(huì)評(píng)委、葡萄牙著名導(dǎo)演寇斯塔說(shuō)“賈樟柯的《公共場(chǎng)所》給紀(jì)錄片帶來(lái)了新的經(jīng)驗(yàn),他的獲獎(jiǎng)是美學(xué)的勝利”。顯然這些評(píng)價(jià)與生活碎片式的處理方式不可分割。這種方式帶來(lái)了一種神秘,沒(méi)有時(shí)間線,沒(méi)有特定的人和事只是依靠拼接組合產(chǎn)生多義化。
(二)“被攝者與拍攝者互動(dòng)式”的真實(shí)呈現(xiàn)
《公共場(chǎng)所》的攝影機(jī)大膽介入了人們的生活,并且保留了“被攝者與拍攝者互動(dòng)式”的真實(shí)呈現(xiàn)場(chǎng)景。拍攝者把攝影機(jī)光明正大的對(duì)準(zhǔn)了被攝者,而被攝者也光明正大的對(duì)鏡頭頻頻張望,這樣的張望對(duì)于傳統(tǒng)的紀(jì)錄片而言是絕對(duì)不允許的。賈樟柯反其道而行之,樂(lè)于表現(xiàn)人們看到鏡頭后的疑惑、驚喜甚至冷漠。攝影機(jī)可以闖入人們的生活,人們也自然可以對(duì)它產(chǎn)生不同的情感對(duì)視,甚至是厭惡,被攝者和拍攝者在平等的互動(dòng)。這種方式非但沒(méi)有削弱紀(jì)錄片的說(shuō)服力,反而增加了真實(shí)感。它是攝影機(jī)介入現(xiàn)實(shí)生活的真實(shí)寫照,與傳統(tǒng)紀(jì)錄片采用暗中拍攝或表演式的效果完全不同。
最重要的是,在拍攝者與被攝者的互動(dòng)進(jìn)展中,光明正大的拍攝者及攝影機(jī)會(huì)漸漸驅(qū)散人們的別扭,人們?cè)诿β抵幸矟u漸開始不會(huì)給予攝影機(jī)過(guò)多的關(guān)注,于是真實(shí)的生活就慢慢從鏡頭中一點(diǎn)點(diǎn)流露出來(lái)。由此,攝影機(jī)就開始了和真實(shí)生活的互動(dòng)與紀(jì)錄,紀(jì)錄片追求的真實(shí)性,一點(diǎn)點(diǎn)的從屏幕中紛至沓來(lái)。
筆者印象深刻的還有一點(diǎn),就是影片中寥寥幾句可聽清楚的話中,有一個(gè)小男孩對(duì)著鏡頭做鬼臉說(shuō)“拍電影呢,啦啦啦”,由此可以看出攝影機(jī)是一種對(duì)于真實(shí)生活毫無(wú)設(shè)計(jì)和安排的介入。
(三)“固定長(zhǎng)鏡頭式”的記錄呈現(xiàn)
賈樟柯在《公共場(chǎng)所》的導(dǎo)演自述中表示這是他第一次用DV拍攝,而且在拍攝前他就確立了一個(gè)原則——“不手持”。或許這也是影片中大量“固定長(zhǎng)鏡頭”記錄式影像呈現(xiàn)的原因。攝影機(jī)架在那里長(zhǎng)久不變,沒(méi)有特別大的景別變化也沒(méi)有特別大的運(yùn)動(dòng),是長(zhǎng)鏡頭是畫框,以一個(gè)單純的固定視角在記錄。而且導(dǎo)演不會(huì)給予任何的主觀評(píng)價(jià),甚至他也不知道鏡頭里下一刻會(huì)發(fā)生什么。像巴贊所說(shuō):“長(zhǎng)鏡頭是現(xiàn)實(shí)的漸近線”[1]。長(zhǎng)鏡頭運(yùn)用是真實(shí)的表現(xiàn),真實(shí)永遠(yuǎn)是記錄片的核心。
而固定長(zhǎng)鏡頭則還有一個(gè)優(yōu)勢(shì),它始終和被攝者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以一個(gè)持久客觀的角度呈現(xiàn)鏡頭前的所有,空間、時(shí)間以及生活狀態(tài)在固定長(zhǎng)鏡頭里都被真實(shí)的紀(jì)錄了下來(lái)。
當(dāng)然影片中也有一些鏡頭的移動(dòng)比如從廢棄汽車餐館到候車室運(yùn)用的移鏡頭,短暫的移出,然后黑幕,過(guò)渡到下一個(gè)場(chǎng)景片段之中。整個(gè)影片在攝取生活碎片式的拼接組合中多用移鏡頭,移出、黑幕、再進(jìn)入,毫無(wú)設(shè)計(jì)的呈現(xiàn)每一個(gè)真實(shí)的生活片段。
筆者認(rèn)為,這樣的實(shí)驗(yàn)性是賈樟柯在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上所呈現(xiàn)的個(gè)人獨(dú)特影像風(fēng)格,他始終在自己的影像美學(xué)上進(jìn)行著一層又一層的探討,并把自己的作品深深打上了“賈樟柯導(dǎo)演”的烙印。
二、空間美學(xué)
賈樟柯作品中也往往探討時(shí)間、空間的美學(xué),《公共場(chǎng)所》這個(gè)以“空間”為主題的紀(jì)錄片呈現(xiàn)出了他在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中更清晰的空間美學(xué)。
(一)異質(zhì)空間
“異質(zhì)空間”這個(gè)詞源自希臘文,其直譯為“差異地點(diǎn)”,也有譯為“異托邦”的。賈樟柯導(dǎo)演在他的作品中一直所打造的就是一個(gè)“城鎮(zhèn)變遷”中的異質(zhì)空間。這個(gè)異質(zhì)化的空間特征是漂泊的、不確定的,代表了社會(huì)底層一代人的尋找與失落。在紀(jì)錄片《公共場(chǎng)所》中,這個(gè)異質(zhì)空間被真實(shí)的紀(jì)錄與呈現(xiàn),而且這個(gè)異質(zhì)空間因攝取生活碎片式的拼接呈現(xiàn)變得更加獨(dú)特而立體。
(二)多義空間
賈樟柯在《公共場(chǎng)所》的導(dǎo)演自述中說(shuō):“空間氣氛本身是一個(gè)重要的方向,另一方面最重要的就是空間里面的聯(lián)系。在這些空間里面,我覺(jué)得很有意思的是,過(guò)去的空間和現(xiàn)在的空間往往是疊加的。比如說(shuō)一輛公共汽車,廢棄以后就改造成了一個(gè)餐館;一個(gè)汽車站的候車室,買票的前廳可以打臺(tái)球,一道布簾的后面又成為舞廳,它變成三個(gè)場(chǎng)所,同時(shí)承擔(dān)了三種功能,就像現(xiàn)代藝術(shù)里面同一個(gè)畫面的疊加,空間疊加之后我看到的是一個(gè)縱深復(fù)雜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2]。這段自述體現(xiàn)了賈樟柯多義化空間新美學(xué)的探討。
賈樟柯通過(guò)空間里的種種,表達(dá)了縱深復(fù)雜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尤其是結(jié)尾,在流行音樂(lè)《用心良苦》下展示著人們的現(xiàn)實(shí)生活,鏡頭還特寫了“認(rèn)真貫徹落實(shí)江總書記關(guān)于安全工作的指示”以及毛主席的掛牌等。這些鏡頭表示著國(guó)家在人們生活中所處于的位置。最后紀(jì)錄片在一曲《走進(jìn)新時(shí)代》中結(jié)束,人們一個(gè)個(gè)從門口涌出,誰(shuí)也不知道這些人將走向何方,但無(wú)論是國(guó)家的前進(jìn)還是政策的變遷,現(xiàn)實(shí)的生活都在時(shí)間與空間的變奏中慢慢改變。
筆者認(rèn)為,《公共場(chǎng)所》切實(shí)呈現(xiàn)了賈樟柯的空間美學(xué),這種美學(xué)在賈樟柯作品中一以貫之。作為“作者導(dǎo)演”,他一直在研究“城鎮(zhèn)變遷下的異質(zhì)空間”,在《公共場(chǎng)所》中,這個(gè)空間得到了最完整、立體的展現(xiàn)。
三、背景聲寫實(shí)
電影是視聽語(yǔ)言的藝術(shù),聲音占著極其重要的地位。美國(guó)著名導(dǎo)演弗朗西絲·科波拉指出:“聲音至少是電影的一半……”[3]。電影藝術(shù)對(duì)“客觀物質(zhì)現(xiàn)實(shí)”的還原不只是對(duì)視覺(jué)維度的還原,也涵括了聽覺(jué)維度的還原。賈樟柯的創(chuàng)作中,也尤其重視聲音維度。
《公共場(chǎng)所》里,始終充斥著各種環(huán)境聲音,風(fēng)聲、汽笛聲、音樂(lè)聲、臺(tái)球聲等。聲音,在多數(shù)情況下,體現(xiàn)出賈樟柯“音聲寫實(shí)”的追求。通過(guò)聲音對(duì)影片場(chǎng)景進(jìn)行時(shí)間和空間的雙重定位。在時(shí)間上表明時(shí)代,比如《公共場(chǎng)所》中《用心良苦》《走進(jìn)新時(shí)代》兩首歌曲的選擇。在空間上背景聲還能暗示場(chǎng)景的轉(zhuǎn)換,比如從候車室到舞廳時(shí)歌曲的變化。背景聲表現(xiàn)了當(dāng)下的社會(huì)實(shí)況,突出了“真實(shí)”的原則。另外,影片中幾處“鐘聲”,又給電影籠罩上了一層獨(dú)特的韻味。
賈樟柯對(duì)于“背景聲寫實(shí)”的重視,即使在《公共場(chǎng)所》這個(gè)30分鐘的短紀(jì)錄片中,可謂也表現(xiàn)的淋漓盡致。
綜上所述,《公共場(chǎng)所》較為淋漓盡致地表達(dá)了賈樟柯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的美學(xué)特征。他追求真實(shí)美學(xué),通過(guò)影像呈現(xiàn),始終關(guān)注城鎮(zhèn)變遷下邊緣人群所處的異質(zhì)空間,同時(shí)始終重視背景聲的運(yùn)用。作為一個(gè)作者導(dǎo)演,他走出了一條獨(dú)屬于自己的作者式創(chuàng)作道路。
參考文獻(xiàn):
[1] (法)安德烈·巴贊著.崔君衍譯.電影是什么?[M].北京: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2008.
[2]賈樟柯《公共場(chǎng)所》導(dǎo)演自述[EB/OL].https://www. douban. com/group/topir,/3414310/.
[3] (美)波德維爾·湯普森著.彭吉象譯.電影藝術(shù)——形式與風(fēng)格[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