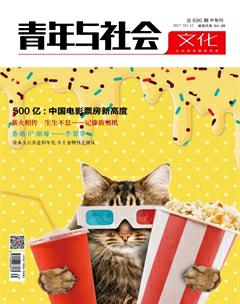好萊塢:全球電影機器
關于好萊塢的新定義:不是美國的電影工業,不是美國娛樂業和傳媒的整合系統,而是一個正在變成霸權的全球化模式。
法國《電影手冊》主編讓·米歇爾·傅東曾來上海參加關于“全球化語境中電影美學”的研討會,他在會議上的主題發言為好萊塢做出新的定義:“不是美國的電影工業,不是美國娛樂業和傳媒的整合系統,而是一個正在變成霸權的全球化模式。”
傅東在完成這個新定義的同時也說明了為什么好萊塢電影是需要警惕甚至抵抗的。因為好萊塢把整個地球視為一個想象中的一元化市場,所以好萊塢電影的根本目的就是讓地球上每個觀眾都接受同一個標準和框架,遵循同一個思想模式。這個來自法國電影學者的直觀預警是對“電影何為”的深化回答,也代表了寰宇對抗好萊塢的思想立場。畢竟電影的重點不止有票房,制作電影與觀看電影的模式不能被好萊塢席卷侵占,不能為了俯就商業利益而削減簡化人們浩瀚無窮的潛在意愿。
2016年,全球電影票房累計386億美元,好萊塢占比80%,幾成壟斷之勢,再一次顯現了好萊塢電影在全球化體系里的迅速擴張與傳播。歐洲完全淪陷,本土產業電影消失殆盡,這導致了各國的反好萊塢活動。
而在看得見的好萊塢電影背后,則是看不見的利益沖突和文化角力。法國《電影手冊》主編讓·米歇爾·傅東這樣定義好萊塢:“一個正在變成霸權的全球化模式。”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多個國家的文化界都在各個層面與好萊塢進行抗爭,既抵抗自由市場體系本身的壟斷性,同時保持文化多樣化與民族特色,拒絕被單一的思想模式同化。
何為電影 電影何為
何為電影,電影何為,關于這兩個問題,不同時代與地域都曾經給出過數不勝數的答案。然而在好萊塢電影工業成為全球最大生產商和供應商以后,答案的多義性被強行削減。
換句話說,電影屬性內的藝術性、民族性和多元化的國別歷史表達被強行削減。好萊塢電影制作假借電影工業流水線標準件的旗號,將一部部電影重新定義為“工具化的全球傳播新媒介”。這個定義包含兩層意思:其一,是指以電影為工具,頌揚美國生活方式及其主要工業產品,凡在美國影片傳播的地方,相伴而來的就是更多美國貨物的銷售;其二,是用電影來創造悅目的外貌、言行、時尚,以此潛在地引導輿論和趣味,不僅影響小范圍的個人生活選擇,而且觸角涉及更大范圍的社會生活,最終影響到其他民族的文明及文明進程。
所有這些包涵文化滲透和經濟利益攫取的行為,都巧妙隱匿在高超的市場營銷技巧里,既幫助好萊塢電影在世界多區域內都占據優勢的票房份額,也修筑起輸出美國主流文化與價值觀的快感渠道。
好萊塢電影在全球化體系里迅速擴張與傳播,造成了它與除了美國之外的其他所有國家的利益沖突和文化角力。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多個國家的文化界都在各個層面與好萊塢進行抗爭,既抵抗自由市場體系本身的壟斷性,同時保持文化多樣化與民族特色,并拒絕被單一的思想模式同化。 好萊塢電影的產業策略:從制造內容調整為培養觀看市場,進而統一預設觀眾的觀看模式和審美體驗,以期更加順暢地傾銷好萊塢模式電影。
自由貿易下的分水嶺
在歐洲電影研究者的分析中,好萊塢電影的全球擴張應該以世貿組織的經濟協定為分野期。《關貿總協定》力圖使電影和其他傳媒產業一并納入產業議題,所針對的就是歐洲各國長期沿用的、針對國家民族電影工業的保護性措施。雙方的爭論催生出關于自由市場的悖論:大力推銷好萊塢電影的美國一方,主張少讓國家行為進行干預,市場競爭就是自由的;處于劣勢一方的歐洲市場保護者則認為,好萊塢自身已經是一個強大的工業體系,它抬高產業門檻,制作昂貴產品卻又廉價銷售,實質上形成的壟斷最終造成市場競爭在本質上的不自由。
根據英國學者邁克·懷納的統計,《關貿總協定》之前,英、法、意等歐洲主要電影產出國共有220部電影進入了美國市場。隨著市場全球化體系的逐步推進,這個數字急遽下滑到83部。
之后,好萊塢電影實現了全球發行,歐洲電影中的80%卻只能在原產國發行,導致歐洲與美國各自輸出影片的總值比例為1:15。貌似自由的文化市場最終造成了歐洲電影制作哀鴻一片,也使更多的文化研究者發現:好萊塢電影的產業策略已經大幅調整,從表面上的制造精彩輸出內容,調整為培養觀看市場,進而統一預設觀眾的觀看模式和審美體驗,以期更加順暢地傾銷單一化的好萊塢模式電影。
以英國電影的市場遭遇為例。作為全球第四大的電影市場,英國長期處于好萊塢電影的覬覦之下,多家美國電影公司在英國投資建立電影院,短期內就讓英國觀眾的觀影次數實現了翻番倍增,然而絕大多數的觀影是沖著美國電影去的,好萊塢五大電影公司的百余部影片一共抽走了英國電影市場總收入的近80%。
法國的應對政策
好萊塢電影在歐洲電影市場上的橫掃之勢引起程度不一的反擊。
法國的電影商人與文化界就此達成前所未有的團結,口徑一致地宣揚“文化例外”,不惜冒著激怒美國盟友的危險,也要保護本國的電影工業。明確一致的觀念保證了法國電影在歐洲電影市場的最好表現——首先是確保本國電影的產出量,不被好萊塢傾軋到大幅下滑,然后是確保本國電影市場的利益分布相對合理,好萊塢電影占到50%左右,法國本土影片占到近四成,另外10%的占比用來支持其他國家影片,尤其關注同屬歐洲的國家,比如波蘭、土耳其等國,共同抵制好萊塢電影在歐洲電影市場上的傾銷。
每一年的戛納電影節都在重申法國電影的“文化例外”政策,通過培育完全不同于好萊塢的藝術影片導演,來艱難卻持續地對抗好萊塢商業片。波蘭導演基耶斯洛夫斯基,土耳其導演錫蘭都在這個名單上。2002年戛納電影節選用伍迪·艾倫的《好萊塢結局》做開幕影片,語帶雙關,繼續用輕盈的幽默口吻諷喻著好萊塢電影重工業道路的終結可能性。
越戰越勇的韓國電影
韓國電影對于好萊塢的感情是復雜而雙重的,由此,他們和歐洲的反好萊塢態度相似但路徑不同,抵制中還帶有顯著的先學習、后超越的勇氣和策略。endprint
在美國施壓韓國政府完全開放電影市場的博弈過程中,韓國電影人的反彈堪稱激烈,先后在1998年和2006年出現兩次集體抗議。前者的成果是功莫大焉的電影配額制,規定每家影院在一年內必須有146天放映本土電影。
由于配額制的積極作用,再加上其他電影產業促進戰略,激發了韓國電影人迎戰好萊塢的士氣,在某種程度上還喚醒了韓國國民在國際貿易戰面前的民族感情與文化身份認同。翌年上映的韓國本土制作《生死諜變》打破了好萊塢大片《泰坦尼克》的票房紀錄,不僅在韓國影史上獲得“電影復興火炬”的美譽,關鍵是扭轉了韓國觀眾首選好萊塢影片的觀影習慣,以至于驚動了美國的評論媒體,測算出當時韓國本土電影的市場占有率達到驚人的80%。由此也拉開了韓美之間圍繞電影市場進行的貿易談判攻防。
2006年,韓國政府宣布削減配額,影院每年必須放映本土電影的時間減為73天。一貫以滿懷血性愛沖動自譽的韓國電影人照例集合起來反抗,主演《老男孩》的崔岷植甚至把“反對好萊塢壟斷”的展板舉到了戛納電影節上。不過,這次韓國國內的輿論卻不像上次全情支持本國電影人那樣一邊倒了,反而很多媒體發嗆聲,提醒本國電影人不要停留于“長不大的孩子”,要為整個國家的工業結構轉型和農產品市場盡到責任……
出乎人們意料的是,就在第二次韓國電影人抗議活動以失敗收場后不久,暑期檔上映的《漢江怪物》再度刷新了韓國的票房紀錄,甚而打入了北美市場,在超過百家的影院里上映。
接下來的韓國電影就在“仿好萊塢”和“反好萊塢”的雙重策略中飛速發展起來。一方面是電影工業的現代化和尋求跨國合作的大制作影片連連刷新票房,同時獲得國際聲譽,如2013年《雪國列車》和2016年《小姐》;另一方面是取材韓國真實本土問題的中小成本影片密集引爆觀眾自發支持,2011年《熔爐》、2012年《斷箭》、2013年《辯護人》以及2016年《鬼鄉》。
這些影片扣緊“韓民族真實的現實與歷史”兩張底牌,用關乎每一個韓國人的經驗問題來牽動電影,又以當代本土電影來進行國民意識教育和集體情感認同。不單作為電影收獲了本土觀眾的熱情,而且真切推動了韓國社會的改變,實現了電影改善社會的終極夢想。韓國電影工業與國民觀眾們彼此構成良性的合力助推關系,在工業形式上接受成熟的好萊塢技術,而在內容趣好上卻完全轉向純粹的韓國歷史與現實。2014年《鳴梁海戰》在創造一連串影史紀錄的同時,獲得了一項針對好萊塢電影特別值得驕傲的榮譽:該片的觀影人次累計數量竟然反超《阿凡達》。
一百年來,好萊塢在向全球輸出一批又一批的商業文化產業的同時,也提高了北美一代又一代綜合素質整體較高的觀影群眾。國內劇情爛片不比好萊塢特效大片少,但別人國內有了一系列完整的電影工業體系、機構、組織、影評人群和審查機制,在如此基礎上輸出文化當然沒有任何不合時宜。可中國呢?中國電影的生產體系和觀影體系,都需要奮起直追的勇氣,2018年,國產電影的票房是否還能突破進口電影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