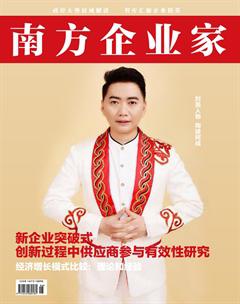探討“逆全球化”治理悖論的理論
雷瓊
摘 要:自2016年英國脫歐和特朗普上臺之后,全球化的基本框架受到沖擊,人們的思維也從剛開始對逆全球化只是一種政治力量的偶然性反應轉向對逆全球化問題的理性思考,中國海洋大學海洋發展研究院院長龐中英指出,逆全球化與全球化問題同樣都是復雜的科學現象,我們不僅要理性看待逆全球化,更要思考如何治理逆全球化。如今,面對如火如荼的中美貿易戰,對全球化與逆全球化問題的思考應不僅僅局限于現象層面,更重要的是剖析“逆全球化”現象背后的治理邏輯。
關鍵詞:逆全球化;治理;一帶一路;合作
近年來,資本主義國家在全球掀起“逆全球化”治理的浪潮,在新自由主義的主導下,肆意發展的金融資本造成實體經濟發展的“空心化”現象,為了控制資本的流向,吸引制造業資本回國,資本主義政府加強對金融資本的監管,采取“逆全球化”的治理戰略。然而,“逆全球化”治理消減了民主的公共利益價值,導致了民粹主義、精英階層的利益受損,進一步加劇了階級矛盾。
“逆全球化”本質上是一種悖論,這是因為“全球化”是受資本牟利和增值本性所驅動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從現代生產力崛起的那一刻起,全球化進程已不可遏制,“逆全球化”企圖改良全球治理機制,是逆歷史客觀規律發展的。中國的全球治理視角是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下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逆全球化”治理的緣由與初衷
新自由主義主導下金融資本的肆意發展
以私有制為核心的資本主義制度歷來對政府的管制保持不信任的態度,政府的角色被定位為國家安全的“守夜人”。20世紀30年代,全面放任的市場經濟模式使資本主義世界陷入了大規模的經濟危機,凱恩斯從《資本論》中獲得啟發,發表了《就業、利息和貨幣理論》,主張政府加強對經濟和社會的干預、提高公共服務供給以解決失業、衛生、人口流動等危機問題。
凱恩斯主義從一定程度上滿足了自由競爭資本向國家壟斷資本轉換的需要,使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獲得了合法性地位。生產過程只是為了賺錢而不可缺少的中間環節,只是為了賺錢而必須干的“倒霉事”。金融資本的本性比產業資本更加貪婪放蕩,它使賺錢避免了生產過程的“倒霉事”,為了攫取更多的利潤,渴望打破任何干預和限制,自由地擴張,激進的“新自由主義”迎合了金融資本的欲望,以哈耶克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將經濟滯脹歸罪于政府的過度干預,他們宣揚極端的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和市場化,認為市場是資源最優配置的無形之手,政府的干預會降低管理的效率,主張“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在國際金融資本的簇擁下,新自由主義迅速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20世紀70年代,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將新自由主義作為執政的理念推行經濟自由化、私有化,減少政府干預,降低福利支出。
資本主義國家實體經濟的“空心化”
過度放任的金融資本大量擠壓實體經濟,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逐漸呈現“空心化”。金融及其衍生品控制了股票市場、期權市場、基金市場以及房地產市場,制造業在金融業的擠壓下被迫大量外遷,削弱了國家財富的生產能力。
在新自由主義的主導下,市場被認為是調節就業的最佳途徑,政府對社會福利的支出降低,社會保障難以為繼,這種以損害弱勢群體的利益為代價換取經濟效率的做法使工人階級貧困化加劇,貧富兩極分化,階級矛盾升級。
越吹越大的金融泡沫和五花八門的金融衍生品加劇了投機詐騙的產生,破壞了正常的市場秩序。除了軍工、石油、農業之外,其他制造業都走向了衰落。對此,資本主義國家如美國政府提出“再工業化”戰略,如收購金融不良資產的TARP計劃、增加政府投資、救助失業者的ARRA法案、改革醫保制度的法案和金融監管制度改革法案等。然而,缺乏實體經濟支撐的經濟就像是站在棉花糖上一樣,無法抵御資本市場的狂風暴雨。
“逆全球化”治理的后果
加劇社會矛盾
由于全球化所帶來的經濟收益在資本主義社會各階層的分配不均,金融資本、大企業和高級技能專業人群是主要受益者,普通中產階級和社會下層勞動者根本沒有受益甚至被迫承受損失,使“逆全球化”得到了平民階層的擁護。然而,這種并非立足于社會公共利益而是滿足個人利益的心理訴求推動民主政治從民主轉向民粹。
新自由主義的極端私有化、自由化的核心理念使“民主”和“自由”從互補轉向對立,民主成為滿足個人私欲的利器,民主政治所具有的政治功能被消解為統治階級收買民心的籌碼,“逆全球化”表面上迎合了平民的欲望,實質上卻消減了民主的公共利益價值,推進了民粹主義,正如奧巴馬所說,“在那些推動我們的經濟走向成功的人當中,越來越少的人能從成功中獲益。”站在峰頂的富人變得越來越富,大多數家庭的利益并沒有得到保護。
削弱經濟發展后勁
發達國家中產階級之所以能夠維持現有的生活水平,或者說民眾之所以能夠享受高于全球平均的生活水平,依靠的是現行的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他們所極力維持的全球經濟不平等使他們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車,資本在流動的全球化中加強了發達國家資本對全球勞動者的剝削,尤其是國際金融資本在流動的過程中獲取了大量利益,因此“逆全球化”治理將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從全球化的利益體系中退出,其民眾也將失去從全球化中獲得的全球福利,從而陷入貧困的境地。
擾亂社會秩序
新自由主義主張的自由放任的經濟發展模式本身就是一個精英階層為主導的發展模式,它必定導致分配嚴重傾向精英階層。在經濟上,金融精英掌握著國家的政治,促使資本在更廣闊的全球市場追逐利潤,經濟和政治精英結合,控制著社會的各個方面。經過20多年的發展,資本已經占領了全球市場,推動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企業與企業、企業與社會、國內與國外之間高度融合,表現出極高的社會化程度。
社會化程度的提高需要有宏觀的主體在更大的范圍內配置資源,然而資本主義是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極高的社會化程度與生產資料的私有制之間矛盾愈演愈烈,演化為生產過剩、高失業率、貧富分化等社會問題。
“逆全球化”治理的悖論
從本質而言,“全球化”是受資本牟利和增值本性所驅動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從現代生產力崛起時起,全球化進程已經不可遏制。“逆全球化”治理是逆歷史客觀規律發展的做法。
首先,“全球化”所產生的問題并不在于全球化,而是生產力發展到資本過剩階段所暴露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矛盾。雖然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曾經通過制度的改良緩解了資本主義制度表面上的問題,但生產到過剩的階段,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還是頻繁地爆發了。雖然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第二章的革命措施給資本主義經濟學家帶來了改良啟發,正如加爾布雷斯所言。
其次,“逆全球化”治理不但不能奏效,反而會進一步擴大貧富差距。不但不能滿足平民階層的欲望,而且損害了精英階層的利益。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問題不是由全球化引發的,不可能通過逆全球化治理得到解決,唯一能夠克服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只能是改變資本主義制度本身。
全球治理的中國視角: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明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要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第十二部分提出:“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這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同志在博鰲亞洲論壇中再次深刻闡述了這一主題,指出:“面向未來,我們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對話協商、共擔責任;同舟共濟、合作共贏;兼容并蓄、和而不同;敬畏自然、珍愛地球。”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全球治理的中國視角,科學回答了“人類社會向何處去”的時代問題。
和平與發展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出發點
首先,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西文化發展的歷史命題。在西方古希臘文化中,城邦是人們共同生活的地方,理想的城邦是個共同體。亞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學》所提出的“Politike Koinonia”,即“市民社會”,就是指共同體或城邦國家。在他看來,人天生就是政治動物,公民必須在城邦中過共同的生活。
城邦的出現是古希臘從野蠻走向文明的標志,城邦與家庭和部落相對,是高于家庭和部落的共同體形式,人只有生活在城邦之中才能過上美好的生活。亞里士多德將城邦與家庭區分,其目的是將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區分。
其次,人類社會是一個復雜的矛盾統一體,既有紛繁復雜的利益沖突和矛盾糾葛,又有追求合作發展的共同之處。當今世界,全球化進程的推動和信息化時代的到來使全球形成了一個共同體,每個國家的發展都與世界的總體發展息息相關,只有世界和平與發展,各個國家的發展才能得到保障。任何霸權主義和戰爭行為只能給人類社會帶來災難,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各國人民在充分認識到自身地位和利益基礎上的科學選擇,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發展,實現共贏的必由之路。
最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是在和平和發展的前提下實現各國的現代化。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實現發展是其根本利益,中國愿意貢獻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倡導各國團結一致,堅持合作,維護和平,推動促進全世界各個國家的現代化發展,努力解決各國發展的不平衡、不合理問題,體現出大國的姿態和歷史責任。
“一帶一路”是通往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路徑
2015年,中國政府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提出中國將秉持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理念,全方位推進務實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十九大提出“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加強創新能力開放合作,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將“一帶一路”作為我國對外開放的重大舉措,深入推進各參與國的互利互助和區域合作,以共贏代替零和博弈,有效整合參與國的優勢,形成產能、資源、技術、資金和市場等方面的互補。
“一帶一路”有利于各參與國之間的互信交流、團結合作;有利于各國文明的溝通,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有利于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格局。
“一帶一路”是各國共同的事業,中國將以開放包容的姿態與參與國攜手共建利益共同體,支持各國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開展經濟文化合作,積極打造開放的合作平臺,與各參與國分享建設經驗,為世界和平與發展做出新的重大貢獻。
(作者單位:廣東財經大學人力資源處)
【參考文獻】
[1]呂世榮.馬克思經濟全球化思想的哲學闡釋邏輯[J].中國社會科學,2015(04).
[2]龐中英.“去全球化”是長期趨勢還是暫時現象——全球化悖論剖析[J].探索與爭鳴,2018(01). [3]叢日云,西方文明的困境——后物質主義如何應對全球化的挑戰[J].探索與爭鳴,2018(01).
[4]李先明,全球化背景下中華文化復興的基本向度與內在進路[J].南京社會科學,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