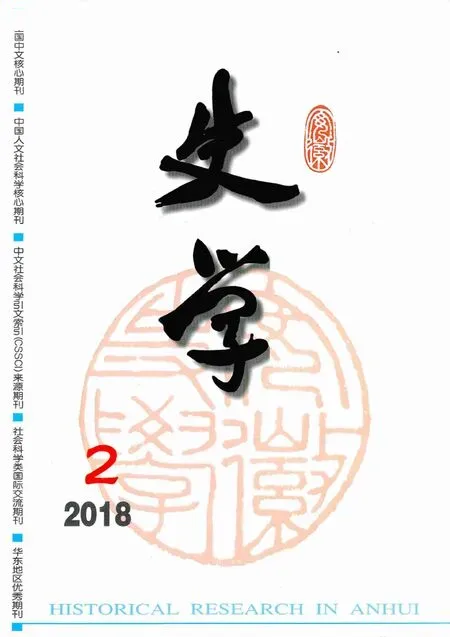現代日本歷史編纂學的幾種伴生觀念
趙軼峰
日本的歷史編纂學雖遠不及中國歷史編纂學源遠流長,但最晚在相當于中國唐代時期開始,歷史記載就作為一種專門的學問發展起來,逐漸形成了可觀的本土歷史編纂傳統,并時時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這一傳統與整個日本社會一樣,在19世紀后期急劇轉變。依照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的說法,日本“比亞洲其他國家早一代人”完成了取代傳統形式歷史研究的現代歷史學建構,并借助發達的大學體制和組織水平很高的圖書館、檔案館,大量依據“西方的研究標準和西方的研究方法”的歷史著作,以及西方歷史文獻的大量翻譯,達到了“在研究上能與西方并駕齊驅”的水平。①[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楊豫譯:《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00頁。全面評價巴勒克拉夫的觀點不是本文的目標,這里借用他的話表示,日本現代歷史學就基本性質而言是一種模仿西方歷史學的建構——亞洲各國的現代歷史學程度不同地具有這樣的色彩,而日本被普遍認為是其中的捷足先登者。模仿西方建構的日本現代歷史編纂學與模仿現代西方建構的后發展社會相類,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中,形似多于神似。所謂形似,主要指日本史學的所謂現代轉變,一般被認為以德國蘭克學派歷史研究者里斯(Ludwig Riess)到日本講授歷史學為標志,蘭克學派所體現的歷史學實證研究方法很快成為日本大學體系的主導方法,“實證主義”也從此成為日本職業歷史學研究的主流。所謂神似未及形似,則是指西方現代歷史學研究方法植根于歷史哲學中,歷史編纂學的具體工作方法以及歷史觀念,處于歷史哲學不斷的評析審視之下,故而西方歷史編纂學能夠不斷實現自我反省,持續出新,而日本的歷史哲學缺乏獨到之處,其歷史編纂學也不具備與西方同樣深刻的反省能力。②學術界關于日本歷史哲學的研究甚少,中國學者的相關研究,可參見卞崇道:《日本世界史學派的歷史哲學》,《日本研究》2006年第3期。在這種情況下,在思維深層對歷史編纂學產生最重要影響的其實是各種各樣的觀念,即通常所說的歷史觀。歷史觀與歷史哲學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重合,但真正的歷史哲學作為一種學術,必須通過嚴格的邏輯方式展開并接受邏輯拷問,具有理論徹底性;歷史觀則可能并不具有同樣的邏輯嚴格性,可能滲透、彌漫在其他多種方式呈現并且通常有更直接現實參與性的言論、著述甚至行為中,容納更多的價值介入,并且難以用邏輯方式加以檢驗。一種歷史哲學必定表達一種歷史觀;一種歷史觀卻未必表達一種歷史哲學。通過西方歷史哲學可以相當透徹地了解西方歷史編纂學;通過歷史哲學卻難以透徹了解日本的歷史編纂學。因此,要了解日本現代歷史編纂學的整體演變歷程,需要對與其伴生的歷史觀做出梳理。一旦嘗試這樣做,立即可以發現,現代日本的歷史觀極其復雜,超過亞洲所有其他國家,如果試圖在一篇文章中將各種歷史觀的歷史與邏輯關系聯通以構成一個統一的譜系,幾乎是不可能達成的。在這種情況下,只能分別梳理,然后對其間可能存在的關聯、共性、糾結做力所能及的分析。
一、亞洲主義
亞洲現代歷史學是在歐洲勢力東來和亞洲各國興起各種形式的圖強自救運動和思想學術變革的背景下逐漸展開的。這一宏觀歷史背景,在19世紀末以后一個多世紀亞洲史學的演變中,始終發生作用。其中,亞洲主義就是一個形成較早而至今活躍的思想潮流。要理解日本史學糾結演變的復雜性,需要看到亞洲主義的影響。
日本推行明治維新后,福澤諭吉提出“脫亞論”,主張與中國文化代表的古代社會傳統切割,擁抱西方文化,實行社會改革,躋身“開化”民族行列,這成為日本現代化變革的巨大思想推動因素。這一論斷竭力肯定西方文化、制度的優越性,主張脫亞入歐,但內里同時包含由日本重新凝聚亞洲各國,與西方抗衡的意識。隨著日本國勢強盛,而中國等周邊國家日形敝敗,由日本整合亞洲與西方抗衡的思想日趨顯明,到19世紀70年代,“征韓”“征臺”主張都在日本流行。甲午戰爭前后,亞洲主義成為日本社會一種重要思潮的時候,其主張差異紛繁,但皆籠罩在日本擴張傾向的總體社會氛圍之中。其中,有的以民權合理性與伸張為原點,主張亞洲各國團結“興亞”,在對抗歐洲殖民主義過程中實現各自平等的現代發展;有的以日本自身的國權、國勢伸張為原點,強調惟日本有資格主導亞洲之興起,日本代表東洋文明,主張日本侵略其他國家以整合亞洲,與歐洲列強爭鋒于世界。“中日提攜”“興亞”“與西方列強爭衡”,強調亞洲區域文化自我,是所有亞洲主義的共同要素。①參見[日]狹間直樹著、張雯譯:《日本早期的亞洲主義》,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戚其章:《日本大亞細亞主義探析》,《歷史研究》2004年第3期;盛邦和:《日本亞洲主義與右翼思潮源流——兼對戚其章先生的回應》,《歷史研究》2005年第3期。按:狹間直樹將“亞洲主義”與“大亞洲主義”相區分,把前者界定為“以對等關系為前提的路線”,后者則為“以日本優勢為前提的壓制路線”。狹間直樹偏重強調亞洲主義的“善意”和合理性,甚至在當下的現實意義,但這種區分也頗可商榷。參見《日本早期的亞洲主義》,第13—14頁。因為亞洲主義興起時代的亞洲國家中只有日本已經成為工業化國家,亞洲主義的所有表述形態背后其實都含著日本主導亞洲的邏輯。大致在中日甲午戰爭前后,日本極端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膨脹,為日本亞洲擴張戰略鋪墊的“戰略亞洲主義”占據壓倒性優勢。其中,樽井藤吉(又名森本藤吉)在《大東合邦論》中主張,面對歐洲列強對亞洲的滲透和侵略,日本應當與中國“合縱”并與朝鮮“合邦”,建成“大東”國,以實現以日本為盟主的三國一體化。②森本藤吉:《大東合邦論》,東京:森本藤吉,1893年,第132—142頁,參見王向遠:《從“合邦”“一體”到“大亞細亞主義”——近代日本侵華理論的一種形態》,《華僑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岡倉天心著有《東洋的理想》,主張亞洲是一個整體,而“日本是亞洲文明的博物館,而且遠在博物館之上”。③岡倉天心:《東洋の理想》,岡倉一雄編:《岡倉天心全集》上巻,東京:聖文閣,1938年,第1—5頁。小寺謙吉《大亞細亞主義論》設計了逐步實現大亞細亞主義的步驟,其中包括使中國拋棄西藏、外蒙古等“外藩部”,“滿洲、內蒙古按照這一基準都應該除外”,保全中國內地,使剩余的中國與日本“輻車相倚”,實際上成為日本的附屬國。④小 寺謙吉:《大亜細亜主義論》,東京:寶文館,1916年,第1111—1112頁,參見王向遠:《從“合邦”“一體”到“大亞細亞主義”——近代日本侵華理論的一種形態》,《華僑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孫中山、李大釗也曾談論亞洲主義,孫中山初以為亞洲主義可以成為亞洲各國實現各自獨立、平等發展的思想旗幟,但不久就看到日本政府的亞洲主義實質上是“大日本主義”,轉而開始對日本亞洲主義進行批評;李大釗談論“大亞細亞主義”時,也對日本亞洲主義的侵略內涵做了多方面批評。⑤參 見孫攀河:《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與近代日本的亞洲主義》,上海中山學社:《近代中國》第24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150頁。
亞洲主義既有多種表述形態和推演變化,其作用也頗復雜,但就其最突出方面而言,主要是充當了日本對亞洲鄰國推行殖民侵略的思想基礎,也影響了日本學術界的歷史觀。它的形成與歐洲殖民主義對亞洲各國造成的威脅密切相關,這在后來的評述者眼中常常被視為亞洲主義合理性的一個因素,但是從一開始,亞洲主義就與日本先已存在的亞洲擴張論糾纏不清,隨后二者緊密結合。其中明顯的黃色人種與白色人種種族競爭意味,背后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種族競爭論。這種種族競爭的邏輯既不否定弱肉強食,也不尊重民族獨立和主權,只是用亞洲人內部的弱肉強食取代不同膚色人種之間的弱肉強食,把亞洲弱國的獨立和主權視為亞洲強國的囊中之物。亞洲各國在西方殖民主義威脅下爭取獨立發展的訴求被日本的殖民主義和亞洲帝國訴求所吞噬。亞洲主義中所包含的區域整合主張,也因為與民族獨立、人民主權的現代社會理念相剝離,成為展開日本國權主義的工具,從一開始就喪失了其在語義層面所包含的積極意義。最近一段時期,亞洲主義仍然是一種活躍的話語,⑥狹 間直樹的《日本早期的亞洲主義》雖然以“早期”即1900年之前的亞洲主義為對象,并且承認亞洲主義與日本侵略的關聯,但總體觀之,還是在強調亞洲主義的合理性。雖然已經脫離了二戰前日本侵略別國的語境,卻依然常在“亞洲”與“西方”兩分或對立的預設語境中徜徉,⑦日本學者溝口雄三指出:“在20世紀的日本,人們大體是站在三個觀察點上來考察世界的,即東方、西方以及日本這三點。這三個觀察點的基礎,實際上是將世界分為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二元論世界觀。即是說,表面上雖有三個觀察點,但日本并不是一個獨立的文明世界,它只不過被設置為東方和西方兩個文明世界的接觸點而已。”見溝口雄三:《日本現階段的中國研究及21世紀的課題》,國際儒學聯合會:《國際儒學研究》第2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頁。在討論亞洲的共性和自我定位時,始終未能透徹闡明,為什么在全球化日益發展,全球聯系已經高度發達的當下時代,還要如此強調區域主義的必要性、合理性,其與舊亞洲主義心曲的婉轉應和也時時可聞。
亞洲主義的倡導者大多并非職業歷史學家,但這種觀念卻深度觸及對于日本、亞洲乃至世界歷史的基本認識,它作為一種比歷史觀覆蓋更廣大的社會思潮,為19世紀末以來日本社會各種歷史思考涂抹了一種基色:通過地域性思維解構世界主義的思維;通過亞洲文化乃至人種共性來深描亞洲各國歷史關聯性和共同命運語境;通過論證日本特殊性來彰顯日本解放、領導乃至統治亞洲各國的合理性。前兩種色素至今明顯,后一種色素在二戰結束后總體上趨于隱晦、淺淡,但并沒有消失,包括其中的極端表述方式也沒有徹底消失。例如在亞洲主義作為深層推動觀念的日本侵略戰爭期間,曾經盛行的“亞洲解放論”,即日本通過武力擴張將亞洲從西方人那里解放出來的論調,在二戰結束后受到壓抑,但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復活。①參見嚴紹璗:《戰后60年日本人的中國觀》,《粵海風》2006年第5期。受到亞洲主義思潮影響的人未必皆有侵略他國的心理,也可能推動一些促進各國團結、往來和知識傳播的事情,如善鄰譯書館就曾在這方面做過一些努力。②參 見[日]狹間直樹:《日本的亞細亞主義與善鄰譯書館》,《近代中國與世界——第二屆近代中國與世界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第2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頁。不過,亞洲主義不是一個剛剛擬出的空洞概念,是一種在一個多世紀的歷史演變中切實產生思想和現實后果的觀念。所以學者在回顧這一方面的歷史時,不應將之與其流行時代的歷史實況以及當時的普遍社會思潮,或者當時中日關系的基本格局走向相剖離。
二、東洋史觀
日本現代史學在世界史學界頗有地位,而其根基肯定不在于世界史,日本史作為其本國史,研究自然比任何其他國家史學家所做的更為細膩具體,但國際學術界對之關注有限。現代日本史學界引起國際學術界關注最多且獲得評價最高的,其實在“東洋史”。③葛 兆光將之稱為“取代‘中國史’的‘東洋史’”,參見葛兆光:《宅茲中國》,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238頁。日本傳統史學中并無“東洋史”名目,這是隨著日本現代史學興起的一種研究對象和方式理念,其興起過程也與日本思想觀念的現代演變以及現代歷史推演相為表里。東洋史學的研究對象,是以中國為主而排除日本的亞洲,其研究理念的技術特征是實證。
日本實證主義歷史學的早期奠基者之一重野安繹是最早的亞洲主義團體“興亞會”的成員,而日本東洋史學的主要創立者白鳥庫吉是重野安繹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擔任史學科教師時的學生之一。重野安繹與其他第一代推動日本歷史研究理念與歐洲史學理念接軌的日本學者一樣,既受中國傳統考證學的影響,也受德國蘭克學派的影響,主張歷史學家“如實直書”,又因主持日本政府的國史纂修,始終保持與日本政府現實立場的一致性。④[日]永原慶二著,王新生等譯:《20世紀日本的歷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8—30頁。“如實直書”的純客觀立場本來與國家主義政治立場不可能一致,但日本現代歷史學在發生期卻實際上開啟了一條學術實證追求客觀真實與政治參與追求國家最大利益兩種不同理念曲折融合的新傳統。也就是說,作為日本現代歷史學早期主要代表的實證主義歷史學在一開始就是實證主義與國家主義的融合體,而亞洲主義則提供了其展開的思想氛圍。
“東洋史”作為一個學科是在1894年由那珂通世提出來的,他主張歷史學應該分為“西洋史”“東洋史”“國史”三科制。⑤三宅米吉述:《文學博士那珂通世君傳》,故那珂博士功績紀念會編:《那珂通世遺書》,東京:大日本図書株式會社,1915年,第32頁。這種學科體制安排,與亞洲主義在觀念深層一致,皆凸顯東洋與西洋的兩元對立。1896年那珂通世成為帝國大學(次年改為東京帝國大學)教授之后,這種三科制就成了日本歷史學教育和研究的主流架構。20世紀初東洋史學完全成型之后,形成東京帝國大學和京都帝國大學兩個學派。前者以白鳥庫吉為代表,因其特重文獻資料的搜集和整理,常被稱為“文獻學派”;后者以內藤湖南為代表,提出了一些宏觀的歷史論證,常被稱為“實證學派”。在尋求共性的視野下,二者都推崇歷史學實證主義性質的研究,就其公開主張而言,都可被歸為廣義的實證主義史學。
白鳥庫吉原以研究西洋史為主,在日本亞洲擴張的時代氛圍中,匯入“創設東洋史研究”的潮流中,改為研究朝鮮史。中日甲午戰爭之后,他開始研究“滿洲”史地,不久創立“亞細亞學會”,再與桂太郎主持的“東洋協會”合并,并負責該會的學術調查部。日俄戰爭之后,日本設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白鳥庫吉向該社建議設立“歷史調查室”,即通常所說的“滿鮮歷史地理調查部”,專門對“滿洲”、朝鮮地區進行詳細調查。其后,又逐步展開了對“蒙古問題”的調查和對中國西北、中亞、南亞史的研究,推動成立東洋史學會、建立東洋文庫。他將語言、地理、民族等學科知識綜合運用于歷史研究,一生著述極豐,是公認日本東洋史學的主要創始人和東京文獻學派的創始人。
“東洋”在中國清代文獻中常特指日本,近代以來又常被用來與“西洋”相對,大致就是所謂“東方”,其中自然包括日本。歐洲先已存在Oriental Studies,直譯當為“東方學”。這種學問最初研究的主要是今天所說的中近東地區,后來延伸到亞洲東部。日本將歐洲的“東方學”譯為“東洋學”,但日本的“東洋學”以亞洲東部為主,又因為“東洋史”盛行時代的日本吞并了朝鮮并將之作為本國史,故其中也不包含朝鮮,從而與歐洲的東方學有很大不同。三科制確定之后“東洋史”的研究對象,是去除日本之后的以中國為主的亞洲,正是當時日本謀劃逐步擴張的地域。“西洋”是“文明開化”的代表,“東洋”則具有非現代、野蠻、落后,甚至權屬未明地域對象的含義。日本地域和歷史上屬于東洋,發展程度和現實自我定位意義上則已“入歐”,于是成了東洋和西洋之間的“連接點”,也成了發達者“開拓”不發達者的前哨。白鳥庫吉在與中國相關研究中提出的“滿洲中立論”“南北二元對抗論”“中國文明停滯論”“堯舜禹抹殺論”,都體現著“東洋”意象,也在時時暗示對“東洋”拓展的合理性。臺灣學者石之瑜就曾評論說:“如果沒有白鳥成功建構一套擺脫漢學界中國觀的東洋史觀在前,中國就在之后不能成為‘落后待解放’的對象,那么日本在所謂‘大東亞共榮圈’中的領導地位便缺乏論述基礎。”①石之瑜:《回到亞洲?——日本認識中國崛起的思想基礎》,《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年第4期。他認為白鳥庫吉“通過中國,將日本的源起置于與歐美平等的地位,再把中國排除在落后的文化保守主義中,最后經由日本的綜合,成就日本的超越。”②石之瑜、李圭之、曾倚萃:《日本近代中國學:知識可否解放身份》,《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1期。白鳥庫吉的學生津田左右吉所寫《白鳥博士小傳》記載,白鳥庫吉“早就認為不能不由日本人來從事東洋研究,日本的東洋學者必須成為中國東洋學的指導者。這種抱負,到此時已逐漸接近實現的境地了。特別是中國學者的塞外研究,幾乎完全依賴于我國學者的研究……由于這種研究,日本人才能夠指導中國的學術界,用學術才能使中國人承認我國的權威。”③津田左右吉:《白鳥博士小傳》,《津田左右吉全集》第24卷,東京:巖波書店,1965年,第156—157、109、160、141 頁。津田左右吉評價白鳥庫吉,“通過學術,為彰顯國威也做出了不少的貢獻”;④津田左右吉:《白鳥博士小傳》,《津田左右吉全集》第24卷,東京:巖波書店,1965年,第156—157、109、160、141 頁。他始終謹奉“大振皇基”的圣旨,“在學術上,貢獻出發展國運的最大努力”。⑤津田左右吉:《白鳥博士小傳》,《津田左右吉全集》第24卷,東京:巖波書店,1965年,第156—157、109、160、141 頁。白鳥庫吉還是個御用學者,他在大正初年擔任東宮“御進講”,為后來的昭和天皇講授歷史,被稱贊“精勵恪勤”。⑥津田左右吉:《白鳥博士小傳》,《津田左右吉全集》第24卷,東京:巖波書店,1965年,第156—157、109、160、141 頁。
白鳥庫吉的國家主義立場在他自己的言論中可以看得更清楚。他曾為明治以后日本對朝鮮、中國的侵略歡欣鼓舞:“實行統一的政治,舉國上下團結一致,其余力遠及國外,這從日本歷史就可預見。明治后很快就掀起了征韓論,出征臺灣,探討了樺太、千島的交換問題,這絕非偶然。明治中期,清國無視朝鮮的獨立。為此,發生了日清戰爭,日本大捷使得中國割讓遼東半島、臺灣,獲得了我國有史以來未曾有過的勝利,南滿洲收入囊中。”⑦白鳥庫吉:《東洋史上より観たる日本》,《白鳥庫吉全集》第9卷,東京:巖波書店,1971年,第259頁。沿著同樣思路,日俄戰爭期間,白鳥庫吉自覺強化了對“滿洲”的研究:“此次戰爭是大事件,待看到最終結果尚需時日,我日本國民在此期間必須從所有方面對當今的時局進行研究,如同我們東洋史學專業的人,從這一角度對此問題進行解釋,也算是對國家盡一點義務吧,絕不是徒勞。”①白鳥庫吉:《満州の過去及び將來》,《白鳥庫吉全集》第8卷,東京:巖波書店,1969年,第17頁。1912年,日本吞并朝鮮之后兩年,白鳥庫吉馬上提醒要為日本的“命運”而立即強化對“滿洲”的研究:“滿洲、朝鮮等是與我國有密切關系的地方,我國國民中沒有不知道的。但我國國民也都知道對于有如此密切關系的滿韓來說,我們了解甚少。朝鮮與我國歷史從始至終都有密切聯系,不斷給我國的利害消長帶來巨大影響,但是我國國民卻對朝鮮幾乎不了解,直到近來,在朝設置統監府,實行合并以來才多少了解了一些。然而,合并以后,還沒有從根本上對朝鮮進行調查,得到精確的知識。更何況朝鮮北邊的滿洲,我國對此更是知識淺薄,或者可以說一無所知。然而,滿洲之地對于關乎日本命運的重要性絕不亞于朝鮮。因為朝鮮意味著我國是否能夠維持勢力,而滿洲則決定我國的策劃是否得當。更進一步也可以說,能否維持東洋的和平關鍵在于滿洲問題,對于具有如此重大關系的滿洲,我國人的知識卻如此淺薄,這十分令我擔憂。”②白 鳥庫吉:《満州問題と支那の將來》,《白鳥庫吉全集》第10卷,第146頁。關于白鳥庫吉本人研究“滿洲”而向日本政界做出的現實戰略性建議,參見趙薇:《白鳥庫吉的中國觀研究》,東北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14年,第76—82頁。日俄戰爭之后,白鳥庫吉認為日本在“東洋”的地位提高,需要開始“為完成戰后之經營,樹立國家百年之大計”思考。并指出:“關于東洋事物——學術上的調查、研究之事尚有不足,對亞洲學界計劃實施之事業雖然頗多,但以往研究拘于最近戰爭及爆發之原因。今后我國盡力經營之任務在于滿洲地方的研究,此最為迫切、緊要。此研究在任何方面來說,在于探究歷史由來,追根溯源,了解事物真相。世間至今沒有看到對滿洲進行研究的歷史資料,不但在我國,即使在中國和歐洲也未曾聽說滿洲歷史這一說法。這不僅是學界的一大憾事,對我國對此經營上來說也是一大缺憾。可以說,滿洲史的研究,真正意義上滿洲歷史的編纂是眼下最為迫切之任務。滿洲地方史,事關國家永久之圖謀,通過這些不可疏略的重要史料,可探視自古以來在此地若干興亡民族勢力消長之線索,以此來考察歷史。”“如果能夠做到以史為鑒,掌握滿洲歷史是重大的任務。我國民應該詳細探究其由來,洞察其形勢,這不只在滿洲經營上,而對于在東洋之國、亞洲文明上具有指導天職的我國的全面政策上來說,乃是必須的事業。滿洲史的研究并不僅僅是學者的職責,亦是擔當國家經營責任施政者的職責、國民的義務。”③[ 日]白鳥庫吉著,武向平、田剛編譯:《滿鐵對中國東北歷史地理的“調查”——白鳥庫吉〈滿洲歷史編纂之急務〉》,《東北史地》2011年第2期。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日本學界已經注意到白鳥庫吉的史學研究與政治的關系。日本學者旗田巍曾撰文指出:“日本的亞洲研究是與日本對亞洲的軍事發展相對應并發展起來的。大致而言,自明治初年直至戰敗,日本的亞洲侵略是在朝鮮→滿蒙→中國→東南亞這一方向前進的,而亞洲研究大體上也是沿著這條線成長的。”④旗田巍:《日本における東洋史學の伝統》,野沢豊編集解説:《歴史科學大系 第14巻 アジアの変革(下)》,東京:校倉書房,1980年,第 41頁。也就是說,東洋史是以日本侵略對象為研究對象的。
內藤湖南與白鳥庫吉大致同時。京都大學是日本政府于1897年成立的,從一開始就有深厚的政府背景。1907年,內藤湖南出任京都大學第一講座講師,兩年后升任教授,內藤湖南多次來華,陸續出版了多部有關中國歷史的研究著作,在日本被稱為“內藤史學”,奠定了日本東洋學中“京都學派”的基礎。學術界曾普遍認為內藤湖南的研究體現日本東洋史學的實證精神和研究水平,但深入考察他的研究成果,卻可以看到實證研究的客觀性被其為日本大陸政策服務的高度自覺性所遮掩。他在1914年發表《支那論》,1924年又寫了《新支那論》,認為當時的中國事實上已經漸漸喪失了對境內五大民族的統轄力,相對于中國的國力而言,領土過于龐大,不可能真實現“五族共和”,解體是必然的。他說:“要說蒙古、西藏,還有土耳其種族,他們本來是在清朝的時候服從支那的,隨著自己的勢力增強,而生起獨立之心,是理所當然的事。不管是蒙古人還是西藏人,他們服從支那,本來服從的是滿洲的天子,只有滿洲的天子統一了他們,他們才服從之,所以壓根兒就沒有服從漢人所建立的國家的意思。在滿洲朝廷倒臺的同時,所擁有的各異種族的領土隨之解體,是當然之事。蒙古人要鬧獨立,西藏人要依附英國,這都是可能的。或者像內蒙古那樣的靠近支那本國的部族,或者一直在北京等地生活的人,從感情上說他們一下子難以分離,但隨著支那政府日益具有民主的傾向,也就越來越失去對異種族的統轄力。今日所謂五族共和,事實上已經沒有什么意義。袁世凱等出于一時的策略,而討好蒙古王和西藏的喇嘛,也許能扯上個人的關系,但解體乃是大勢所趨。”①②內藤湖南:《支那論》,《內藤湖南全集》第5巻,東京:筑摩書房,1972年,第339—340、509頁。并請參見王向遠:《近代日本“東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華圖謀——以內藤湖南的〈支那論〉〈新支那論〉為中心》,《華僑大學學報》2006年第4期。因此,中國應該放棄“滿洲”等地,也沒有必要維持國防。這種言論正當日本吞并中國東北前夕,實際上為后來的歷史推演做了鋪墊。內藤湖南在《新支那論》中還提出,中國雖曾是“東洋文化”的中心,但在近世以后逐漸失去中心地位,東洋文化中心已經漂移到日本,日本為振興東洋文化精神,就必然要如以往歷史上周邊民族入主中原一樣進入中國,而中國人將接受那種現實:“現在的日本已經成為超越支那的先進國家,盡管對于日本的隆盛,支那人投以猜忌的眼光,但倘若通過某種機緣,使日本與支那形成一個政治上統一的國家的話,文化中心移入日本,那時即使日本人在支那的政治上社會上很活躍,支那人也不會把這視為特別不可思議的現象。”②這自然會鼓勵當時的日本軍政界侵入中國的意圖。當日本在中國東北建立“滿洲國”的時候,內藤湖南評論說:“這個新國家不是抱著軍國主義的希望而誕生的,而是要在這片肥沃的大地上建設一個世界民族共同的樂園。”③內藤湖南:《滿洲國建設に就て》,《內藤湖南全集》第5巻,第170頁。參見[加]傅佛果著,陶德民、何英鶯譯:《內藤湖南——政治與漢學(1866—1934年)》,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93頁。
一些現代學者偏重強調內藤湖南對中華文化心懷崇敬,但這種崇敬是相對于古代中國的,對晚清時代的中國,內藤湖南則認為已經無可救藥,必須由日本收拾局面。同樣的心態,也體現在他對臺灣的態度上。他多方嘆賞臺灣歷史古跡,卻明確主張日本吞并臺灣,主張日本占領者在臺灣推行使臺灣人與日本人同化的政策,同時保持臺灣人低于日本人社會地位的格局,不可“一視同仁”,要把大批日本人遷移到臺灣。④參見黃俊杰:《十九世紀末年日本人的臺灣論述——以上野專一、福澤諭吉與內藤湖南為例》,《開放時代》2004年第3期。
日本學者水野明指出:“戰前有很多的日本學者發表了很多似是而非的中國論,加速了侵略戰爭。”他特別指出,發表此類言論的歷史學家中包括內藤湖南,內藤湖南的“中國政治無能論”“中國非國論”“文化中心移動說”等主張,“無疑的是給日本侵略主義、軍國主義提出了根據。因之,我們不能不說,內藤的‘東洋文化中心移動說’乃是把日本之對中國的經濟侵略、軍事侵略正當化了而已。也就是‘大東亞戰爭史觀’的張本人。”⑤[ 日]水野明:《日本的“中國非國論”的檢證》,《東南文化》1997年第1期。溝口雄三也認為20世紀初日本的中國研究形成了3個特點:其一是尊崇中國古典文化,將之視為日本文化的淵源并抱有親近感;其二是中日文化同根觀,體現在把日本江戶時代以前漢學家的著作也視為廣義的漢文化;其三是對近現代中國完全不感興趣或者將之作為蔑視的對象。“因而,這些中國研究者——我在此稱其為古典派——中的大部分人面對日中戰爭時,從同根文化的觀點出發支持滿洲立國和日本軍隊占領大陸;又從日本消化了‘近代’即西方文明的自負出發蔑視中國;另一方面,又從發揚東洋精神這一國粹立場出發,尊重中國的古典文化。”⑥[日]溝口雄三:《日本現階段的中國研究及21世紀的課題》,國際儒學聯合會編:《國際儒學研究》第2輯,第122—134頁。近年來,中國學者對內藤湖南歷史研究與其日本擴張主義觀念之間關系的研究已經很多,有的學者對內藤湖南宋代近世說的實證基礎提出諸多質疑,認為其表面看去屬于事實考證性的研究并不嚴謹,受其現實意圖的影響是出現這種情況的重要原因。①參見黃艷:《“貴族政治”與“君主獨裁”——內藤湖南“宋代近世說”中的史實問題》,《古代文明》2014年第4期;《內藤湖南“宋代近世說”研究》,東北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16年。
雖然學術界已經發表了許多批評性的研究,但白鳥庫吉和內藤湖南在日本史學界的權威地位至今穩固。如大阪大學學者近年在中國的講學中依然說:“東京大學初期的東洋史研究者包括白鳥庫吉、池內宏、加藤繁都重視實證和有客觀性的研究。”“京都帝國大學比東京晚一點新設東洋史學的時候,內藤湖南成為了中心,他主要研究文化,在把握中國史全面的方面是優秀的。”②[ 日]中村圭爾:《日本東洋史研究》,《陰山學刊》2007年第4期。加拿大約克大學教授傅佛果(Joshua A.Fogel)指出:“《支那論》實際上可以說是在20世紀的中國史研究領域中提出了最重要問題群的著作。今天的歐美學術界所屢屢提出的許多觀點,其實與湖南在該書中有關中國社會文化方面的諸多新見解都是相通的。不過,這些觀點往往是在他們不知道有《支那論》這一著作存在的情況下提出來的。”③[ 加]傅佛果著,陶德民、何英鶯譯:《內藤湖南——政治與漢學(1866—1934年)》,第193頁。傅佛果看到內藤湖南提出了其影響深遠的“唐宋變革”說,而且其關于中國現實的種種主張正是以歷史觀為基礎的,但是他在自己的敘述中,還是對內藤湖南的歷史見解給予了高度評價,并認為其關于中國歷史的許多論說至今是西方歷史學界的共識。另外,留心晚近史學動態的學者也不難看到,內藤湖南的許多言論,與“新清史”中某些學者刻意強調的清代中國非整體性觀點存在諸多相通之處。可見,東洋史學的影響至今不可忽視。④參 見趙軼峰等:《關于“新清史”的對話》,陳啟能主編:《國際史學研究論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121頁。
三、皇國史觀
“皇國史觀”是日本特有的國家主義歷史觀。它把日本古代文獻《古事記》中的神話與歷史混合,將天皇視為整個日本歷史演變的核心線索,將所謂“萬世一系”的天皇當作為日本不可動搖的國體和歷史評價的基點,主張絕對忠誠于天皇的“大義名分論”,強調日本國粹,進而把明治維新以后的天皇制和對外侵略行為合理化。這種國家主義歷史觀淵源流長,可以上溯到日本南北朝時期南朝北畠親房編寫的《神皇正統記》,該書論述了從古代到后村上天皇時期的歷史,意圖說明南朝的正統性。江戶時代,水戶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圀召集學者編寫《大日本史》,繼承《神皇正統記》的觀點,形成了前期水戶學,為近代日本皇國史觀鋪墊了基礎。明治時期尊王,在官學中占據主導地位的皇國史觀進一步整合,神化“萬世一系”的天皇、大和民族、日本文化,將國家權威和日本以天皇為中心的所謂國體絕對化,強調依托國家權威強行改革,“萬法歸于天皇之凌威”,統合國民思想,對外則憑借日本特殊精神,“解放”亞洲,建立“八纮一宇”的世界性殖民帝國。
日本東洋史學的奠基人物白鳥庫吉很早就通過論證“國體”表達了皇國史觀與日本歷史學之間的密切關聯。⑤參 見趙薇:《白鳥庫吉的中國觀研究》,第99—105頁。昭和時期,皇國史觀作為官方意識形態與天皇制國家體制表里呼應,依托國家暴力,推動國民參與戰爭。該時期皇國史觀代表人物平泉澄曾在《國史學精髓》等著作中詳細闡釋皇國史觀。⑥平泉澄:《國史學の骨髄》,東京:至文堂,1932年。亞洲主義者大川周明也是皇國史觀鼓吹者之一,他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道》一書中特別強調天皇與國民關系中包含家族的父親、部族的族長、國家的君主的兼有身份。他說:“日本與外國的最大不同點就是天皇與國民的關系。日本天皇是家族的父親,部族的族長,并隨著共同體的發展而成為國家的君主。從國初以來,國祖的子孫就一直君臨國家。”⑦大 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の道》,東京:行地社出版部,1926年,第85—86頁。1937年以后,皇國史觀通過日本文部省制定的《國體本義》等全面滲透到國民教育體系之中。⑧日本國體本義編纂審議會編纂:《日本國體本義》,東京:平凡社,1932 年。二戰結束后,天皇不再擁有現實政治運行權,并在1946年發表《人間宣言》,正式宣布天皇為人而非神,但天皇在戰后未被追究戰爭責任,仍保持著國家元首的崇高地位,這使得戰后日本對于明治以來歷史的認識始終難以徹底擺脫回護天皇的心態。①關于裕仁天皇的戰爭責任,井上清指出:“開戰的最高責任在于天皇,這是明明白白的事實。因為1930年以來,天皇親自選擇了依附于最好戰派集團的道路,而且肯定、激勵、鼓舞了國民所不愿意進行的戰爭……結束戰爭的功績不在于天皇,這也是清楚的事實。因為天皇在接受《波茨坦公告》時僅僅是以保住自己的地位作為唯一條件的,也僅僅是為了這一點才投降的,因而對國民來說是沒有任何‘功績’之可言的……就天皇同國民的關系這一點看,天皇有開戰之罪,而無結束戰爭之功。”井上清:《天皇制》,商務印書館 1975年版,第198—199頁。皇國史觀雖然已經失去完整的現實制度基礎,但仍有部分制度基礎和深厚的文化基礎。平泉澄在戰后被從大學解職,并受到馬克思主義史學為主“戰后歷史學”的批判。但是隨著冷戰局面形成,美國占領當局開始壓制日本左翼民主力量,解除對日本戰犯的清洗,皇國史觀重新抬頭,平泉澄的著作也再度流行。②平泉澄的著作在中國近年有黃宵龍等譯《物語日本史》(3卷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
四、戰后歷史學與現代化史觀
二戰結束后的最初約10年間,日本史學界以批判為基調對戰爭歷史進行反省,其中馬克思主義史學保持了較大影響力。史學界大致將這一時期的日本歷史學主流稱為“戰后歷史學”。溝口雄三對二戰以后日本中國學基本傾向的歸納反映了這種情況。他認為,戰后日本中國學有4種傾向:其一,否定亞細亞停滯論,否定對中國的蔑視;其二,批判日本的天皇制帝國主義;其三,對侵略中國一事加以自我批判并否定大東亞共榮圈構想,采取支持亞洲民族解放或獨立的立場;其四,批判日本“脫亞入歐”的近代化路線,重視亞洲的團結。③[日]溝口雄三:《日本人為何研究中國》,《新史學》1卷2期,1990年6月號。雖然這種局面在冷戰開始以后逐漸轉變,但堅持對日本戰爭歷史進行批判的研究到冷戰結束之際,還能發出有力的聲音。并且,這種反省的基調比較充分地體現在戰后一個時期的歷史研究和教科書編寫中。
井上清是戰后日本史學界對戰爭歷史反省比較深刻的學者。他在1975年出版了《天皇的戰爭責任》,以豐富資料論證天皇負有戰爭責任。該書后來多次重印,形成很大的社會影響。④井上清:《天皇の戦爭責任》,東京:現代評論社,1975年。1994年,井上清、廣島正又編輯了《日本軍隊在中國做了什么》文集,對甲午戰爭中的“旅順大屠殺”“上海八·一三事變中的暴行”“南京大屠殺”“在河北與山東的‘三光政策’”“毒氣戰”“石井細菌部隊”“從軍慰安婦”等等問題,逐一討究,追問日本的戰爭責任。⑤井上清、廣島正編述:《日本軍は中國で何をしたのか》,熊本:熊本出版文化會館,1994年。另一位著名現代思想史家竹內好也認為,日本的近代化始終不過是對西洋的表面模仿,內在的封建性要素保存下來,并未變革。相比較而言,倒是中國的革命將封建要素徹底顛覆,推進了一種深具亞洲特點的近代化。⑥溝口雄三評論說,“文革”結束以后,大量中國大陸留學生到日本,口口聲聲要學習日本的近代化,使得批判日本道路的日本研究者失去了方向,“竹內好親中國大陸的中國觀是被中國大陸的青年們否定掉的。”溝口雄三:《日本人為何研究中國》,《新史學》1卷2期,1990年6月號。
隨著冷戰格局形成,美國亞太政策向扶植日本、遏制中國轉向,日本政界和學術界重新肯定日本近代以來亞洲擴張政策的言論逐漸高漲。反對戰后歷史學的聲音在20世紀60年代以后聲調日高,一個重要節點是1960年在箱根舉行的“近代日本研究會議”。⑦Sebastian Conrad,“Japanese Historical Writing”,in Axel Schneider and Daniel Woolf eds.,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Vol.5),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643—644.這是一次有美國福特財團資助并由美國學者主導的會議,美國學者霍爾(John Whitney Hall)做了題為《日本近代化——概念構成的諸問題》主旨報告,標志著現代化論全面引入日本。①中文中的“現代化”和“近代化”皆出自英文詞匯modernization,其內涵亦無根本不同,本文除引用原文時遵依原來寫法外,一律用“現代化”表示。這樣處理的好處是,在討論“后現代主義”時可以無需解釋地進入兩個概念的相關語境。其后,美國駐日本大使兼歷史學家賴肖爾(Edwin O.Reischauer)發表了關于日本歷史的近代化論主張。賴肖爾曾與哈佛大學著名學者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合作,提出亞洲近代史中的“刺激—反應”論。他認為:“1,日本的封建制度與歐洲的封建制度相類似,這是日本近代化的前提;2,日本通過接受歐洲機器文明和科學知識才實現近代化,近百年日本的變化都是由技術上的變化引起的;3,日本近代化是歐洲以外最成功的近代化,是亞洲各國效法的榜樣。”②沈 仁安、宋成有:《日本史學新流派析》,《歷史研究》1983年第1期。這一論說在日本史學界迅速展開,不斷得到擴展性論述,并深入滲透到許多歷史學家的具體研究中,逐漸成為冷戰開始以后日本歷史觀的一個重要基點。這種歷史觀預設了“現代化”為基點的普遍價值尺度,并把歐洲各國實現“現代化”的歷史經驗視為普遍且合理的道路,其中包含對于殖民主義合理化的敘述。在這樣的視角下,日本近代以來歷史的基調,就是一個東方國家如何擺脫傳統束縛而迅速進入現代國家行列的歷程,日本也就成了亞洲乃至所有非西方國家的榜樣。在這種語境中,反省戰爭歷史也就被襯托成次要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事情了。
溝口雄三是對日本侵略歷史能夠加以反省的學者,即使這樣一位學者,也會基于現代化史觀來為日本侵略歷史做出一些通向合理性的解釋。他強調“記憶”差異對中日兩國人民歷史認識不同的作用,指出:“在日本,國民的戰爭體驗主要偏重于所受美軍空襲的體驗方面,大體上看,這是與明治以后的脫亞入歐路線基本暗合的。就是說,在此歷史認識的理路上,日本是與歐美對抗、與歐美爭戰,最后敗于歐美特別是美國,而非敗給了亞洲。從這個思考理路來講,把‘廣島’定位為向歐美發出新挑戰的出發點是順理成章的。它同時也成為從戰敗中站起來之不屈精神及國民困苦與勇于奮斗的象征。而誘導這些思考的就是關于近現代的歷史認識。”③[日]溝口雄三:《創造日中間知識的共同空間》,《讀書》2001年第5期。廣島悲劇的確是美國投放原子彈直接造成的,但溝口雄三過于輕便地忽略了導致廣島悲劇的日本因素,繞開了日本“與歐美對抗”主要是以極其野蠻的方式發動對亞洲鄰國的侵略——這對于他國民眾說來根本不具有任何合理性,把戰爭記憶梳理到日本不屈抗爭的方向上來。而他的最后一句話更為重要,即這種思考的基礎是關于近現代的歷史認識。溝口雄三認為中國人對“不肯謝罪的日本人”的抗議情緒或嫌憎情緒中可能融合進了中國人傳統的對島國“小日本”的記憶,而日本的反華、排華情緒里則可能交織著“近代的優越”意識和對抗中國“大國”意識的情結。④[日]溝口雄三:《創造日中間知識的共同空間》,《讀書》2001年第5期。這種“近代的優越”意識,是指日本率先成為“近代”國家的優越感。他說:“在有關近代歷史的討論中,無論把日本的近代化過程視為帝國主義之近代,還是視為文明開化之近代,日本的近代是較亞洲各國在經濟、軍事、制度上處于優越地位的近代,在這一點上認識是共同的。如果把此一觀點稱為‘入歐的近代’,初看起來似乎在歷史意識的層面上與‘抵抗的近代’不同,但實際上就共有一個西洋‘近代’的軸心這一點而言是相同的,至少在日本人的歷史價值觀中,‘入歐’是被視為優越的。”⑤[日]溝口雄三:《創造日中間知識的共同空間》,《讀書》2001年第5期。溝口雄三在用半推測的方式把“近代的優越感”融合到日本民眾歷史意識之中后,立即指出這造成要求日本“謝罪”在日本思維中的不合邏輯性:“日本人就本國的侵略行為向中國人謝罪,并對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始于中日甲午戰爭這一事實進行反省時,即使未必是有意的,但仍是以‘資本主義化的成功’這一優越性為潛在的前提,而其謝罪本身亦是寓于‘謝罪之傲慢’這一認識中的。而就同一問題的另一面而言,中國人如果視日本的近代化為成功而給予肯定性評價,在邏輯上便完全可能容忍日本的侵略,從而使自己陷入兩難之境。”“如果戰爭記憶里滲透了這樣的歷史意識,我們日本人對于戰爭要謝什么罪,謝罪到什么范圍?是僅就殘酷暴行謝罪,對出兵侵略中國本身謝罪,還是對明治以來的近代化全過程謝罪?可是,一個國家的歷史全過程就這樣成了對其他國家的罪孽,這難道是可能成立的事嗎?”“為什么日本的侵略戰爭行為與日本近代化的過程被視為不可分割的整體呢?這里有著東亞近代觀的復雜交錯關系。就是說,在這里存在著以近代化的遲早、先后為衡量其民族的歷史與文化之優劣標準的歷史,而且,基于這種歷史意識上的記憶仍以現在時態存在著。”①[日]溝口雄三:《創造日中間知識的共同空間》,《讀書》2001年第5期。溝口這里從評論者角度推論日本民眾心理的說法,其實也是他自己要表達的看法,所以,他接下來就將中國人對日本的“謝罪”要求歸結為中國人的一種自相矛盾的“焦慮”:“不管中國人是否意識到,通過控訴日本人的殘酷暴行,中國人是在對從自尊心上無法接受的日本人近代優越意識之傲慢進行焦慮的抗議。而且,當中國人站在西洋標準的近代史觀上,身處不得不承認日本近代的優越性這一兩難之境時,則更加焦慮。所抗議的對象輪廓的不清晰,使得抗議之矢不知何時如同‘歸去來器’般又刺向自身,于是這時其焦慮便越發嚴重。”②[日]溝口雄三:《創造日中間知識的共同空間》,《讀書》2001年第5期。在溝口雄三的論說中,他沒有表述對“西洋標準的近代史觀”的任何批評,在沒有提出任何理由的語境中假定中國人和日本人一致地懷有這種西洋標準的近代史觀,進而判定,因為都懷有這種近代史觀,所以日本人如果謝罪就否認了日本的近代化努力,而中國人要求日本人謝罪就是在否定自己的歷史觀。這樣,我們就看到了一個現代化史觀如何成為把戰爭時期歷史是非攪成渾水的經典例證。
溝口雄三似乎對現代化史觀的局限有所了解,否則他就不會在另一篇文章中,表示樂于把自己歸為“市民史學”中人。他所說的“市民史學”是指二戰以后涌現的新一代研究者不滿意于前代人的方法論,并受法國年鑒學派或美國東方學論爭的啟發,開始關注“不被國家概念局限的社會史研究,或是以語言、宗教或地域性為基礎的民族的研究,一部分人則跳出西歐——亞洲的對抗關系,站在系統論(例如朝貢體系)的觀點進行研究。”他們也關心亞洲或日本的未來,但關注點不是民族、國家或體制如何,而是市民自由或社會公正等問題,并能透過歷史來批判性地認識現代,超越利己的利益夢想,也淡化了因侵略中國的贖罪意識或者批判日本近代經歷的意識。“可以說,他們每個人都是自由的。這一點,是與歐美的中國研究者站在共通的基礎上。也就是說,他們所懷抱的,不是背負民族、國家命運的理念,他們只是站在人類普遍的立場,以一個個人,自由的思考世界。這使得他們的研究得以與歐美的研究者具有共同的課題或目的。就自由的個人這個意義來看,這可說是市民派中國研究的誕生。”③[日]溝口雄三:《創造日中間知識的共同空間》,《讀書》2001年第5期。這似乎可以被視為一種普世情懷、自由主義、后現代主義三種要素綜合的學術意識。陳義雖高,溝口雄三的論說卻表明,他并沒有真正進入那種境界。
五、自由主義歷史觀與歷史教科書
二戰后,在反省戰爭的歷史觀探索展開的同時,為侵略戰爭辯護的歷史觀也逐步展開。早在東京審判過程中,日本辯護團副團長清瀨一郎就在法庭陳述中提出過“國家無罪”的說法。④參見姜克實:《日本人歷史認識問題的癥結點》,《抗日戰爭研究》2007年第1期。隨著冷戰深化以及日本經濟高速發展期來臨,為侵略戰爭開脫的各種說法蔓延開來。1951年7月,日本文部省發表《改定學習指導要領》,將歷史教科書中敘述日本侵略歷史的方式加以模糊化,以后又幾次重新擬定類似指導要領。此后,日本教科書中“侵略”一詞多改為“進出”。1952至1964年間,東京大學教授家永三郎編寫的幾種日本歷史教科書在文部省審查中屢屢遭受挫折,或被判定“不合格”,或被要求做大幅度修改,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家永三郎的教科書中盡量保持對侵略歷史的反省立場。家永三郎公開出版了《教科書審定》(日本評論社,1965年)一書,敘述原委,并在1964年向東京地方法院提出針對文部省的法律訴訟。①[日]家永三郎著,石曉軍等譯:《家永三郎自傳》,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157頁。該訴訟過程復雜,多次審理中,有時家永勝訴,有時文部省勝訴,有時家永部分勝訴。到1997年8月,日本最高法院裁定家永教科書中關于南京大屠殺、七三一細菌部隊、日本軍隊強征慰安婦等問題的記述合適,家永獲得賠償,但最高法院并不認可家永三郎對文部省審查教材為違反憲法行為的指控。
20世紀60年代,作家林房雄提出“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強調日本在戰爭時期奉行的是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日本從事的是解放亞洲殖民地的戰爭和自衛戰爭。②林房雄于1963—1965年間在《中央公論》雜志連載《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后結集為《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和《續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由番町書房于1964、1965年相繼出版,其后多次再版、重印,參見王向遠:《戰后日本為侵略戰爭全面翻案的第一本書——林房雄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安徽理工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1984—1987年,田中正明出版了《“南京大屠殺”之虛構》和《南京事件之概況:否定大屠殺的十五項理由》,公開否認南京大屠殺。③田中正明:《“南京虐殺”の虛構:松井大將の日記をめぐって》,東京:日本教文社,1984年;《南京事件の総括:虐殺否定十五の論拠》,東京:謙光社,1987年。并請參見魏楚雄:《歷史與歷史學家:海外南京大屠殺研究的爭議綜述》,《歷史研究》2009年第5期。1985年,中曾根康弘發表題為《新的日本主體性——戰后政治總決算,邁向“國際國家”日本》講演,聲稱:“戰前的日本,有所謂皇國史觀。然而,自從戰敗以后,太平洋戰爭史觀,亦即為人稱之為東京審判的戰爭史觀出現了。什么都是日本壞的一種動輒自我虐待式的思潮充斥于日本。如今還殘留著……我早就說過,我反對這種想法。”④中曽根康弘:《新しい日本の主體性——戦後政治を総決算し,「國際國家」日本へ》,《月刊自由民主》,1985年9月,第25—37頁。并請參見文國彥等:《戰后日本的右翼運動(1945—1990年)》,時事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頁。此時,日本政界人物頻繁參拜靖國神社,政府高官一再發表否認日本侵略歷史的言論。1993年,部分自民黨議員組織成立“歷史研究委員會”,推動通過歷史教科書修正來貫徹新的歷史觀。
1994年以后,東京大學教授藤岡信勝在《社會科教育》上連續發表文章,批評近現代教育培養的日本人缺乏對本國歷史的自豪感,認為這是戰后使日本人始終懷有罪惡感的結果,主張把日俄戰爭開始以后的對外戰爭描寫為日本的自衛戰爭,倡導從自由的立場上大膽修正歷史,以達到多樣化目的的歷史觀。1995年7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50周年之際,藤岡信勝為首的“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正式成立。⑤參 見步平:《關于日本的自由主義史觀》,《抗日戰爭研究》1998年第4期。藤岡信勝從4個方面解釋了自由主義史觀:第一,“健康的民族主義”,即與民族排外主義和自戰前以來完全否定民族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相對的民族主義;第二,“現實主義”,即以日本國家和國民的生存和繁榮為最高目的;第三,從所有的意識形態中脫離而變得“自由”,即“自由主義史觀”是一種最自由的立場,對每個人的多樣化見解保持寬容的精神,通過討論和對話使真實更為明確是其探究方法的基本;第四,“官僚主義批判”,即區分普通軍事和軍國主義,將昭和時期的軍國主義作為極端的官僚主義而進行批判。⑥藤 岡信勝:《自由主義史観とは何か——教科書が教えない歴史の見方》,東京:PHP文庫,1997年,第179—180頁。自由主義史觀表面上置身于“東京審判史觀”“共產國際史觀”“謝罪外交史觀”與“大東亞戰爭肯定史觀”之間,實際上則猛烈抨擊前者而對后者從未批評。1996年8月,由該委員會資助的19位學者就歷史問題進行講演,講稿匯編為《大東亞戰爭的總結》,由日本輾轉出版社出版,其核心就是否定“大東亞戰爭”的侵略性質,認為日本發動戰爭是為了擺脫美國、英國、中國、荷蘭等國的經濟封鎖(即“ABCD包圍圈”),是為了“自存自衛”的無奈舉措,提出“侵略未定義論”,要求消除“東京審判史觀”。1997年,西尾干二擔任會長的“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在東京成立,四年后編寫了《新歷史教科書》,通過文部省檢定后由扶桑社出版。⑦西尾幹二等:《新しい歴史教科書》(市販本),東京:扶桑社,2001年。該書竭力否定戰爭歷史,引起亞洲鄰國的強烈抗議。
誠如日本歷史學家山根幸夫所指出的那樣:“實際上,日本有許多人并不承認那場日中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是侵略戰爭,他們把承認日本的侵略戰爭當作‘東京審判的史觀’而加以拒絕。換言之,他們認為那場戰爭對于日本來說絕不單純是侵略戰爭,而是為了把從屬于歐美殖民地主義的亞洲各民族解放出來的戰爭。”“具有這樣歷史觀的日本人非常之多……”。①[日]山根幸夫:《戰后五十年與日本》,《外國問題研究》1994年第3、4期。
結 語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認為,對日本史學研究在亞洲的“領先地位”應該從日本的特殊性中來理解:“一個世紀以來的日本史學,即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史學,整個說來,所走的道路與其他亞洲國家完全不同。只要回憶一下日本近代史的突出特征,如成功地抵制了殖民主義的壓力,有能力在平等的條件下處理與歐洲列強和美國的關系,即使在失敗的情況下也能保留自己的民族特色,以及日本后來作為世界領先的工業國家之一的出現——就會認識到日本歷史學家的思想遺產同大多數亞洲國家的歷史學家的思想遺產是完全不同的。”②[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楊豫譯:《當代史學主要趨勢》,第 198、199—200,200,201,202 頁。在巴勒克拉夫看來,日本較早走上現代化道路是其歷史學“領先”于亞洲其他國家的主要條件,并稱:“與此同時,他們自己的歷史經歷不同于亞洲其他國家,這也意味著他們的興趣以及他們首先關心的問題很不相同。日本從未淪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因此,日本歷史學家不必首先關注殖民主義問題,而對這個問題的關注卻恰恰是亞洲其他國家當前歷史著作中最突出的一個特征。”③[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楊豫譯:《當代史學主要趨勢》,第 198、199—200,200,201,202 頁。“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史學界內民族主義的沖動是異常強大的,但是戰爭與失敗,原子彈的大屠殺和外國軍隊的占領等使日本受到損傷,已經使民族主義的歷史學名譽掃地,從此一蹶不振。”④[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楊豫譯:《當代史學主要趨勢》,第 198、199—200,200,201,202 頁。“亞洲歷史著作中大量存在的民族主義基調和意識形態色彩在日本歷史著作中卻是沒有的。”⑤[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楊豫譯:《當代史學主要趨勢》,第 198、199—200,200,201,202 頁。巴勒克拉夫的這本書在中國“文革”之后不久出版,對近乎自我封閉的中國史學界造成了不小的沖擊,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構成了當時中國史學界了解世界歷史學狀態的窗口。這種沖擊力和啟發性也多少遮掩了這本書自身的局限,如前述看法就有一定的片面性。一般地判定截止當時日本的歷史學達到很高的水準,可以找到許多依據,但巴勒克拉夫把接近于西方歷史學的程度作為“先進”與否的理由是明顯西方中心主義的、自以為是的武斷說法;日本歷史學并非如巴勒克拉夫所說的那樣沒有民族主義色彩及無需關注殖民主義問題,反之,日本史學受民族主義的影響既深且更極端化。溝口雄三就承認日本存在民族主義,他說:“當前在日本成為一個潮流的反華、排華情緒,或者對中國的優越感,以及與此互為表里的日本民族主義之由來,正可以通過古森的話語來向讀者揭示:這是日本歷史中一個不能忽視的語境。”⑥參見[日]溝口雄三:《創造日中間知識的共同空間》,《讀書》2001年第5期。伊格爾斯和王晴佳也曾指出,無論在西方還是非西方,“當19世紀歷史的學術研究首先在德國作為一個職業性的學科誕生并很快在西方普及,同時也在明治時期(1868—1912年)的日本誕生時,歷史研究自以為忠于科學的客觀性,而實際上是利用它的研究技術去支撐民族的神話……而日本歷史學家利用蘭克的考證方法去批判儒家史學,轉而又極力支持日本的帝國傳統,以推動日本的民族主義。”⑦[ 美]格奧爾格·伊格爾斯、王晴佳:《全球史學史——從18世紀至當代》,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頁。印裔美國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也曾指出:“日本人的民族身份認同是靠大亞細亞主義以及日本在保護其他亞洲國家免遭西方資本主義的腐蝕中獲得其特殊地位這一觀念來支撐的。對于日本民族主義來說,追求西方式的‘文明’國家與保持一種西方之外的自主性之間的張力的消解有賴于東洋史的建構……從東洋史建構中所產生出來的大亞細亞主義為日本帝國主義吶喊助威。”⑧[美]杜贊奇著、王憲明譯:《從民族國家中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導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3頁。更明白地說,近代日本民族主義是體現在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這些更極端的意識形態中,同時又用諸如亞洲主義、文明論、現代化論之類詭辯性言說包裝的。
現代日本歷史學與亞洲其他國家的歷史學一樣,也是在西方殖民主義東來大背景下以對本民族和國家的重新體認作為核心關照的。差別是,日本在受到西方殖民主義威脅之后,迅速調適,避免了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命運。但在殖民主義與現代性相互裹挾的全球性潮流中,日本沒有滿足于保持本民族的獨立地位以及現代化發展,而是以比西方殖民主義更激烈的方式迅速擴張,成為殖民者。巴勒克拉夫稱“日本的歷史學家不必首先關注殖民主義問題”,這是一句顢頇不清的話。日本歷史學家不必關心自己被殖民地化的問題,但它非常關心如何把他者殖民地化的問題。換言之,日本擺脫了殖民地的自我意識,營建起了殖民者的自我意識——這同樣是殖民主義問題。西方殖民者在很多情況下,是把未形成發達文化和國家組織的“原住民”區域變成自己的殖民地,日本作為殖民主義列強中的后來者,卻是試圖把歷史文化悠久的比鄰國家變成自己的殖民地,因而遭遇的反抗更激烈,日本的殖民主義擴張也就更殘忍,也需要更大的欺騙性。在這種背景下,日本的現代歷史學始終存在呼應日本自我重塑的潮流,試圖將日本從東方文化成員改塑為西方文化成員,從殖民主義征服的目標改塑成殖民者,從落后國家改塑成先進國家,從東亞小國改塑成東亞解放者和霸主,從中國文化的學習者改塑成中國的指導者和中華文明的唯一繼承者。前面梳理的日本歷史觀諸潮流,正是在這一層面相互激蕩,其中最具有持續性并在多數時間范圍占據主導地位的幾種歷史學觀念,都是日本自我重塑的積極參與要素。在這一視角下,亞洲主義、東洋史學、皇國史觀、自由主義史觀、現代化歷史觀之間,有一條或隱或顯的貫通線,使晚近日本的歷史學觀念與明治以來的歷史觀藕斷絲連。實證主義歷史學在這種推演中,并沒有真正構成超越現實意圖的力量,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實現現實意圖的工具。從這一視角看,日本現代歷史學中的實證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技術實證主義,其歪曲的歷史事實不勝枚舉。現代化論歷史觀則把日本和同樣具有殖民主義歷史的西方收攬到一起,把追求現代性作為開解侵略擴張歷史的說辭,同時為亞洲歷史學設立了西方中心主義的一種別樣標尺。
前述梳理,沒有充分考察晚近日本歷史學嘗試超越民族國家歷史敘述的研究,以及運用后現代主義、全球史話語展開的超國家思考,這有待稍后的研究。但這里仍要指出,這些努力,總體上仍然沒有徹底擺脫對日本民族國家自我重塑的心態氛圍。日本現代歷史學受歷史哲學的影響淡漠,而受各種歷史觀的影響頗深。各個史學流派,包括推崇客觀性的實證主義史學,都長期處于現實意識強烈的學術氛圍之中。這種強烈的現實意識,使得現代日本歷史編纂學基本從屬于日本現代社會思潮,而其關注的核心,其實是通過歷史學來實現對日本民族和國家的自我重塑,而自我重塑又必然地與對他者的重塑緊密糾纏。這里有許多問題有待澄清。今人對現代日本史學無需一味贊嘆其高深,更不應籠統地把東洋史學之類研究視為模板或者與國際學術接軌的捷徑。對于現代日本史學,當與對待其他學術傳統,包括西方和中國自身的學術傳統一樣,保持批評性審視的自覺。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史學與社會——當代亞洲四國史學演變比較研究”(13JJD770006)的階段性研究成果。研究和寫作過程中得東北師范大學孫志鵬幫助查核日文文獻,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