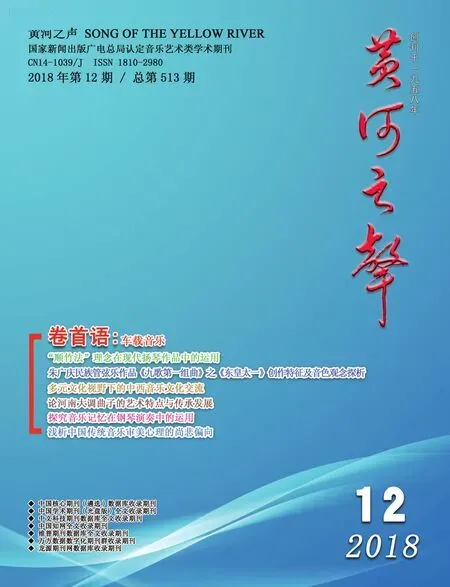中國傳統民間音樂的藝術性
修桂祺
(江蘇師范大學,江蘇 徐州 221006)
若論音樂的藝術邊界,首先要看清楚音樂藝術性范疇,有了范圍,才有范圍之外,才有邊界一說。中國傳統民間音樂是否站在了邊界之外?西方音樂與中國的民間音樂相比,為什么會有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的地位區別的看法?若談到音樂的藝術性,那想必中國在20世紀之前是沒有“話語權”的,按照西方音樂的音樂詞典的定義來看,西方音樂的歷史進程是一部音樂的藝術史,那么中國是沒有“中國音樂藝術史的”。可以被稱得上是藝術的作品通通來自于藝術家的筆下,西方的音樂史就是由音樂家和他所作的作品組成的,若以這樣的定義來看中國的傳統音樂,會發現中國傳統音樂是缺乏“藝術性”的,大都是由民間音樂和建立在民間音樂之上的宮廷音樂、宗教音樂等組成的,沒有明確的作曲人,就是一首民間的小調旋律擺在那里,大家都會唱,更像是一種傳承、一種生活,一首流傳下來的作品是由眾人歷時所創造的,是否這樣的音樂就是非藝術性的,答案肯定是否定的,那么音樂的藝術邊界到底在哪里,中國傳統音樂是否可以稱得上為音樂藝術。
一、何為藝術
對于“藝術”下一個精準的定義,是非常難的,藝術就同文化一樣,每個人都感覺自己理解這個詞,但是卻又表達不出來它的具體含義,表面上來看,可以稱它可以為日常生活中的唱歌、雕塑、繪畫、練字,但是探究其深層的含義,卻是無法形容與表達的。《現代漢語詞典》中對藝術的解釋是:“用形象來反映現實但比現實有典型性的社會意識形態。包括文學、繪畫、雕塑、建筑、音樂、舞蹈、戲劇、電影、曲藝等”。馬克思認為:“藝術是一種社會生產,與一般的社會生產勞動都是一樣的。藝術也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也是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
音樂從古至今從國內到國外都可以稱得上為一種無國界的交流方式,它能夠抒發不同語言的同樣的情感,也是人類不同語言之間交流的媒介。在《圣經》中有這樣的記載:“神創造出人類之后,人類開始變得驕傲起來,由于他們說著同一種語言,沒有語言障礙的限制,人類的力量逐漸壯大起來,他們自認為可以造一座高塔到達神那里。神憤怒了,因而變亂了人的語言,人的力量也因為語言的障礙而變弱了,不過所幸的是人類依然保留了音樂——這個無國界的語言,世界各國的人們依然有著各種備樣的音樂文化交流活動。其實藝術就是跨越了語言之上的.人類共同的情感交流。”
藝術雖然是現代產生的詞匯,但是藝術一詞所包含的范疇是隨著歷史發展的進程一直存在的。唐代的張彥遠曾在他的著作《歷代名畫記》中寫道:“用直尺畫出來的畫是‘死畫’,而像吳道子那樣‘意存筆先’、‘守其神,轉其一’,才是‘真畫’”。古人對于藝術作品有自己的定義,對于符合這個范疇的,便可稱為有價值的藝術作品,這種行為應該看作是一種藝術定義的萌芽。
雖然中國古代就已經產生對藝術作品價值判斷的定義了,但是繪畫又與音樂不同,繪畫作品一般是由一個人獨立完成的,就像西方的藝術家有自己獨立的作品一樣,這些作品都被稱為“藝術品”,所以中國古代對于“畫”是否具有審美價值能夠有一定的認識,但是中國傳統音樂的歷史上,沒有確切的、精確到個人所創作的作品形式,所以對于其是否具有“藝術性”,成為一種難以評判的局面。
二、從審美價值來看中國傳統音樂的藝術性
在藝術一詞最初出現的時候,都是與審美掛鉤的,二者不能分開,有審美的才是藝術的,好的藝術作品即是能夠被人欣賞的,可以喚起人們心中情緒的共鳴,可以達到身體器官的審美反應,能夠成為人民所樂于去視聽的作品都可以被稱為“藝術作品”。若以這種定義來看中國傳統音樂,那么中國傳統歷史上的無論是民間的、還是宮廷的都可以被稱得上為藝術,因為民間音樂與宮廷音樂本就是源于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更是服務于人民的娛樂審美與情感表達,就如少說民族中的畬族,他們的民族傳統就是以對唱情歌來找尋終身伴侶,畬族男女青年在達到一定的年齡后就可以以對歌的方式找尋配偶,畬族的青年男女崇尚自由戀愛,在經過互相的對歌“肚才”之后,認為互相是最為合適的伴侶時,就可以互相贈送定情信物作為訂婚的禮物。還有很多的少數民族,他們的民族音樂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民族音樂本就是長在少數民族的生活中,根據人民的日常生活所產生的、由大眾智慧所創造的。所以,能夠流傳至今并且廣為傳唱的都具有較高的人類性和文化性。經歷史實踐的反復檢驗,存活到了今天的音樂經過了無數次審美的檢驗和改變,才積淀為現在的音樂形態,除了要適應前人對于音樂的審美標準,也要滿足后人的精神需求,在長期的社會發展中形成民族對于這種音樂形態的欣賞習慣,這是前代人與后代人共同所創作的、經過反復的篩選與改變才鑄就今天的各民族的音樂形態。
建立在民間音樂之上的宮廷音樂也亦如此,宮廷音樂大都來源于民間的小調或者外族流傳被納入宮廷的音樂。除了在功能性上與民間音樂有出入以外,在藝術性與審美價值方面,都是不分前后極具有價值的、由歷史所形成的音樂。
三、從不同功能來看中國傳統音樂的藝術性
雖然藝術看似凌駕于生活之上,但是卻不是架空在生活之上,而是源于生活并且服務于生活,具有一定的功能性。馬克思所說的藝術是一種社會生產、藝術也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也暗指其具有一定的社會作用,既然是上層建筑,那就一定會反作用于“經濟基礎”。“所謂音樂的社會功能性,即音樂在社會文化生活中為什么應用,又是如何被應用,音樂在被應用的過程中究竟有怎樣的用途和意義。僅僅是為人們所欣賞、審美,還是被人們賦予了其他層面的意義”。
傳統音樂在過去的社會中的功能分為政治功能、教育功能、實用功能。在封建社會的過去,等級制度森嚴,每一個等級都有其所適用的禮樂,這時的音樂就是統治者的輔助工具。禮樂制度開始于西周,周朝統治者為了維護國家最高統治者的權利以及統治人民和鞏固貴族內部關系,以“禮”作為一種治理手段。周公制定的禮樂制度的出現,剛好適應了當時的社會政治、文化發展的需要,其實西周的禮樂制度就是等級制度。禮樂制度的等級之下,要求人民按照等級的劃分去行使各自的權利,什么樣的身份使用什么樣的音樂,可以說,禮是樂的核心,樂只是禮的外在表現形式,樂是禮的表現手段之一。禮和樂的彼此相輔相成,除了能夠更好的服務于通知階級之外,還可以更好的統治人民。《史記·樂書》中提到:“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由此可以看出,樂雖然是附屬于禮,但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種制度的形成,肯定是要建立在有人服從的基礎之上的,禮樂制度在于禮的實施,禮是外在規范性的事物,而樂則是內在服務于禮的途徑。
教育功能則是附屬于禮樂功能上的樂教功能。圣人制禮作樂的依據是天理人情,目的是使社會秩序合乎天道。施政主要不依靠刑罰,那么治理國家的重點就應該是民眾的教化和引導,則是實行先教后刑的國家政策。治人之情的重要內容在西周統治者來說是“德治”,那就需要一套人人都要遵守的社會倫常。雖然西周統治者說樂教可以“德治”,但其實是統治者利用樂作為統治的工具,加強他們對被壓迫階級的精神奴役,從政治思想上合法的加強了他們的統治。西周貴族中提倡樂教,使他們能根據統治階級的意圖,利用樂鞏固、控制他們的政權,其實樂對貴族階級是教育作用,而對庶民階級來說那就是教化作用了。西周統治者把樂教視為“國教”,可以看出統治階級充分認識到樂不僅具備祭祀娛樂的功能,而且也具有教化的功能,所以他們用樂教的手段來達到治國安民的政治目的。西周樂教具有相對完備的教學制度和教育機構,統治者使教育機構與行政機構融為一體,自然而然樂教本身就具備了“政教合一”的性質。但是樂教從相比情況下也使西周社會安定、以及社會意識形態和審美觀念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一定程度上來說樂教也得到了政治以及禮樂制度的推動和發展。西周樂教在實施過程中,一直遵循禮的規范,受禮的約束,不過這也成就了禮樂制度的鼎盛時期。但是樂成為禮的附庸,還是違背了樂自身本質的特點和發展規律,忽視了樂本身就是發自人的內心感受和表達情感的感性內容。西周時期的樂教是一種綜合性的藝術教育,如郭沫若所說:“中國舊時的所謂樂,它的內容包含很廣,音樂、詩歌、舞蹈本是三位一體不用說,也包含著繪畫、雕刻、建筑等造型藝術,甚至連儀仗、田獵、肴饌等都可以涵蓋。所謂‘樂者,樂也’,凡是使人快樂,使人的感官可以得到享受的東西,都可廣泛地稱之為樂。”所以說西周樂教是全面發展的,主要內容可分樂德、樂語、樂舞三個方面:樂德主要包括人倫、道德、政治以及宗教思想的教育,樂德教育是一種政治需求,其內容是與分封制、宗法制的思想一致的,所以也是被西周歷代統治者最重視的樂教內容;樂語即樂詩,是通過借古喻今的方法來培養受教育者賦詩配樂、文筆寫作的能力以及對賦、比、興的審美情感的提升;樂舞的學習是可以受教育者緬懷祖先們的豐功偉績,了解民族發展歷史,并在奏樂、歌唱、舞蹈的綜合實踐中得到審美情感的體驗。樂教的德育內容和情感內容相輔相成,從而得到“以樂教和”的目的。從西周禮樂制度下樂教的精心安排,可以清楚的看出當時人們用樂的意圖和審美意識的強烈。
實用功能,一般是指不論宮廷與民間,人民日常生活中所要用到的、必不可少的。無論是宮廷還是民間,都會有祭祀和祈禱的活動,民間祭祀形式比較簡單,一張桌子、香爐、貢品和執行祭祀儀式的出家之人,與天地神靈溝通的就只能是他們所唱出的音樂。這種以念白為主的說唱形式一直發展到今天,在宗教的活動中,音樂可以幫助人們抒發、宣泄情緒,讓受眾者產生一種美的聽覺享受,間接喚醒人們心中積極的正面能量,進而走出艱難悲傷的局面,以向上的態度面對自己的困難和痛苦,最終擺脫困境。圣樂家麥柯說:“詩與音樂不是宗教生活的裝飾品,而是宗教生活的心臟地帶。歌唱與信仰生活密切相關,詩歌是傳遞信息的有效途徑,是激勵人心的重要媒介”。當然,實用功能不止宗教方面的,還有日常生活中的婚喪嫁娶,都需要音樂來渲染氣氛。比如民間愛用嗩吶來運用于紅白事,因為嗩吶的音高,穿透力強,在過去的整個村里都可以聽見,這樣就像是一種便捷的信號傳遞,音樂的聲音一響,所有住在這個區域內的人都知道你家中有了事情,這樣就避免了挨家挨戶去通知的麻煩和尷尬的局面。
這些功能造就了傳統音樂在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地位,所謂“存在就是合理的”,在長達千年的孕育中,這些合理的存在已經上升到了具有極高價值的地位。正是由于這些功能性的體現,使傳統音樂在審美藝術性之上,還多了功能藝術性。
四、結語
在20世紀上半葉的時候,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社會產生了浩瀚如海洋的民歌和歌舞,數以百計的說唱、戲曲和器樂品種,演唱、演奏、創作、理論各個方面代有杰出人,文獻的積累凝結著無數哲人的心血。總之,中國的音樂遺產,包含文獻的、口頭的、實踐中的,根源深遠、眾人歷史的音樂放在西方音樂的面前,就像是一個兒童仰望著一位巨人,收到西方音樂對于藝術的定義的思想影響,無論是國內學者還是國外學者對于中國傳統音樂的評判都是拒絕的,認為其是“農民”所創造的,只具有低俗的娛樂價值而沒有任何的藝術性,在世界音樂面前是“上不了臺面的”。但是筆者認為,中國傳統音樂不僅具有藝術性,還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與西方音樂相比,雖然中國傳統音樂作品不是確切的、出名的音樂家所作,但是它是經過了一代又一代人智慧和審美的改變與凝練,集思廣益的音樂作品要比個人作曲家抒發自己的感情所作的作品要有更深遠的意義。所以當我們去看待音樂的藝術邊界時,不能只關注這部作品是哪一位藝術家所創作的,這樣的門檻,會使我們失去很多優秀的藝術作品,來自于民間的并非就是“非藝術性”的,所謂“高手在民間”,很多民間音樂現在成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這就是對于這些音樂的藝術性的肯定。現代很多學者把《西方音樂史》稱為《西方音樂藝術史》,在筆者看來,這種稱謂可以說得上是具有誤導性的,西方音樂史書中并沒有西方的民族音樂,難道西方的民族音樂就不具有藝術性嗎,所以,對于音樂的藝術性的判斷,并非從作品的出處來判斷,只需觀賞作品的本身,是否值得去審美,是否有其一定的功能性,這樣對于音樂的藝術性才能不失偏頗。音樂的藝術邊界,本就是一種意識形態,取決于審美,判斷于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