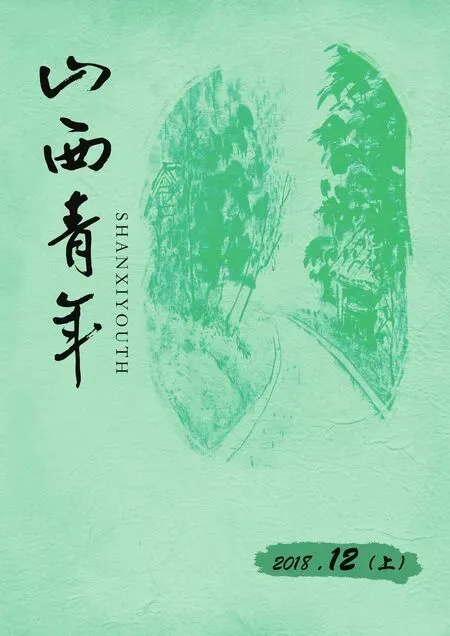漢魏之際的儒法融合
——以北方士族為例
楚 宜
(南昌大學人文學院,江西 南昌 330000)
漢以來儒家獨尊,儒家被作為唯一的執政觀念,其作為學術思想的本身內涵萎靡,導致儒學嚴重片面化。漢魏之際,曹操的嚴刑峻法,智謀術勢的表現不僅僅是陳寅恪先生謂摧毀“士大夫儒家體用一致及周孔道德之堡壘”的儒法之爭。應當注意的是,曹操亦有尚禮崇德之行,儒家士族也開始接受施法用刑。儒法未必涇渭分明,兩者具有一定聯系,也可相互滲透。
一、儒法學術思想上的聯系
儒家和法家作為一種獨立的學術思想,其目的都是為了建立全新的統治秩序以加強中央集權,達到并維護社會穩定。兩者具有其內在聯系。毫無疑問,儒家具有明顯的德治傾向,單純的德治對人民素質和覺悟要求很高。當時的社會經濟和教育條件是不可能使社會道德普遍達到儒家的理想狀態。法家的“法治”則需要嚴酷完善的法律和龐大嚴密的官僚體系來維系和執行。傳統中國的地域條件及科技水平等因素亦明顯制約了這種非人性的單純法治。儒學作為一種學術思想,歷經發展完善,內涵豐富而圓融。孔子曾判斷:“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孟子也主張舜應執殺人的舜父。儒家經典著作也有表述,《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荀子是公認的儒家學說集大成者,但他也揚棄地汲取了其他諸子思想,尤其是法家,他明確提出了“禮法治國”。盡管儒家之“法”與法家之“法”有所差異,但已然表現了儒家在一定程度承認純德治具有片面性,這也為法家的滲透提供了理論縫隙。
上述可知,儒法學術上的內在聯系,純德治和純法治的不合理性以及儒家學說本身對法家的兼容性決定了儒法融合的可能性。
二、漢末儒學對法家的排斥
作為學術思想的儒學經過董仲舒的改造,迎合了統治者的心理,被定為官方執政思想,成為一尊,儒學開始逐漸官方意識形態化。東漢儒學作為唯一的執政思想,受其他的學術思想影響較少,開始無限制發展,并逐漸走向僵化。甚至儒學為了證明其學說的獨霸性,刻意地劃分與其他學說的區別,斬斷與其他學說的聯系,與其他學說對立。作為官方執政思想的儒學與作為學術思想的儒學相比,明顯缺乏了許多與法家等諸子學說相通的內涵。東漢中后期儒學官方意識形態化尤為嚴重,其排斥法家的傾向更為明顯。
從官方執法的內容看,當法律條令與儒家倫理道德沖突時,官方化的片面儒家倫理道德以及其影響下偏執的社會輿論和風氣踐踏了法律。何颙“少游學洛陽……顯名太學”可見其儒學修養很高,非一般俠士豪杰。但“友人虞偉高有父仇未報,而篤病將終,颙往候之,偉高泣而訴。颙感其義,為復仇,以頭醊其墓。”卻未見何颙伏法。為親復仇的案例在漢末不勝枚舉,而伏法見刑者實為罕見。更有官員袒護復仇者,甚至有為赦復仇者而棄官的現象。
“擒滅盜賊,在于明法,不在數赦,今不顯行賞罰以明善惡,嚴督牧守以擒奸滑,而反數赦以勸之”的施政手法更是對于“議者必將以為刑殺當不用,而德化可獨任”這種畸形社會風氣的具體描繪。
從儒家士大夫觀念來看,如楊賜者,其祖楊震,父楊秉都是大儒,祖傳《尚書》,屬儒家士族無疑。漢靈帝欲以楊賜為廷尉,而“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皋陶不與焉,蓋吝之也。’遂固辭。”而廷尉“掌刑辟,凡獄必質之朝廷,與眾共之之義也。兵獄同制。”自我認同為儒家非法家,從其言論中可見他對法家的排斥甚至否定。因此廷尉這種執法官職亦被他認為應由法家代表就任,故辭而不受。史書上多次記載的儒家士族以儒家理論為依據對文法吏的指責抨擊也代表了儒家士大夫觀念上對法家的排斥。
尊儒排法造成的社會流弊在東漢末期展露無遺,盜賊四起,天下大亂。這也決定了漢魏之際儒法融合的必要性。
三、北方士族觀念的轉變
東漢中后期,政治黑暗,法制廢弛。崔寔,王符等個別士人就開始呼吁法家思想的回歸。然而朝中大多官員價值取向仍是以儒為本,與法對立,甚至對他們認為的法家代表,所謂的文法俗吏亦大加指責。漢末魏初的社會動蕩明確地宣告了官方意識形態化的儒家思想已無法維系社會的穩定,一些士人的思想觀念開始發生轉變,法家思想走進了他們的視野。北方獲得統一后,入仕的北方儒家士族皆屬曹操,曹操的儒法并用向士人證明了其思想的合理性,并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北方儒家士人。北方士族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法家思想。
服膺儒學的北方士族繁多,況且北方士族中亦仍有尊儒排法之例,因而不便一一列舉。故分漢末鴻儒,早期追隨曹操,原附世家大族袁紹這三類士族舉例論述北方儒家士族兼容法家思想的現象和趨勢。
史載,“后漢獻帝之時,天下既亂,刑法不足以懲罪,于是名儒大才崔實、鄭玄、陳紀之徒,咸以為宜復肉刑。”足以表明鄭玄這些漢末鴻儒針對時局已開始接受法家的嚴刑手段和儒法并用的思想。
荀彧屬服膺儒學的穎川士家大族,早年就追隨曹操,他在論曹操與袁紹交戰有“四勝”時談到:“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土卒雖眾,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明確地批評了袁紹法令寬緩,肯定了曹操明法令。“魏武秉漢政,下令又欲復肉刑”,而“相國鐘繇亦贊成之”,立場鮮明地持肯定態度。鐘繇是穎川大族,早年即被曹操所用。更有較早歸順曹操的穎川士族陳群針對此事論:
“《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刖、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于古制;至于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剪毛發,非其理也。”
此論雖立足于減刑輕法,但用儒家理論證明法律的合理性,再用法維護儒家秩序的思路是明顯的。
袁紹四世五公,為以儒入仕之世家大族無需多述。袁氏門生故吏天下遍布,附于其勢力者亦大部為儒家士族。高柔是袁紹外甥高干的從弟,在家族等級森嚴的東漢,與袁紹聯姻的家族自然有較大影響力。高柔歸順曹操后為管長,“縣中素聞其名,奸吏數人,皆自引去。柔教曰:‘昔邴吉臨政,吏嘗有非,猶尚容之。況此諸吏,于吾未有失乎!其召復之。’咸還皆自勵,咸為佳吏。”此為德教成功案例。而他在《諫就獄殺公孫晃疏》上曾引:“《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儒法融合的思維方式亦十分明顯。
綜上所述,儒法兩家作為學術思想本有一定的相互兼容性。秦定法家為執政思想而十余年即亡,使法家本身備受指責,歸于沉寂。官方意識形態化的儒學作為唯一的執政思想排斥法家,趨于萎靡,最終無法維系統一穩定時,一些儒家士人開始肯定部分法家思想,法家思想逐漸走向前臺。儒法并用的實踐得到了統一北方的成功,逐漸成為一種思維方式,并影響了北方儒家士族,儒法進一步融合,成為普遍的現象和不可阻擋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