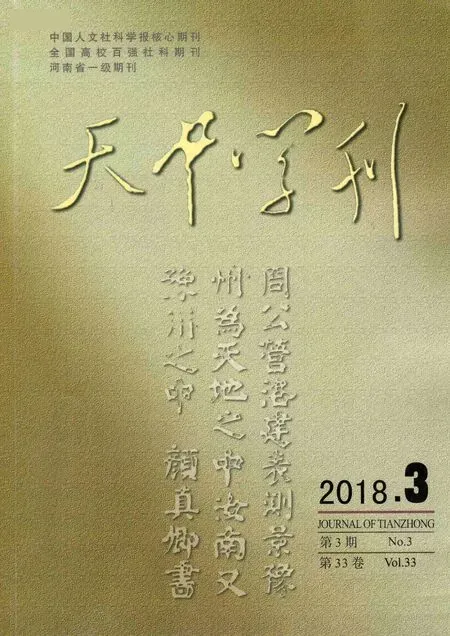揚州學派名家朱彬交游補考
程 希
(揚州大學 文學院,江蘇 揚州 225002)
揚州學派名家朱彬(1753―1834年),字武曹,號郁甫,江蘇寶應人,乾隆六十年(1795年)舉人。朱彬著有《禮記訓纂》49卷、《經傳考證》8卷、《游道堂集》4卷等。《清史稿》卷481、《清史列傳》卷69等均有其傳。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將其歸為皖派經學家之列,但關于其卒年則誤記為 81歲①,實則朱彬享年 82歲。關于朱彬之詳細生平,寶應朱氏后人,朱彬六世孫朱慶裴編纂有《朱彬先生年譜》②一書。該書為朱彬首部年譜,其篳路藍縷、開辟榛莽之功自不容忽視,但作為首創之作,疏誤脫漏之處亦為數不少,筆者曾撰文略加更正③。對于朱彬之交游情況,藍瑤《朱彬交游考述》一文初步予以探討,得劉臺拱、王念孫、王引之、李惇、汪中、邵晉涵 6人④,后來在其碩士論文第一章第二節“朱彬的交游”中增加汪喜孫 1人⑤,但兩者相加不過7人,且基本限于其友朋一輩,未能全面反映朱彬畢生交游之概況,未免有遺珠之憾。有鑒于此,筆者重新梳理相關文獻,對朱彬交游情況補苴缺漏,另考得喬億、朱賽、賈田祖、范鏊、葉世倬、吳瑭、陸繼輅等7人,當為考察朱彬詩學觀、古文觀、理學觀乃至醫學觀之重要材料。今按其年齒先后為次臚列如下,使讀者對朱彬之生平學行有更清晰、全面的認識,對于深化揚州學派個案研究及寶應朱氏家學研究當不無裨益。
一、喬億
喬億(1702―1788年),字慕韓,號劍溪,江蘇寶應人,喬萊孫、喬崇修子,善談論,以國學生應棘闈試,不售,輒棄去,專肆力于詩,其五言宗漢魏,其近體亦不屑作大歷后語。時沈德潛主東南壇坫,海寧查氏以詩鳴浙西,億與之游,頗能自樹一幟。喬億著有《元祐黨籍傳略》《暮齒宜鑒錄》《藝林雜錄》《小獨秀齋詩》《窺園吟稿》2卷附《江上吟》1卷、《三晉游草》1卷《附錄》1卷、《夕秀軒吟草》1卷附《惜余存稿》1卷、《劍溪文略》1卷、《時燕石碎編》1卷、《劍溪外集》1卷、《素履堂稿》1卷、《小獨秀齋近草》1卷、《集古》1卷、《古詩略》《蘭言集》《大歷詩略》6卷、《杜詩義法》2卷、《劍溪說詩》2卷《附錄》1卷、《杜詩偶評》《詩蒙記》《王孟韋柳詩評》《喬劍溪遺集》等。乾隆六十年(1795年)朱彬曾為
喬億遺著《蘭言集》作序。喬億乃朱彬祖父一輩,以詩名江淮間,并以此提攜后學,邑中人士多以其為師,朱彬伯父宗光、叔父宗大皆終身受業,朱彬父宗贄亦常向其請教詩藝。朱彬少時亦曾以詩向喬億請教:“憶童稚時以詩請業,翁謬許為可從事于古,或有言于翁者曰:‘朱氏子,其父方教以帖括,將以求科取名。先生顧以詩教,毋乃盭乎?’翁笑不應。越日,余再以詩進,翁正告之曰:‘吾視子之材,方期以大且遠者。慎毋以詩自汩。’余于是悚然不敢為詩。”[1]613朱彬本來有很好的詩歌天賦,其晚年曾說:“予束發即好詩。時侍先祖,命題構思,每成一詩,先祖輒色喜。”[1]615但世重科名,朱彬之父希望其攻習時文,邑人亦以此提醒喬億,喬億因之不便勉強,本也可以理解,但由此導致朱彬自此不再作詩,至今無一首詩傳世,卻不免有所遺憾。朱彬后來也曾有悔意:“迄今三十年……因復自悔,假而少即肆力于詩,親得翁之指授,庶幾萬一有所成就,廁名篇末,有余慕焉,為慨焉三嘆而識之。”[1]613朱彬最終雖未能成為一位詩人,但他對詩歌卻自始至終保持著熱愛,也從未放棄過對詩藝的鉆研。他廣泛涉獵大量古今詩作,對先祖中有朱應登、朱曰藩、朱克生等著名詩人引以為傲,稱“吾邑本風雅之宗,而吾家實開其先”[1]617–618,并自覺承擔起傳風續雅、不使斷絕的責任,不僅搜集大量清初至清中葉同里詩人詩作匯編而成《白田風雅》24卷,還撰有詩文評類著作《游道堂詩話》,除此之外還為不少親友及前輩詩人如朱應辰、喬億、朱賽、葉世倬等人詩集作序、跋⑥。從中不難看出朱彬著意保存鄉邦文獻、闡揚先賢流風遺韻之良苦用心,亦可見其在詩歌上造詣匪淺,值得重視。究其原因,除受家風家學的熏陶浸染之外,同邑前輩詩人喬億、朱賽等的關愛提攜亦不可忽視。《白田風雅》收喬億詩61首,為諸人之冠,足見朱彬對其推崇。《游道堂詩話》評其詩曰:“先生詩早宗六朝三唐,晚歲肆力于杜。自少至老,無一日去書。與沈尚書德潛、沈光祿起元為忘年交。然詩品清高深穩,不難上掩古人,不因揄揚而重也。”[2]353此外,朱彬還在《劍溪先生墓表》中再次追憶其18歲時以詩向喬億請教的情景,喬億勉勵他:“以子之材,當務其大且遠者,詩非所以涃吾子。”而朱彬也自稱“余輟詩不為而求六藝自茲始”[1]634。可見朱彬對此事記憶猶新,難以忘懷。喬億對邑中后學最為喜愛者為朱彬及劉臺拱二人,曾對二人囑托:“吾老矣,身后茫昧不可知,唯賴子與端臨爾。”[1]634既有以詩文相托付的信任,又有對二人的殷殷期望。喬億卒后30年,朱彬猶念念不忘當年重托,親撰墓表,表彰其嘉言懿行,足見喬億其人對朱彬影響之深遠。
二、朱賽
朱賽,字祈年,號佛景,又號南樓、諸生,居東鄉界淘溝,足跡不輕涉城市,閉門課子,以吟詠自適,與苗莊、胡豳、劉玉堂、郭楷等為詩友,著有《屠蘇集》《青苔居士集》《蘗樹山莊集》《佛影集》《南樓雜詠》《黯然集》等。朱彬在《白田風雅》中將其與喬億共列第11卷,收其詩17首。《游道堂詩話》評曰:“南樓先生為副使公嘉會之裔,與吾族通譜最久。少時于途次見之。時吾邑稱詩者喬劍溪先生外惟先生可肩隨。喬孤介,少與先生由由與偕。邑后輩多宗仰之。身后其家秘其稿不以示人,僅從友人齋中所傳暨其次孫所記憶鈔錄者以見一班,后得其全稿,所錄無一存者,則散佚者甚多也。”[2]359道光五年(1825年)朱彬為朱賽遺集作序,將其與喬億并稱。而朱賽對朱彬亦頗賞識,對其期許有加,朱彬回憶道:“彬幼年侍先祖,遨游市中,途遇先生,見先祖,正立拱手。先祖命揖,先生執余手曰:‘聞汝頗有志乎古,暇時蓋過我。’余逡巡不敢對。”[1]614朱彬祖父澤代卒于乾隆三十六年(1767年),是年朱彬14歲,蓋朱賽與朱彬交接當在1767年之前。朱賽與朱彬分屬界淘朱氏與朱翁朱氏兩支后裔,兩家雖非同族,但自明代開始即交往密切,情誼甚篤。明朱嘉會與朱應登同舉進士,遂聯譜牒,至清初朱賽祖父與朱彬曾祖“以詩投契,情好尤篤,以故兩家子弟歡若一族”[1]614。而朱彬后來雖未能以詩名世,但卻成為揚州學派經學名家,也算不辜負朱賽對他的一番厚望。
三、賈田祖
賈田祖(1714―1777年),字禮耕,號稻孫,清高郵人,乾隆時廩生,好學,多所瞻涉,喜《左氏春秋》,未嘗去手,旁行斜上,朱墨爛然,著作凡三千余篇,清雄博奧,見者驚為奇才。賈田祖
性耿直,與同邑李惇、王念孫及從弟成祖友,皆善飲,酒酣,輒鉤析經疑,間以歌詩,往牒舊聞,泛演旁出,雅噱風生,《清史稿》有傳,著有《春秋左氏通解》、《稻孫詩集》4卷、《容瓠軒詩鈔》4卷、《禮耕存稿》1卷等。《贈吏部尚書郁甫朱公墓志銘》(以下簡稱《墓志銘》)載朱彬“年十八,補諸生,與高郵賈稻孫田祖、李孝臣惇、江都汪容甫先生中諸先生為友,皆閎洽才而鉤貫經史”[3]581–583。藍瑤《朱彬交游考述》一文對李惇、汪中與朱彬之交往情況有所述及,唯獨不及賈田祖。二人定交之年朱彬18歲,該年當為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賈田祖長朱彬39歲,是年已經57歲,兩人算得上忘年交。汪喜孫撰《容甫先生年譜》中引朱彬語有言及賈田祖者:“賈君以詩名,世人謂容甫之學出于賈稻孫,誤也。”[4]可見朱彬比較認可賈田祖的詩歌成就。但賈田祖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即去世,兩人相交不過7年,故所存來往資料無多。賈田祖長于《春秋》學,朱彬則于禮學用力較深,其《禮記訓纂》及《經傳考證》等書亦未見有引賈田祖論說者。但可以肯定的是賈田祖作為揚州學派早期代表人物,在諸同好中年輩又最長,無疑具有很強的向心力及號召力,聯系上文朱彬放棄作詩而專力于經學亦在此年,則賈田祖由文學而樸學的學術經歷對朱彬無形中的感召作用是無疑的。
四、范鏊
范鏊(1743―1802年),字叔度,號攝生,順天府大興人,原籍江蘇上元,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進士,選庶吉士,歷任刑部貴州司主事、湖廣司員外郎、陜西司郎中、陜西道監察御史、浙江司郎中、鴻臚寺少卿、通政使司副使、光祿寺少卿監盧溝橋賑務,曾四充會試同考官,典湖北、四川等省鄉試。朱彬與范鏊定交當在嘉慶三年(1798年),《墓志銘》載朱彬:“簡淡寡交游,嘗居京師,足不履貴人門,惟與王觀察石臞、邵學士二云、范光祿叔度三先生以文章道義相愛重。”[5]710對王念孫、邵晉涵二人,藍瑤《朱彬交游考述》已有述及,獨于范鏊語焉不詳,或因資料不足所致。范鏊于 4年之后的嘉慶七年(1802年)去世,則兩人交往時間較賈田祖更短。另據《墓志銘》交代,朱彬長女適大興廩貢生江西候補府經歷范承英,而朱珪所撰范鏊墓志銘載,鏊二子一名準,一名潤,字號則未詳⑦。承英是否為范鏊子嗣尚不可考,但至少應是范氏族人,寶應朱氏與大興范氏締結姻親之好,則朱、范二人并非泛泛之交。
五、葉世倬
葉世倬(1752―1823年),字子云,號健庵,江蘇上元人,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舉人,四十八年(1783年)充《四庫全書》館謄錄,五十年(1785年),議敘知縣,分發四川,后歷任嘉興乍浦同知、湖北德安府同知、陜西西安府同知、興安府知府、福建延建邵道、臺灣道、江西按察使、山西布政使、山西巡撫、福建巡撫兼署閩浙總督,身后入陜西名宦祠、鄉賢祠,著有《健庵日記》《四錄匯抄》《退思堂詩文集》等,主修《續興安府志》8卷。寶應朱氏與上元葉氏乃世交,朱彬之父宗贄與葉世倬之父均官即相友善,均官曾任寶應主簿,并延請宗贄教其二子(即世經、世倬兄弟)。朱彬在《葉健庵六十壽序》中稱“余之友未有先于健庵者,年十三四時健庵師事先君子……”[1]623可見二人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左右即已結交,后來兩家又結為兒女親家,世倬長女嫁朱彬次子士達,婚姻洽比,情好日篤,兩家關系更進一步。朱彬晚年深情回憶二人于嘉慶三年(1798年)的交往情形:“戊午,余赴禮部試,君亦守選北上,驅車并行,至京同寓櫻桃斜街。寒夜擁爐,論今道古,漏下三鼓始就寢。平生朋友之樂,無逾斯時者。”[1]623今《游道堂集》卷2尚留存有朱彬致葉世倬書信1通,約略可見二人論學情形。在信中朱彬敞開心胸,縱論古今,臧否人物,抨擊陸、王,推崇朱子,甚至對于友人李惇排斥理學的偏頗之舉亦直言不諱予以指正,頗能反映朱彬本人的學術宗尚。正是因為將葉世倬視為知己,故而才會無話不談,直抒胸臆,表達自己對各家各派的真實看法。此外朱彬還為世倬詩集作序,稱其詩“深造自得,出入于樂天、子瞻、務觀諸家”[1]615。朱彬本來戒詩不做已數十年,及至世倬以詩囑其點定,“予性到,間一屬和,忘其前戒”[1]615,蓋因性情投合、不由自主,二人相交之融洽無間可見一斑。至世經、世倬兄弟相繼辭世,朱彬又為二人分別撰寫碑銘,述其實績、表其德行。在朱彬所交往的友人當中,其論交之久、往來之頻繁、情誼之深篤者無過于葉世倬。
六、吳瑭
吳瑭(1758―1836年),字配珩,號鞠通,清江蘇淮安府山陽縣人,清代著名醫學家。吳瑭年19其父即久病不愈而逝,其遂有志于醫學,但家貧,乃棄舉子業,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赴京師,時四庫館開,傭書以自給,得以博覽醫學名著,自此醫道精進。乾隆五十八年(1793)京師瘟疫流行,經誤治而死者,不可勝數,瑭以溫病法救治,存活者甚眾,名聲大噪,自此步入醫林,長期在京行醫。吳瑭對溫病研究深刻,創溫病三焦辨證理論體系,被后世譽為清代溫病四大家之一,著有《溫病條辨》6卷首1卷、《醫醫病書》、《吳鞠通醫案》4卷。嘉慶十六年(1811年)朱彬在京師與吳瑭定交,得觀其《溫病條辨》,大為贊賞,欣然為之作序,稱其“自溫而熱而暑而濕而燥,一一條分縷析,莫不究其病之所從生,推而至于所終極;其為方也約而精,其為論也閎以肆,俾二千余年之塵霧,豁然一開。昔人謂仲景為軒岐之功臣,鞠通亦仲景之功臣也。”[6]1除此之外,朱彬還對全書一一批閱點評,據筆者統計,其評語至少有179條之多,皆簡明扼要之語,少者一二字,多者亦不過數十字。朱彬對吳瑭此書頗為推崇,比如卷一中評《辛涼平劑銀翹散方》云“妙甚”,評該方之“方論”云“要著”“精能之至”“著眼。止此二語,沾丐后學無窮矣”[6]16–18等,亦可見出朱彬雖不以醫學名世,然對醫道頗有研究,醫學修為亦非同小可。否則以其樸學家的身份,必定不會妄施丹黃,輕易為《溫病條辨》作批點。朱彬82歲而卒,在揚州學派諸學人中算得上高壽,應與其本人通醫道不無關系。值得一提的是,朱、吳二氏的友誼延及后輩,朱彬長子朱士彥與吳瑭亦為知交,士彥曾撰《吳鞠通傳》,載吳氏《醫醫病書》一書,稱其“居心仁厚,篤于故舊,與人能盡言,處事悉當……豈獨精于醫哉?”[7]
七、陸繼輅
陸繼輅(1772―1834年),字祁孫,別號小元池居士、修平居士,江蘇陽湖人。繼輅幼孤,生母林嚴督之,非其人,禁勿與游,甫成童,出應試,得識丁履恒,歸告母,母察其賢,始令與結,其后益交莊曾詒、張琦、惲敬、洪飴孫輩,學日進。其乃嘉慶五年(1800年)舉人,選合肥訓導,以修《安徽省志》敘勞,遷貴溪令,三年引疾歸。繼輅儀干秀削,聲清如唳鶴,不以塵務經心,惟肆力于詩,其詩清溫多風,如其人也。常州自張惠言、惲敬以古文名,繼輅與董士錫同時并起,世遂推為陽湖派,與桐城相抗。繼輅著有《崇百藥齋文集》20卷、《續集》4卷、《三集》12卷、《合肥學舍札記》12卷、傳奇《洞庭緣》、《秣陵秋》(與莊逵吉合撰)等。《清史稿》卷486、《(光緒)陽湖武進縣志》卷26均有傳。朱彬《游道堂集》卷2有《與陸祁孫書》1通,在信中朱彬為陸繼輅暢論為文之道,品評各家得失,頗為宏通。信中交代,朱彬13歲時讀方苞古文,推崇備至,認為其為北宋諸家之后第一,后來經表兄劉臺拱推薦讀歸有光《震川文集》,又得清初作家宋犖所選《國朝三家文鈔》讀之,按圖索驥,又遍讀侯方域《壯悔堂文集》、魏禧《魏叔子文集》、汪琬《鈍翁類稿》三家原著。朱彬認為,“叔子廉悍非常,而少儒者雍容氣象;朝宗倜儻,而文氣未能調適;鈍翁近之矣,而緩弱抑又甚焉”[1]610,皆不甚洽于心。朱彬自言及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赴泰州應試,與汪中定交,其古文得到汪中贊許,治古文自此始。此后朱彬廣泛涉獵南宋以后之文,認為“皆懦鈍不中法”,40歲之后讀姚鼐、劉大櫆之文,以為皆不如歸有光及方苞,而在歸、方兩家之中,認為“震川文似平衍,而寬博有余之氣勝;方望溪峭蒨近介甫,而紆余委備實遜震川”[1]610,以為歸有光更勝一籌。朱彬對汪中的文章評價很高,謂其“風發泉涌,雄厲凄清。碑銘頗效柳子厚,瑯瑯可誦,其序事之文亦甚謹嚴。自孟堅而下逮六朝人,擷其菁英,入其奧窔”[1]610,但對汪中“詆宋人為不足學”及方苞“謂東漢以后之文為衰,必胎息《左》、《史》,具體韓、歐,始可為古文”[1]610的看法卻絕不茍同,主張對歷代散文博觀約取、兼收并蓄,摒棄門戶之見。至道光六年(1826年)左右朱彬通過陸繼輅友人薛畫水得觀陸氏所編《七家文鈔》⑧,得知陸氏亦治古文,于是讀其文集,認為其“與姚、劉諸君子相類似”,將其與姚鼐、劉大櫆等桐城派名家相提并論,并對其寄予厚望,“由是而之焉,歸、方不足多也”[1]610,認為其繼續努力當可追攀歸有光、方苞兩家。此外朱彬還對治經學者疏于研習古文的現象頗有微詞,信中稱“斯道之難成,久矣!劉古塘云:‘人皆可以為堯、舜,而不可以為班、馬。’此言至妄,而實有至理。某求友于天下,方今稽經諏古以及六書九數之學,上掩古人者多矣,而成學治古文者實鮮。豈材固不可以強而有邪,抑劉君之言信而有征也。”[1]610他感嘆樸學家在稽經諏古、鉆研六書九數方面固然有超越前人之處,但“成學治古文者實鮮”,繼而發出“豈材固不可以強而有邪,抑劉君之言信而有征也”的疑問,既一針見血地指出樸學家學術成就的局限與不足,又以身作則,終身研治古文并倡導樸學家重視古文以繁榮創作。無怪乎汪中亦稱贊其在古文上的實績:“治經者固多,文章則無作者,故君于文用力尤深。”[8]后來曾國荃為朱彬《游道堂集》作序,肯定朱彬“工于文”,符合實際,確非諛辭。在信末朱彬還說“某衰老無似,唯好古文之心孜孜弗怠”[1]610,并向繼輅索求其《崇百藥齋文集》及姚鼐所編《古文辭類纂》。可見其研習古文之熱情自少至老,始終不減。
注釋:
① 詳見支偉成著《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岳麓書社1998年版)第106頁。
② 朱慶裴編纂《朱彬先生年譜》,中國科學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
③ 詳見筆者拙文《〈寶應朱氏世代事略〉〈朱彬先生年譜〉指瑕》(《阜陽師范學院學報》2017年第4期)第66―70頁。
④ 詳見藍瑤《朱彬交游考述》(《文教資料》2007年3月號上旬刊)第73―75頁。
⑤ 詳見藍瑤《朱彬〈禮記訓纂〉研究》(南京師范大學 2007年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碩士論文)第6―10頁。
⑥ 分別為《跋逍遙館漫鈔》《蘭言集序》《宗老南樓先生詩序》《葉子云詩序》,見《游道堂集》卷二。
⑦ 詳見朱珪《知足齋文集》卷五《光祿寺卿范君墓志銘》(《清代詩文集匯編》第 376冊)第710頁。
⑧ 七家分別為劉大櫆、張惠言、惲敬、方苞、姚鼐、朱仕倫、彭績。
[1] 朱彬.游道堂集[G]//清代詩文集匯編:第43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 朱彬.白田風雅[G]//揚州文庫:第82冊.揚州:廣陵書社,2015.
[3] 朱為弼.蕉聲館文集[G]//清代詩文集匯編:第50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4] 汪中.新編汪中集[M].田漢云,點校.揚州:廣陵書社,2005:13.
[5] 朱珪.知足齋文集[G]//清代詩文集匯編:第37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6] 吳瑭.溫病條辨[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3.
[7] 李劉坤.吳鞠通醫學全書[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135.
[8] 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M].長沙:岳麓書社,1998: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