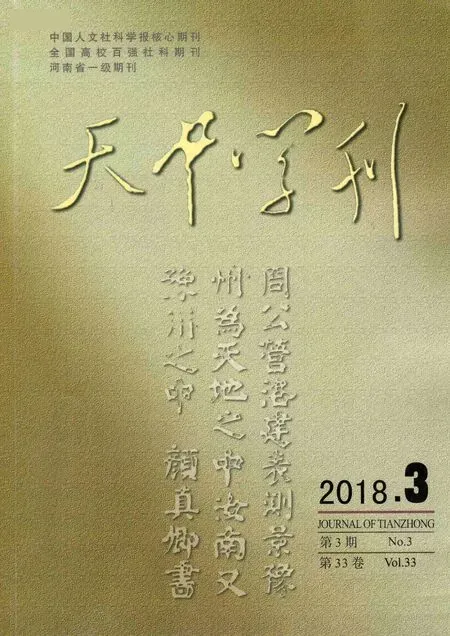媒體與政治:1916年“偉人索款”風(fēng)波論析
李 喆
(河北師范大學(xué) 歷史文化學(xué)院,河北 石家莊 050024)
1916年8月到1917年6月通常被稱作“共和復(fù)活”時(shí)期。與民國初年類似,此一時(shí)期在政治上實(shí)行議會(huì)、政黨體制。然而,“多黨制”架構(gòu)下,前國民黨人與前進(jìn)步黨人仍無法“共存立”,相互間沖突不斷,爭(zhēng)端迭起。1916年末,孫中山等人以償還討袁起義中的欠債為由向當(dāng)局請(qǐng)款。該消息傳出后,前進(jìn)步黨人利用所屬機(jī)關(guān)報(bào),持續(xù)對(duì)“偉人索款”加以鼓噪、發(fā)揮、指摘,而國民黨系機(jī)關(guān)報(bào)則進(jìn)行澄清與回?fù)簦瑑煞焦餐鲗?dǎo)了一場(chǎng)輿論層面的風(fēng)波,持續(xù)近三月之久①。本文嘗試梳理該事件的前后經(jīng)過,解析各方言論背后的意圖,希望通過此番考察,展現(xiàn)當(dāng)時(shí)報(bào)紙媒體在“黨爭(zhēng)”中的角色,并以此為出發(fā)點(diǎn),進(jìn)一步認(rèn)識(shí)特定時(shí)期的政治生態(tài)。
一、護(hù)國之役結(jié)束后的黨派與黨報(bào)
1916年6月袁世凱亡故后,北京政府與反袁各派達(dá)成妥協(xié),此前遭袁氏推倒的舊國會(huì)、舊約法均告恢復(fù),政治復(fù)入“共和民主”之軌。民國二年被禁絕的政黨此時(shí)亦逐漸復(fù)蘇:原進(jìn)步黨演化為“研究系”,并再度成為北洋政府的支持者;原國民黨則分化為若干黨團(tuán),步調(diào)雖難一致,但基本仍屬同一陣營,尤其在面對(duì)研究系時(shí),各政團(tuán)尤能“表現(xiàn)一致、協(xié)同戰(zhàn)斗”[1]。總之,盡管各黨團(tuán)在實(shí)際斗爭(zhēng)中關(guān)系復(fù)雜,但兩方對(duì)壘的總體態(tài)勢(shì)仍然存在。而這種對(duì)峙與沖突同樣體現(xiàn)在輿論層面。
自清末以來,隨著西方技術(shù)、文化的傳入,報(bào)紙這一大眾媒介迅速發(fā)展,其在政治宣傳、群眾動(dòng)員、社會(huì)整合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顯。各黨派無不自覺地將辦報(bào)作為其政治活動(dòng)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回顧1912年到1916年的歷史,“歷次重大政治事件,都伴隨著激烈且錯(cuò)綜復(fù)雜的輿論斗爭(zhēng)”。特別是在護(hù)國之役中,進(jìn)步黨、國民黨二派報(bào)紙因政治目標(biāo)的重合而暫時(shí)攜手,為反袁發(fā)揮了重要輿論動(dòng)員作用[2]。因此,各黨報(bào)在“共和復(fù)活”后繼續(xù)深度參與政治、展開輿論較量,實(shí)屬必然。而“偉人索款”風(fēng)波,即是其中相當(dāng)?shù)湫偷囊焕?/p>
由于資料上的缺失,當(dāng)年黨派報(bào)刊的全貌已難以確悉。這里只選取一些常見的、具有代表性的黨報(bào)來加以考察,主要有:研究系的《時(shí)事新報(bào)》(上海)、《晨鐘報(bào)》(北京)、《國民公報(bào)》(北京);國民黨系的《民國日?qǐng)?bào)》(上海)、《中華新報(bào)》(上海)。此外,天津《大公報(bào)》當(dāng)時(shí)為段祺瑞一派人士控制,其政治立場(chǎng)與研究系各報(bào)趨同,故亦作為考察對(duì)象。
二、騰說百端:“偉人索款”消息之披露與黨報(bào)交鋒
1916年11月30日,上海的研究系機(jī)關(guān)報(bào)《時(shí)事新報(bào)》率先對(duì)“偉人索款”予以報(bào)道。該報(bào)在“北京專電”中披露:“近日向政府索款者,除吳大洲一百四十萬李烈鈞五十萬已交付外,孫文以中華革命黨用費(fèi)為詞,要索二百八十萬,昨已通過國務(wù)會(huì)議,其余續(xù)起要索者,鈕永建九十萬,譚人鳳七十萬,大抵皆系黨費(fèi)之用,段總理雖有難色,然國務(wù)員中頗有力主照給者,政府將一一借款以應(yīng)之。”[3]這則消息透露,孫中山、鈕永建、譚人鳳等“革命偉人”當(dāng)下正在向政府索取款項(xiàng),數(shù)目達(dá)幾百萬之多。事實(shí)上,自護(hù)國之役結(jié)束后,此類請(qǐng)款事件便層出不窮:一方面,云南、廣西等省份作為舉義討袁之基地,支用巨大,不得不請(qǐng)政府接濟(jì)行政費(fèi)[4];另一方面,一些參與討袁的護(hù)國軍、民軍亦請(qǐng)款于上,用于軍隊(duì)之遣散改編。由此可知,請(qǐng)款之事大致均與護(hù)國之役的善后有關(guān)。作為參與過討袁護(hù)國的國民黨領(lǐng)袖孫中山等人以“中華革命黨用費(fèi)”為由向政府請(qǐng)款,似亦在意料之中。不過,根據(jù)《時(shí)事新報(bào)》的判斷,黨人索款與起義善后無關(guān),“大抵皆系黨費(fèi)之用”。此外,這則報(bào)道還包含兩個(gè)關(guān)鍵信息,一是索款“已通過國務(wù)會(huì)議”,為政府所答允;二是“政府將一一借款以應(yīng)之”,意味著當(dāng)局將通過向外國借債的方式酬應(yīng)偉人。
《時(shí)事新報(bào)》刊出“偉人索款”消息后,與國民黨對(duì)立的各派報(bào)紙紛紛跟進(jìn)報(bào)道,并加以評(píng)論。在“索款”的進(jìn)展問題上,研究系各報(bào)均稱“索款”已為政府通過,即將付款。說法上略有不同的是《大公報(bào)》。該報(bào)指出,政府方面對(duì)于索款并“無所謂通過”,而是要先核查黨人索款之用途,再定準(zhǔn)駁。但隨即又分析說,革命黨人的籌款多在海外,政府進(jìn)行核實(shí)的難度很大,故“孫中山果然開出報(bào)冊(cè),當(dāng)局?jǐn)酂o不予核銷之理”[3]。可見其仍將索款通過視作必然。
此外,“借外債付索款”更成為各報(bào)議論的焦點(diǎn)。北京《晨鐘報(bào)》代“小民”立言,對(duì)索款增加國家負(fù)債與民眾負(fù)擔(dān)頗感激憤:“此數(shù)百萬鉅款從何籌得?計(jì)惟有乞命于外債,然外債仍歸小民負(fù)擔(dān)。嗚呼!小民誠無樂乎!有此革命與此革命偉人矣!”[5]而同一天的《時(shí)事新報(bào)》亦發(fā)表評(píng)論:“借款未成,而索款者已紛至……嗚呼!如之何而不受外人監(jiān)督耶!”[6]當(dāng)時(shí)中國在向列強(qiáng)借款時(shí)往往要給予對(duì)方部分監(jiān)督財(cái)政之權(quán),故該報(bào)根據(jù)“借債付款”之說,將“偉人索款”與主權(quán)受損相聯(lián)系。至于“索款用作黨費(fèi)”,《大公報(bào)》解釋這與前國民黨人組織“大黨”的秘密籌劃有關(guān):“外間盛傳某派所以紛紛索款之故,實(shí)以組織大黨之計(jì)劃暗中進(jìn)行甚力,不日即將揭曉,即有黨不能無黨費(fèi),故若是其急急也。”[7]
總的來看,“偉人索款”披露之初,圍繞其進(jìn)展、酬應(yīng)方式以及真實(shí)用途,與國民黨對(duì)立的各派機(jī)關(guān)報(bào)進(jìn)行了密集而又類似的報(bào)道。略加考察可知,此類報(bào)道一般都包含“大抵”“盛傳”等限定詞,卻又往往對(duì)其消息來源只字不提,更沒有列舉可靠的證據(jù)來加以證明,這就說明,有關(guān)報(bào)道不過是一種主觀推測(cè)而已。問題的關(guān)鍵在于,以上各報(bào)何以必欲對(duì)“索款”事件作出如此揣測(cè)呢?不難看出,所謂“索款已為政府答允,即將付款”,不過是為了渲染事態(tài)的緊迫性,激促公眾對(duì)該事件作出反應(yīng);而對(duì)“借債付款”的強(qiáng)調(diào),對(duì)“索款”導(dǎo)致“監(jiān)督財(cái)政”之惡果的鼓噪,無疑是要加罪于國民黨人,引發(fā)公眾惡感;至于判斷“偉人索款”將用作“黨費(fèi)”,則在根本上否定了其要求的正當(dāng)性。有國民黨報(bào)紙對(duì)此評(píng)論說:“近日京滬各報(bào)紛紛登載各偉人要求鉅款……而謾指為黨費(fèi)之用,將欲以墮民黨之信用,起人民之惡感,其用意實(shí)別有所在也。”[8]
面對(duì)各報(bào)的種種騰說,國民黨方面不得不作出應(yīng)對(duì)。《民國日?qǐng)?bào)》首先駁斥了“索款以造黨”之說,指出孫中山已宣言“不入政界,專心從事實(shí)業(yè)”,所謂的“造黨”計(jì)劃并不存在[9]。該報(bào)還透露,“二次革命”后,孫中山在海外堅(jiān)持“倒袁”,所籌經(jīng)費(fèi)多數(shù)屬于借款,故孫氏此次向政府請(qǐng)款,實(shí)際上也是為了還債。隨后,上海《中華新報(bào)》主筆吳稚暉,更與《時(shí)事新報(bào)》的張君勱展開了直接交鋒。吳氏批評(píng)張君勱對(duì)“偉人索款”的評(píng)議過于離奇,強(qiáng)調(diào)報(bào)人不應(yīng)濫用“有聞則述”之權(quán)力,以“有改無勉”為借口任意刊布消息[10]。經(jīng)過論戰(zhàn),張君勱最終承認(rèn)了之前一些說法的失實(shí),并一度暫停了對(duì)“偉人索款”的評(píng)論。
此外,《中華新報(bào)》還特別刊文,對(duì)原國民黨人請(qǐng)款之正當(dāng)性予以闡發(fā)。該文論道,袁世凱帝制自為,各地革命黨人紛起舉事,“雖或以潰敗或以破散,無甚赫赫之績(jī)”,但起到了“牽制敵兵,挫喪賊焰”的作用,給予護(hù)國軍至大之助力。假如無民軍之響應(yīng),西南之護(hù)國軍“未必其有成功也,即成功亦未必若是之速也”。因此,原國民黨人對(duì)于恢復(fù)共和的貢獻(xiàn)是不容忽視的,而所有因舉事所耗之款,理應(yīng)由國家撥付。該報(bào)最后表示,希望外界能“一本其良心上之評(píng)判,而無徒為不知痛癢之言也”[8]。
應(yīng)當(dāng)說,《中華新報(bào)》上述言論是較為坦誠的,它并未回避本派在討袁護(hù)國中的實(shí)際地位。受限于自身之實(shí)力,革命黨人的討袁行動(dòng)多以暗殺以及小規(guī)模起義為主,有時(shí)甚至需借助地方上的會(huì)黨、幫會(huì)勢(shì)力[11],相對(duì)于擁有正規(guī)軍和數(shù)省根據(jù)地的護(hù)國軍而言,革命黨并不被認(rèn)為是討袁的主力②。既如此,對(duì)于恢復(fù)共和并不起主導(dǎo)作用的革命黨人,何能向政府索取幾百萬巨款呢?以上情況成為該派在解釋請(qǐng)款時(shí)所必須面對(duì)的現(xiàn)實(shí)困境,同時(shí)也隱含著時(shí)人對(duì)于護(hù)國之役中各方表現(xiàn)的真實(shí)看法。
從實(shí)際情況看,盡管國民黨方面對(duì)于“索款”一事進(jìn)行了全面的澄清與反駁,但卻未能在總體上遏制對(duì)立各報(bào)的鼓噪。以《晨鐘報(bào)》《大公報(bào)》為代表的京津地區(qū)報(bào)紙,仍舊不遺余力地對(duì)“偉人索款”加以指摘。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媒體在其后續(xù)報(bào)道中,還善于運(yùn)用多種形式來鼓噪此事。如《大公報(bào)》就刊登了一通所謂“皖省公民抗阻偉人索款”的電文[12],以此來體現(xiàn)“民意”;至于《晨鐘報(bào)》,則專門轉(zhuǎn)述了《英文京報(bào)》對(duì)索款事件的批評(píng)言論[13]。這些所謂的“公民來電”與“外人評(píng)論”,都帶有某種“公論”色彩,以此來凸顯黨人索款的“不得人心”,顯然更具宣傳效力。
三、枝節(jié)橫生:當(dāng)事方發(fā)聲與各黨報(bào)之指摘
經(jīng)過各報(bào)的持續(xù)報(bào)道,“偉人索款”迅速引起各界關(guān)注。國會(huì)方面,議員紛紛向政府提出質(zhì)問,要求立即公布“偉人索款”的相關(guān)情況。據(jù)筆者統(tǒng)計(jì),相關(guān)質(zhì)問共有6起,“有于孫文之外兼問鈕、譚、吳、諸人者,有專問孫文之事者”。12月16日,政府作出簡(jiǎn)要“答覆”,稱確曾收到孫中山請(qǐng)款270萬之來函,其名義為“清償債務(wù)”,也就是償還為運(yùn)動(dòng)討袁所借外債。不過,政府方面并未答允孫氏之請(qǐng),而是致函其人,要求提供借款、用款的相關(guān)憑證[14]。
顯然,當(dāng)局的這一“答覆”構(gòu)成了對(duì)各報(bào)相關(guān)說法的否定,這是研究系方面所不能接受的。《晨鐘報(bào)》發(fā)表評(píng)論稱,政府“答覆”唯獨(dú)對(duì)孫中山一人的情況作出說明,這足以證明“孫氏以外之人(如鈕、譚、吳等)所要索者確已照付也”。隨后,該報(bào)又刊載了一則駭人聽聞的消息:“昨得確實(shí)消息,孫、譚、鈕三人所索之?dāng)?shù),公府已密飭煙酒公賣局總辦鈕傳善迅速設(shè)法撥付二百萬,鈕奉令即暗中分飭各省分局繳款矣……則前日之答覆全屬誑語。”[15]這則報(bào)道否定了政府“答覆”的真實(shí)性,宣稱當(dāng)局通過秘密途徑酬應(yīng)黨人。緣此而進(jìn),《晨鐘報(bào)》更對(duì)政府方面大加責(zé)難,聲言要追究當(dāng)局“虧空公帑”之責(zé)。隨后,《大公報(bào)》《時(shí)事新報(bào)》也相繼刊載了完全一致的內(nèi)容。
不難看出,以上各報(bào)自報(bào)道索款事件以來,便一直在其進(jìn)展問題上大做文章,乃至宣稱有暗中撥款一事。然而,政府方面究竟有無撥付黨人請(qǐng)款之舉呢?這一點(diǎn)大致可從孫中山等人的函件中找到答案。孫中山于1916年9月委派廖仲愷赴京交涉請(qǐng)款,其中一部分用以償還海外助款之華僑。此后,孫氏多次向華僑通報(bào)請(qǐng)款進(jìn)程。1917年1月初,他在回函中提到:“現(xiàn)在交涉償還軍債之件,已經(jīng)閣議許可,而外間不察者,每有反對(duì),尚未決定妥當(dāng),盡力與政府磋商。”[16]3可見請(qǐng)款一事遭遇阻力,仍在磋商之中。直到當(dāng)年4月,孫中山在給華僑徐統(tǒng)雄的信中仍表示:“〈寄呈〉總統(tǒng)、總理、參眾院呈文一件,均已收到。如此辦法,于還債前途,或少有裨益。廖君仲愷尚仍在京守候,若稍有眉目,當(dāng)即布聞。”[16]24徐統(tǒng)雄可能是在請(qǐng)款問題上有一些變通辦法,故向政府呈文說明。而孫中山在肯定其辦法“于還債前途,或少有裨益”的同時(shí),也道出了請(qǐng)款尚未有眉目的實(shí)情。值得注意的是,自當(dāng)年2月以來,由于堅(jiān)定反對(duì)中國對(duì)德宣戰(zhàn),孫中山等與奉行參戰(zhàn)政策的段祺瑞政府已漸入對(duì)抗?fàn)顟B(tài)。在這種情形下,孫中山等事實(shí)上已不大可能得到當(dāng)局的撥款。5月,國會(huì)未能通過段政府的參戰(zhàn)案,政潮隨即爆發(fā),結(jié)果是南北再次分裂,孫中山等南下“護(hù)法”。總之,請(qǐng)款未能撥付的可能性極大③,《晨鐘報(bào)》的有關(guān)報(bào)道當(dāng)屬無稽之談。
繼政府作出“答覆”以后,孫中山本人亦公開發(fā)聲。12月22日,孫氏在國民黨各機(jī)關(guān)報(bào)上發(fā)表《致參眾兩院議員書》,就“倒袁經(jīng)費(fèi)”的籌借、使用及未來的清償問題一一作出說明。關(guān)于籌借問題,自“二次革命”失敗流亡后,為籌集經(jīng)費(fèi)“推翻專制”,孫中山分別向華僑、日商借債一百七十萬元和一百萬元,同時(shí)發(fā)給“證約”,承諾必為償還。他特別指出:“所借華僑之款,為埠以百計(jì),皆有證據(jù)可稽;其日本商人之款,今亦無從秘密,可任調(diào)查。”關(guān)于借款的使用,孫中山羅列了中華革命黨的各項(xiàng)討袁軍事,指出有關(guān)活動(dòng)大致均由借款資助:“凡此聯(lián)絡(luò)、發(fā)難、維持之費(fèi),及解散費(fèi)之大部分,均由籌集之款以支持。一切出入,井然可稽。”至于未來的償還問題,孫中山表示仍會(huì)接受政府監(jiān)督:“償還之際,政府自有稽核之權(quán),抑無俟辯矣。”[17]
孫中山本人的發(fā)聲,可謂是對(duì)外界種種傳言的有力回應(yīng)。《晨鐘報(bào)》隨即于 12月 27日、28日發(fā)表長(zhǎng)篇評(píng)論,對(duì)孫氏“自辨書”大加指摘,并最終羅列了五點(diǎn)反對(duì)請(qǐng)款的理由:“吾人期期反對(duì)孫氏之索此巨款者也,語其理由,第一孫氏是否曾因革命而舉債;第二孫氏所舉之債是否涓滴投諸革命事業(yè)而非供其個(gè)人之浪費(fèi);第三使彼得如愿相償,是否用以轉(zhuǎn)償華僑及日人而非移為他用;第四,因革命受損失者,不僅孫氏一人,不僅海外華僑,此端一開人人皆得援例要索,政府非有銅山金穴,何以應(yīng)之;第五,今當(dāng)財(cái)政極困之秋,日日借債度日,安可突增國庫不合法之支出,橫加國民不應(yīng)擔(dān)之擔(dān)負(fù)?”[18]不難發(fā)現(xiàn),以上諸理由中,前三點(diǎn)正是對(duì)孫中山“倒袁經(jīng)費(fèi)”的籌借、使用以及未來的清償過程的質(zhì)疑。就其質(zhì)疑本身來說,大體上言之成理,甚至在“移為他用”一點(diǎn)上,孫中山等人也并非毫無這方面的考慮④。然而,問題的關(guān)鍵在于,孫氏在其《致議員書》中的表態(tài)已使這三點(diǎn)質(zhì)疑失其必要。無論是華僑借款還是日商借款,“皆有證據(jù)可稽”“可任調(diào)查”;而在這些款項(xiàng)的使用上,同樣是“一切出入,井然可稽”;至于相關(guān)債務(wù)的最終清償,孫中山亦聲明政府有監(jiān)督之權(quán)。總之,在孫中山已公開確認(rèn)“討袁用款”的各環(huán)節(jié)皆有憑證,愿接受政府監(jiān)督的情況下,《晨鐘報(bào)》至多只能要求政府嚴(yán)格稽核而已。其所列舉的三點(diǎn)質(zhì)疑,顯然沒有任何意義,某種程度上更像是一種惡意指摘。
關(guān)于第四點(diǎn)理由,即一旦答允孫氏之請(qǐng),那么其他情況類似者將紛起效仿,政府必然左支右絀,暫不論此種推測(cè)是否有出現(xiàn)可能,需說明的是,最早以“清償討袁借款”為由請(qǐng)款的,并非孫中山。1916年3月,岑春煊等為接濟(jì)護(hù)國軍、運(yùn)動(dòng)各方討袁而向日商借款100萬元。其后護(hù)國軍統(tǒng)帥機(jī)構(gòu)軍務(wù)院成立,直接提用了其中的 50余萬,岑氏遂于7月呈請(qǐng)政府核銷此款,得到了當(dāng)局的批準(zhǔn)[19]。孫中山等人之請(qǐng)款始于當(dāng)年9月,可見其恰為援例者,而非造端者。至于第五點(diǎn)理由,完全無視孫中山因公請(qǐng)款的性質(zhì),強(qiáng)行將其判定為“不合法”,顯然難以成立。
四、以謠喙對(duì)謠喙:“僑商聲明”與“研究會(huì)索款”
孫中山《致議員書》發(fā)表后不久,政府方面又對(duì)其他黨人之“索款”作出說明,指出鈕永建請(qǐng)償革命用費(fèi)47萬元,已令其將憑證造冊(cè)開單,等待稽核。至于譚人鳳,其人只是請(qǐng)當(dāng)局發(fā)給所持公債票之本息,并無“索款”之事[20]。至此,“偉人索款”的原委與進(jìn)展已經(jīng)比較清楚。然而,進(jìn)入1917年1月,研究系各報(bào)對(duì)該事件仍間有議論。如《晨鐘報(bào)》借最近傳出的柏文蔚請(qǐng)款一事,宣稱“索款”已成國民黨人之“傳染病”:“一傳十十傳百,傳染復(fù)傳染,將來繼起來索者復(fù)不知尚有幾何也。”[21]又如,《時(shí)事新報(bào)》評(píng)論,國家如若償還革命費(fèi),則革命成為一種“企業(yè)”,革命捐款成為一種“股票”,“而國家自此無寧日矣”[22]。一若革命者之動(dòng)機(jī)本與“逐利”的投機(jī)者無異。緊隨其后,各報(bào)又接連刊載了所謂的“僑商聲明”,遂使“索款”事件再興波瀾。
1月28日,《晨鐘報(bào)》刊布消息說,印尼梭拉巴查(即泗水)中華商會(huì)來電,指出此前曾向?qū)O中山助款220萬,“實(shí)為幫助政府起見,未嘗望其償還”[23],請(qǐng)政府拒絕孫氏請(qǐng)款要求。之后,《國民公報(bào)》亦報(bào)道稱,有印尼爪哇、泗水地區(qū)的華僑來電,表示前交孫中山之款純屬樂輸,為的是“協(xié)助政府”[24]。此類“僑商聲明”一出,中外各報(bào)紛紛予以轉(zhuǎn)載。《晨鐘報(bào)》隨后發(fā)表評(píng)論,再次否定孫中山請(qǐng)款的正當(dāng)性[25]。
“僑商聲明”的出現(xiàn),等于證明黨人之請(qǐng)款完全是假托名義、謀攫私利,其可能造成的影響十分惡劣。因此,國民黨方面迅速通過各報(bào)予以駁斥。孫中山首先發(fā)表通電,表示自己只收到過由泗水當(dāng)?shù)攸h人劉亞泗等匯回的1萬余元,根本未見 220萬之巨款[26]。隨后,《民國日?qǐng)?bào)》翻譯并刊載了中華革命黨人孫君的一份英文聲明,孫君聲稱,革命黨在泗水所籌之一萬余元正是自己所捐,“已將為擁護(hù)共和所用款項(xiàng)開列詳細(xì)清單,送呈政府”[27]。不久,該報(bào)又刊載了華僑徐瑞霖致泗水中華商會(huì)一函,徐氏在信中頗為驚異地表示,泗水商會(huì)長(zhǎng)期抵制孫中山及其黨人的革命活動(dòng),從不肯“為絲毫之助”,何此次忽然慷慨助款220萬之巨?《民國日?qǐng)?bào)》最后論斷,所謂的“僑商聲明”乃海外“帝制黨”在研究系的唆使下所發(fā)[28]。
眾所周知,中華革命黨各項(xiàng)經(jīng)費(fèi)的籌集是在海外多個(gè)地區(qū)分多次開展的,各個(gè)地區(qū)捐資總額不等,大多不超過10萬元,一地捐輸220萬之巨款顯然極為反常。此外,根據(jù)曾到南洋籌集經(jīng)費(fèi)的革命黨人羅翼群回憶,泗水的籌款活動(dòng)遭到過當(dāng)?shù)刂腥A商會(huì)的干擾,很多已認(rèn)募“革命債券”的華僑最終未能繳款,致使所籌數(shù)目由30余萬銳減到10萬。羅氏還指出,泗水商會(huì)長(zhǎng)期為康、梁“保皇黨”勢(shì)力所控制[29]。據(jù)此而論,泗水中華商會(huì)確屬與革命黨對(duì)立的團(tuán)體,該會(huì)所發(fā)之聲明顯系誣捏,背后的策劃者很可能正是以梁?jiǎn)⒊瑸槭椎难芯肯怠V档米⒁獾氖牵皟S商聲明”出現(xiàn)時(shí),正值政府收到孫中山所報(bào)送的請(qǐng)款清單之際[30],研究系各報(bào)對(duì)此的種種鼓噪,似乎更有誤導(dǎo)輿論,施壓于當(dāng)局,從而阻止撥款的意圖。
不難發(fā)現(xiàn),自各派報(bào)紙圍繞“偉人索款”大起風(fēng)波以來,國民黨系機(jī)關(guān)報(bào)一般只進(jìn)行回應(yīng)與解釋,似乎處于一種“守勢(shì)”。不過,此種情況亦非絕對(duì)。1917年1月6日,研究系領(lǐng)袖梁?jiǎn)⒊M(jìn)京與各方商榷政見,一時(shí)頗為各方所矚目。1月底,《民國日?qǐng)?bào)》等突然披露了“研究會(huì)索款”的消息,大意謂,研究系在此前的參議院改選中大舉賄選,耗去巨額款項(xiàng),為彌補(bǔ)虧空,梁?jiǎn)⒊刖┖罅⒓聪蜇?cái)政總長(zhǎng)陳錦濤索取500萬元以應(yīng)急需[31]。緊接著,《民國日?qǐng)?bào)》連續(xù)發(fā)表三篇時(shí)評(píng),指責(zé)研究系置國事窮困于不顧,勒索巨款。該報(bào)提醒當(dāng)局,黨人之正當(dāng)請(qǐng)款尚不撥發(fā),遑論研究系之勒索乎?值得注意的是,不久后國民黨系各報(bào)在這件事上的報(bào)道又有所變化,不僅索款數(shù)額降為200萬,且索款用途也變成了“造黨費(fèi)”[32]。
顯然,在缺乏直接證據(jù)和可靠的消息來源,且前后報(bào)道又不一致的情況下,“研究系索款”之說實(shí)難憑信。甚至是同屬國民黨陣營的《中華新報(bào)》亦表示,對(duì)于此類傳聞“不敢信其果確”[33]。大體而言,以上報(bào)道應(yīng)該只是該派的一種宣傳。前已述及,研究系報(bào)紙長(zhǎng)期圍繞黨人請(qǐng)款一事渲染、發(fā)揮,乃至策劃了無異于誣捏的“僑商通電”,不徒“是非幾不能辨”,更致黨人形象失墜,故《民國日?qǐng)?bào)》等回以“研究系索款”之說,雖有“以謠喙對(duì)謠喙”之嫌,但亦是出于抵消負(fù)面影響、挽回自身形象的無奈之舉。
五、結(jié)語
綜上所述,原國民黨領(lǐng)袖請(qǐng)款一事所引發(fā)的風(fēng)波,實(shí)質(zhì)是對(duì)立黨派之間為達(dá)到各自政治意圖而展開的一場(chǎng)輿論層面的較量。就請(qǐng)款本身而言,討袁用費(fèi)的因公性質(zhì),加之政府批準(zhǔn)岑春煊護(hù)國債款的先例,都表明國民黨方面所請(qǐng)的正當(dāng)性。然而,研究系各報(bào)卻圍繞此事大做文章,始則在其用途、進(jìn)展以及酬應(yīng)方式上加以發(fā)揮,繼則對(duì)孫中山之自辨通電橫加指摘,最后更刊登不實(shí)的“僑商聲明”混淆輿論。凡此皆體現(xiàn)出該派言論背后的政治意圖,而與所謂“具有憂患意識(shí)的知識(shí)分子的不滿情緒”無關(guān)⑤。而就國民黨系各報(bào)來說,其回應(yīng)與反駁亦出于維護(hù)本派形象的考慮,至于刊載“研究會(huì)索款”,還以其人之道,則表明在當(dāng)時(shí)的政治環(huán)境下,無論何派均難獨(dú)善其身。
根本而言,此番風(fēng)波的出現(xiàn)與當(dāng)時(shí)整體的政治生態(tài)有關(guān)。民國前期,中國通過革命迅速終結(jié)了王朝體制,建立起共和體制。從政治格局的角度看,此即一種由“一元”到“多元”的轉(zhuǎn)換。在此種“多元化”的政治架構(gòu)下,各政黨之間本應(yīng)圍繞政見展開競(jìng)逐,然由于種種原因,當(dāng)時(shí)的黨派爭(zhēng)競(jìng)逐漸淪為利益之爭(zhēng)、意氣之爭(zhēng),造就了一種惡質(zhì)的政治生態(tài)⑥。“偉人索款”風(fēng)波中各派報(bào)紙所表現(xiàn)出的無原則,即是此種政治生態(tài)的產(chǎn)物。百年前中國一度建立起的多黨制最終為國人所厭棄,某種程度上也與這種政治生態(tài)的反復(fù)上演、長(zhǎng)期持續(xù)、無法自我改良有關(guān)。
注釋:
① 以往研究對(duì)孫中山請(qǐng)款一事有所述及,但似乎并未注意到各派黨報(bào)在該事件上的大量報(bào)道與評(píng)論。有關(guān)論述見熊秋良《中華革命黨的財(cái)政管窺》(《社會(huì)科學(xué)研究》2004年第3期)。
② 據(jù)記述,討袁時(shí)期,孫中山領(lǐng)導(dǎo)的中華革命軍在海外華僑中的威望遠(yuǎn)遜于護(hù)國軍,導(dǎo)致革命黨的海外籌款活動(dòng)遭遇困境。國內(nèi)人民的觀感應(yīng)與華僑相去不遠(yuǎn)。參見羅翼群《有關(guān)中華革命黨活動(dòng)之回憶》(《廣東文史資料:孫中山史料專輯》,廣東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4頁)。
③ 現(xiàn)有研究對(duì)請(qǐng)款是否撥付的考察存在舛誤。《中華革命黨的財(cái)政管窺》等文完全根據(jù)孫中山在1917年8月的兩件信函證明請(qǐng)款未能撥付。查《孫中山全集》中兩函之原文,均提到“日內(nèi)由廖仲愷君赴京,與政府面商”,可知此兩函完成時(shí)孫中山尚未派人赴京請(qǐng)款,則其寫作年份不可能為1917年。事實(shí)上,此兩函之原件只標(biāo)有月、日信息,其年份本是孫中山文集的編者所加。據(jù)此而論,此兩函的真實(shí)寫作時(shí)間應(yīng)糾正為1916年8月。有關(guān)研究在史料年代研判錯(cuò)誤的情況下所作的考證當(dāng)然也是無效的。參見孫中山《致曾允明等函兩件》(《孫中山全集》第4卷,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134、135頁)。
④ 孫中山的有關(guān)信函透露,有華僑曾建議孫將請(qǐng)得款項(xiàng)自留,用以籌辦本黨的金融機(jī)構(gòu)。參見孫中山《復(fù)徐統(tǒng)雄函》(《孫中山全集》第 4卷,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24頁)。
⑤ 有研究認(rèn)為,《晨鐘報(bào)》對(duì)索款的批判主要與國家財(cái)政困厄的現(xiàn)實(shí)背景有關(guān),該報(bào)此舉體現(xiàn)了報(bào)人的“憂患意識(shí)”。參見李曉蘭《審視與批判:〈晨鐘報(bào)〉視域中的民初社會(huì)》(2011年上海大學(xué)博士學(xué)位論文)。顯而易見,此種說法忽視了《晨鐘報(bào)》言論背后的政治意圖。
⑥ 參見馬建標(biāo)《袁世凱與民初“黨爭(zhēng)”》(《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3期,第127頁)。
[1] 沈太閑.略述國會(huì)恢復(fù)和非常國會(huì)的情況[M]//文史資料選輯第82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195.
[2] 陳忠純.民初的媒體與政治:1912―1916年政黨報(bào)刊與政爭(zhēng)[M].廈門:廈門大學(xué)出版社,2011:253–264.
[3] 北京專電[N].時(shí)事新報(bào),1916-11-30(2).
[4] 云南急電索款[N].晨鐘報(bào),1916-12-07(2).
[5] 索款[N].晨鐘報(bào),1916-12-01(3).
[6] 索款與借款[N].時(shí)事新報(bào),1916-12-01(3).
[7] 索款與造黨[N].大公報(bào),1916-12-02(6).
[8] 我之偉人索款觀[N].中華新報(bào),1916-12-03(3).
[9] 償還孫先生革命用款之真相[N].民國日?qǐng)?bào),1916-12-03(3).
[10] 稚.答張君勱先生[N].中華新報(bào),1916-12-06(2).
[11] 字林報(bào)之北京政聞[N].申報(bào),1916-12-05(3).
[12] 皖公民亦反對(duì)黨人索款[N].大公報(bào),1916-12-06(2).
[13] 西報(bào)之偉人索款觀[N].晨鐘報(bào),1916-12-19(3).
[14] 政府答覆孫文索款之真相[N].晨鐘報(bào),1916-12-17(2).
[15] 索款者得了二百萬[N].晨鐘報(bào),1916-12-18(2).
[16] 孫中山全集:第4卷[M].北京:中華書局,2006.
[17] 孫中山先生致參眾兩院議員書[N].民國日?qǐng)?bào),1916-12-22(2).
[18] 再評(píng)孫文致國會(huì)議員書[N].晨鐘報(bào),1916-12-28(2).
[19] 張總長(zhǎng)與軍務(wù)院借款之關(guān)系[N].中華新報(bào),1917-02-22(6).
[20] 政府將答覆議會(huì)關(guān)于偉人索款之質(zhì)問[N].大公報(bào),1917-01-04(2).
[21] 偉人索款之傳染病[N].晨鐘報(bào),1917-01-13(3).
[22] 孫中山索款問題[N].時(shí)事新報(bào),1917-01-29(6).
[23] 華僑竟證明孫中山未曾借款[N].晨鐘報(bào),1917-01-28(3).
[24] 華僑聲明孫文并無借款[N].國民公報(bào),1917-01-30(2).
[25] 孫文何以自解耶?[N].晨鐘報(bào),1917-01-30(3).
[26] 孫中山電詰泗水商會(huì)[N].民國日?qǐng)?bào),1917-01-31(3).
[27] 孫中山友人辨正西報(bào)誤會(huì)[N].民國日?qǐng)?bào),1917-02-01(6).
[28] 反對(duì)孫中山請(qǐng)款者平心思之[N].民國日?qǐng)?bào),1917-02-06(6).
[29] 羅翼群.有過中華革命黨活動(dòng)之回憶[M]//廣東文史資料:孫中山史料專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79:75–79.
[30] 孫文索款之清單已至[N].國民公報(bào),1917-01-31(2).
[31] 梁?jiǎn)⒊儇?cái)政部[N].民國日?qǐng)?bào),1917-01-27(3).
[32] 陳瀾生受擠原因:某派索款未遂故[N].民國日?qǐng)?bào),1917-02-07(6).
[33] 某派與梁系攜手之陰謀[N].中華新報(bào),1917-02-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