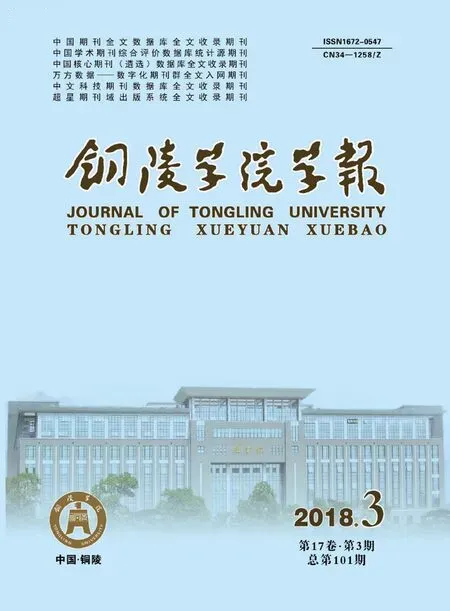論徽墨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祖曉敏 周致元
(1.安徽冶金科技職業學院,安徽 馬鞍山243001;2.安徽大學,安徽 合肥 230601)
徽墨是“文房四寶”之一,因產于徽州而得名。在徽州地區獨特的自然資源和豐富的文化資源雙重滋養下,帶著鮮明徽州印記的徽墨在墨林中獨樹一幟,成為中國墨的唯一代表。1915年,徽墨珍品——地球墨在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榮獲金質獎章。近現代以來,受到社會文化的變遷以及書寫習慣的改變等影響,徽州墨業幾經浮沉,但在一代代徽墨傳承者的努力下,千古墨脈從未斷絕。2006年,“徽墨制作工藝”申報成為我國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之一。隨著國家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力度的加大,以徽墨為代表的傳統工藝得到了有效的保護與傳承,并不斷創新,古老的工藝重新煥發出新的光彩。
一、徽墨的歷史沿革與特點
(一)興起于五代
徽州地區的制墨史最早有文獻記載:“南唐李廷珪,易水人,本姓奚,父超,唐末渡江至歙,以邑多松留居造墨,后主賜姓李,人得其墨而藏者。不下五六十年,膠敗而墨調,其堅如玉、其文如犀,寫數十幅不費一二分。”[1]五代時期,南唐的李姓皇帝耽心翰墨,對奚氏父子制墨倍加稱賞,后又招易水墨工張遇,張遇利用徽州的優質松煙、況桐?油煙制墨,將徽州墨從單純的松煙墨推向與油煙墨并舉發展的時期,全國制墨中心至此南移至徽州。穆曉天先生曾說:“制墨業的繁榮,可以說是南唐地區文化藝術繁榮的顯著標志。”[2]
(二)發展于兩宋
隨著李唐王朝漸行漸遠,大宋王朝經過初期的休養生息,王朝經濟快速發展,商業逐漸活躍,文學藝術活動日益繁榮,科舉制度影響下的讀書風氣日盛,為徽墨提供了廣闊市場,徽墨業得以蓬勃發展。正如《野獲篇》所描寫:“今徽人家傳戶習”、“新安人例工制墨”[3];《歙縣志》記載“至宋時,徽州每年以龍鳳墨千斤為貢。”[4]可見大宋政權對徽墨有著強勁的需求。《野獲篇》還寫到:“宋徽宗以蘇合油溲煙為墨,后金章宗購之,黃金一斤,才得一兩,可謂好事極矣。”[5]宋徽宗愛好翰墨,又親予研制,更促進墨業的大振。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歙州改名徽州,從此徽墨馳名天下。
(三)興盛于明清
經過長期動蕩、分裂后統一安定的明王朝經濟文化空前發展,促進了墨業更大規模生產并追求更高質量。在這樣的背景下,徽州墨業呈現出一些不同的情形:一是在原料上不同,從普遍使用“松煙”轉而使用“桐油煙”和“漆煙”制墨,由于這兩種原料既易得又價廉物美,有利于徽墨擴大生產、提高質量;二是無論在五代還是兩宋,徽墨都以進貢和滿足官府需要為主,但到了明代,雖然還有大量墨品進貢,但因社會需求量增大,徽墨生產漸漸轉以滿足市場需求為主;同時,由于市場需求的多元化,徽墨在這一時期逐漸發展成集繪畫、書法、雕刻等多種形式于一體的綜合性藝術。清初政府重視經濟的恢復發展,對漢文化采取包容政策,促進了徽墨需求市場的恢復和發展。尤其是清初幾任帝王皆崇尚漢學、才學俱佳,對書畫不僅喜愛而且有著非常深厚的造詣,這樣的社會導向,使徽墨業的昌盛順理成章。
作為徽州工藝的典型代表,徽墨用料考究,制作精細。有人贊其色質為“拈來輕,嗅來馨,磨來清”,有人描述其手感與外形為“豐肌膩理,光澤如漆”;有人贊其品質是“十年如石,一點如漆”。而徽墨之所以享譽文壇藝苑,關鍵在質量,清代制墨大師曹素功曾云:“法必師古,而創以心裁”[6]。一代代徽墨巨匠在取材用材上悉心傳承,敢于創新,成就了大批名墨,也造就了無數用墨人與造墨人相互切磋,共襄文壇盛事的佳話。
徽墨歷來是書畫家至愛的信物。古人說“有佳墨者,猶如名將之有良馬也。”[7]何薳作《墨記》時曾感慨道:“黃金易得,李墨難求。”[8]蘇軾乃大文豪,詩詞書畫無所不通,然遍用墨錠,仍最重徽墨。徽墨高手潘谷死后,蘇軾寫詩悼念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9]將潘谷與李白并列,將徽墨與詩歌并重。對制墨大師贊頌最高的,莫過于大文人董其昌,談到著名制墨大師程君房,不吝贊美之詞:“百年之后,無君房而有君房之墨;千年之后,無君房之墨而有君房之名。”[10]
二、徽墨文化傳承的要素分析
“傳統工藝美術被當代人重視,是因為其手工性中蘊含著豐富的人文價值與精神。”[11]徽墨作為一種內涵豐富、制作精湛的藝術表現形式,自嘉靖至萬歷近百年的時間是其全盛時期,“墨之在萬歷,猶詩之在盛唐”[12]不論是墨的使用價值還是藝術價值、收藏價值、市場價值都達到了高峰,這一盛況并延續至清初。這一時期,也是傳統徽文化逐漸形成并高度發展的時期。博大精深的徽文化給徽墨業的發展提供了最適宜生長的土壤。
(一)徽州宗族的就業觀念維護了徽墨制作技藝的傳承
歷史上,墨模制作工藝的存在和發展一度關系到徽墨業的存亡興衰。徽州墨業的輝煌不僅依賴于豐富的自然資源,更有賴于徽州地區發達的手工業。不僅從業者眾,而且不乏藝術造詣深厚的能工巧匠。普遍存在于村落社會中的宗族勢力是徽州手工業家族式傳承的幕后推手。徽州人歷來具有濃厚的鄉土觀念,從商授藝論鄉音為知己,視族姓為凝聚。族規家訓是徽州人用來規范族內子弟行為的法典,“士農工商,所業雖別,是皆本職;”“士農工商皆為本業”;“或于四民之事,各治一藝”[13];這些倡導“四民皆本”職業觀念的條款在徽州宗族族規家訓中屢見不鮮,平等的就業觀無疑為族中子弟自主擇業提供了廣闊天地。以歙縣虬村黃氏為例,“上而籀篆鐘鼎之古,下逮花鳥蟲魚之細,書畫篆刻,不爽毫發……子振之世其業,藝事精能不墜家學。”[14]虬村的黃氏祖祖輩輩手握刻刀,刻工技藝是他們的衣食之藝,其中的技巧秘不示人,世代家傳。同時作為宗族代言人的宗族勢力,對其藝的發揚也竭力扶持。《潭渡孝時黃氏族譜》卷4家訓載:“族人乃一本所生,彼辱則吾辱,當委曲庇履,勿使失所,切不可視為途人以添吾祖……茍有一材一藝與可以造就之子弟,則培植推薦,務俾成立。”[15]黃氏刻工在宗族前輩的言傳身教之下,一代代名匠被培養起來,著名的《程氏墨苑》和《方氏墨譜》即邀請了虬村黃氏行刻。他們將祖傳的刻工技藝發揚光大,為明清墨業的繼承與傳揚做出重要貢獻。
(二)文人制墨的濃厚風氣豐富了徽墨的文化內涵
徽州人重視教育,崇尚儒學。所謂“十戶之村,無廢誦讀”,正是徽州儒風獨茂的真實寫照。在這樣濃厚的文化氛圍中,眾多文人不僅用墨愛墨賞墨而且自身參與制墨,成為徽墨業的一大特色。《歙縣志·食貨志》中,依據制墨的目的將當時的墨家劃分為 “好事精鑒”、“文人自怡”、“市齋名世”三種類型。“好事精鑒”是指為了貽人炫能出精品、名品;“市齋名世”為了市肆售賣,或為施齋墨,“文人自怡”就是指知識分子為了“自怡”,自賞,自娛,自藏。萬歷年間的歙縣名士汪道昆、汪仲淹、汪仲嘉三人號稱“明代三汪”,他們皆學識淵博,善詩書,都曾自制墨,汪道昆自制的“千秋閣”墨,為時人所雅好。程瑤田,號一卿,是清代徽州樸學大師之一,世人少知他會造墨。姚鼐《論墨絕句》有:“我愛瑤田善論琴,博聞思復好深湛。才傳墨法三千杵,已失家財十萬金。”[16]說他用相當的代價去造好墨。《尺木堂墨品》有題跋一則:“族兄易田見古法淪沒,搜討諸家遺意,參以心裁,絕不珍奇,歸于適用。所作大小劑不下數百種,題其面曰一卿氏。海內寶一卿墨者,黃金不啻也。”可見當時“一卿”之墨難求;程瑤田提出制墨要“歸于適用”的主張,后人評價說:“在花樣形式之風已趨沒落的時候,這一主張對制墨事業起了整頓促進之功。嘉、道之后制墨的形式轉于樸素單淳,不能不說是程氏的流風所被。”[17]
(三)多種藝術門類的滋養提升了徽墨的文化品味
由于配料使用等原因,徽墨在其發展過程中逐漸從重視質地,到兼具外形。尤其到了明代,徽墨在配料上基本定型,徽墨名家為了達到最佳的經營效果,非常注意外在形式的裝飾美化,力求圖文并茂,提高文化品味和市場占有率。徽州不僅是詩理之鄉,在詩書、畫、金石篆刻等領域,技藝精湛的大師也代有人才出。《歙縣志·人物志》曾記:“吾歙書人見于志者,明方元煥,字兩江,信行人。羅文瑞,呈坎人。劉然,字季然,新安衛人,工小楷行草。羅伯符、汪昶、洪朝宷皆然派。黃尚文,字無文,工小楷行草。吳元極,篁南人,工榜書……。然如金檠齋、巴子安、程讓堂、鄭松蓮輩,皆以書名而志不載,知所遺多矣。”[18]在此列舉出的歙縣書家不僅知名者人數眾多,而且各有所長。關于歙縣的畫家,書中也有一段文字論述:“歙畫家見于志者,明鄭重,字千里。丁云鵬,字不棄。吳羽,一字廷羽,字左干,從丁南羽畫佛像,兼工山水花鳥……皆歙畫家之矯矯者,志俱未及采也。余擬有暇遍搜各畫史中之歙人,匯為一編,姑發端于此。”[19]由此可窺徽州畫壇之盛。書畫之盛為徽墨的發展提供了源源不絕的養料,為徽墨藝術的不斷突破創造了條件。著名的《程氏墨苑》和《方氏墨譜》即請丁云鵬、吳左干等知名畫家作圖,從現存世的眾多《墨譜》來看,徽墨墨模藝術已經成為當今中國美術史中的一塊瑰寶。
(四)先進的營銷理念拓展了徽墨的市場需求
徽商在主要從事鹽鐵布匹等產業的經營之外,還有一些從事徽墨、歙硯等文化產業的經營。徽州墨工和墨商往往合二為一,既是制作者、又是經營者,從描述徽州墨工及其豐富的史料中可以看出徽商在徽墨經營中的貢獻。一是徽商豐富和拓展了徽墨的題材。明清以來,徽商的足跡遍布全國,他們在從商過程中將徽州文化帶到了不同區域,同時也把不同地域的文化融匯于徽墨的制作與設計中,擴大了徽墨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客觀上促進了徽墨的普及與推廣;二是良好的政商關系促進了徽墨的生產經營。有鑒于朝廷對墨需求,整個清代的徽墨名莊都與朝廷保持著良好的關系。如歙縣曹素功,民國《歙縣志》有:“清曹圣臣,字素功,巖鎮人,能傳程、方法。康熙朝帝幸江寧,進墨,蒙賜‘紫玉光’三字。后之制墨者,皆宗之。”[20]光緒三十年,帝頒諭要求胡開文制貢墨。此后,曾國藩為胡開文書匾“胡開文墨莊”,李鴻章等當朝權貴在胡開文店定制珍藏墨。胡開文墨業在朝廷和達官貴人的庇蔭下,一路通達,在長江流域各城市遍設分號;三是徽商收藏之風對徽墨的銷售推波助瀾。徽墨的收藏,得益于名墨的難得,名流的提倡、名士的風雅以及徽商“好儒”之風。“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則賈,相代若踐更。”[21]史料如此描述收藏之盛況:“是時休歙名族乃程氏銅鼓齋、鮑氏安素軒、汪氏涵星研齋、程氏尋樂草堂,皆百年巨室,多蓄宋元書籍法帖、名墨佳硯、奇香珍藥之屬。每出一物,皆歷來賞鑒家所津津稱道者,相與展玩嘆賞,或更相辨論,龂龂不休。”[22]收藏之興刺激了人們對藝術品的追求,客觀上有利于徽墨市場的繁榮。
三、徽墨文化的傳承路徑
清末至民國時期,國家處于風雨飄搖之中,教育文化領域歷經疾風暴雨式的巨大變革,新的書寫方式逐步替代舊的書寫習慣,徽墨市場需求下降,行業經營每況愈下。新中國成立后,政府對徽墨行業進行了全面幫扶,恢復名墨市場,施行科學化管理,集中研制了一批具有時代特征的新墨。進入新世紀以來,國家高度重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工作,不斷從傳統徽文化中汲取養料,古老的徽墨在借鑒和創新中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
(一)現代學徒制是保證徽墨行業后繼有人的重要途徑
家族學徒制是傳統徽墨業培養熟練勞動力的主要方式。通常墨業作坊都是從同鄉或者親戚中挑選年輕人充當學徒,學徒期滿后合格者升為墨業的正式員工。現代學徒制將傳統學徒與現代職業教育相結合,以職業院校取代家族勢力,校企聯合招生招工,教師與師傅聯合傳授知識技能,工學交替、實崗育人。當前徽州地區的墨業企業以現代學徒制試點為契機,加強與當地職業院校的合作,開設徽墨技藝傳授班, 邀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傳承人和老一輩制墨藝人授課,同時注重提升學員的綜合素質,通過弘揚工匠精神,打造具有溫度的手工徽墨,引導更多的年輕人學習傳統工藝,愛上傳統工藝。
(二)現代營銷體系是推動徽墨行業品牌發展的有效抓手
明清時期徽墨業的經營已是登峰造極。全國同步的產品質量與價格、通暢的供銷渠道、新穎的設計包裝、良好的品牌形象,這些制勝法寶成就了大墨莊經營的輝煌。現代徽墨業一方面繼承了傳統徽墨的經營模式,在各地開設連鎖店,同時與時俱進,努力追趕時代前進的步伐。新一代徽墨商人積極探索建立以網上營銷體系為中心的電子商務系統,以胡開文墨業為代表的徽墨企業紛紛在互聯網上設立旗艦店,實現線上線下并行的銷售運行機制。消費者既能夠體驗線上銷售的便捷,同時又能在線下第一時間獲得產品的直觀體驗,在全新的現代營銷環境中,乘著互聯網的翅膀,徽州墨業又開始一次新的起航。
(三)新的消費環境是促進徽墨行業自身造血的關鍵環節
清末以來,導致徽墨市場不斷萎縮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傳統消費市場的消逝,隨著新媒體技術日新月異,電子記錄漸漸成為常態,傳統的墨錠逐漸小眾,徽墨的消費市場退守收藏以及書畫領域。當前,國家為了弘揚中華文化,進一步保護徽墨業,將書法課列入中小學的必修課程和大學選修課程,同時鼓勵墨企與書院、美院等高校廣泛開展合作,吸引更多的藝術家參與墨模的制作與設計,增強徽墨產品的時代感、觀賞性、紀念性, 開拓徽墨收藏市場,提升徽墨的收藏價值。更多依靠政府的力量,將徽墨業與徽州優質的旅游文化相融合,建立徽墨博物館,開發旅游紀念墨,在景區設置特殊景點,供游人親自體驗徽墨制作過程,在享受DIY樂趣的同時,了解和傳播徽墨文化,增強國人的文化自信。
四、結語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傳統工藝的流傳絕不只是表面的模仿,手藝的繼承、文化的沉淀、藝術的創新都是傳承的重要因子。厚重博大的徽文化孕育出名揚天下的傳統徽墨,現代徽墨的傳承與保護仍舊離不開徽文化這一廣闊的文化背景。面對市場的現實挑戰,徽州墨業必須不忘初心,堅守手工制墨的傳統,將“質量至上”奉為圭臬,同時與時俱進,挖掘內在的文化價值,不斷突破自身的局限,找準并開發潛在市場,肩負起傳承發揚徽文化的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