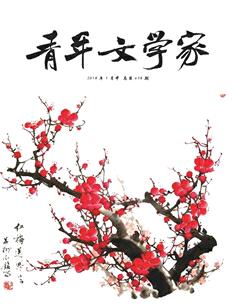淺析《左傳》行人辭令委婉風格
基金項目:沈陽師范大學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創新訓練項目:《左傳》行人辭令特色及當代價值(項目編號:20171016620092);沈陽師范大學大學生科研基金A類項目:《左傳》行人辭令之美及多元價值(項目編號:W2016048)。
摘 要:《左傳》中的行人辭令是指春秋時期各諸侯國之間外交人員進行外交活動時的言辭,因特殊的外交場合的需要,言辭中多使用比喻修辭手法,多引用《詩》、《書》中語,形成委婉含蓄的風格,呈現出鮮明的文學特色,對后世散文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關鍵詞:《左傳》;行人辭令;委婉風格
作者簡介:王秋實(1997-),沈陽師范大學文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02-0-02
《左傳》是先秦時期最重要的史學著作,也是儒家經典之一。主要記述了魯隱公元年至魯哀公二十七年間豐富多彩的歷史事件。《左傳》行人辭令是指春秋時期各諸侯國之間外交人員進行外交活動時的言辭,因特殊的外交場合的需要,行人辭令存在技巧性,言辭中多使用比喻修辭手法,多引用《詩》、《書》中語,形成委婉含蓄的風格,呈現出鮮明的文學特色,對后世散文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現詳加論述。
一、行人辭令中的比喻修辭
修辭有助于提高語言表達能力,修辭重點在于對語言的駕馭和妙用,行人辭令作為一種政治的、涉外的語體,更需要加入修辭。唐代劉知幾在《史通·惑經》中云:“春秋之世,莫不微婉其辭,隱晦其說。”[1]67所謂微婉、隱晦就是指不完全、直接地說出內心想法以及訴求,而是通過少言巧言達到意無窮的效果。而這些文辭之妙都脫離不開精彩的修辭手法,“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中的“文”就是文采、文飾的意思,也就是語言藝術性。《左傳》行人辭令中修辭的運用增強了其表現力、感染力、說服力,提升了表達的效果,正因為《左傳》行人辭令中運用了修辭,鑄成其委婉風格。辭令中最常用常見的修辭方法就是比喻。
《左傳》行人辭令中的比喻修辭,是巧妙地運用語境,將眼前的外交和自然界以及其他時空下的社會環境相連接,從而達成一個共性,這樣更有利于說理,旨在以古喻今,借古諷今。行人辭令中運用的具體比喻形式與現代漢語中的常見比喻形式基本相同。
明喻是《左傳》行人辭令中最顯著、最常見的比喻形式,其中典型明喻與現代漢語中的明喻用法幾近相同。本體、喻體、喻詞均出現。例如:“臣為隸新,然二子者,譬如禽獸” [2]1063(襄公二十一年)此處的二子指的是殖綽、郭最。州綽認為他們二人與自己人想比只相當于禽獸,恨不得割其肉當飯吃,剝其皮做褥睡。此之喻可謂用心良苦,大恨之下仍以巧思表述之。再如:“然猶犯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2]1192(襄公三十一年)子產認為制止人們的這些議論就像堵塞河流一樣,河水大決口所造成的傷害必然會很多,我們是不能挽救的啊。子產在談論中,旨在不毀鄉校,行于忠善方可減少怨恨,向人們施展權威固然能防止怨恨,但是這卻如同“防川”,終有一天會發生決堤出險的慘劇,傷及人民難以挽回。此喻以治水喻治國,輿論和人心如同川堤,簡潔易懂地說明了民心所向的重要性,毋以暴政抑民心。后來《國語》中邵公諫厲王弭謗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比喻與此相似相通。
暗喻在行人辭令中也是占有突出地位的一種比喻形式,但辭令中的暗喻和現代漢語中的暗喻形式上有所區別。現代漢語中的暗喻辭格中,“是”為標志詞,格式為“甲是乙”,而《左傳》行人辭令中的暗喻形式則為“甲,乙也”、“甲,乙”。例如“越在我,心腹之患也”[2]1664(哀公十一年),心腹之患后來成為一個成語,指人身體內部致命的疾病,比喻嚴重的隱患,越國在我看來,是身體內部的癰患。對于“甲,乙也”形式的比喻,其實經過語境翻譯為現代漢語的過程中,仍為“甲是乙”的形式,故無大礙。而更加簡短的暗喻形式“甲,乙”,無語氣詞停頓。“夫魯,齊晉之唇”[2]1647(哀公八年),這是齊魯鞌之戰中的比喻,將魯國比作齊國和晉國之間嘴唇,以體現其重要的地緣與戰略地位,以此作比,彰顯重要性的同時委婉地勸諫君主做出明確政治抉擇。
借喻比暗喻關系更近一層,正文和比喻的關系更加接近。“輔車相依,唇亡齒寒”[2]307(僖公五年)是《宮之奇諫假道》中的名句,輔為臉頰,車為牙床,借此比喻虞虢兩國同呼吸共命運的關系,以防借道于秦自招禍患。秦伐鄭,鄭國皇武子前往秦人客館欲勸退駐扎在鄭國的秦國軍隊。“秦有具囿”[2]496(僖公三十三年),將“具囿”借喻秦國,以獵場喻國家,故之后皇武子說:“您想獵取麋鹿還是回到您的國家去吧,來給我們鄭國以安閑喘息。”就顯得順理成章了。而運用借喻對其進行修飾,既具有技巧性,又達到了委婉有效的勸諫目的,使讀者感受到其委婉語言風格。
《左傳》行人辭令因其行文簡短的特征,在比喻這一修辭手法運用上,更多表現為簡潔無形式標志的暗喻之中。古代漢語的比喻句中,存在著詞類活用的現象,行人辭令中的比喻也有活用現象的出現,譬如:“以蕃屏周”,此處的“蕃”可理解為“像屏障一樣”的意思。這種詞類活用現象更加體現其簡短靈活的特點,故在翻譯的時候有意識地加入喻詞,結合語境更能反映出說者的意愿及其委婉風格。
二、行人辭令中的引用
《左傳》中的辭令,引用《詩》、《書》并借其章句表意是其一大特色。通過引用《詩》、《書》中句子婉曲地表達自己的主張,增強了辭令的藝術性和說服力。在朝堂之上,熟諳《詩》、《書》,言行如之,就具有被推薦勝任要職的資格,可見,當時社會對于《詩》、《書》的追求和遵守。
由于《詩》本身就存在著“興觀群怨”的作用,故行人辭令對于《詩》的引用更有助于深層次地表達個人見解,更好地實現自己的目的。在春秋時期,人們對于《詩》的看法集中于祭祀典禮、外交辭令等方面。周人認為《詩》具有典禮、賦詩、言語的功用,而典禮和諷諫正是《詩》自身的原始功用。“賦詩言志”是春秋戰國時期的貴族知識分子階層在典禮和外交場合慣用的外交方式。在這里《詩》本身的要義已經變得不甚重要,反而成為言志抒情之詩,無論勸諫君王或說明自己,諷喻對手或是上通下達,《詩經》已經被披上“目的”的外衣。“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2] 這可以理解為:辭令和諧,百姓就團結。辭令動聽,百姓就安定。可見,引用《詩》已成為國家治理過程中的一種手段。比如子產論政寬猛中,“惠此中國,以綏四方”[3]293(昭公二十年),借《詩》中這一句來表達寬政嚴政相互結合以起到調整政治的意愿。《詩》所具有的興觀群怨的作用使行人在辭令中引用并轉述,借此來表達政治愿望,《詩》中的語言已經成為治國安邦直接引用的信條。鬬轂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后借助《詩》“豈不夙夜,謂行多露。”[3]291(僖公二十年)評之,難道不想早晚都趕路,實在是因為路上太多朝露。然而,深層次地可以理解為,事情的成敗在于自己,而不在一些外界因素,從“謂行多露”的自然狀況映射出“善敗由己,豈由人哉”的社會現實。這樣為文對于隨國不自量力而遭到討伐這一事件的記述,更具有文學意義和深刻啟發。
不僅在為政治國、行軍戰爭這些國與國交鋒的場合會引用《詩》,以示尊禮,即使是在表達私人意愿時,也會有相關的引用。成語“齊大非偶”典出自鄭太子忽辭不受文姜一事,在他的辭令中有“《詩》云:‘自求多福”[3]17(僖公十四年),表示自己不愿接受這樣一門婚事,先是表明人皆有偶這樣的常態,然后說雖然齊國很強大,但是我不能接受,隨后引用詩經中“自求多福”,借求助自己會比求助他人獲得更多的幸福之意,表達不受之意。如果太子忽直截了當地拒絕,首先對于個人層面會顯得無禮,更甚的是,作為鄭國貴族,個人言行的不當會致使兩國關系的惡化,故引用《詩》中這樣一句話就會將個人意志與禮法規范結合,合乎規矩但又不失委婉,在禮制與人情之間產生平衡,有利于人際關系、邦交關系的穩定發展。
《左傳》成書于春秋時代,社會變革,王室衰微,諸侯爭霸,卿士大夫興起。遵循周禮法度,開展對于他國的外交任務, “禮”成為其主要目標和手段。《左傳》載孔子語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信。”[2]1106如果言辭之中缺乏禮儀就難以走得很遠。從中可見當時辭令的地位之高、意義之重。修辭服務于時代,在相關的行人辭令之中,修辭可以體現出一個時代的風貌。在《詩》、《書》系列傳統典籍以及禮樂文化的熏陶下,誕生于這樣一個特定社會背景之下的行人辭令具有時代特色,與春秋時期的社會文化背景相輔相成。孔子所說的“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4]258指的就是禮樂制度作為當時社會貴族生活行為的規范。《詩》、《書》作為邦國來往、人際交流的語言文字范本,對于《左傳》行人辭令委婉風格的形成起到極大的影響作用。
《左傳》中的行人辭令通過運用比喻修辭手法、引用《詩》、《書》成句表情達意,形成了兼具語言美和實效性的委婉風格,使《左傳》這部史學著作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
參考文獻:
[1]劉知幾.史通·惑經[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2]楊伯峻.春秋左傳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1.
[3]程俊英.詩經譯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4]楊伯峻.論語譯注·季氏篇·第十六[M].北京:中華書局,2015.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