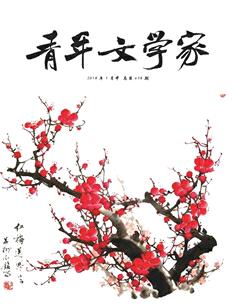淺談《浮士德》中靡非斯特的形象
聶戀懿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02--01
與《神曲》、《哈姆萊特》、《伊利亞特》并稱為“歐洲古典四大名著”的《浮士德》,為我們塑造了兩個鮮明的藝術典型:浮士德博士和惡魔靡非斯特。浮士德,這位老博士,他花一輩子的時間窮究學問,當面臨晚景凄涼時卻與惡魔靡非斯特簽下協議,以自己的靈魂為條件,換取青春與愛情。當我看到郭沫若在《浮士德》的譯后記中寫:“歌德的一生努力凝聚成浮士德……”時,我回顧自己閱讀《浮士德》的過程,發現自己并沒有對主人公有什么特殊的想法。這也許是對時代背景以及歌德生平了解太少的緣故。而作為反面角色出現的惡魔靡非斯特倒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就像堂吉訶德離不開桑丘·潘沙一樣,浮士德也離不開靡非斯特。如果說浮士德是歌德自身,那么,靡非斯特就是歌德一生無法擺脫的陰影。我認為,靡非斯特既是歌德所依賴的,又是歌德所厭惡的,甚至從某種方面講,他就是歌德所難以言喻的一面。
將靡非斯特落實為一個具體的人物之前,不妨先談談作為抽象化存在的靡非斯特。靡非斯特,引領著浮士德走出一個人的書齋世界,走進屬于兩個人的愛情的“小世界”,又走進更加復雜紛紜的“大世界”。雖說他的動機在于用眼前的享受和滿足誘使人類墮落,但卻往往刺激了人類更大的欲求。設想一下,假若沒有靡非斯特的出現,浮士德就不想去追求他心愛的女人,不想去建功立業,不想去創造屬于自己的世界嗎?我從書中讀出,早在惡魔出現以前,年老的博士已經不甘于困死書齋,做一個瓦格訥式的唯技術主義者了。他要去愛,去追求。所以,靡非斯特更大的意義似乎在于,他是浮士德手中一件無往不利的工具。只要浮士德想要的,他都能想方設法幫他弄到手。當浮士德迷上瑪甘淚時,靡非斯特給他買禮物,給他創造約會機會,甚至替他干掉了前來捉奸的瑪甘淚的哥哥;當國王要求復活海倫和帕里斯時,靡非斯特通過魔法使兩個人真的出現在現實世界中;當浮士德沉溺于海倫的美貌時,又是靡非斯特,將他帶往“坤元”這一神秘之境,讓他能與夢中情人牽手;在最后兩幕里,靡非斯特先是幫助國王擊敗叛軍,為浮士德贏得封地;爾后又完成了浮士德宏偉的建設計劃。沒有靡非斯特,浮士德將像一個空懷抱負而毫無行動能力之人一樣寸步難行。當然,從靡非斯特的所作所為也不難看出作者心中歷史的發展形式——美好的愿望總是由齷齪骯臟的行為完成。這一點,對于我加深對歌德看法國大革命的認識非常重要。過去,因為意識形態和國家建立方式的影響,我國研究者或出于真心,或迫不得已,都對歌德關于法國大革命的看法大加撻伐。而現在,當“人的文學”(在我國由周作人首倡,錢谷融繼之)的觀念逐漸為國人所接受,回頭再看那些動輒死傷無數,流血漂櫓的革命,又何嘗沒有“靡非斯特”的色彩?
除了作為浮士德的帶毒的利器,靡非斯特還是天帝的工具。在《天上序幕》里,天帝自言:“人們的精神總是易于馳靡,動輒貪愛著絕對的安靜;我因此纔造出惡魔,以激發人們的努力為能。”靡非斯特窮盡了人類追求的一切可能,浮士德要么輸掉與他的打賭,要么永不止步,成為加繆筆下受到懲罰卻仍勇敢地挑戰荒誕的西緒福斯。總之,無論何種結果,《浮士德》都只能是“一部悲劇”。
剝離開所有非“人”的因素,靡非斯特作為一個的“活”的人物形象顯然要容易理解得多。
首先,他是“人類伙伴”這一天帝設定的形象具體化。在我們每個人的生命中,都會有一兩個靡非斯特式的伙伴。他們當然不像惡魔那樣動機不純,但是,他們一樣會讓我們感到氣憤,可同時又讓我們無法舍棄。他們是真正的朋友。歌德的漫長的一生里,當然也有屬于自己的靡非斯特,比如赫爾德,比如麥爾格。所以,當歌德自身化身為浮士德時,他的高明的伙伴,也就自然而然地化身為充滿智慧的靡非斯特了。
當然,惡魔畢竟是惡魔。假如不是一個收容一切罪惡的箭垛式人物,那么,與浮士德訂下賭約的也就不一定要靡非斯特。關于他的殘忍,冷酷,虛假,以及愚蠢的例子,在整部詩劇中可謂俯拾皆是,這里我也不再贅述。引起我特別注意的倒是他在珀涅俄斯河上游的表現,面對眾多的美麗精靈,靡非斯特渾身不自在,他寧可去找丑陋無比的福爾基亞斯,就像他當初找瑪甘淚的鄰居鬼混一樣。作者借這種反常的行為似乎想告訴我們:墮落的人往往是自甘墮落。所以,在他們將其他人拉入地獄之時,根本不會有什么內心的障礙。
最后,一個很大的可能是,惡魔從某種程度上講也是歌德本身。他身上濃厚的虛無主義色彩和玩世不恭(“教堂有個強健的胃腑,他從不曾因過量而食傷,雖已經吃遍了各處地方;能夠消化這不義之財的,慈惠的信女們,只有教堂。”),都像極了未入魏瑪之前的青年歌德。而他的刻薄(“不是任何處女都那么干凈”),也符合不少人對于歌德的看法。甚至他的對上的諂媚,也完全可以當成歌德自己對自己的批判。總而言之,正像“惡魔”這個符號本身所昭示的,歌德在靡非斯特身上灌輸的屬于自己的部分,都是“不足為外人道”的,它們有些也許在現在看來是正確的,但卻無法見容于時人。這一點,我想我們還是可以肯定的。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02--01
與《神曲》、《哈姆萊特》、《伊利亞特》并稱為“歐洲古典四大名著”的《浮士德》,為我們塑造了兩個鮮明的藝術典型:浮士德博士和惡魔靡非斯特。浮士德,這位老博士,他花一輩子的時間窮究學問,當面臨晚景凄涼時卻與惡魔靡非斯特簽下協議,以自己的靈魂為條件,換取青春與愛情。當我看到郭沫若在《浮士德》的譯后記中寫:“歌德的一生努力凝聚成浮士德……”時,我回顧自己閱讀《浮士德》的過程,發現自己并沒有對主人公有什么特殊的想法。這也許是對時代背景以及歌德生平了解太少的緣故。而作為反面角色出現的惡魔靡非斯特倒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就像堂吉訶德離不開桑丘·潘沙一樣,浮士德也離不開靡非斯特。如果說浮士德是歌德自身,那么,靡非斯特就是歌德一生無法擺脫的陰影。我認為,靡非斯特既是歌德所依賴的,又是歌德所厭惡的,甚至從某種方面講,他就是歌德所難以言喻的一面。endprint
將靡非斯特落實為一個具體的人物之前,不妨先談談作為抽象化存在的靡非斯特。靡非斯特,引領著浮士德走出一個人的書齋世界,走進屬于兩個人的愛情的“小世界”,又走進更加復雜紛紜的“大世界”。雖說他的動機在于用眼前的享受和滿足誘使人類墮落,但卻往往刺激了人類更大的欲求。設想一下,假若沒有靡非斯特的出現,浮士德就不想去追求他心愛的女人,不想去建功立業,不想去創造屬于自己的世界嗎?我從書中讀出,早在惡魔出現以前,年老的博士已經不甘于困死書齋,做一個瓦格訥式的唯技術主義者了。他要去愛,去追求。所以,靡非斯特更大的意義似乎在于,他是浮士德手中一件無往不利的工具。只要浮士德想要的,他都能想方設法幫他弄到手。當浮士德迷上瑪甘淚時,靡非斯特給他買禮物,給他創造約會機會,甚至替他干掉了前來捉奸的瑪甘淚的哥哥;當國王要求復活海倫和帕里斯時,靡非斯特通過魔法使兩個人真的出現在現實世界中;當浮士德沉溺于海倫的美貌時,又是靡非斯特,將他帶往“坤元”這一神秘之境,讓他能與夢中情人牽手;在最后兩幕里,靡非斯特先是幫助國王擊敗叛軍,為浮士德贏得封地;爾后又完成了浮士德宏偉的建設計劃。沒有靡非斯特,浮士德將像一個空懷抱負而毫無行動能力之人一樣寸步難行。當然,從靡非斯特的所作所為也不難看出作者心中歷史的發展形式——美好的愿望總是由齷齪骯臟的行為完成。這一點,對于我加深對歌德看法國大革命的認識非常重要。過去,因為意識形態和國家建立方式的影響,我國研究者或出于真心,或迫不得已,都對歌德關于法國大革命的看法大加撻伐。而現在,當“人的文學”(在我國由周作人首倡,錢谷融繼之)的觀念逐漸為國人所接受,回頭再看那些動輒死傷無數,流血漂櫓的革命,又何嘗沒有“靡非斯特”的色彩?
除了作為浮士德的帶毒的利器,靡非斯特還是天帝的工具。在《天上序幕》里,天帝自言:“人們的精神總是易于馳靡,動輒貪愛著絕對的安靜;我因此纔造出惡魔,以激發人們的努力為能。”靡非斯特窮盡了人類追求的一切可能,浮士德要么輸掉與他的打賭,要么永不止步,成為加繆筆下受到懲罰卻仍勇敢地挑戰荒誕的西緒福斯。總之,無論何種結果,《浮士德》都只能是“一部悲劇”。
剝離開所有非“人”的因素,靡非斯特作為一個的“活”的人物形象顯然要容易理解得多。
首先,他是“人類伙伴”這一天帝設定的形象具體化。在我們每個人的生命中,都會有一兩個靡非斯特式的伙伴。他們當然不像惡魔那樣動機不純,但是,他們一樣會讓我們感到氣憤,可同時又讓我們無法舍棄。他們是真正的朋友。歌德的漫長的一生里,當然也有屬于自己的靡非斯特,比如赫爾德,比如麥爾格。所以,當歌德自身化身為浮士德時,他的高明的伙伴,也就自然而然地化身為充滿智慧的靡非斯特了。
當然,惡魔畢竟是惡魔。假如不是一個收容一切罪惡的箭垛式人物,那么,與浮士德訂下賭約的也就不一定要靡非斯特。關于他的殘忍,冷酷,虛假,以及愚蠢的例子,在整部詩劇中可謂俯拾皆是,這里我也不再贅述。引起我特別注意的倒是他在珀涅俄斯河上游的表現,面對眾多的美麗精靈,靡非斯特渾身不自在,他寧可去找丑陋無比的福爾基亞斯,就像他當初找瑪甘淚的鄰居鬼混一樣。作者借這種反常的行為似乎想告訴我們:墮落的人往往是自甘墮落。所以,在他們將其他人拉入地獄之時,根本不會有什么內心的障礙。
最后,一個很大的可能是,惡魔從某種程度上講也是歌德本身。他身上濃厚的虛無主義色彩和玩世不恭(“教堂有個強健的胃腑,他從不曾因過量而食傷,雖已經吃遍了各處地方;能夠消化這不義之財的,慈惠的信女們,只有教堂。”),都像極了未入魏瑪之前的青年歌德。而他的刻薄(“不是任何處女都那么干凈”),也符合不少人對于歌德的看法。甚至他的對上的諂媚,也完全可以當成歌德自己對自己的批判。總而言之,正像“惡魔”這個符號本身所昭示的,歌德在靡非斯特身上灌輸的屬于自己的部分,都是“不足為外人道”的,它們有些也許在現在看來是正確的,但卻無法見容于時人。這一點,我想我們還是可以肯定的。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