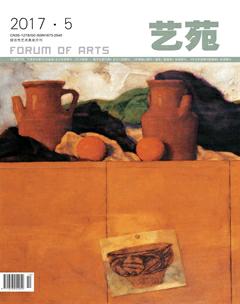華人的文化身份認同建構
【摘要】 新加坡系列電影《小孩不笨》是由新加坡華人導演梁志強執導的反映社會問題的兒童題材影片。影片以探析教育問題和代際溝通矛盾的根本原因為出發點,另辟蹊徑,結合新加坡華人的歷史際遇和現實狀況,分析在后殖民語境下,面對中西文化對撞的困境,新加坡華人的文化身份認同建構。
【關鍵詞】 新加坡電影;《小孩不笨》;文化身份認同;新加坡華人
[中圖分類號]J90 [文獻標識碼]A
新加坡系列電影《小孩不笨》是由新加坡華人導演梁志強執導的反映社會問題的兒童題材影片,它深入了孩童的內心世界,以孩子的視角刻畫他們與家長溝通的隔閡和障礙,反思了家長以及學校、社會在教育兒童時的諸多難題,兩代人在影片的鏡頭下終于越過屏障,實現了遠程對話。不可否認,《小孩不笨》承載了一定的社會教育意義,但是其流暢的剪輯、嫻熟的鏡頭語言、輕松幽默的氛圍、真切的情感流露、對熱點問題的關注,尤其是塑造的幾個鮮活立體的人物形象使影片無論是在新加坡還是在國內都廣受好評。
電影關注的是代際關系,導演選取了代際溝通間的矛盾作為敘事動因。《小孩不笨》中的代際矛盾主要是圍繞孩子的成績問題展開的,孩子的成績未能達到父母的預期,于是父母無所不用其極的督促學習以期成績的提高,幾乎所有的問題皆因學習成績而起,父母沒有聽從孩子內心的聲音甚至不給孩子發聲的機會,只顧一味灌輸,耳提面命式的教育方法未曾奏效甚至適得其反。然而代際溝通不暢只是引發教育矛盾的冰山一角,筆者認為另有深層原因。
在《小孩不笨》系列電影中,存在這樣一種現象,即:演員們說著略顯蹩腳的中文,也說極具新加坡特色的Singlish(新加坡式英語),除此之外還夾雜著馬來語和各種語言的音譯詞匯。事實上,這是語碼轉換的現象。語碼轉換,指的是言語者從一種語言轉到另一種語言的現象。這一特殊現象也幾乎存在于任何一部新加坡電影中。顯然,這是由新加坡的種族多樣性決定的,多種族造就了多元的語言環境,也帶來了豐富的文化。華人作為新加坡占比最大的族群,其帶來的中華文化自然也成為新加坡多元文化的中流砥柱。在新加坡,另外一支不可小覷的文化力量則是西方文化。中西文化在這個神奇的國度碰撞、融合、再生產,也為新加坡華人建構出一個文化身份認同的第三空間。正是這種由于中西文化的矛盾與對立而產生的夾縫中的文化認同,激發了《小孩不笨》中的教育矛盾。
面對教育問題,社會和華人家長是如何應對中西文化的碰撞的?新加坡華人又是如何在中西文化的間隙中來建構自身的文化身份認同的?我們可以在影片中找到答案。
在兩部影片中,泰瑞的父親、國賓的父親和教華文的符老師都格外強調華文的重要性。國賓的父親不止一次地強調:“作為華人怎么可以說不好華文。”另一個戲謔的平行剪輯也使我們關注到華文在新加坡華人中的尷尬境地,Selena在華文課上被老師提問用中文說出自己的志愿,而她的回答是:“做個洋人,因為如果是洋人就不用學華文了。”Selena作為華人后裔不重視甚至排斥華文。這時候導演將老師教育Selena華文重要性的鏡頭與廣告公司招聘策劃的鏡頭剪輯到一起,將老師的教育與廣告公司老板的回答平行剪輯,我們來看以下對話:老師:“如果你不懂華文。”老板:“完全沒有問題。”老師:“生長在這個環境里,華文華語的用途是超越你的想象的。”老板:“像我一樣,不懂華文但生活得非常好。”老師:“不懂華文,將失去了解中華文化的機會,不懂華文,將會使我們不了解自己的族群。”老板:“在新加坡是不會失去做生意的機會的。”這一組對話的交叉剪輯,形成了一種隱喻關系,意在說明華文的重要性遠在金錢之下,在這種諷刺的對比中,華文的地位消解于無形。實際上,這也從反面暗示了導演本人對于華文的重視。
在影片的另外一條敘事線索中,泰瑞精通華文,但英文稍差的他被劃分到第三等級的班級——EM3學習,而像晶晶和泰瑞的姐姐Selena一樣華文不精的學生,誤用成語、白字連篇是常有之事,對他們來說華文變成了為應付考試而不得不負擔的累贅,甚至在他們的生活中,英文已經代替了華文成為使用最多的語言。晶晶也反復強調:“校長作為成功人士也不精于華文,可見華文并不重要。”而面對質疑的符老師竟也一時語塞。語言作為一個民族思維的工具,是一個民族重要的文化符號。因此,導演反復強調華文對于孩子們,對于家長們和社會的重要性。
新加坡作為一個移民國家,由華人、馬來人以及印度人等組成,政府規定的官方語言有普通話、泰米爾語、馬來語、英語等。華人作為新加坡占比最大的族群,華文的普及程度理應很高,然而正如導演在影片中所關注的現象一樣,在今天的新加坡,像泰瑞一樣精通華文、理解傳統文化的新一代華人已經少之又少,而英文和西方文化則讓家長和孩子們趨之若鶩。
一個重要的表現是,在《小孩不笨1》中,幾位小主人公國賓、文福、泰瑞所在的班級被分為EM3,而等級劃分的依據則是學習成績,這個學習成績又是以英文和數學為主要標準的,華文則不被納入參考項。正如國賓的母親所說:“在新加坡只看數學和英文成績的”,所以哪怕像泰瑞一樣華文很棒但英文卻不佳的學生也沒有資格讀高等級的班級。另一個表現是,作為EM3的學生,他們“學習成績”不好被EM1、EM2班級的孩子嘲笑、被家長批評、被老師和學校遺棄,沒有人關注他們。成績不好成為了他們撕不掉的標簽,而一旦被貼上這張標簽,他們的優點則被全部抹殺。國賓擅長繪畫,泰瑞擅長華文,文福頭腦靈光、仗義勇敢,但老師家長們在乎的只是英文和數學成績。孩子天性中的美好一點點被吞噬,取而代之的是自我懷疑、自我否定,這是對孩子心靈的戕害。父母們總是奉“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為圭臬,讀書的作用確實不可小覷,但成績并非檢驗讀書成果的唯一依據。這種唯讀書有用論其實是實用主義和金錢至上的產物,是現代化的文化遺留和后現代主義的滲透。在新加坡,擁有好的成績能讀“好的學校”,而優等學校的一紙文憑能讓其擁有者在就業大軍中拔得頭籌,薪水自然頗豐。追根溯源,讀書的目的實際是出于對成功事業、社會地位和大把鈔票的追求,這難道不是美國夢在新加坡華人心中的投射嗎?西方文化觀念對新加坡的影響之深,由此可見一斑。endprint
對西方文化的狂熱追求,究其原因是西方的殖民統治。這也是造成新加坡華人文化身份選擇障礙的罪魁禍首。由于殖民征服,一些被殖民的國家被“邊緣化”從而納入到世界體系中,取得獨立地位后,國家內部存在著文化、宗教、經濟地位等各種差異,新加坡正是如此,由于缺乏為民族獨立而進行的斗爭而國家認同極弱,因此只能通過政府的權威建立以制度認同為機制的國家認同。
殖民的歷史遺產,似乎給新加坡帶來了不少“好處”,經濟的快速發展,對西方模式的學習,使后殖民時代的新加坡人民物質生活比以前更為舒適,眼前的成就合理化了新加坡西化的選擇,而且由于不具有悠久的歷史,因此殖民時期的歷史變成了參照物。然而,一旦新加坡的經濟發展速度減慢,其國家認同將面臨嚴重危機,而新加坡華人的文化身份認同也將遭受割裂,繼續西化還是退守中華文明將是他們面臨的艱難選擇。
另外,在文化身份選擇前還存在著兩種文化的沖突,這也是造成新加坡華人文化身份認同割裂的重要原因。新加坡由于自身地緣及歷史因素,在中西文化的交叉路口上,其文化認同先天存在不足。中西方文化在哲學基礎以及文化模式上天壤之別。中國文化以儒道兩家為哲學基礎,強調和諧與辯證統一;而西方則注重科學、理性、分析與實證。在文化模式上,中國強調家國觀念;而西方信奉的則是個人本位。
上述種種不僅反映出新加坡的教育崇尚西方文化而忽視中華文化,同時也折射出了教育矛盾背后的深層原因。多元的文化顯得雜而不精,正像獅城象征魚尾獅所傳達的精神一樣,中西方文化的交匯造就了新加坡,但同時也使新加坡始終徘徊在中西文化的邊緣,喪失了中華傳統文化的一脈,對于西方文化的追隨和模仿僅停留在照貓畫虎的階段。正是這種文化身份認同上的兩難使得新加坡的教育存在著不足。
這個問題指向了一個社會學和文化學的現象,在新加坡這個國小民寡的國家,華人缺乏合理或者統一的文化身份認同。新加坡華人的文化認同在中西文化的裂隙間生存徘徊,存在著分層和斷裂。面對原生的中華文化,既有變異,也有保持,加之主流西方文化的干預更使他們的文化身份選擇模棱兩可,左右為難。20世紀七八十年代,新加坡政府力圖在文化認同的基礎上,建構更高層次的國家認同,從而改造自己文化邊緣的狀態,進入了文化轉型與國家認同建構階段。然而即使是在自我建構的過程中,除去主體自身的弱點,仍舊存在著程度相當之深的羈絆。比如在《小孩不笨》中,第一代華人移民,講閩南語的“奶奶”必須將普通話作為自己的民族符號去接受并認同,這本身就造成了對華人原初文化身份認同的一種解構。
在主體自我重構的過程中,新加坡華人又不斷面對中西方文化對撞的沖擊,一邊是西方后現代主義的滲透,而另一邊則是深入骨髓的中華民族的歷史記憶與文化遺留。新加坡的華人始終面臨著文化身份認同的兩難選擇,無法完全摒棄一方而投入另一方的懷抱。于是,在第一個層面上,傳統的中華文化被消解,新加坡華人對于中華文化的身份認同呈一種尋根不歸根的態勢,在另一個層面上,西方文化源源不斷的介入新加坡華人的生活,在困惑中他們開始了新的嘗試。因此雙重的文化身份形成了互相滲透的關系。實際上,在后殖民語境下,隨著全球化的加深,整個世界國際性的增強,加之新加坡華人移民經歷的積累,文化解構與交融已經完成,可供選擇的兩種走向為華人的身份選擇生產出了一個“第三空間”。這是新加坡華人對于自身文化身份認同的想象,也是一種基于現實的自我重構。這種身份認同更廣泛的可能性不在于那種穩固的民族或文化認同,而在于一種矛盾的、迷茫的“混雜式的身份認同”。
不僅是在影片中,現實生活中也存在著千千萬萬個“國賓、文福、泰瑞、成才、Tom、Jerry”,這些新一代的新加坡華人作為移民后裔,在歷史和現實之間、在中西方文化之間、在教育的矛盾之間,他們不知何去何從,文化的兩難讓他們喪失了主體選擇的權利,被動地接受與吸收。他們在文化身份認同上遭遇的困境,不禁讓人聯想起電影《刮痧》中的男主人公許大同。與許大同類似,新加坡華人似乎也徘徊于兩種文化身份的十字路口。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識話語,成為純粹的西方人已經變得無法實現,只能永遠作為西方想象中的文化“他者”而存在;回歸中國文化,重新做回中國人更不現實,因為對他們來說,“移民只是單程旅行”,過去的一切早已是塵封的記憶。
作者簡介:張瑞文,南京大學戲劇影視專業研究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