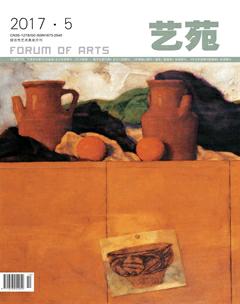《白鹿原》上的主角們
鄧海琪
【摘要】 《白鹿原》是當代文學的經典作品之一,其改編電影為觀眾對《白鹿原》的理解和認識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性,但同時因與原著主題內涵有較大出入而引起爭議。文章圍繞《白鹿原》小說和電影兩種不同的文本形式,以主要人物為切入點,分為儒家文化代表、叛逆力量代表和政治話語代表三種類型,力圖展現電影與小說相比的缺憾之處,以及探討中國電影在表現以宏闊民族特色為背景的史詩作品中對民族文化的審視問題。
【關鍵詞】 《白鹿原》;人物分析;小說;電影;大眾文學
[中圖分類號]J90 [文獻標識碼]A
雖然在90年代才面世,《白鹿原》一直被公認為是“80年代”的作品,其中的“去革命化”敘事、對傳統文化的肯定以及帶有一定魔幻現實主義風格的寫法,都昭示其受反思文學、尋根文學及西方“拉美大爆炸”的影響。陳忠實也曾表示他的創作動機和80年代的關系:“這大致是1986年的事情,那時候我的思想十分活躍。”“我再也耐不住性子繼續實踐那個要寫夠10個中篇的計劃了,原因是一個重大的命題由開始產生到日趨激烈、日趨深入,就是關于我們這個民族命運的思考。”[1]《白鹿原》是一部公認的大書,其扉頁引用巴爾扎克的名言:“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奠定了這本書是民族史詩的宏大格調。
然而結合80年代末發生轉變的文化語境與小說本身存在的問題,由《白鹿原》改編的電影籌備9年,歷時3年,在千呼萬喚中于2012年上映。可電影上映后卻讓大多數人大失所望,其中電影與小說的“非良性互動”[2]究竟為哪般?這將是接下來要探討的問題。
一、文化的尷尬:朱先生、白嘉軒的存在矛盾
在90年代,《白鹿原》作為“尋根文學”的代表作之一,小說闡發的對于民族歷史文化的思考曾引起熱烈反響。在陳忠實在小說的前半部分,深刻闡釋了儒家思想至今深深植根于中國鄉土生活的普遍現象。從小說剛開始,白嘉軒娶七房太太和對于“香火”的執念,“唯小人女子難養也”的思想使母親、妻子的鮮活個性皆黯然隱于白氏、三姑娘、胡氏的代詞之下,再到祭祖、修祠堂、制定“耕讀傳家”的鄉約,貫穿了農民本土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在小說后半部分,違背儒家文化所倡導的“仁義禮智信”的鹿家、田小娥、黑娃等人幾乎沒有好下場的情節內容,似乎都已非常明顯的表明作者對于儒家傳統文化問題的站位。
然而,細讀文本則容易發現,陳忠實依然沒有回避儒家文化與現代文明遭遇和碰撞后導致的水土不服。朱先生和白嘉軒,在《白鹿原》中毫無疑問象征著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宗法勢力,但他們在文本中面臨的矛盾地位和人生困局,則暗含著作者對于儒家思想與現代生活交匯的隱憂。
在小說中,值得琢磨的一點是有關白鹿村的統治權問題。事實上,作者弱化了小說中的階級斗爭,呈現在讀者眼前的并不是傳統意義上“農民”和“地主”的沖突,而是白、鹿兩大家族的斗爭。在白嘉軒心中,“家”是擺在首位的。白嘉軒制定的鄉約為“耕讀傳家”,“傳家”這一點就已顯要說明,在白嘉軒心里“家族”是最為重要的,而伴隨而生的“夫為妻綱”、“父為子綱”的“三綱五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有家才有國”的儒家思想則被白嘉軒身體力行地實施在各個方面。從家庭外部看,他對于白鹿村各個方面事務治理高效的做派,讓大家都能在“村長”手下安分守己、安居樂業,而對于田小娥“不能進祠堂”的問題,他的態度則強硬得令人發指,即使全村人因田小娥之死而染上瘟疫也在所不惜;從家庭內部看,體現在對家風的嚴苛要求上。白孝文、白孝武、白孝義的包辦婚姻及嚴加管教,都是為了以后能夠兒子能成為“耕讀傳家”活生生的體現,有資格繼任祠堂族長,而當白孝文一旦觸犯家規,則立刻嚴懲不貸、就地分家。“凡是生活在白鹿村炕腳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遲早都要跪倒在祠堂里頭的。”[3]115這句話是白嘉軒思想的活標簽。
生活在20世紀上半葉的白嘉軒,他所引以為傲的最大成就,就是他將白鹿村治理得井井有條,但他所能施展的極限,也就僅局限在一方祠堂而已,其思想早已與社會脫節。現代社會之所以為現代,是與社會、歷史息息相關的,面對現代性極其強大的影響力及隨之而來的改造力,儒家文化與現代社會的交鋒,結局是情理之中的慘烈。在“交農事件”中,白嘉軒尚能與法院周旋,盡管辯詞已經顯露些微格格不入的迂腐,“他又去找了法院,又掏出麻繩來要法院的人綁他去坐牢”“‘要是不放人,我就碰死到大門上!”[3]87但是好歹有朱先生的影響力和金錢的強大力量,也就讓白嘉軒堪堪“蒙混過關”,把鹿三等弟兄解救出來;但在“黑娃事件”中,白嘉軒振振有詞的擔保已經顯得蒼白無力。他無法理解,自己有理有據的一套話語在陌生、冰冷而又復雜的現代法律制度下,竟已經不起絲毫作用。儒家文化所代表的傳統思想,或許已經演變成遭遇現代社會另一套語言體系的節節敗退。“《白鹿原》的全部故事表明,歷史給予白嘉軒的活動范圍越縮越小,最終只能局限于白鹿村,從而定格為一個不合時宜的鄉村遺老。”[4]如果白嘉軒代表的是儒家文化實體本身,那么朱先生就是小說中代表儒家更高層次的精神領袖。在儒家文化處于主流地位的古代社會,倡導的是“學而優則仕”,儒學是正統,是讀書人升官進爵的敲門磚。白嘉軒在白鹿村的領袖地位毫無疑問,而朱先生則是白嘉軒最尊敬的精神導師,是儒家文化踐行的根基。
在小說前半部分,朱先生是唯一有資格書寫“耕讀傳家”牌匾的人;可以奉命犁掉白嘉軒種的罌粟,因為覺得罌粟的存在有辱儒門,在犁之前還要求“耕讀傳家”的匾額要遮掉;可以以一敵百,以一人之力摒退二十萬清軍,連法院都不得不賣他的面子,可以說,朱先生是一個可以呼風喚雨的、極其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然而,隨著小說情節的展開,朱先生的存在卻逐漸淡化。他與七個同僚的抗日宣言到最后落了個竹籃打水一場空,到小說后半段已經完全不參與世事紛爭,閉門修縣志去了。朱先生的人生經歷,恰恰表明了儒家文化遭遇現代社會的尷尬處境。甚至在結局最后,作者將朱先生提拔到未卜先知的神化配置,他象征的“白鹿精魂”,是否在某種程度上也暗含了作者在面對儒家文化與現代社會無法自恰的無奈現實,只能通過這些神秘而夸張的情節渲染,作為一種理想而無力的補償?endprint
如果說文本內部體現了作家對于儒家文化如何適應現代社會所暗含的淡淡憂慮與無奈,那么在由小說改編的電影的文本外部,儒家文化的意義則以更為徹底的方式被幾乎消解殆盡。在電影中,白嘉軒在小說中的絕對主體地位已經移除,除去開頭帶領全村村民在祠堂誦讀“耕讀傳家”的鄉約,宣告他是儒家文化的擁躉者,對比田小娥和三個男人,電影已少有他的鏡頭。在小說里,白嘉軒的形象是多維立體的,他樂善好施、重情重義、光明磊落、有責任感,但同時又極好面子,冥頑不化,但在電影中,白嘉軒的形象幾乎被矮化成單向度的負面形象。在電影中,小說用以凸顯白嘉軒最大功用的“交農事件”、治理政策全部被砍除,鏡頭語言集中聚焦在呈現白嘉軒是違背鄉約就要受到處罰的施刑者、是對田小娥發生的一切毫不妥協的冷血人,個性是面對鹿子霖即使心想收回家產卻面色不改的嘴硬風格和結尾遭遇日軍戰機轟炸的一臉無措——無措的原因是對于儒家文化在現代社會的無所適從,而電影(公映版)的敘事斷裂使得沒有讀過小說的觀眾深感莫名其妙。電影中極力想表達的是在有限的資源和舞臺上,白嘉軒的極力抵抗都是徒勞。
而對比小說,朱先生這條副線在電影中更是已經徹底消失。這當然有關電影鏡頭語言呈現朱先生這一抽象的、充滿神秘色彩形象的難度,正如導演本人所言:“在改編的時候,簡單地來說,如果跟情感有關聯的,是講故事的,就在電影里比較適合。如果講意境的,比如講道,講風水的,就不適合電影來表達。”[5]同時,我們也意識到以朱先生為代表的“翻鏊子”的歷史觀,與當下主流政治意識形態相悖。但更重要的是,朱先生這條重要支線的砍除,也暗含導演的態度。對傳統文化意義的消解表現得更為明顯的,是電影著力選擇表現關于白孝文“行不行”的問題上。在小說中,白孝文是因為剛開始在床事上表現得過于勇猛,以至于遭到母親強力壓制,但電影里改為白孝文剛開始就“不行”,后來和白嘉軒脫離關系后被田小娥“弄成了”的前后對比。在電影前半部分,白孝文在父親的嚴厲控制下,是安守本分、老實忠厚的族長接班人,但是他在性事上是有遺憾的,因此一直沒有孩子;然而在遭遇了田小娥有意的誘惑,與家族徹底叛變之后,他壓抑已久的個性解放,人性丑惡面也得到了釋放,最終“弄成了”,田小娥還懷上了他的孩子。這兩種對比,闡釋了電影試圖表達儒學對于人性本能的極度壓抑,以及即使面臨解放,卻只能造成適得其反結局的控訴。
以電影為代表的大眾傳媒發展,我們不難看到,現代社會的發展講求思想解放、張揚個性的個人利己主義與儒家文化所倡導的家國一體、克己復禮的概念是有沖突的。傳統一套的儒學思想體系面對商業化、市場化的復雜現代體制,顯露出捉襟見肘的頹勢。然而,這是否意味著儒家文化將會永久失勢?儒學的“第三期”繁榮可能出現嗎?——至少我們可以說,儒家文化的中興不會是復古主義者的單純希冀,而將會成為時代的必然。從文化方面看,儒家文化中的“禮”,有利于現代精神世界的建設。“20世紀的歷史已經證明,在資本主義經濟沖動籠罩世界、市場經濟法則支配全球化的當今世界,僅僅依靠法律和民主并不能建設起有序和諧的社會”[6],而東亞傳統中的禮文化,可以經由選擇性的應用于教育、社會基礎建設、社會關系調整等多方面,從而提升人們的生活質量。從經濟方面看,“新儒學”的提出,使傳統儒學與現代性的結合成為了可能,特別是在80年代。其中興起的最重要原因是現代儒商、東亞經濟發展圈的崛起。儒家文化里蘊含的重商意識、“藏富于民”的經濟策略、“高產乃為善”的經營理念[7],正暗示了其在現代市場經濟社會發展的前景;另一方面,雖然后殖民時代,文化合作實際是文化競爭,強勢文化的引入必然導致傳統文化失去應有的地位,但是我們也應看到后現代主義所倡導“宏大敘事”的解體,也意味著多元文化的涌入成為必然的趨勢,誰又能預言儒家文化未來無法在多種文化競相角逐占有一席之地?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如何將傳統的儒家思想文化體系納入復雜多元的現代話語中交流和競爭,是我們需要思索的問題。
二、性的叛逆:田小娥與黑娃、鹿子霖、白孝文的情欲糾葛
《白鹿原》的電影改編版本,最大的爭議就是文本結構的處理。在原著中,敘事核心為白嘉軒,文中以白、鹿兩大家族在社會風云變幻的大背景下,祖孫三代的興衰榮辱為主線,又以黑娃與田小娥的反叛、鹿兆鵬與白靈等新式青年與傳統思想的斗爭為副線,通過主線與副線的感情糾葛與歷史的發展動向相結合,形成一個復雜交織的網狀敘事。而在電影里,《白鹿原》的敘事結構與原著差異極大。主線更改為以田小娥為中心,著重展現其與黑娃、鹿子霖、白孝文的性事糾葛,她的生存狀態與社會歷史變遷緊密相連。小說中的主要人物白嘉軒,在電影中則作為與田小娥為首的叛逆力量作斗爭的傳統衛道士代表,形成電影與主線對抗的副線。
電影這種簡化處理必然有其合理性因素。毫無疑問,文學創作是從“無”到“有”的寫作過程,但電影創作是從“看不見”到“看得見”的視聽藝術。電影改編,并不是對原著本身“再現”,而是忠于自身媒介本身特性,從抽象到直觀的二度創作,其中要考慮到市場接受、資本對接、政治審查等方方面面。何況是面對“最難改編的電影”《白鹿原》,從小說本身錯綜復雜的人物情節和史詩性的龐大體量,再加上編劇蘆葦的幾度易稿最終也沒有拍成的坎坷過程,簡化線索是必然出路。
然而,為何導演會選擇田小娥與三個男人的感情線作為主線則是耐人尋味的。從小說結構上來說,三十四章的篇幅里,田小娥在第九章出場,第十九章就已經魂歸九天,可以說只是一個輕量級的小人物。但電影單獨將這條線拎出來處理,把“民族史詩”拍成“女人史詩”,是有一定原因的。
首先,從導演王全安拍攝風格而言,女性視角的敘述形式在導演以往作品中有跡可循。從《月蝕》中的梁勝花、《驚蟄》中的陜西女孩、《圖雅的婚事》中的蒙古女人圖雅、再到《白鹿原》中的田小娥,王全安對女性敘事顯然是偏愛的。這是因為“王全安認為首先是因為母親哺育了生命,對本能的東西把握的更精準;其次是因為女性更加感性,更加富有自然的色彩,與男性的理性世界相比,女性和命運的關系更加貼近,通過對女人困境的展示更容易切入問題的實質”[8],選擇田小娥,體現了導演的拍攝習慣和拍攝風格。endprint
但是同是女性,為什么不選擇文中個性極為鮮明,更容易迎合政治正確的白靈,而是選擇了田小娥?這又涉及到田小娥形象背后可供挖掘的商業因素。
在形象塑造上,小說與電影就已截然不同。小說田小娥的出場是日常而安靜的小女人姿態:“黑娃忍不住瞧了一眼敞開的窗戶,小女人正在窗前梳理頭發,黑油油的頭發從肩頭攏到胸前,像一條閃亮的黑緞。小女人舉著木梳從頭頂攏梳的時候,寬寬的衣袖就倒持到肩胛處,露出粉白雪亮的胳膊。”[3]128然而,在電影中,田小娥搖身一變美嬌娘,出場的排場很大,散發著挑逗媚態的風情。在一片金黃的、象征著成熟和繁衍的小麥田中,田小娥乘著小轎、輕搖團扇悠然出場,嬌媚的坐在轎子里,用毫不掩飾的眼神直直地望著麥田里年輕力壯的麥客們。小說里的田小娥除了是供人泄欲的小妾,每天還要給麥客做飯,而在電影里變成了吃好穿好、每天打麻將、抽大煙的姑奶奶。可以說,小說里的田小娥是一個生活在社會底層,精神和肉體都被封建社會壓迫的悲劇人物,但在電影里搖身一變成仰視一眾麥客,錦衣玉食的嬌姨娘——欲望化的符號。小說中利用田小娥格格不入的放蕩,旨在批判傳統文化禁錮下的性本能,而田小娥最終的悲劇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后來整個白鹿村因為其死亡而染上瘟疫,是在于作者意圖通過田小娥和白嘉軒的沖突,借此沖擊白嘉軒在白鹿村苦心經營的傳統烏托邦。然而在電影中,田小娥的存在意義似乎只有在三個男人之間糾纏輾轉:因為郭舉人“正經事都從來沒辦成一回”,田小娥與黑娃的結合,是出于男女之間的性本能;跟鹿子霖歡愛是黑娃出走后,出賣肉體尋求安全庇護,但卻忘情的對鹿子霖說“再甭提黑娃了,我現在離他遠得看都看不見了”;與白孝文之間或許是真正的愛,但卻夾雜著陰謀利用與情欲糾葛——即使如此,也僅僅只是愛情而已。
在電影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場景是白孝文正式與家族脫離關系后,和田小娥在一片曖昧的粉色氛圍中歡愛,田小娥嬌媚的吟哦“桃花源”,女性的柔媚深入骨髓,白孝文從此跌入黯然銷魂的桃花溫柔鄉,這樣的欲望敘事雖然有利于烘托氣氛,但是是否真正符合小說原本意旨?選擇田小娥這個形象作為主線,是否站得住腳?
其實在小說中,作者對田小娥的態度本身就是模糊而曖昧的。一方面,她是“妖女”、是“白鹿村乃至整個白鹿原上最淫蕩的女人”[3]352;但另一方面,陳忠實受“五四”運動以來新文學傳統對女性問題關注的影響,強調女性獨立解放的立場。這樣一個矛盾的人物,既寄予了作者希望其突破傳統思想禁錮牢籠的希冀,但又與小說本身擁護禮儀道德的主旨精神相違背。既是“解放者”,又是“受害人”,在電影要重現田小娥的這一形象,一沒把握好,就顯得格外尷尬。
另外,不難看出,田小娥個人遭際與性格遭遇從小說到電影的變化,更大程度上是因為要迎合現代市場化、商業化的大環境,田小娥的改變是現代社會狂歡化、欲望化、個人化的商業文化消費符號的縮影。當媚俗的身體敘事,成為吸引大眾的有力手段,的確更有市場、更有話題,然而我們也應看到這樣的敘事手段,使原本具有深厚思想精神的民族史詩降格成幾個男人圍繞一個女人展開的個人傳記,這不僅不忠于作者賦予人物本身的功能意義,更弱化了小說本身嚴肅的史詩性、宏觀性,也解構了原著的內核精神。在現代社會的今天,大眾文化娛樂意識大勢所趨,伴隨而來的是深度的淺化、多元的簡化和立體的平面化。我們必須承認,阿多諾對于“消遣”的發現是極具洞察力的:“人們需要找樂子,對于那些承受著巨大的生活壓力,從而在空余時間既要擺脫無聊又不想勞作的人,全神貫注而自覺的藝術經驗是不可能的。廉價商業娛樂的整個領域都反映著這種雙重欲望,它導致放松,因為它是有套路的,被預先消化過的。”[9]
因此出現了矛盾的現象:既然消解了原本的精神內涵,卻不能成功建構另一個完整的思想內核。單純的拍女性,直觀的呈現欲望與《白鹿原》本身的厚重思想內涵相違背,改編電影既要尊重原著,又要大刀闊斧的刪繁就簡,還要“叫好又叫座”,因此導演只能請出白嘉軒這一衛道士的形象,在影片中做著隔靴搔癢的看似平衡的對抗——反而適得其反,顯示出電影主線副線皆失衡凌亂的倉促之態。
三、政治話語的失語:白靈、鹿兆鵬、鹿兆海的敘事斷裂
白靈這一小說形象是討喜的。她頑劣又聰明,性格剛烈,為了爭取到進城求學的機會,不惜刀橫在脖子上;她執著又富有責任感,一心一意追隨共產黨,放棄了代表“國”的鹿兆海的熾烈愛情而投向共產黨戰友鹿兆鵬的懷抱,卻諷刺地在共產黨內部肅反中被活埋致死。可以說,白靈是除了朱先生以外“白鹿精魂”的另一化身,在白靈死后,白嘉軒還夢到白鹿精靈留下眼淚離他遠去。而白靈與鹿兆鵬、鹿兆海的感情糾葛也直接與國共兩黨之間發生的政治事件緊密聯系,可以說,白靈及其這一形象所衍生出來的整條副線是極其重要的。電影將白靈刪去,使得代表新式思想的反叛力量弱化,也很難展現小說中意圖表達的新思想與傳統文化對壘過程中的艱難發展。因此白靈被刪去,只留鹿兆鵬偶爾在每個時間點出現的“打醬油”角色,是不少人詬病的另一個地方。
然而,通過仔細探究可以發現,刪去白靈這條副線確是情理之中。
一是因為電影本身篇幅受限,保留田小娥與白嘉軒的對立已經占用了太多的鏡頭,電影本身長度和篇幅的局限,要求其必須在集中的時間突出主要人物關系,形成強烈的戲劇沖突,而這些田小娥與白嘉軒兩大人物已然具備。王全安之前在專訪中就表示:“白靈這個人物其實試了一下,還是不行,因為一旦上手至少要十幾場戲才能鋪墊得過來,那個空間其實根本裝不下。”[10]
二是因為白靈這條線背后蘊含的政治敏感話題,能否過審也是大多數導演選擇拍攝的一個重要參考。相反,這樣的處理使得部分人對電影持認可態度,例如戴錦華就曾表示“原作比較有80年代遺風,比較是那種政治性的判斷”、“我喜歡電影削弱了原作想有太多說法的愿望”。外部的因素從客觀上間接導致了白靈及鹿兆鵬、鹿兆海的存在感缺失,而從內部來看,小說文本本身的敘事斷裂是電影零碎敘事方式的直接原因。以白靈、鹿兆鵬、鹿兆海所承擔起的敘事脈絡,背后承接的是國共兩黨關系的幾次轉折,從國共第一次合作到十年內戰,再到抗日戰爭,白靈和鹿家兄弟兩人的關系是直接以此作為背景依托的。這條線本身沒問題,有問題的是這一線索與白嘉軒的主線、田小娥的副線脫節。白嘉軒與田小娥的斗爭象征著傳統禮教與其叛逆力量的齟齬,斗爭的舞臺是白鹿原,然而一旦脫離了白鹿原,當背景擴展到更大的歷史舞臺時,白靈及鹿家兄弟和這兩者之間沒有形成強有力的網狀聯系。endprint
白嘉軒與田小娥的沖突是交錯縱橫的,然而這兩者與白靈等人的關系更多體現在單純的血緣上——并沒有最根本的性格沖突。即使最強有力的沖突,也不過是白靈與白嘉軒的關于新式教育的爭執上,而當白靈脫離了白鹿原這個地域局限,由其構造的人物格局顯然與白鹿原本身沒有什么聯系了。從小說中第二十二章白靈對白孝文宣布要教書、打算加入共產黨開始,隨后兩章著重介紹了白靈與鹿兆鵬、鹿兆海的感情關系和革命動作,而在第二十五章,白靈等人的革命活動戛然而止,舞臺重新復歸“白鹿原又一次陷入毀滅性的災難中”,又開始重新敘述白鹿村里遭受瘟疫的事情,下一章也幾乎再無出現白靈一干人等的名字。可見白靈等人所代表的新式的、革命的敘事脈絡根本上是與白鹿原上發生的事件幾乎隔離的。“相對于白、鹿家族內部的故事,這些片段仿佛是一些外圍的資料,沒有來龍去脈,也沒有從開端發展到高潮的情節能量。”[4]這樣的敘事斷裂,也造成了電影政治話語的缺位,于是,我們只能看到,電影中的鹿兆鵬像個報幕員一樣,在幾個時間節點蜻蜓點水般地客串一下,只起到提示劇情的作用。
結語:當中國電影遭遇民族史詩題材
《白鹿原》電影一經上映,就引發強烈爭議。其中有一個問題引人深思:相較重量級史詩電影頻出的外國,中國為什么很少有人拍出成功的民族史詩電影?除了《紅高粱》、《霸王別姬》、《荊軻刺秦王》等是少有的口碑之作,更多的是像《趙氏孤兒》、《滿城盡帶黃金甲》、《長城》等重量級史詩大電影遭遇口碑滑鐵盧。為什么中國電影少有民族史詩題材?為什么中國人難以駕馭民族史詩題材?
首先,筆者認為,除去純粹追求由大量金錢、科技技術支撐和粉絲效應的爆米花電影,中國電影始終在西方世界與本土文化之間找不到調和維度,還沒有形成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的精神內核和民族品牌,是其難以拍好民族史詩題材的主要原因。
第一,中國一方面渴望“走向世界”,另一方面希望通過展現自身的民族性來達成這一目標。80年代,改革開放的春風帶來思想開放的同時,以西方中心主義為主導的文化霸權也在潛移默化的擠壓著中國本土思想的生存空間。如此個中調和的最好結果是張藝謀、陳凱歌等第五代導演憑借《紅高粱》、《活著》等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國故事演繹在國際電影節上屢屢獲獎。不否認這些電影所取得的成就和開創性意義,然而這種現象背后卻催生許多渴望走“電影節路線”的作品,打著“民族性”的大旗,在電影中力圖向國際展現中國特有的“文化特色”,賣力兜售民族苦難,其實不過是用來迎合西方人對于所謂“東方”的集體想象——這些作品大多不過是披著“民族”的外衣,內核是西方思想的另類“討喜”。
第二,試圖純粹建構由國家及政府控制的、完美且強大的國族形象,與西方霸權抗衡。例如《建國大業》《建黨偉業》的拍攝,更多的不受市場本身控制,這類民族史詩,通常是“叫好不叫座”的。一方面是部分觀眾對其中過于明顯的主流意識形態宣傳的抵觸,另一方面是受商業化、扁平化、特效化的好萊塢商業電影的影響,電影觀眾更多尋求感官刺激。這當然是都市人現代生活壓力負重過大的一種有力發泄,但是如果市場一味只注重視聽效果極佳、或思想流于淺俗的爆米花電影,卻拒絕對追求藝術和思想上厚重和深刻的先鋒嘗試不夠包容,中國電影的發展前景是不容樂觀的。對此也有人想出一種對策,就是試圖將極度依賴市場的“粉絲經濟”與主旋律電影結合,例如“建國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建軍大業》。然而多數人卻對此種結合報以排斥態度,普遍認為由演技尚有待考量的“小鮮肉”來詮釋經典歷史是違和的、不能勝任的,更有人笑稱這是“革命偶像劇”。筆者認為,演員陣容的選擇,基于票房市場的商業因素考量無可厚非,但過于考慮市場的“大眾之作”,往往都是“難以服眾”的。
此外,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重要把關者——中國電影審查制度,導致擔心因“尺度過大”而“難以過審”也是民族史詩題材電影無法成型的原因之一。與承擔主流意識形態宣傳的電影比較,中國如果要拍出真正有中國味道而觀眾又買賬的民族史詩,必然會涉及到政治、宗教和歷史問題,甚至以此為主題進入全方位的、多角度的、多種形式的深入探討,而這些問題都是現在電影審查體制極力回避的。不說《白鹿原》小說本身經過幾次修改才最終評上“茅盾文學獎”的辛酸,由小說改編的電影,公映版也從內部評價較好的220分鐘版直接刪減成156分鐘,人物關系僵硬,電影情節支離破碎。而20世紀的《鬼子來了》,在國外風光拿獎,在國內卻無法上映,不得不說在中國目前的體制下,拍出被主流意識形態和大眾認可的優秀史詩電影是極具挑戰性的。電影市場的良性循環,不僅關乎大眾的文化品位,更重要的是擁有信心接納更多不同類型的中國電影涌入市場。正如戴錦華所言:“一個健康的電影市場應該是分眾的、分層的,讓不同趣味的觀眾都能在影院中找到他的影片。”[11]
因此,中國要想拍出真正的優秀民族史詩電影,可謂任重而道遠。一方面必須平衡 “西方中心論”和“本土民族”之間造成的思想偏至,另一方面必須從內部改革,以良好的心態歡迎更多的思想爭鳴。縱然當今的話語主權仍然是以西方世界為中心,但是隨著亞洲國家的逐漸崛起,作為東方文化最重要代表的中國,正力爭成為更有競爭力和發言權的文化主體,以平等互利姿態融入國際秩序。一個優秀的民族,不僅要擁有“有容乃大”的氣魄,更要有力圖真正自信自強的民族共識。
參考文獻:
[1]陳忠實.《白鹿原》創作漫談[J].當代作家評論,1993(4).
[2]孫宜君,高涵.從《白鹿原》改編看電影與文學的非良性互動[J].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1).
[3]陳忠實.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
[4]南帆.后革命的轉移[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5]王全安回應九大質疑:張藝謀也不敢怠慢《白鹿原》[EB/OL].騰訊網.http://ent.qq.com/a/20120919/000074.htm.
[6]陳來.儒家“禮”的觀念與現代世界[J].孔子研究,2001(1).
[7]馬濤.儒家傳統與現代市場經濟[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
[8]張婷.論《白鹿原》的地域文化內涵[D].河北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12.
[9]馬泰·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M].上海:譯林出版社,2015.
[10]孟靜.電影《白鹿原》:土地的視角[J].三聯生活周刊,2012(36).
[11]戴錦華.中國的資本邏輯如何統御文化市場[EB/OL].
http://cul.sohu.com/20151119/n427150531.shtml.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