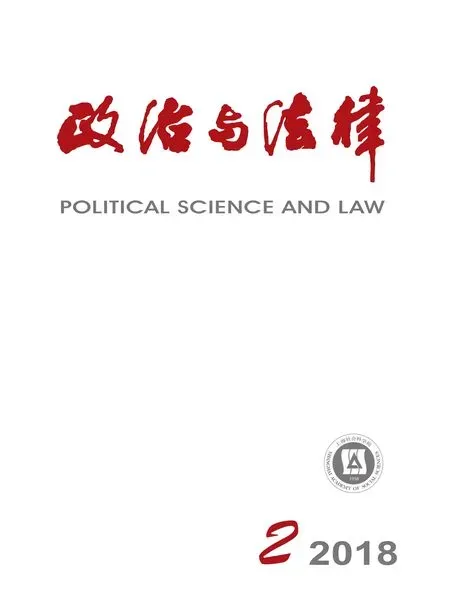緘默形式詐騙罪的表現及其本質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北京 100872)
一、問題的提出
在社會生活網絡化的條件下,人們的交往方式發生著深刻的變革,因此有必要加深對詐騙罪的學理分析。在我國現行法律框架下,盡管我國《刑法》第266條未加以明確表述,但通常認為,詐騙罪的罪狀是“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503頁。以錯誤信息告知對方進而取得對方財產的形式,屬于詐騙案件中較少爭議的類型。然而,若被告人未以如此明顯的方式使對方陷入認識錯誤,而是采用了緘默的辦法(即“隱瞞真相”),最后卻取得相應財產,又當如何認識呢?如:[捷安特自行車案]某日,顧客某甲到自行車用品店選購了一款捷安特牌ATX 830系列的山地自行車,某甲與老板某乙一陣討價還價后商定好4700元的價格,老板娘某丙正好回到店里。某乙遂將某甲介紹給某丙:“你給這位顧客開票,4700元,ATX 830。”某乙說罷就在一旁忙著修車。某丙將某甲領進里屋開好發票后便出來忙其他事情,沒有收取某甲應付價款。某乙夫婦間其實發生了誤會,某丙以為某乙先前已經收了款,自己只負責開票,某乙卻以為某丙開票后同時收了款,故兩人均無要求某甲付款的表示。某甲覺察到兩人的不默契,于是將山地車騎走,某乙和某丙均未加阻攔。待某甲走遠后,某乙、某丙才發覺雙方都忘收錢了。后公安機關迅速偵破,將某甲抓獲。*參見李方政、張理恒:《不作為詐騙罪的認定》,《人民法院報》2011年12月29日,第7版。
在該案的審理過程中,對于某甲行為的認定,出現了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成立盜竊罪;第二種意見認為,成立不作為的詐騙罪。兩種觀點各執一詞的背后,實際上反映出理論梳理工作存在欠缺。以緘默形式取得財物,不限于盜竊罪和消極形式的不作為的詐騙罪,它還涉及隱匿重要信息的積極形式的詐騙罪,商業社會中“不提供信息”的交易行為隨處可見,尤其是進入網絡、媒體普及化的社會大分工時代后,人際交往出現了間接化和縮減化的趨勢。*Vgl. Eisenberg, Kriminologie, 6. Aufl., 2005, § 47, Rn. 11.這也是工業社會的典型特征。人際間直接交往的減少和格式化文字表述的增加,正在深刻地影響人們對于知識、信息、信任和自由等的理解。以信息傳遞(意思互動)作為其本質內容的詐騙罪,自然也在信息化的進程中,出現了從“一對一”個體交往領域向集體場合乃至匿名場合擴張的趨勢。人際交往形態方面出現的變化,不僅使特定條件下出現了盜竊和詐騙界分上的模糊,而且在詐騙罪內部,也產生了默示形式和不作為形式詐騙的區分困難。在人們就財產轉移未發生正面的意思互動的條件下,緘默形式的財產轉移更易發生,有鑒于此,本文主要圍繞緘默形式的詐騙罪展開分析,并附帶論及盜竊和民法上的不當得利等問題,以有助于相關案件的處理。
二、物體操縱:詐騙罪抑或盜竊罪
在財產犯罪中,盜竊和詐騙的區分不僅關涉此罪和彼罪之認定,而且與處罰的輕重有著密切的關系。因盜竊的入罪數額較低(以1000元為起點),而詐騙數額需達3000元才予以追訴,故被告方一般均以不成立盜竊,至多構成詐騙作為其辯護理由。這就使得在成立詐騙罪時,應將盜竊案件合理地排除出去。將盜竊案件合理地排除出詐騙罪的范圍,取決于如何回答以下問題:如果被告人對某一客觀物體實施操縱,進而使他人對該物體的認識出現錯誤,宜認定為盜竊抑或詐騙?在該情形下出現定性困難,并非偶然。以下即對此作進一步的分析。
(一)以意思互動作為“欺騙”的內涵
物體操縱問題帶來的定性困難,涉及如何理解盜竊與詐騙之間的關系,對此,有必要從國際和國內兩個角度做一刑法史的梳理。
早在歐洲中世紀,盜竊和詐騙便混合在一種稱為“作偽”的罪名之中,理由是兩者皆可能在特定條件下使人陷入認識錯誤。而在現代歐陸刑法中,基于限縮詐騙犯罪成立范圍以促進市場經濟以及滿足將詐騙手段明確化、典型化的需要,詐騙從“作偽”中析出(這也意味著和盜竊相分離),成為利用不真實的手段侵犯財產的犯罪。*Vgl. Maurach/Schroeder/Maiwald, Strafrecht BT I, 2003, § 41, Rn. 3 ff.之后,詐騙罪中的“欺騙”的含義被理解為與他人產生意思互動(交往),從而使對方陷入錯誤,由此,詐騙罪便以溝通交往作為其特征。換言之,直接針對他人認知施加影響,進而獲得財物的為詐騙,而直接針對物理世界加以操縱,進而獲取財物的為盜竊。即便是在不作為的環境下,也可以將某些不作為獲取他人財物的行為認定為詐騙,因為此情形中本該采取溝通交往行為,而被告人卻違反義務地沒有這樣做。*Vgl. LK-Tiedemann, 1999, § 263, Rn. 4, 22.
有鑒于此,單純地操縱某一物體,由于缺乏本應采取的溝通交往,該操縱行為本身便難以成立詐騙。具體而言,被告人為了不繳納電費或少繳納電費,事先采用不法手段,使電表停止運行的,被告人與受害人之間未發生溝通交流,只宜認定為盜竊(電力)。*參見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013頁。類似地,被告人潛入被害人家中拿走財物的案件中,也發生了緘默形式的財產轉移,此時,財物的位置改變不為被害人所知,即使被害人由此陷入認識錯誤,以為財物仍然處于原來的位置,也只宜認定盜竊。與單純操縱物件宜成立盜竊類犯罪相異的是,如果當事人在實施操縱行為后,將該錯誤信息傳遞給被害人,之后獲取財產性利益,比如,偽造文書后使用該“文書”以獲取經濟利益以及改動商品價簽后拿此商品結賬,那么,一旦發生后續的溝通交往行為,則應認定詐騙,至于前面的操縱行為,只是詐騙的預備行為。*同前注⑤,Tiedemann文,第263條,邊碼23。在騙免電費的案件中,被告人正常大量用電后,在電力公司人員即將按電表收取電費時,產生不繳納或少繳納電費之念,于是使用不法手段將電表數調到極小數值,使收費人員誤以為沒有用電,從而免除其電費繳納的,亦屬詐騙行為。*參見前注⑥,張明楷書,第1013頁。操縱行為只是詐騙的預備行為,而之前的用電行為則為合法行為。
在我國1949年后歷次刑法草案中,除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大綱草案》第142條有列明“以詐欺方法騙取他人財物者,為詐欺”外,其余皆只表述為“詐騙他人(或公私)財物”。在作為當時我國立法重要參考的蘇俄刑法中,1922年《蘇俄刑法典》即規定:“作虛偽的報道,或故意隱瞞應當進行報道的情況的,都是欺騙行為。”直到20世紀50年代,蘇聯刑法學中仍流行以“虛偽報道”和“隱瞞應報道的情況”這兩種表現形式作為“欺騙”的定義。該“所謂虛偽的報道,應當理解為對下述一定情況的報道,即對過去或現在實際上都不存在的情況說有”。*參見蘇聯司法部全蘇聯法律科學研究所編:《蘇維埃刑法分則》,中國人民大學刑法教研室譯,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283-284頁。由此可見,在蘇聯刑法學中,以“報道”作為溝通交流的標志,其“欺騙”也具有明顯的意思互動含義。在我國晚近司法實踐中,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有如下一件指導性案例。*參見《關于印發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九批指導性案例的通知》(2017年10月12日):“董亮等四人詐騙案”(檢例第38號)。
[騙領車費案]2015年,某網約車平臺注冊登記司機董某等四人,分別用購買、租賃未實名登記的手機號注冊網約車乘客端,并在乘客端賬戶內預充打車費十元、二十元不等。隨后,他們各自虛構用車訂單,并用本人或其實際控制的其他司機端賬戶接單,發起較短距離用車需求,后又故意變更目的地延長乘車距離,致使應付車費大幅提高。由于乘客端賬戶預存打車費較少,無法支付全額車費。網約車公司為提升市場占有率,按照內部規定,在這種情況下由公司墊付車費,同樣給予司機承接訂單的補貼。四被告人采用這一手段,分別非法獲取網約車公司墊付車費及公司給予司機承接訂單的補貼4萬元到6千余元不等。法院認定被告人董某等四人行為構成詐騙罪,分別判處其有期徒刑一年到八個月不等,各處罰金人民幣一千元。
針對該案,案例發布方指出:“在網絡約車中,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通過網約車平臺與網約車公司進行交流,發出虛構的用車需求,使網約車公司誤認為是符合公司補貼規則的訂單,基于錯誤認識,給予行為人墊付車費及訂單補貼的行為,符合詐騙罪的本質特征,是一種新型詐騙罪的表現形式。”*同上注。可見,在指導性案例中,也明確以“交流”作為認定“欺騙”的前提特征。當然,若該“交流”并無實際的意思互動內容,*例如,向ATM機輸入自己猜的密碼,則只能算是機械性的程序處理,和普通詐騙罪(不等同于機器詐騙罪)所要求的真實的意思互動有所區別。則宜認定為盜竊而非詐騙。
(二)意思互動標準在案例中的應用
以上對詐騙罪有別于盜竊罪之處進行了相應的理論梳理,得出應將詐騙罪理解為溝通交流型犯罪的結論。溝通交流意味著被告人和被害人之間發生意思互動,被告人做出了相應的表意,而被害人也進行了相應的判斷。借助該意思互動的標準,可以更為明了地處理如下案件。
[二維碼案]某大學校內有一便利店,店主把女兒的支付寶和微信二維碼貼在柜臺上,方便顧客進行電子支付,一天,張某趁店主上廁所的間隙,把店主柜臺上的支付寶收款二維碼調換成自己的收款二維碼,一周后,店主才發現二維碼被換,此時,張某已經獲利1800元。
該案在我國引起了民眾議論盜竊、詐騙之區分的盛況。通常情況下,收款人會在付款人離開之前確認是否收到其所付款項,故而,一般認為,該種案件只會在如下場合發生:單筆支付較大數額時,付款人聲稱已付款成功但網絡延遲,在獲得收款人允許后離開交易場所。然而,現實生活往往超出人們的一般想像。針對在廣東佛山已經發生的飯店支付二維碼被換的真實案例,*參見馮雷亮、張聰:《飯店二維碼被換,營業款進了賊包》,《南方都市報》2016年11月29日,第FB06版。有觀點指出,該案店家從未“占有”顧客要轉讓的銀行債權,故被告人所侵犯的是顧客而非店家的財產,顧客陷入認識錯誤而處分自己財產,進而給店家造成損失,屬于一種新類型的“三角詐騙”。*參見張明楷:《三角詐騙的類型》,《法學評論》2017年第1期。這種觀點,正是對“緘默形式的財產轉移”缺乏合適的理解,以至于將未發生具體溝通交流的盜竊案件,扭曲認定為詐騙案件。在該案中,被告人與店主、顧客之間均未發生針對財產決策的溝通交流或意思互動,被告人只是通過操縱二維碼抽象地使店主、顧客等人陷入行為錯誤之中,他并未拿著該二維碼明白地向對方收錢,故不應肯定被告人欺騙了顧客。在店主明示交付渠道的條件下,顧客更無義務對支付渠道之真假予以追查,故無所謂陷入認識錯誤。顧客的掃碼行為,充其量只是“轉移錯誤”。*參見王安異、許姣姣:《詐騙罪中利用信息網絡的財產交付》,《法學》2015年第2期。因此,該案被告人正是利用“緘默形式的財產轉移”,占有了本應由店主收取的錢款。除“二維碼案”這類新型的案件外,在現實生活中,“緘默形式的財產轉移”更常表現為如下案件。
[找零案]李某在購買家電后的支付過程中,賣家陸某看錯了李某付款數額(多看了一個零),進而多找給李某數千元,李某收到錢后默不做聲地拿走。
此情形與前述[捷安特自行車案]一樣,均涉及詐騙罪、盜竊罪、民法上的不當得利等問題。在這兩起案件中,由于某甲與李某針對財產轉移均缺乏任何積極的表示,如果對之皆以盜竊罪(或所謂“公然盜竊”)論處,則明顯過于嚴厲,畢竟在這兩起案件中,被告人與被害人雙方皆處于一個具體的溝通交流場景中,且被害方都出現了溝通交流上的疏忽和過失。如果應以詐騙罪處理,便只可能成立“隱瞞真相”的詐騙罪,而某甲與李某似乎也缺乏刑法上的保證人地位,那么,其應當以作為形式還是不作為形式的詐騙罪論處呢?由此便有必要先對詐騙罪的成立條件和不同形態做一分析。
三、隱瞞真相:默示詐騙抑或不作為詐騙
“緘默形式的財產轉移”不僅造成了盜竊和詐騙的界分難題,而且在詐騙罪的內部,也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詐騙罪不同形態之間的界限。在刑法原理上,詐騙罪分為積極形式的詐騙和消極形式的詐騙。其中,積極形式的詐騙體現為作為形式的詐騙,它具體又可分為二種:明示形式的詐騙和默示形式的詐騙。消極形式的詐騙,即指不作為形式的詐騙。作為形式的詐騙和不作為形式的詐騙之區分,在刑法理論上有著重要的意義。前者不限犯罪主體,任何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被告人,只要實施了相應的欺騙行為,皆可能成立詐騙罪;后者則只限于具有相應保證人地位的被告人才能構成,不具備刑法上的保證人地位,就缺乏排除相應危險的保證人義務,此時即便對方陷入認識錯誤、轉移財產,也不能成立不作為形式的詐騙罪。
(一)默示詐騙和不作為詐騙的區分標準之梳理
在我國《刑法》第266條中,“緘默形式的財產轉移”對應于“隱瞞真相”這一表述。在我國的刑法教科書中,很容易找到如下解釋:“隱瞞真相……是指掩蓋客觀存在的事實,使人產生錯覺……隱瞞真相既可以是作為的形式,也可以是不作為的形式”“隱瞞真相,即隱瞞客觀上存在的事實情況,既可以是隱瞞部分事實真相,也可以是隱瞞全部事實真相”。*王作富主編:《刑法分則實務研究》,中國方正出版社2013年版,第957頁;同前注①,高銘暄、馬克昌主編書,第504頁。類似理解,同樣見諸蘇聯刑法學,即“所謂隱瞞,不應當僅僅理解為積極的作為,即掩蓋其重大的缺點。隱瞞也可以表現為不作為,即對某些情況緘口不言。被害人如果知道一種事實便會終止實施某種行為,這樣的事實就是應當報道的事實。”同前注⑩,蘇聯司法部全蘇聯法律科學研究所編書,第284頁。然而,另一種有影響力的觀點認為:“不作為的詐騙罪,是指行為人負有特定的告知真相之義務卻隱瞞不告,致使被害人陷入或維持錯誤,因此處分財產并遭受財產損失的犯罪……從規范的角度來評價,隱瞞真相是指行為人負有告知真相的義務卻故意不予告知的行為,這顯然是不作為。”*王剛:《論不作為的詐騙罪》,《政治與法律》2015年第2期;參見前注③,陳興良、陳子平書,第273頁。有鑒于此,“隱瞞真相”究竟是單指不作為形式的詐騙罪,還是既指不作為詐騙,也包括默示形式的詐騙,就出現了分歧。應該承認,默示形式和不作為形式的詐騙存在明顯的相似性,被告人所告知對方的事實皆不完整,被害人接收該種信息后,均在決定性的問題點上產生了偏差性理解。*NK-Kindh?user, 2013, § 263, Rn. 146.換言之,被告人均對事實保持了緘默或者都隱瞞了真相,只不過在默示詐騙場合,被告人實際上表達出了某種意思(即所謂隱瞞部分事實真相),而在不作為的場合,似乎沒有這種意思(即所謂隱瞞全部事實真相)。因此,宜將“隱瞞真相”解釋為包括默示形式和不作為形式的詐騙這兩者。然而,如何區分默示形式和不作為形式的詐騙呢?對此,理論上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如下幾種。
第一種觀點(“意思表示內容說”)認為,*S/S-Cramer/Perron, 2010, § 263, Rn. 11 f., 18; Fischer, StGB, 2011, § 263, Rn. 14; Küper, Strafrecht BT, 2008, S. 287; MK-Hefendehl, 2006, § 263, Rn. 87.積極的詐騙以其具有特定意思表示的內容為要件,明示和默示詐騙皆然。該意思表示的內容以意思表示的對象的理解作為其認定根據。默示詐騙的意思表示內容,則借助各個交往情境下的社會經驗以確定風險和說明責任的分配,進而決定哪些是應予以默認的意思表示內容。在默示詐騙和不作為詐騙的區分上,該學說以明白表達出的內容和未表達出來的內容二者之間是否存在事實聯系為判斷標準:有,則為默示的詐騙;無,則為不作為形式的詐騙。除非根本不存在任何作為,或者作為和認識錯誤之間缺乏任何關系,才可考慮不作為。不作為詐騙的認定,以被告人具有相應的保證人地位為前提,這種保證人地位使其負有說明義務。他必須履行這種義務,以糾正對方事先陷入的認識錯誤。
第二種觀點(“致損局勢說”)提出,*Vgl. Kühne, Gesch?ftstüchtigkeit oder Betrug, 1978, S. 35 ff., 42.如某種局勢使得被告人和被害人間出現了互動、交往和促成自損所必要的便利,那么,就宜以是否造成此種“引發損害”的局勢(即“致損局勢”)作為辨別默示詐騙與不作為詐騙的標準。如果被告人主動觸發了這種“致損局勢”,則可認定其引起了對方的認識錯誤,屬于默示的欺騙;如果只是利用既已存在的局勢的,則為不履行說明義務(不作為形式的詐騙)。
第三種觀點(“不作為詐騙否定說”)直接否定了認定不作為詐騙的必要性,其認為,詐騙罪以促成認識錯誤的(明示或默示)誤導性意思表示為其內容,不存在缺乏意思表示內容的(純粹)沉默形式的詐騙。*Vgl. Herzberg, Unterlassung und Garantenprinzip, 1972, S. 72, 81 f.如果積極形式的詐騙以具有意思表示內容的舉止為必要,那么基于不作為犯中的“等值性”原理,不作為詐騙亦需意思表示內容。“沉默”通常鑲嵌在主動的舉止之中,這就使得該種舉止從總體上可認定為默示的欺騙,因此,盡管會有不作為詐騙的表象,但詐騙罪在實際上便只有作為這一形態。
第四種觀點(“被害人反應說”)則認為,意思表示的內容并非決定性的標準,而是需依照社會交往的經驗,根據不同的交易類型抽取出其中的風險分配標準,這種分配標準決定了被告人在明白宣稱的具體信息之外,默認了以哪些其他信息為前提。*Vgl. LK-Lackner, 10. Aufl. § 263, 1988, Rn. 29 ff., 53 f.默示詐騙和不作為詐騙一樣,被告人均違反了說明義務。如果受騙者在信任被告人合乎義務地行事的前提下,從被告人的舉止中得出了錯誤的結論,則為默示的詐騙;倘若受騙者事先已陷入認識錯誤或從它處得到錯誤信息,那么,宜認定為不作為的詐騙。從被告人一方而言,則應以被告人引發了認識錯誤作為認定默示詐騙的標準。
以上諸種觀點皆存在一定的局限。第一種觀點采用“意思表示的內容”作為其區分的標準,應該承認其在多數情況下的可行性。依此觀點,容易得出[找零案]中的某甲缺乏保證人地位,不成立不作為詐騙罪,其行為宜以民法上的不當得利論處。*參見前注,王剛文,第39-40頁。然而,第一種觀點的不足之處在于,其確定“意思表示之內容”的方法是依靠被害人的期待是否產生認識錯誤來確定的,而這通常是在欺騙行為之后的第二步才予以考慮的,如此有架空欺騙行為這一認定步驟之嫌;*Vgl. Wittig, Das tatbestandsm??ige Verhalten des Betrugs, 2005, S. 257.在認定默示詐騙的意思表示內容上,該觀點主要借助的是社會交往經驗上哪些屬于默認的前提來判定,可問題是,如果處于新興的交易方式中,尚不存在固定的交往經驗,似難以得出交易方應對哪些內容做出說明。*Vgl. Frisch, FS-Jakobs, 2007, S. 102.
第二種觀點的局限在于,過于強調被告人的“主動”動作,例如,某甲在未接受任何委托的條件下,有目的地向某乙出售屬于某丙的蘋果電腦,是被告人創設了“致損局勢”;若某甲突然從某乙處得到一個要約,要購買某甲手頭的蘋果電腦(該電腦實為某丙所有),某甲當場同意,也應認定某甲默示了其有處分權。*參見前注,Kindh?user文。既然如此,被告人是否主動地創設了“致損局勢”,就不是關鍵。
第三種觀點的問題在于,其要求不作為詐騙也需有誤導性意思表示的內容。然而,在不作為的場合,當事人的行為并不直接包含某種意思表示。例如:[騙取養老金案]2003年3月到2006年7月間,被告人郭某某隱瞞其公爹趙某某死亡真相(其公爹趙某某已于2003年3月死亡),繼續領取趙某某生前所在單位鄭州鐵路局洛陽工務段養老金共計人民幣28687.8元。河南省衛輝市人民法院認定,被告人郭某某在法律上具有“告知”的義務,詐騙罪成立,判處有期徒刑1年零3個月,并處罰金3000元。*參見張淼主編:《刑事案件訴辯審評——詐騙罪》,中國檢察出版社2014年版,第186頁以下。
第四種觀點以被害人的表現作為區分標準,偏離了“國家—行為人”的刑法模式,使得被告人受不受刑事處罰,不再取決于是否違反刑法規范,而受制于被害人不確定的事后反應。*Vgl. Maa?, GA 1984, 266 f.; S/S-Cramer, 2001, § 263, Rn. 15.并且被告人默示表達出的內容,也屬于已表達的信息,不能將之與他有義務予以說明的內容相混淆,畢竟后者屬于尚未表達出來的內容。例如,被告人出售屬于他人的某貴重物品,他實際上是默示地欺騙對方他擁有處分的權利(默示的詐騙),然而,在出售行為作出之后,他才具有清除對方的認識錯誤的說明義務(不作為的詐騙)。*參見前注,Kindh?user文。由于不作為乃是從屬于作為的,屬于對作為犯的補充,此時只能認定作為形式的默示詐騙。
(二)“意思表示的內容說”在案例中的應用及其修正
盡管存在以上不同的觀點,但采取第一種觀點(“意思表示內容”說)顯然更容易找到判斷案例中發生的行為是默示詐騙還是不作為詐騙的標準。
[操縱足球比賽案]被告人某甲具有多年體育博彩經驗。自2000年起,他積極投注,年獲利(歐元)達六位數。他對體育的了解,使得其相對于博彩商經常擁有優勢,并獲得可觀利潤。鑒于該高額盈利,柏林地方博彩商限制了他的購彩機會。2003年后,他只被允許在一特定博彩商處下注,在該處他只能獲得“全歐最差的勝率”。他還只被允許購買組合彩票(即同時投注不同場次的比賽),而不能光投注一場比賽。到次年春,他累計虧損30萬至50萬歐元,以至于他決心通過行賄球員和裁判來影響比賽,進而提高投注勝率、扳回損失。他當然沒讓博彩商知情,以免失去購買彩票資格。他一共作案十起并針對每場比賽下注。在他同伙的協助下,他以三千到五萬歐元不等的價格成功收買了裁判某乙、某丙和運動員某丁等人,使他們錯誤裁判和消極比賽以操縱比賽結果。涉嫌的比賽包括地區聯賽、聯邦次級聯賽等。有的場次某甲操縱失敗,有的組合彩票則受制于其他場次的結果也未能中獎。他中了其中四注,并由此獲得明顯收益(介于30萬到87萬歐元之間),剩余賭注則歸于失敗。*BGHSt 51, 166 f.
該案審理過程中,法院作出了如下的認定。某甲在交付對賭憑證時即默示地表示,未參與操縱對賭對象,他借此欺騙了博彩商,使后者陷入錯誤,并與之簽訂了后來造成損失的合同。從合同要約中可以默示地推出,賭方未以違法操縱的方式破壞對賭之前提,隱瞞操縱事實意味著其以行為表象實施了欺騙。在默示欺騙的場合,被告人并不以明示的言語,而是利用交往上的經驗通過其舉止傳遞虛假信息。舉止中蘊含的意義,不僅可從溝通交流明白表達出的內容得知,而且也可以來自于對當時具體情形的總體判斷。該未予明示的內容主要取決于聽者的合理期待,該期待又受制于具體的交往圈及相應的法律規則。對于充當法律行為的舉止而言,決定性的標準除各交易類型的具體情況外,還包括交易雙方之間典型的義務分配和風險分配。法官通常可從交往經驗和法律規則所框定的諸種期待中推導出默示型交流的實際內容。該推導過程受制于規范性的期待,并不會導致意思表示上的“擬制”。判例也已根據各交易類型和義務、風險分配歸納出默示型交流的典型內容。默示表示的內容,還可以是未發生某種事情(即所謂“消極事實”),就像一項投標便應以投標者之間不存在事先的價格協議為其實現前提。當事方交往所針對的合同標的不應受到故意的操縱,更是屬于默示表示中的“消極事實”。體育博彩是一種射幸性質的賭博游戲。此時的合同標的乃是尚未受博彩當事方影響的預定賽事。當事方在買賣彩票之時便認可此標的。簽約時各方均默示地聲明:標的上的風險沒有不利于對方地被自己操縱、改變。不僅售賣方對購買方有此期待,反之亦然。當事人根據其操縱球賽之計劃開始施加具體影響之時(如事先收買球員,并得到對方同意),便已可成立欺騙了。僅在該場合,他才會大量投注在不太可能出現的比賽結果上。默示欺騙異于不作為欺騙之處在于從當事人積極的舉止中可得出的表示內容。因此,若意思表示已可視為欺騙行為,法官便通常應重點考察積極的作為,而非不作為。被告人需保證交易的基本條件未被破壞。在本案中,締約這一積極舉止,即為刑法關注的欺騙行為,以合同標的未受影響為其表示內容。既然已有積極作為的欺騙,便無需討論不告知操縱行為的不作為詐騙了。*同上注,第167頁以下。
以上案例運用第一種觀點的方案加以判決,已顯示了該種方案的實際操作性。然而,其并未解決第一種觀點存在的不足,即先判斷被害人認識錯誤后認定欺騙行為的順序倒置,以及未明確在不典型或新興的交易模式中,如何認定被告人所傳遞的虛假信息。因此,宜對其做一修正:如果在被告人與被害人進行“信息傳遞”過程中,被告人就財產決策的有關事項明確地表達了虛假的信息(此為意思表示的內容),或者以無瑕疵的表面舉止為表象(即信息的載體),默示地傳達了虛假的前置性信息(此為意思表示的內容,例如,某人若發出締結買賣某財物契約的要約,則該要約在邏輯前提上默示地表明,其有權轉讓該財物),則為作為形式的詐騙;不作為則相反,它缺乏這樣一個“信息傳遞”過程。*Vgl. Kindh?user, FS-Tiedemann, 2008, S. 579 ff.借助該修正式方案,可以更為合理地分析如下案件。
[贖表案]甲和朋友乙到一當鋪,將自己典當的手表贖回。在贖回過程中,工作人員錯將別人典當的名貴手表取出并打算交給甲。甲見狀正想告訴工作人員實情時,乙卻向甲使了個眼色,并佯裝說他們還有要事待辦,要求工作人員快點。甲會意后,即刻取過該名表離去。
在該案處理上,有的觀點認為,應直接以誠實信用原則確認當事人具有告知義務,進而成立不作為詐騙罪。*參見常磊:《不作為的詐騙罪與不當得利的界分》,《時代法學》2009年第3期。更值得關注的是另一種“區分性方案”觀點:*同前注,王剛文。第一種情形,如果工作人員的錯誤認識已經定型,不再準備通過其他舉措來最終確認手表的歸屬時,乙說的話對工作人員處分手表的行為不會產生實質影響,因而不具有等價性,不成立詐騙罪;第二種情形,如果工作人員的錯誤認識尚未定型,還準備通過其他舉措——核對典當合同、向甲詢問、請其他工作人員協助確認等來最終確認手表歸屬的,乙說的話客觀上強化了工作人員的錯誤認識,工作人員因此不再確認而直接交付手表的,可以構成不作為的詐騙罪。甲認可了乙的行為并隱瞞真相,基于誠實信用原則產生的告知義務在此情況下具備了刑法意義,甲與乙構成詐騙罪的共犯。
就[贖表案]而言,案情的表達需進一步細化,此點并無疑問。在工作人員的錯誤已經定型的條件下,是工作人員一方自己陷入錯誤,甲、乙不負有清除錯誤的保證人義務,不成立不作為詐騙,也無疑問。有疑問的是第二種情形,此時工作人員的錯誤認識尚未定型(處于“懷疑”狀態),還準備進一步核查,乙卻阻止了甲的“信息傳遞”,進而中止了對方的核查流程,最終消除了雙方進一步溝通的可能性。此并非不作為詐騙,而是“信息傳遞”過程中發生的作為形式的詐騙,乙聲稱的“還有要事待辦,快點吧”加上甲的配合性緘默,讓對方得到了“整個交易沒有錯誤”的信息,由此導致工作人員不再懷疑,真正地陷入認識錯誤。甲乙共同成立默示形式的詐騙罪。如果在第二種情形中認定為不作為詐騙,那就應基于誠實信用原則來論證甲、乙具有保證人地位,而在詐騙罪原理上,單憑誠實信用原則一般不足以論證保證人義務的成立,由此便無法得出成立不作為詐騙的結論,進而只能以無罪處理。司法實踐中,更為明顯的不作為詐騙案件如下。*參見前注,張淼主編書,第46頁以下。
[何某詐騙案]被告人何某(女)因女兒賈某杰與被害人章某亢談戀愛而與章某亢相識。二人戀愛期間,被害人章某亢先后以賈某杰的名義在鎮江市和北京市分別購買了一處房產。其中在鎮江市所購得房產價值56萬元,系由章某亢直接付款方式購得,在北京市購買的房產價值180余萬元,是由章某亢將錢款打入賈某杰賬戶后由賈購得。2009年7月初,被告人何某明知賈某杰已決定和章某亢終止戀愛關系,并于同年9月29日至北京與賈某杰新男友任某生見面,雙方商定于同年10月6日訂婚,10月16日舉行結婚儀式,11月12日登記注冊結婚。同年10月5日何某至內蒙古呼倫貝爾市任某生家中參加賈某杰與任某生的訂婚儀式。從2009年7月至同年11月,何某為了能夠繼續保留章某亢出錢購買的兩處房產,一直對章某亢隱瞞賈某杰已與他人戀愛并準備結婚的事實,假裝同意兩人繼續保持戀愛關系,又先后4次騙得章某亢人民幣87.8萬元占為己有。鎮江市經濟開發區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何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女兒與他人談戀愛之機,隱瞞事實真相,明知女兒已與他人訂婚和即將結婚,以欺騙的方法,騙取他人財物87.8萬元,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構成詐騙罪,依法應予懲處。依照我國《刑法》第266條、第61條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關于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被告人認罪案件”的若干意見(試行)》第9條之規定,被告人何某詐騙罪成立,判處有期徒刑10年,并處罰金10萬元。
該案中,何某在同意女兒與他人成婚(先行行為)后,仍向被害人隱瞞真相,致使對方給予其80余萬元財物,屬于不作為形式的詐騙。在賈某杰結婚后,何某之后續行為并無變化,難以推導出戀愛關系存否的明確結論,故不為默示詐騙。*關于先行行為的不作為犯罪,我國《刑法》未予規定,在我國臺灣地區的有關規定中有“因自己行為致有發生犯罪結果之危險者,負防止其發生之義務”之字樣,在《韓國刑法》(1988年修訂)第18條中亦有“負有防止危險發生的義務或者因自己的行為引起危險,而未防止危險之結果發生的,依危險所致的結果處罰”之表述,可資參考。若對[捷安特自行車案]略做修改,即“顧客某甲到自行車用品店選購了一款山地自行車,某甲與老板某乙一陣討價還價后商定好4700元的賣價。接著,某甲對某乙說‘您忙您的,我到老板娘處付款’,某乙于是就在一旁忙著修車。老板娘某丙見某乙未一同進入,以為已經付過款。某甲此時覺得有機可乘,在開好發票后,便大搖大擺將車騎走。事后,老板和某乙夫婦才發現未收款”,則宜成立基于先行行為的不作為詐騙,因為顧客依約需向某丙付款,某丙陷入認識錯誤,乃是由于顧客事先排除某乙的付款請求權所致,某乙有義務清除某丙的認識錯誤。此外,我國《保險法》第16條規定了投保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針對有關事項的告知義務,有觀點認為,可以基于該告知義務認定隱瞞相關事項者為不作為詐騙犯。*參見張明楷:《詐騙罪與金融詐騙罪研究》,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頁。在筆者看來,如此認定或有疑問,因為以保險法上的義務作為不作為詐騙罪的保證人義務,不僅可能使刑法從屬于其他部門法,而且這似乎在我國找不到相應案例,即使違反了告知義務,在實踐中也多以民事糾紛處理。
四、詐騙犯罪中要求真實信息的權利
在不作為詐騙的場合,通常需要考察當事人是否具有保證人地位。然而,無論是在作為形式的犯罪中,還是在不作為形式的犯罪中,實際上均存在一種廣義的保證人地位,即當事人應當避免法律所要求他避免的事情,他必須保證不侵犯到法律所保護的權益。可見,作為和不作為之間在規范邏輯上有一定的相通性。*同樣注意到不純正不作為犯違反“不得實施某種犯罪”之誡命的,參見前注,王剛文;趙書鴻:《意思說明與說明義務違反:論詐騙罪中的欺詐行為》,載劉志偉、王秀梅主編:《時代變遷與刑法發展》,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613-614頁。有觀點指出,詐騙罪的三分法(默示詐騙、明示詐騙和不作為詐騙)是一種“現象式”的概念,是否成立詐騙,取決于是否給具備合理信任感的被害人造成了這樣一種假象,即進行財產處分的特定事實性條件已經滿足,而實際上該事實性條件并不存在。*Vgl. Frisch, FS-Herzberg, 2008, S. 753.因此,在詐騙罪中,作為和不作為的詐騙,只是在表現形式上有所不同:明示和默示詐騙是從被告人的言行本身即可直接得出或明確推導出相應的錯誤信息,而不作為詐騙則無法從其言語、行為本身直接得出或明確推導出相應的錯誤信息,只有結合其保證人的義務,才可以(間接地)“擬制”出錯誤信息。*在不作為詐騙的場合,并不存在作為形式的詐騙中“那種形式”的意思表示的內容,之所以也認定為詐騙,并非因為其“形式”與作為犯的相同性,而是由于效果上的可類比性。似乎偏離的觀點,參見前注,趙書鴻文,第611、615頁。依該觀點,“詐騙罪中的欺詐并不是具有意思表示的價值的行為”,這有欠準確,畢竟作為形式的欺詐是有“意思表示的價值(即內容)”這種形式的,準確的表述應是“詐騙罪中的欺詐并非皆屬有意思表示的價值的行為”。盡管有如上表現形式上的區別,但從本質上講,無論明示形式、默示形式,還是不作為形式,被告人在侵犯財產之時,均侵犯到了對方要求真相的權利。換言之,任何形式的詐騙罪,即如“虛構事實、隱瞞真相”所言,皆以違反真實義務為其內容。*參見前注,Kindh?user文。然而,我國理論界對溝通交流中“要求真相的權利”似乎存在誤解。如有觀點指出:“詐騙罪中,當雙方信任關系升高時,存在認知優勢的欺詐人處于特定的保證人地位,他有義務避免因自己行為而給被害人財產造成損害的危險。但欺詐人卻利用自己認知上的優勢,積極控制和支配了這種危險,從而造成了被害人財產的損害。”*同前注,趙書鴻文,載同前注,劉志偉、王秀梅主編書,第615頁。如果這種表述成立的話,又應如何將詐騙從背信類犯罪(例如,我國《刑法》第169條之一“背信損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和第185條之一“背信運用受托財產罪”)的犯罪行為中區別出來呢?
(一)信息赤字的防止及要求真相之權的演變
既然欺騙行為以侵犯到對方要求真相的權利為其核心特征,那么,何時足以認定該權利遭受到侵犯了呢?有學者認為:“當被害人本有權從行為人處獲悉完整、準確的諸種信息卻未能獲知時,則可認定真相權利遭遇了侵害……這并不取決于欺騙是明示地、默示地,還是以不作為形式發生。毋寧說關鍵之處在于,是否應由被告人對被害人獲知特定的信息及其出現的信息上的赤字負責。”*Pawlik, Das unerlaubte Verhalten beim Betrug, 1999, S. 97.該學者繼續指出,在當代的詐騙罪中,有權要求真相的人,并非接受到虛假信息的任何人,而只是其中那些遭受到相應財產損失的財產持有者。*參見上注,Pawlik書,第83頁。如此理解,限制了可以要求真相的權利者范圍,表面上似乎體現出了刑法的所謂“謙抑性”特征,然而,這種主張其實是歷史的產物,而非法政策上的一時興起。
在歐洲,詐騙罪起源于羅馬法中的盜竊以及偽造之罪。在中世紀德國法里,存在一種包含有今日詐騙、偽造文書以及盜竊三種犯罪的混合型犯罪,它不區分不純正(正宗)罪(Unechtheitsverbrechen)和不真實罪(Unwahrheitsverbrechen),以致本來含義的詐騙和偽造合在一起被稱作“作偽”。有的法律還將任何隱秘形式的財產損害(尤其是盜竊),也稱為“作偽”。*參見前注④,Maurach/Schroeder/Maiwald書。在這種情況下,詐騙罪所保護的內容便是籠統的要求真相之權利。*Vgl. Mittelalterliches Kriminalmuseum, Justiz in alter Zeit, 1984, S. 304.這樣,人們在社會交往中,對幾乎任何事項都事無巨細地負有說明的義務,如此寬泛的說明義務,在中世紀那種較慢的社會經濟運轉中是可以實現的,但在進入機器大生產的近代以后,整個社會經濟生產力出現了跨越式發展,如此苛刻的詐騙罪條款便成了經濟交易的壁壘。它不僅降低了社會經濟交往的效率,也不符合人們日益覺醒的基本權利需要。于是,在法國大革命之后,借助1810年《拿破侖刑法典》,詐騙罪開創了以保護財產為其內容的現代法律傳統。該法典第405條規定:“利用錯誤的名號、描述或欺騙性的方法,以使人陷入錯誤的推斷或相信虛構的方法及其可行性,或者使人對某種成敗或其他虛構事件產生期待或畏懼,從而獲得他人給予或交付的任何資金、動產、債券、處分權、票據、允諾(付款)、債務免除或債權讓予;或者以此類任何方式欺騙性地獲得或試圖獲得他人財產之全部或一部,應處以不低于一年,不超過五年的監禁,并處不低于50法郎、不高于3000法郎(罰金)。”*http://www.napoleon-series.org/research/government/france/penalcode/c_penalcode3b.html ,2017年10月19日訪問。有鑒于此,現代詐騙罪所保護的,不再是任何事項的真實性,只有財產決策之相關事項的真實信息,才屬于詐騙罪關注的內容。*參見前注,Cramer/Perron 文。將詐騙罪的法益從普遍的真相轉移到財產之上,大大縮小了詐騙罪所要求的真實信息的范圍,進而降低了財產刑法對經濟活動的限制程度,在增強財產刑法的可操作性的同時,也推動了市場經濟的發展。
現代的詐騙罪理論普遍將詐騙罪定位為“侵犯財產罪”,此點為中外刑法的通例。結合被告人侵犯對方要求真實信息之權利,詐騙罪自應如此理解:若被告人以侵犯財產權方要求真相之權利的方式造成了財產權方的財產損失,則應以詐騙罪論處。此時,無論是作為、不作為,皆被包含于內。緘默形式的詐騙罪,即便其可能兼具作為和不作為兩種形式,在行為不法上,也以侵犯財產權方要求真實信息之權利作為其本質。在盜竊案件中,被告人也處于緘默狀態,然其未與財產權方發生任何溝通交流,而是從更為根本的角度取消了對方溝通交流的機會。相對于詐騙案件而言,盜竊案被告人的這種行為,乃是對財產權方相關權利更為嚴重的貶損。盡管盜竊和詐騙同樣侵犯財產,在經濟上具有同樣的結果不法,但在行為手段上,盜竊的不法程度較之于詐騙不法更重。這也體現在我國的刑事立法之中:處罰盜竊罪以更低的數額起點為前提。在有關的司法解釋中,雖然沒有明確表達理由,但也間接地反映出了隱蔽手段的犯罪,應受到更重的處罰。例如,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的《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在電信詐騙中,“利用‘釣魚網站’鏈接、‘木馬’程序鏈接、網絡滲透等隱蔽技術手段實施詐騙的”,應“酌情從重處罰”。
(二)要求真實信息之權利的兩種限制
如前所述,現代的詐騙罪立法通常只保護財產流轉不受到他人的誤導,因此,只有與財產決策有關的信息,才屬于詐騙罪關注的對象。然而,當事人是否需要保證與財產決策有關的所有信息皆屬真實呢?此方面存在以下兩點限制。
首先,不影響理性地財產處分的信息,相應的交往方即不享有要求其真實性之權利。例如,商家在售賣汽車時,宣稱“這是世界上最好的汽車”或“全國銷量第一”,就不宜將該類廣告性質的信息列入詐騙罪的保護內容,除非商家認真地為其宣傳性口號提供有相應資質的品級證書和專業鑒定意見,一般不宜認為,商家需為此履行詐騙罪意義上保證信息真實的義務。由此也可推導出,誠實信用原則無法直接作為保證人義務的根據,不然,保證人義務的范圍將極為寬泛,進而脫離我國社會實情。*參見陳興良、陳子平:《兩岸刑法案例比較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75頁。盡管在日本,其判例廣泛承認誠實信用原則可充當告知義務的基礎,但在德國,除在二手車買賣中賣家有義務告知對方車輛的車損記錄和在長期業務合作關系中當事方有告知變故的義務之外,誠實信用原則卻并不當然地被視作保證人義務的來源。*參見[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論》,王昭武、劉明祥譯,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02頁;前注⑥,Tiedemann文。在我國的[捷安特自行車案]中,也有實務部門的觀點支持以誠實信用原則作為認定不作為詐騙罪的保證人義務來源,從而成立不作為詐騙罪,*參見前注②,李方政、張理恒文。然而,在筆者看來,其之所以如此認定,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避免成立盜竊罪。有鑒于此,筆者不贊成賦予誠實信用原則以刑法上的資格,故[捷安特自行車案]和[找零案]一樣,皆宜適用我國《民法總則》第122條規定的不當得利規則。
其次,要求真實信息之權利還會遇到的另一種限制是被害人同意。如果被害人明知被告人提供的信息屬于虛假,卻仍然作出財產決策,進而將財產轉移于他,也不能認定被害人要求真實信息的權利遭到了侵犯。當然,如果被害人并不明知該風險,只是懷疑可能有問題,無證據證明其虛假,即便信息的真實程度據當時估計低于百分之五十,也仍然不排除被告人詐騙罪的成立。*Vgl. BGHSt 34, 201 f.畢竟在許多案件中,被告人的詐騙行為無法做到百分之百排除疑點。除非被害人已經產生了特別嚴重的懷疑(該種嚴重程度的懷疑,已經不再適合稱作“懷疑”了),以至于只要被害人還是理性的,就不應轉移財產,此時,即應認定其進入了“明知”該風險的范疇,可以判定其具有故意并成立被害人同意。*參見前注,Kindh?user書;Rengier, FS-Roxin, 2001, S. 822 f.
五、結 論
在社會網絡化、信息化的過程中,人們的溝通交流方式發生著深刻的變化。人際間的溝通模式從以往占據主流的“面對面式”線下溝通,逐漸轉向依賴技術手段的線上溝通。線上溝通的特點使人們在信息傳遞方式上更有選擇性,這促成了溝通模式的多樣化、高效率,也使溝通交流出現了匿名、緘默的特點。溝通模式的變革,自然也影響到了財產犯罪的表現形式,新支付方式語境下的“二維碼案”便是其例。該案除涉及傳統財產刑法上盜竊罪和詐騙罪之區分這一問題外,還進一步引發了“溝通交流”在財產刑法中究竟占有何種地位的思考。人與人之間的言說,屬于溝通交流的應有之義。言說中附帶緘默以及完全的緘默,在溝通交流中也不時發生。在涉及財產的情形下,溝通交流便不再是單純的信息流通,已進入產權界定的領域。在財產犯罪領域,緘默條件下的財產轉移,既有可能涉及盜竊案件,也可能與詐騙案件有關。在詐騙罪內部,默示詐騙和不作為詐騙也都涉及對于緘默的含義及其地位的理解。在財產決策事項上完全排除被告人與被害人溝通交流要素的,由于未介入被害人的互動,宜以盜竊論處;若就財產決策事項與被害人發生了意思互動,則宜在被告人表示出與財產決策有關的某種虛假性信息時,成立作為形式的詐騙罪;在未表示出該類虛假性信息,進而只是不糾正對方已經發生的認識錯誤的情形下,則僅當具備相應的保證人地位,才宜以詐騙罪論處。在詐騙罪中,明示詐騙、默示詐騙和不作為形式的詐騙,只是在表現形式上存在不同:明示和默示詐騙是從被告人的言語、行為本身即可以直接得出或明確推導出相應的錯誤信息,而不作為詐騙則無法從其言行本身直接得出或明確推導出相應的錯誤信息,只有結合其保證人的義務,才可以(間接地)“擬制”出錯誤信息。無論是明示詐騙、默示詐騙還是不作為詐騙,均侵犯了被害方獲取與財產轉移決策相關聯的真實信息的權利。與財產轉移決策無直接關聯的信息,不屬于詐騙罪保護范圍內的內容。被害人明知財產決策所依賴的信息屬于虛假,卻仍然轉移財產,也不宜認定詐騙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