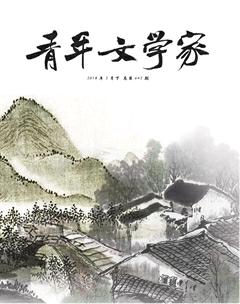音韻學中的語言論
作者簡介:楊峰(1987.7-),男,漢,浙江臺州人,碩士,現在溫州大學攻讀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碩士學位,研究方向:語言接觸研究。
[中圖分類號]:H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06--01
把語言論導入音韻研究是當代研究語音學的新思路,筆者對此做了一定的探索和嘗試,現在將在聲調和音韻學方面的一些思考總結如下,期待能拋磚引玉。
一、關于漢語聲調的起源和發展
首先反駁三個觀點:
1、只有漢藏語系有聲調
事實上所有的語言都有聲調,英文單詞book的主音節就能明顯聽出是個去聲,只不過漢藏語系的聲調是屬于音位系統,具有區分意義的功能。
2、藏語是受漢語影響而有聲調的
應該說是受漢語影響使聲調具有音位特性。
3、漢語缺少形態變化
任何語言在其初期,由于語法詞(各種虛詞)不發達,語序不嚴格,都是要靠形態的變化來達到語法目的的,漢語也不例外,只不過上古漢語由于獨字詞和不表音的特點無法在書面上記錄其內部屈折。
作為世界上僅存的古老語言,漢語文字是有獨特之處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其文字在誕生初期不是為了擬音的,而是擬物的。這在其他文明的古老文字中是普遍的。
六書之中最早的三種造字法——象形、指示、會意,是不和語音掛鉤的,由于漢文明的早熟,出現了這樣罕見的情況:中原地區書同文,話語完全各異,各地按照自己的方音去讀,但意義基本固定。進一步演化,形成了一字多音現象,這時的上古漢語由于虛詞及不發達,語序也不嚴格,需要有豐富的形態變化來達到語法目的。但由于漢語在上古時是單音節詞為唯一形式的,所以無法像其他表音語言由于使用多音詞而可以通過改變其中一個音節的音質或者通過增加音節的方式(前者為屈折語,后者為粘著語)來表現形態變化,于是作為單音節詞的漢語只能選擇變調的方式來體現其形態變化。
所以上古漢語不但有主動被動的形態變化,還有時態、性、格等的變化,可惜這些不同的聲調的單音節詞在書面上只能使用一個相同的字來表現。
總之,聲調在上古漢語是為了表現形態變化的,到了近代漢語,隨著大量雙音節詞的出現,其功能發生了改變,變成區分詞義的手段。
那現代漢語為什么缺少形態變化,那是因為漢語的虛詞發展已豐富,詞序也嚴格了,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形態變化了。由此可知,一種語言需要多少種語法范疇來完成表達是有一個定額的,在這個定額之內可以用這個多一點,或者那種多一點,總量差不多。這種現象套用一個物理學術語,我且稱為是一種“自洽”。
值得注意的是印歐語系中的多種語言出現了形態變化減少的現象,比如英語中的“性”這一語言范疇幾乎消失,“格”也只保留在人稱代詞中,“數”只剩下單數和復數,雙數消失。這時與其虛詞發展豐富后,語言的“自洽”作用有關的。
那是不是孤立語比其他語言類型要先進呢?這個結論下的恐怕為時過早。
二、音韻偽學考
當然不是所有的音韻書或觀點是偽學,但我敢說其中的百分之八十是的。我們的工作是要找出哪些是偽學,哪些是錯論。
試想古時并沒有全國性的統一發音,沒有拼音,沒有國際音標,連同一地區的方言都略有差異,古人移動能力有限,大部分人一生活動的范圍局限于本縣本省,對語音的差異有比較麻木。加上文讀和當地的發音迥異,生活中又不用,發音更是主觀臆想,十分隨意。所以,古人的讀音在空間上的差異一定比現在的要大。
從時間上看,古時沒有錄音設備,字詞讀音靠師生之間口口相傳,其變異、口誤、臆斷比比皆是。兩代以上其文讀音必迥異。
古代注音先是以字摹寫字音,后來受印度梵文影響用反切,但其實還是以字模擬字音,加上那些經師來之各地,更是以訛傳訛,韻書流傳,各地學習者又自行解讀、誤讀。
中國文字不表音,自身對讀音的約束性十分弱(因為讀音差異不會表現在文字上)。在這種種情況下,要保證相對一致的文字讀音是十分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所以古代的音韻學只能是地區性的,而且只適用于人口集中、商業發達的城市中。古人很可能對讀音會隨著時間空間的轉移而發生巨大變動的事實認識不清,故造成的問題也是巨大的。
首先,所謂的聲訓其實不足為訓。《說文解字》中的聲訓大部分為許慎根據當時當地的讀音去牽強附會,主觀臆斷,沒有科學性。但中國一直有信奉經典的傳統,所以聲訓具有八九分的偽學性。
其二,后代又根據聲訓去推斷那些字是同音共部的,也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即使推斷正確,那也只是許慎的那個時代那個區域的字音的情況,不能推而廣之、擅自臆斷。
三、結論
總之,現代的音韻研究已經十分充分了,在繼續埋頭故紙堆之前,我們是不先停下來做一做去偽存真的工作?這樣才不至于浪費時間和精力。
當代音韻的研究更應該注重現代性,研究當今的語音對現在行文,文學創作上的作用,研究如何使文章和作品更有音律美,我覺得意義更大。
參考文獻:
[1]薩丕爾. 語言論:言語研究導論[M].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2.13.
[2]高明凱,石安石 《語言學概論》[M].北京 中華書局,201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