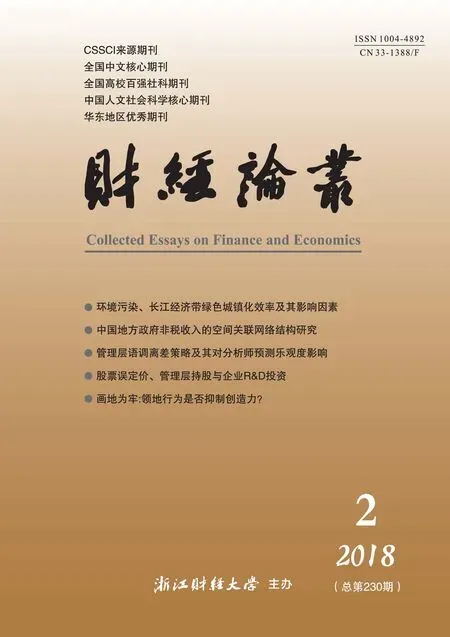環(huán)境規(guī)制、綠色技術(shù)效率與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
徐鵬杰
(聊城大學(xué)商學(xué)院,山東 聊城 252000)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經(jīng)濟(jì)發(fā)展取得巨大成就,但成績背后存在的地區(qū)經(jīng)濟(jì)差距和環(huán)境污染問題也逐漸凸顯。東部地區(qū)經(jīng)濟(jì)高速增長,但環(huán)境趨于惡化;中西部地區(qū)經(jīng)濟(jì)發(fā)展滯后,而環(huán)境容量則相對(duì)富余。那么,在考慮中西部地區(qū)環(huán)境承載力的前提下,通過促進(jìn)污染密集型行業(yè)的合理區(qū)際轉(zhuǎn)移,成為緩解東部地區(qū)環(huán)境危機(jī)與助力中西部地區(qū)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合理選擇。鑒于東部地區(qū)對(duì)資本的吸引力大于中西部地區(qū),因此促進(jìn)污染密集型行業(yè)合理轉(zhuǎn)移有必要從環(huán)境規(guī)制層面進(jìn)行頂層設(shè)計(jì),通過增加污染企業(yè)生產(chǎn)成本,使其主動(dòng)遷出東部地區(qū)。然而,如果地方政府對(duì)污染企業(yè)的依賴性較強(qiáng),便可能出于自身利益考慮而阻止企業(yè)遷出,因此還需通過促進(jìn)綠色技術(shù)進(jìn)步,使政府財(cái)稅來源向新興綠色產(chǎn)業(yè)傾斜,以削弱污染企業(yè)遷移的體制障礙。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促進(jìn)污染密集型行業(yè)合理轉(zhuǎn)移,實(shí)現(xiàn)地區(qū)均衡可持續(xù)發(fā)展,有必要首先厘清環(huán)境規(guī)制、綠色技術(shù)效率與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的關(guān)系。
環(huán)境規(guī)制對(duì)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的影響是學(xué)者們爭論的話題,多數(shù)學(xué)者對(duì)此持肯定意見[1][2],但也有學(xué)者認(rèn)為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易導(dǎo)致中西部地區(qū)的“污染避難所”問題[3][4],而這一觀點(diǎn)同樣遭到質(zhì)疑[5][6]。關(guān)于技術(shù)進(jìn)步與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的研究也有諸多成果出現(xiàn),少部分學(xué)者關(guān)注到技術(shù)進(jìn)步的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效應(yīng),認(rèn)為技術(shù)進(jìn)步是我國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的重要影響因素[7][8],更多的成果則集中于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的技術(shù)溢出效應(yīng),熱衷于對(duì)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技術(shù)溢出機(jī)制與效果的分析[9][10]。此外,關(guān)于環(huán)境規(guī)制與綠色技術(shù)效率的關(guān)系問題也有部分成果展現(xiàn),但相關(guān)學(xué)者對(duì)環(huán)境規(guī)制的技術(shù)進(jìn)步效應(yīng)持有不同意見[11][12][13]。
現(xiàn)有相關(guān)研究具有實(shí)際意義,但也存在不足:第一,缺乏將環(huán)境規(guī)制、綠色技術(shù)效率與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納入統(tǒng)一體系的研究;第二,對(duì)污染行業(yè)轉(zhuǎn)移的測算普遍基于區(qū)位熵,并未很好論證該方法的合理性;第三,運(yùn)用動(dòng)態(tài)空間計(jì)量及面板門限模型開展的相關(guān)實(shí)證研究較少。為此,本文在綜合考察環(huán)境規(guī)制及綠色技術(shù)效率對(duì)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影響機(jī)理的基礎(chǔ)上,對(duì)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進(jìn)行重新界定和測算,并運(yùn)用中國30個(gè)省2001~2014年的面板數(shù)據(jù),構(gòu)建動(dòng)態(tài)空間自回歸及面板門限模型進(jìn)行實(shí)證研究,具有一定的創(chuàng)新性和實(shí)際指導(dǎo)價(jià)值。
一、機(jī)理分析
考慮存在兩個(gè)地方政府分別負(fù)責(zé)各自區(qū)域經(jīng)濟(jì)發(fā)展,同時(shí)存在中央政府對(duì)各地區(qū)進(jìn)行環(huán)保督查。基于上述假設(shè),我們將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數(shù)設(shè)定為:
(1)
其中,Yi(E)為地區(qū)的生產(chǎn)函數(shù),E表示環(huán)境規(guī)制強(qiáng)度。由于放松環(huán)境規(guī)制可促進(jìn)經(jīng)濟(jì)增長,因此Yi(E)是E的減函數(shù)。θYi(E)表示地方政府從經(jīng)濟(jì)增長中收獲的正效用。由于污染排放超出地區(qū)環(huán)境容量會(huì)受處罰,因此κ[(1-E)Pi-Mi]表示污染排放超標(biāo)的負(fù)效用。Pi為污染排放函數(shù),Mi為環(huán)境容量。(1)式代表污染排放不超標(biāo)和超標(biāo)時(shí)的地方政府效用。
對(duì)生產(chǎn)函數(shù)的界定,假設(shè)經(jīng)濟(jì)體以資本為主要投入進(jìn)行生產(chǎn),且存在污染資本與綠色資本兩類。污染資本生產(chǎn)受環(huán)境規(guī)制制約且作為落后產(chǎn)能不存在技術(shù)進(jìn)步,綠色資本的生產(chǎn)不受環(huán)境規(guī)制制約且作為新興產(chǎn)能存在技術(shù)進(jìn)步。因此,我們可將生產(chǎn)函數(shù)設(shè)定為:
(2)

由于地區(qū)的污染水平與污染資本存量成正比,污染函數(shù)可簡單表示為:
Pi=γKPi
(3)
基于上述三個(gè)設(shè)定,我們可分析環(huán)境規(guī)制及綠色技術(shù)效率對(duì)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的影響。生產(chǎn)函數(shù)和污染函數(shù)代入效用函數(shù)后可得:
(4)
假設(shè)東部地區(qū)處于排污超標(biāo)狀態(tài),西部地區(qū)處于不超標(biāo)狀態(tài),以符合本文對(duì)污染資本轉(zhuǎn)移合理性的界定。同時(shí),假設(shè)初始綠色資本全部集聚于發(fā)達(dá)的東部地區(qū)。求該效用函數(shù)組對(duì)污染資本的一階偏導(dǎo),可得出東西部地區(qū)對(duì)污染密集型行業(yè)的需求強(qiáng)度為:
(5)
地方政府對(duì)污染資本需求強(qiáng)度越高,越有動(dòng)力吸引企業(yè)遷入,因此需求強(qiáng)度是影響污染資本轉(zhuǎn)移體制因素的集中體現(xiàn)。那么,污染密集型行業(yè)區(qū)際合理轉(zhuǎn)移的條件可表示為:
(6)
即欠發(fā)達(dá)地區(qū)對(duì)污染資本的需求強(qiáng)度超過發(fā)達(dá)地區(qū)。整理該不等式后可知,實(shí)現(xiàn)污染密集型行業(yè)合理轉(zhuǎn)移,地區(qū)的綠色技術(shù)效率水平須滿足以下條件:
(7)
即綠色技術(shù)效率水平必須達(dá)到一定水平,否則無法滿足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的基本要求。

(8)
在不影響結(jié)果的前提下,簡化(8)式相關(guān)外生系數(shù)并對(duì)環(huán)境規(guī)制求導(dǎo)后可得:
(9)
這一結(jié)果表明KPe與E同樣為反向變動(dòng)關(guān)系,因此轉(zhuǎn)移東部地區(qū)污染資本,還須努力提高環(huán)境規(guī)制水平。
綜合(7)、(8)、(9)式所得結(jié)論,我們可總結(jié)兩個(gè)理論命題:
命題1: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需達(dá)到一定的綠色技術(shù)效率門檻。當(dāng)綠色技術(shù)效率很低時(shí),綠色技術(shù)效率及環(huán)境規(guī)制無法對(duì)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產(chǎn)生顯著影響。
命題2:當(dāng)綠色技術(shù)效率上升到一定水平后,綠色技術(shù)效率越高,環(huán)境規(guī)制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污染密集型行業(yè)合理轉(zhuǎn)移。
二、研究設(shè)計(jì)
(一)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測算方法
對(duì)行業(yè)轉(zhuǎn)移問題的測算,傳統(tǒng)方法往往將某地區(qū)特定行業(yè)在全國產(chǎn)值中的比值減小視為區(qū)際轉(zhuǎn)移,使用這種產(chǎn)值占比的變化來衡量該地區(qū)特定行業(yè)遷出,具體可表示為:
(10)
其中,ITit大于0表示行業(yè)遷出,小于0表示行業(yè)遷入。許多學(xué)者使用類似方法測算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但該做法存在一定的缺陷。鑒于我國區(qū)域產(chǎn)業(yè)發(fā)展與環(huán)境容量差異較大的事實(shí),由中西部尤其是西部承接?xùn)|部污染密集型行業(yè),對(duì)各地區(qū)均利大于弊,因此污染密集型行業(yè)的遷移不應(yīng)僅以遷出量衡量,而需因地制宜設(shè)定合理的衡量指標(biāo)。為此,本文在以“地均污染排放量”衡量地區(qū)的環(huán)境容量的基礎(chǔ)上*環(huán)境容量的計(jì)算方法為:先將區(qū)域空氣污染、水污染和垃圾污染物排放總量的加權(quán)求和,然后除以省域地理面積,從而得到單位面積的污染承載量。其中,空氣污染采用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煙粉塵的加權(quán)排放量表示,水污染采用地區(qū)化學(xué)需氧量排放量表示,垃圾污染則采用地區(qū)固體廢棄物排放量表示。,設(shè)計(jì)如下“污染資本承接合理系數(shù)”的計(jì)算公式:
(11)

(12)
與傳統(tǒng)方法相比,這一算法以承接系數(shù)的正負(fù)號(hào)對(duì)污染資本轉(zhuǎn)移的合理性進(jìn)行校準(zhǔn),從而更有效地衡量了地區(qū)污染密集型行業(yè)遷移的合理水平。
(二)綠色技術(shù)效率的測算
DEA是學(xué)術(shù)界測算綠色技術(shù)效率普遍使用的方法。考慮到超效率模型可更好地比較各地區(qū)綠色技術(shù)效率符合實(shí)證研究需要,因此本文運(yùn)用MAXDEA軟件并基于SUPER-DEA模型計(jì)算各地區(qū)的綠色技術(shù)效率。測算使用的產(chǎn)出變量為經(jīng)濟(jì)產(chǎn)出與環(huán)境污染。其中,以2000年為基期平減后的地區(qū)GDP表示經(jīng)濟(jì)產(chǎn)出。環(huán)境污染則作為測算綠色技術(shù)效率必須的非期望產(chǎn)出,它包括空氣污染、水污染和垃圾污染,并以此三類污染物排放總量表示地區(qū)環(huán)境污染水平。投入變量包括資本、勞動(dòng)力和能源。資本投入以2000年為基期平減的年度固定資產(chǎn)投資額表示,勞動(dòng)力投入以地區(qū)年度城鎮(zhèn)單位就業(yè)人員數(shù)量表示,能源投入以地區(qū)年度消耗的標(biāo)準(zhǔn)煤數(shù)量表示。基于上述方法,本文測算我國30個(gè)省2001~2014年的綠色技術(shù)效率水平,圖1為各省綠色技術(shù)效率的年均指數(shù),我們可看出東部地區(qū)的綠色技術(shù)效率水平整體較高,而中西部地區(qū)則相對(duì)較低,這也從一定層面體現(xiàn)了通過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提升中西部地區(qū)技術(shù)和經(jīng)濟(jì)水平的重要性與合理性。

圖1 各省2001~2014年綠色技術(shù)效率年均值*原始數(shù)據(jù)來自《中國統(tǒng)計(jì)年鑒》《中國環(huán)境統(tǒng)計(jì)年鑒》《中國工業(yè)經(jīng)濟(jì)統(tǒng)計(jì)年鑒》及各省市年鑒。
三、實(shí)證檢驗(yàn)結(jié)果及分析
(一)模型設(shè)定
由于理論分析表明綠色技術(shù)效率對(duì)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的影響具有門限效應(yīng),因此需構(gòu)建面板門限模型對(duì)這一結(jié)論進(jìn)行實(shí)證檢驗(yàn)。門限檢驗(yàn)結(jié)果顯示,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的綠色技術(shù)效率門檻為顯著單一門檻(門限值為1.516)。基于此,本文構(gòu)建如下的面板門限模型:
LnPITit=α0+α1LnTECit(LnTECit≤γ)+α2LnTECit(LnTECit>γ)+α3LnERit(LnTECit≤γ)+α4LnERit(LnTECit>γ)+α5LnGDPit+α6LnULit+α7LnFDIit+α8LnFICit+εit
(13)
其中,t表示時(shí)期,i表示地區(qū),γ為門限變量,LnPITit表示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LnTECit為綠色技術(shù)效率,LnERit為環(huán)境規(guī)制,LnGDPit表示經(jīng)濟(jì)增長,LnULit代表城鎮(zhèn)化水平,LnFDIit表示經(jīng)濟(jì)開放水平,LnFICit表示地區(qū)金融發(fā)展水平,εit為隨機(jī)干擾項(xiàng)。
考慮到產(chǎn)業(yè)區(qū)際轉(zhuǎn)移可能具有空間相關(guān)性,因此同時(shí)使用空間計(jì)量經(jīng)濟(jì)模型進(jìn)行實(shí)證檢驗(yàn)。參考Li(2017)使用的方法[14],本文構(gòu)建經(jīng)濟(jì)距離空間權(quán)重矩陣并對(duì)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的空間相關(guān)性進(jìn)行檢驗(yàn),基于截面數(shù)據(jù)的Moran’s I指數(shù)計(jì)算結(jié)果如表1所示。

表1 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的年度Moran’s I指數(shù)
注:*** 、** 和*分別代表在1%、5%和10%的水平下顯著;限于篇幅,表中僅列出部分結(jié)果。
表1顯示,各年度Moran’s I指數(shù)均高度顯著為正且總體上呈增大趨勢,表明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具有顯著的空間相關(guān)性并逐漸增強(qiáng)。同時(shí),考慮到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在時(shí)間上的連續(xù)性,本文構(gòu)建如下的動(dòng)態(tài)空間自回歸模型:
LnPITit=α0+α1LnPITi(t-1)+ρW×LnPITit+α2LnTECit+α3LnERit+α4LnTECit×LnERit+α5LnGDPit+α6LnULit+α7LnFDIit+α8LnFICit+εit
(14)
其中,LnPITi(t-1)為被解釋變量的滯后一期考察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的時(shí)間慣性,W表示經(jīng)濟(jì)距離空間權(quán)重矩陣,ρ為空間相關(guān)性系數(shù),交叉項(xiàng)LnTECit×LnERit表示環(huán)境規(guī)制的綠色技術(shù)效率效應(yīng)。
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和綠色技術(shù)效率的計(jì)算方法如上文所述*對(duì)污染密集型行業(yè)的界定,本文參照相關(guān)學(xué)者的研究成果[2]。根據(jù)各產(chǎn)業(yè)的污染排放強(qiáng)度,將采掘業(yè)、化工原料及化學(xué)制品制造業(yè)、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業(yè)、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業(yè)、化學(xué)纖維制造業(yè)、非金屬礦物制造業(yè)、電力和煤氣及水的生產(chǎn)供應(yīng)業(yè)、造紙及紙制品業(yè)定義為污染密集型行業(yè)。。此外,我們采用地區(qū)工業(yè)污染治理投資完成額與地區(qū)工業(yè)增加值的比(即環(huán)境保護(hù)成本)衡量環(huán)境規(guī)制強(qiáng)度,平減后表示地區(qū)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的人均GDP衡量經(jīng)濟(jì)增長,地區(qū)城鎮(zhèn)人口與總?cè)丝谥群饬康貐^(qū)城鎮(zhèn)化水平,年度實(shí)際使用外資額與GDP的比表示地方經(jīng)濟(jì)開放水平,地區(qū)金融機(jī)構(gòu)存貸款總額與GDP的比表示地區(qū)金融發(fā)展水平。本文使用的30個(gè)省2001~2014年面板數(shù)據(jù)來源于《中國統(tǒng)計(jì)年鑒》《中國環(huán)境統(tǒng)計(jì)年鑒》《中國工業(yè)經(jīng)濟(jì)統(tǒng)計(jì)年鑒》及各省市年鑒。為保障數(shù)據(jù)的平穩(wěn)性,本文在對(duì)負(fù)值進(jìn)行相應(yīng)處理的基礎(chǔ)上對(duì)數(shù)化有關(guān)數(shù)據(jù)。
(二)實(shí)證結(jié)果分析
本文使用面板門限模型對(duì)綠色技術(shù)效率及環(huán)境規(guī)制的門限效應(yīng)進(jìn)行初步分析(結(jié)果如表2所示)。從回歸結(jié)果可看出,當(dāng)綠色技術(shù)效率對(duì)數(shù)LnTEC小于門限值時(shí),其回歸結(jié)果不顯著,表明此時(shí)的綠色技術(shù)效率無法對(duì)污染密集型行業(yè)合理轉(zhuǎn)移產(chǎn)生影響,這與理論命題1相符。變量LnER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為正,表明此時(shí)的環(huán)境規(guī)制水平提升可對(duì)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產(chǎn)生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從系數(shù)和顯著性層面看,這種影響并不大。當(dāng)LnTEC跨越門檻后,回歸結(jié)果發(fā)生顯著變化,此時(shí)LnTEC的系數(shù)高度顯著為正,表明綠色技術(shù)效率的提高成為促進(jìn)污染密集型行業(yè)合理轉(zhuǎn)移的重要影響因素。而LnER也高度顯著為正,表明此時(shí)的環(huán)境規(guī)制水平提升也促進(jìn)了污染密集型行業(yè)合理轉(zhuǎn)移,這與理論命題2相符。
從整體上看,面板門限模型的回歸結(jié)果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理論分析的正確性,但面板門限模型也存在一定的缺陷。該模型未考慮到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的空間效應(yīng),同時(shí)也無法考察綠色技術(shù)效率與環(huán)境規(guī)制的交互作用。因此,本文同時(shí)使用空間計(jì)量模型進(jìn)行回歸,以增加實(shí)證的穩(wěn)健性。由于我國的污染密集型行業(yè)主要從東部轉(zhuǎn)出而由中西部地區(qū)承接,通過分析東部地區(qū)平均綠色技術(shù)效率發(fā)現(xiàn),門限值1.516發(fā)生在2005~2006年前后。為此,我們將全部數(shù)據(jù)劃分為2001~2005年和2006~2014年兩個(gè)時(shí)間段,分別進(jìn)行空間計(jì)量回歸(結(jié)果如表3所示)。

表2 面板門限的回歸結(jié)果
注:*** 、** 和*分別代表在1%、5%和10%的水平下顯著。
從模型的檢驗(yàn)結(jié)果看,SAR-M1和SAR-M2的Log likelihood都很大,而AIC與SC指數(shù)很小,表明空間計(jì)量模型比線性模型更適于分析本文關(guān)注的問題。比較各空間計(jì)量模型的似然值還可發(fā)現(xiàn),L-sar高于L-sdm,表明選取空間自回歸模型更合理。模型M1和M2的Adj-R2分別達(dá)到0.426和0.517,表明本文選取的解釋變量較好地反映了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的影響因素。空間自相關(guān)系數(shù)ρ在兩個(gè)模型中均顯著為正,表明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具有較強(qiáng)的空間集聚性。而模型SAR-M2中ρ的系數(shù)更大、顯著性更強(qiáng),表明跨越門檻后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的空間集聚性增強(qiáng),“東出西進(jìn)”的態(tài)勢更加明顯。變量LnPIT(-1)在兩個(gè)模型中均高度顯著為正,表明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具有較強(qiáng)的時(shí)間慣性。

表3 空間計(jì)量回歸結(jié)果
注:*** 、** 和*分別代表在1%、5%和10%的水平下顯著;括號(hào)內(nèi)為z值。
從自變量的回歸結(jié)果看,變量LnTEC在模型M1中不顯著,而在M2中高度顯著為正,表明綠色技術(shù)效率對(duì)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的影響確實(shí)存在門限效應(yīng)。當(dāng)綠色技術(shù)效率較低時(shí),地方政府在經(jīng)濟(jì)利益的驅(qū)動(dòng)下愿意承擔(dān)污染成本,以拉動(dòng)經(jīng)濟(jì)增長,發(fā)達(dá)地區(qū)由于存在整體優(yōu)勢而對(duì)污染密集型資本形成吸引力,從而造成相關(guān)企業(yè)在東部地區(qū)集聚,因此綠色技術(shù)效率對(duì)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影響不顯著。隨著發(fā)達(dá)地區(qū)技術(shù)進(jìn)步及產(chǎn)業(yè)現(xiàn)代化帶來的綠色技術(shù)效率提升,污染密集型行業(yè)對(duì)地方經(jīng)濟(jì)的意義逐漸減弱,且前期積累的較為嚴(yán)重的環(huán)境污染超出地區(qū)環(huán)境承載能力,最終迫使地方政府驅(qū)逐這些污染企業(yè)。相比之下,欠發(fā)達(dá)地區(qū)在經(jīng)濟(jì)效益的驅(qū)動(dòng)下樂于接納污染企業(yè),因此產(chǎn)生綠色技術(shù)效率促進(jìn)污染密集型行業(yè)向欠發(fā)達(dá)地區(qū)轉(zhuǎn)移的效果。變量LnER在模型M1中不顯著,而在M2中高度顯著為正,表明環(huán)境規(guī)制對(duì)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的影響同樣存在以綠色技術(shù)為門檻的門限效應(yīng)。當(dāng)綠色技術(shù)效率較低時(shí),由于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需要,地方政府寧愿承擔(dān)高昂的環(huán)境治理成本或冒著被中央政府懲罰的風(fēng)險(xiǎn)也要留住污染企業(yè),此時(shí)的環(huán)境規(guī)制對(duì)地方政府發(fā)展策略的影響較小。隨著發(fā)達(dá)地區(qū)綠色技術(shù)效率提升,地方政府從污染密集型行業(yè)中得到的經(jīng)濟(jì)收益逐漸小于執(zhí)行中央環(huán)境政策帶來的經(jīng)濟(jì)成本,而污染的加劇也使治污的邊際成本不斷提高,因此環(huán)境規(guī)制開始產(chǎn)生排斥污染密集型行業(yè)的效果。欠發(fā)達(dá)地區(qū)則由于產(chǎn)業(yè)發(fā)展水平低、環(huán)境容量還有富余,仍處于經(jīng)濟(jì)效益大于環(huán)境成本的狀態(tài),從而樂于接受污染密集型行業(yè)的轉(zhuǎn)入,最終在整體上形成環(huán)境規(guī)制促進(jìn)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的態(tài)勢。交叉項(xiàng)LnTEC×LnER在模型M1中不顯著,而在M2中顯著為正,表明在綠色技術(shù)效率較低時(shí)不存在環(huán)境規(guī)制的綠色技術(shù)效率效應(yīng),而當(dāng)綠色技術(shù)水平較高時(shí),由于整體生產(chǎn)效率提高且環(huán)境規(guī)制成本加大,此時(shí)的環(huán)境規(guī)制水平提高迫使地方政府投入更多資源用于促進(jìn)綠色技術(shù)效率提升,依靠技術(shù)的高邊際收入抵消環(huán)境規(guī)制的高邊際成本,因而間接提高綠色技術(shù)效率對(duì)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的促進(jìn)作用。
從控制變量的回歸結(jié)果看,LnGDP在模型M1中顯著為負(fù),而在M2中顯著為正,表明在綠色技術(shù)效率水平及經(jīng)濟(jì)總量仍處于低位時(shí),東部地區(qū)出于刺激經(jīng)濟(jì)的需要而對(duì)污染密集型行業(yè)形成較強(qiáng)依賴,此時(shí)的經(jīng)濟(jì)增長表現(xiàn)為對(duì)污染密集型行業(yè)的吸引力。但隨著發(fā)達(dá)地區(qū)經(jīng)濟(jì)水平的進(jìn)一步提高,其對(duì)污染密集型行業(yè)的依賴度逐漸下降,從而形成經(jīng)濟(jì)增長促進(jìn)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的結(jié)構(gòu)性變化。變量LnUL在兩個(gè)模型中均不顯著,表明城鎮(zhèn)化并沒有促進(jìn)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表明普通居民的環(huán)保訴求并沒有得到政府的充分重視,以經(jīng)濟(jì)發(fā)展為核心的社會(huì)建設(shè)與達(dá)到“以人為本”的要求尚有一定距離。變量LnFDI在兩個(gè)模型中均高度顯著為負(fù),表明從國際視角看我國仍是發(fā)達(dá)國家污染行業(yè)的輸出地,地方政府為吸引FDI而將大量的國外污染企業(yè)引進(jìn)中國,從而導(dǎo)致環(huán)境約束本就較強(qiáng)的東部地區(qū)被進(jìn)一步污染。變量LnFIC僅在模型M2中顯著為正,表明在技術(shù)和經(jīng)濟(jì)水平達(dá)到一定程度后,金融業(yè)發(fā)展帶來的資本流通效率提高才能促進(jìn)污染密集型行業(yè)合理轉(zhuǎn)移。
四、結(jié)論與政策建議
通過構(gòu)建數(shù)理模型,本文研究環(huán)境規(guī)制、綠色技術(shù)效率與污染密集型行業(yè)合理轉(zhuǎn)移的關(guān)系。分析結(jié)果顯示,上述因素對(duì)我國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的影響存在以綠色技術(shù)效率為門檻的門限效應(yīng)。在對(duì)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進(jìn)行重新測算的基礎(chǔ)上,利用中國30個(gè)省2001~2014年的面板數(shù)據(jù),構(gòu)建面板門限模型及動(dòng)態(tài)空間計(jì)量模型,以驗(yàn)證理論命題的正確性。實(shí)證結(jié)果表明,當(dāng)綠色技術(shù)效率較低時(shí),環(huán)境規(guī)制和綠色技術(shù)效率的提升并不能促進(jìn)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只有綠色技術(shù)效率水平達(dá)到門檻值以上時(shí),綠色技術(shù)效率和環(huán)境規(guī)制才對(duì)污染密集型行業(yè)的合理轉(zhuǎn)移產(chǎn)生顯著的促進(jìn)作用。
基于理論及實(shí)證分析結(jié)果,為促進(jìn)我國污染密集型行業(yè)的合理轉(zhuǎn)移,本文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議:(1)由于西部地區(qū)環(huán)境容量尚有富余,又需引進(jìn)資本和技術(shù)來發(fā)展當(dāng)?shù)亟?jīng)濟(jì)、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因而中央政府應(yīng)加大對(duì)污染密集型行業(yè)從東向西轉(zhuǎn)移的支持力度。據(jù)此,應(yīng)從宏觀頂層設(shè)計(jì)層面出臺(tái)相關(guān)政策,為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提供便利;從中觀層面加強(qiáng)對(duì)地方政府相關(guān)行為的監(jiān)管,為污染密集型行業(yè)東出西入掃清地方保護(hù)主義等區(qū)域性障礙;在微觀層面為污染密集型企業(yè)的轉(zhuǎn)移提供稅收及經(jīng)濟(jì)扶持。(2)由于現(xiàn)階段綠色技術(shù)效率的提升已形成促進(jìn)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的有效機(jī)制,因此中央政府應(yīng)要求東部地區(qū)加大提升綠色技術(shù)效率的相關(guān)投入,并從財(cái)政層面為綠色技術(shù)效率進(jìn)步較快的地區(qū)提供財(cái)政支持或獎(jiǎng)勵(lì)機(jī)制。地方政府則應(yīng)主動(dòng)通過加大相關(guān)R&D投入、增強(qiáng)第三產(chǎn)業(yè)及工業(yè)現(xiàn)代化發(fā)展等途徑促進(jìn)地區(qū)綠色技術(shù)效率的提升,以促使污染密集型企業(yè)主動(dòng)遷移。(3)環(huán)境規(guī)制不僅有助于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同時(shí)還通過倒逼綠色技術(shù)效率提升進(jìn)一步強(qiáng)化其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效應(yīng),因此中央政府應(yīng)加大對(duì)東部地區(qū)的環(huán)境污染的管制力度,充分發(fā)揮環(huán)境規(guī)制的積極效應(yīng);對(duì)西部地區(qū)則應(yīng)制定適應(yīng)性的環(huán)境規(guī)制政策,既不能因規(guī)制過于苛刻而對(duì)西部地區(qū)接納污染密集型行業(yè)造成體制上的障礙,也不應(yīng)完全以促進(jìn)污染密集型行業(yè)轉(zhuǎn)移為目的而過度放松環(huán)境規(guī)制,避免西部地區(qū)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1] 張彩云,郭艷青.污染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能夠?qū)崿F(xiàn)經(jīng)濟(jì)和環(huán)境雙贏嗎?——基于環(huán)境規(guī)制視角的研究[J]. 財(cái)經(jīng)研究,2015,(10):96-108.
[2] 張平,張鵬鵬.環(huán)境規(guī)制對(duì)產(chǎn)業(yè)區(qū)際轉(zhuǎn)移的影響——基于污染密集型產(chǎn)業(yè)的研究[J].財(cái)經(jīng)論叢,2016,(5):96-104.
[3] 王艷麗,鐘奧.地方政府競爭、環(huán)境規(guī)制與高耗能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基于“逐底競爭”和“污染避難所”假說的聯(lián)合檢驗(yàn)[J].山西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6,(8):46-54.
[4] 侯偉麗,方浪,劉碩.“污染避難所”在中國是否存在?——環(huán)境管制與污染密集型產(chǎn)業(yè)區(qū)際轉(zhuǎn)移的實(shí)證研究[J].經(jīng)濟(jì)評(píng)論,2013,(4):65-72.
[5] Porter M.E.,Linde C.V.D.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5,9(4),pp.97-118.
[6] Eskeland G.S.,Harrison A.E.Moving to Greener Pastures? Multinationals and 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3,70(1),pp.1-23.
[7] 梁紅巖,王靜,秦志琴,董威勵(lì).中國污染密集型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及其影響因素研究[J].生態(tài)經(jīng)濟(jì),2016,(10):32-35.
[8] 崔建鑫,趙海霞.長江三角洲地區(qū)污染密集型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及驅(qū)動(dòng)機(jī)理[J].地理研究,2015,(3):504-512.
[9] 關(guān)愛萍,李娜.金融發(fā)展、區(qū)際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與承接地技術(shù)進(jìn)步——基于西部地區(qū)省際面板數(shù)據(jù)的經(jīng)驗(yàn)證據(jù)[J].經(jīng)濟(jì)學(xué)家,2013,(9):88-96.
[10] 馬永紅,李玲,王展昭,張帆.復(fù)雜網(wǎng)絡(luò)下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與區(qū)域技術(shù)創(chuàng)新擴(kuò)散影響關(guān)系研究——以技術(shù)類型為調(diào)節(jié)變量[J].科技進(jìn)步與對(duì)策,2016,(18):35-41.
[11] 陳超凡.中國工業(yè)綠色全要素生產(chǎn)率及其影響因素——基于ML生產(chǎn)率指數(shù)及動(dòng)態(tài)面板模型的實(shí)證研究[J].統(tǒng)計(jì)研究,2016,(3):53-62.
[12] 何楓,祝麗云,馬棟棟,姜維.中國鋼鐵企業(yè)綠色技術(shù)效率研究[J].中國工業(yè)經(jīng)濟(jì),2015,(7):84-98.
[13] 譚政,王學(xué)義.綠色全要素生產(chǎn)率省際空間學(xué)習(xí)效應(yīng)實(shí)證[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huán)境,2016,(10):17-24.
[14] Li B.,Li T.,Yu M.,et al.Can Equalization of Public Services Narrow the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China? A Spatial Econometrics Approach[J].China Economic Review,2017,44(3),pp.67-78.
- 財(cái)經(jīng)論叢的其它文章
- 職場中公民行為壓力與員工創(chuàng)造力的曲線關(guān)系
——自我效能感的情境機(jī)制 - 畫地為牢:領(lǐng)地行為是否抑制創(chuàng)造力?
- 財(cái)務(wù)業(yè)績異質(zhì)性、高送轉(zhuǎn)與股東超額回報(bào)
- 社會(huì)資本投資、政府補(bǔ)貼與研發(fā)投資
——基于民營上市公司的研究 - 股票誤定價(jià)、管理層持股與企業(yè)R&D投資
——基于我國高新技術(shù)上市公司的經(jīng)驗(yàn)證據(jù) - 管理層語調(diào)離差策略及其對(duì)分析師預(yù)測樂觀度影響
——基于A股制造業(yè)上市公司MD&A文本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