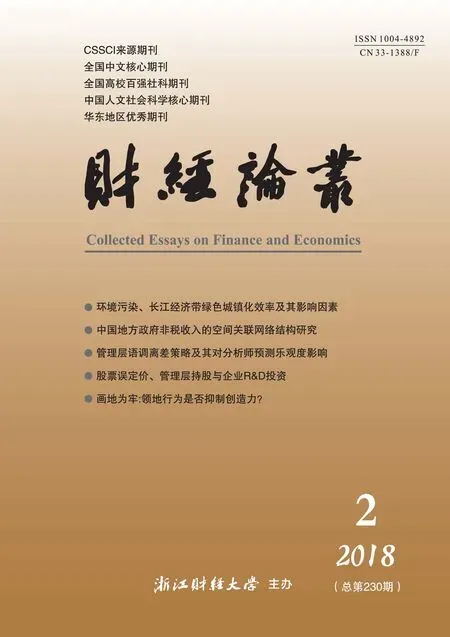中國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的空間關聯(lián)網絡結構研究
吳金光,毛 軍
(1.湖南財政經濟學院財金系;湖南 長沙 410205;2.海南師范大學數(shù)學與統(tǒng)計學院,海南 海口 571158)
一、引 言
近年來,在經濟發(fā)展新常態(tài)下,隨著我國步入以調整帶動發(fā)展的“三期疊加”新階段,地方政府呈現(xiàn)出財政支出剛性增長而稅收收入增幅放緩的格局。對于受制于稅權約束的地方政府而言,在地方債務融資平臺日益規(guī)范的情況下,政府非稅收入仍然是一個具有相對優(yōu)勢的籌資渠道,尤其是在支出壓力不斷加大的情況下,削弱地方政府壓縮非稅收入的動力。據(jù)統(tǒng)計,我國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由2000年的832.8億元增長到2014年的16736.7億元;地方政府非稅收入占財政收入比例由2000年的13.00%(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為6406.1億元)增長到2014年的22.1%(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為75860億元),非稅收收入增長速度遠遠高于同期GDP的增長速度(同時期GDP年均增長比例為8 %~9%)[1]。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的快速增長導致財政收入結構失衡,政府間日趨激烈的區(qū)域競爭致使地方政府延緩了“清費降負”的步伐,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我國結構性減稅改革的實施效果。在我國當前市場主體稅負是否過重的爭辯討論中,地方政府非稅收入規(guī)模問題便進入我們的視線,我們有必要重新認識我國地方政府財政競爭模式,是否在稅收競爭的同時還存在非稅競爭。因此,對地方政府非稅收入規(guī)模及其空間關系的研究,不僅有利于我們深化對市場主體負擔來源的理解,而且也能為加強我國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管理提供實證依據(jù)。
對于政府非稅收入變動規(guī)律及其影響因素,許多學者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從財政體制與制度安排、現(xiàn)實經濟環(huán)境以及地方政府行為取向等方面進行了分析與探討。在制度安排上,由于長期以來我國大量非稅收入游離于預算管理之外,非稅收入缺乏必要的硬性約束,為非稅收入的擴張?zhí)峁┝酥贫惹疤?張麗華等,2009)[2],從制度入手,推行全口徑預算管理,堵塞“制度性漏洞”成為解決非稅收入所面臨問題的關鍵(鄭建新,2014)[3]。除此之外,有些學者認為,當前地方政府存在發(fā)展經濟壓力與財力缺口并存的矛盾,地方政府面臨的宏觀環(huán)境與制度結構不匹配(王玲,2009;馮輝,2014)[4][5],受財政供養(yǎng)人員規(guī)模、轉移支付規(guī)模以及市場化進程的影響(白宇飛等,2009;王志剛和龔六堂,2009)[6][7],非稅收入成為地方政府重要而便利的融資工具選擇,因此,優(yōu)化經濟發(fā)展環(huán)境和健全公共財政體系,從財政壓力、收入基礎和交易成本三方面著手進行有效的制度設計,是保持非稅收入健康發(fā)展態(tài)勢的前提(白宇飛和張紫娟,2015;武玉坤,2015)[8][9]。

圖1 中國地方非稅收入增長率情況圖
從現(xiàn)有文獻來看,另外一個視角就是從政府行為入手探討地方政府競爭對非稅收入的影響。Crowley and Sobel(2011)[10]研究證實了地方政府間存在非稅收競爭;Brueckner(2003)[11]認為地方政府非稅負擔會受到周邊地區(qū)因素的影響;王佳杰等(2014)[12]發(fā)現(xiàn)政府間稅收競爭強度和地方財政支出壓力會導致非稅收入規(guī)模擴大。在這類研究方面,其中一個重要趨勢就是運用空間計量方法,反映非稅收入競爭的空間特征。陳工和洪禮陽(2014)[13]采用空間滯后面板模型研究表明,當前我國不同區(qū)域存在著強度不同的非稅收入競爭;童錦治等(2013a)[14]利用空間杜賓模型研究發(fā)現(xiàn),地區(qū)間的非稅競爭成為地方政府“為增長而競爭”的重要工具;孟天廣和蘇政(2015)[15]采用空間面板模型研究發(fā)現(xiàn)我國地方政府非稅收入存在“同儕效應”和“鄰居效應”;Revelli(2001)[16],Devereux et al.(2007)[17]、童錦治等(2013b)[18]用空間動態(tài)面板模型研究發(fā)現(xiàn),地方政府在非稅收入上存在顯著的同級“橫向策略互動”和跨級“縱向共同反應”。總的來看,現(xiàn)有研究大多采用空間計量方法(ESDA)分析我國地方政府非稅收入存在的空間相關性和空間集聚特征。然而,空間集聚特征揭示的是地方政府非稅收入在空間地理上的“相鄰”效應,由此得出的結論難以從整體上把握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的空間關聯(lián)特征,其政策建議不能完全包含我國地方政府非稅收入均衡發(fā)展目標的實現(xiàn)。其次,空間計量方法基于“屬性數(shù)據(jù)”,考察的是地方政府非稅收入“量”的效應,難以刻畫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空間關聯(lián)的整體網絡結構特征,無法揭示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空間關聯(lián)“關系”的影響效應。考慮到空間網絡分析方法運用的是“關系數(shù)據(jù)”,可以揭示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空間關聯(lián)的結構形態(tài)和空間聚類方式,將空間網絡方法運用于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的研究可使分析結論得到進一步豐富。因此,本文基于2000~2014年我國地方政府非稅收入數(shù)據(jù),通過構建修正的引力模型測算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的空間關聯(lián)關系,并借助社會網絡分析(SNA)方法對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的空間關聯(lián)網絡結構及影響效應進行實證分析,以期揭示我國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的空間關聯(lián)關系,并為地方政府非稅收入改革提供新的視角。
二、我國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空間關聯(lián)網絡的實證分析
(一)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的空間分布格局
文章以2014年我國地方政府人均非稅收入*文章所指地方政府非稅收入屬于狹義上的非稅收入,是指納入預算內管理的非稅收入。地方政府非稅收入,通過各省域非稅收入總額除以當?shù)啬昴┤丝跀?shù)得到地方政府人均非稅收入。,運用地理信息系統(tǒng)(GIS)的可視化方法,采用自然斷點(Natural Breaks Jenks)法對數(shù)據(jù)進行劃分,繪制出中國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的空間分布格局,以此描述我國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的空間非均衡特征(見圖2左圖)。同時,運用地理統(tǒng)計分析中的趨勢分析工具描繪出我國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的空間分布趨勢(見圖2右圖),圖中每根豎線代表各個省份地方政府非稅收入在東西向和南北向正交平面上的投影,將地方政府非稅收入作為高度屬性值(Z值),將投影點采用二次多項式生成一條最佳擬合線,并旋轉合理的透視角度并生成三維透視圖。我國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的最優(yōu)擬合線在東西呈現(xiàn)出“U型”曲線,南北呈現(xiàn)出向下的曲線,說明我國地方政府非稅收入東部地區(qū)高于中西部地區(qū),北部地區(qū)高于南部地區(qū)。不難發(fā)現(xiàn),我國地方政府非稅收入水平呈現(xiàn)出顯著的空間非均衡分布格局。

圖2 中國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的空間分布格局及趨勢圖
(二)空間溢出關系識別及空間關聯(lián)網絡結構特征分析
為識別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空間溢出關系,綜合考慮區(qū)域間地理距離和經濟距離對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空間溢出的影響,本文選擇使用修正的引力模型,運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展開分析。修正的引力模型如式(1)所示,其中,i和j代表地區(qū);Rij為地區(qū)i和地區(qū)j間非稅收入的引力;kij為地區(qū)i對于兩個地區(qū)i和j間地方政府非稅收入聯(lián)系的貢獻率;Pi為地區(qū)i的年末總人口數(shù),Pj為地區(qū)j的年末總人口數(shù);Gi為地區(qū)i的GDP,Gj為地區(qū)j的GDP;Ni為地區(qū)i的地方政府非稅收入,Nj為地區(qū)j的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經濟地理距離”用地區(qū)i和j間的距離(Dij)與地區(qū)i和j人均GDP的差值(gi-gj)的比值來表示。根據(jù)修正的引力模型計算出引力矩陣,對各行取平均值作為臨界值。引力值大于臨界值的地區(qū)記為1,說明該行地區(qū)對該列地區(qū)的地方政府非稅收入存在空間溢出;引力值小于臨界值的地區(qū)記為0,說明該行地區(qū)對該列地區(qū)的地方政府非稅收入不存在空間溢出。
(1)
基于修正的引力模型,文章構建出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空間溢出的關系矩陣。圖3展示的是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空間溢出關系的關聯(lián)網絡圖。由圖3可知,我國地方政府非稅收入呈現(xiàn)出復雜的和多線程的空間溢出關系,因此,從非稅政策的地區(qū)差異和地理近鄰效應兩個維度探尋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空間溢出的來源對于地方政府非稅收入跨區(qū)域協(xié)同治理以及非稅政策的實施提供了思路與依據(jù)。

圖3 中國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的空間溢出網絡圖
在關系網絡中,網絡密度反映網絡中各區(qū)域地方政府非稅收入之間關聯(lián)關系的疏密程度,是指網絡中的實際連線數(shù)與整個網絡中最大可能連線數(shù)之比,該指標的取值范圍為[0,1]。網絡中存在的關聯(lián)關系數(shù)量為N×(N-1),其中,N為網絡中的區(qū)域數(shù)量。網絡密度Dn=L/[N×(N-1)],其中,L為網絡中節(jié)點間擁有的關聯(lián)關系數(shù)量。2000~2014年我國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的空間網絡密度呈現(xiàn)出穩(wěn)定趨勢,空間網絡密度維持在0.2355至0.2484之間。隨著我國推行的“財政收支兩條線”改革和加強非稅收入預算管理等一系列規(guī)范地方政府非稅收入行為的政策,地區(qū)政府空間網絡密度趨于穩(wěn)定狀態(tài)。關聯(lián)性是指地方政府非稅收入聯(lián)動網絡自身的穩(wěn)健性,該測度的取值范圍為[0,1]。關聯(lián)度C=1-V/[N×(N-1)/2],其中,V為網絡中不可達的點對數(shù),N為網絡中的區(qū)域主體數(shù)量。2000—2014年我國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的空間關聯(lián)關系維持在219個至230個之間。在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的空間網絡結構影響下,僅關注重點地區(qū)非稅政策改革,并不能對降低全國非稅收入形成長效機制。因此,需要考慮地方政府非稅收入在不同區(qū)域存在的競爭對地方政府非稅收入決策的影響,根據(jù)不同地區(qū)實際情況,制定差異性的非稅改革政策。網絡等級是指在有向網絡中區(qū)域地間非對稱可達程度,反映網絡中各區(qū)域間的等級結構,該測度的取值范圍為[0,1]。等級度H=1-K/max(K),其中,K為網絡中對稱可達的點對數(shù),max(K)為最大可能的對稱可達的點對數(shù)。2000—2014年我國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網絡等級度呈現(xiàn)出下降趨勢,這說明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空間網絡中,森嚴的等級結構被逐步打破,更多的地區(qū)脫離所在空間網絡中的從屬和邊緣地位,反映了近年來我國地方政府非稅收入政策的制定和落實情況,表明區(qū)域競爭迫使地方政府主動謀求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的“話語權”,國家在限制重點省份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的同時,也兼顧到其他省份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的公平性。網絡效率是指地方政府非稅收入聯(lián)動網絡中各地區(qū)間的連接效率,該測度的取值范圍為[0,1]。網絡效率E=1-M/max(M),其中,M為網絡中冗余線的條數(shù),max(M)為網絡中最大可能的冗余連線條數(shù)。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的空間網絡效率的下降,表明我國具有相似地方政府非稅收入關聯(lián)結構的區(qū)域間地方政府非稅收入關聯(lián)關系數(shù)量呈現(xiàn)出上升趨勢,而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的空間網絡效率上升,則表明不同空間關聯(lián)結構的區(qū)域間地方政府非稅收入關聯(lián)關系數(shù)量增加,從我國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網絡效率的演變趨勢看,2000~2014年呈現(xiàn)出先下降后上升的“V”型曲線。
(三)個體空間網絡特征分析
接下來通過各節(jié)點的網絡結構特征考察地方政府非稅收入在空間關聯(lián)網絡中的地位和作用,由點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等指標進行刻畫,表1顯示了2014年我國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的空間網絡中心性分析結果*僅對考察期內2014年的計算結果進行展示,如需其他年份的計算結果可向作者索要。。點度中心度為CAD=(C1+C2)/(2N-2),其中,C1為點出度,C2為點入度,N為有向網絡的節(jié)點數(shù),是根據(jù)連接數(shù)來衡量我國地方政府非稅收入在聯(lián)動網絡中所處中心程度,點度中心度越高,意味著該地區(qū)與其它地區(qū)間聯(lián)系越多,也就表明該地區(qū)處于網絡中心位置;點出度是指該地區(qū)指向其它地區(qū)的連線數(shù),反映該地區(qū)對其它地區(qū)的輻射程度;點入度是指其它地區(qū)指向該地區(qū)的連線數(shù),反映其它地區(qū)對該地區(qū)的影響程度。在我國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的空間網絡中,平均點數(shù)中心度指數(shù)為35.48,點數(shù)中心度指數(shù)高于均值的省份有12個省份,點度中心度較高的省份經濟較為發(fā)達,這些省份在網絡中局部關聯(lián)關系數(shù)較多;網絡中關聯(lián)關系最少的有5個省份,這些省份由于地理位置偏遠、經濟規(guī)模相對較小,與其他省份之間較難形成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的空間關聯(lián)關系。
中介中心度是指地區(qū)對其它地區(qū)地方政府非稅收入聯(lián)動關系的控制程度。地區(qū)在網絡中處于中心位置,意味著該地區(qū)中介中心度越高,起著重要的“橋梁”和“中介”作用。N為有向網絡的節(jié)點數(shù),地區(qū)j和k之間存在gjk條捷徑,bjk(i)為控制能力(即i處于j和之間捷徑上的概率k),bjk(i)=gjk(i)/gjk,中介中心度可表示為:

(2)
中介中心度的均值為2.40,超過均值的省份有6個省份,這些省份在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的空間網絡中,具有控制其他省份的地位。中介中心度較小的新疆、黑龍江、貴州等省份在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的空間網絡中更易于受中介中心度較大的省份的影響。此外,中介中心度排名的省份均處于我國經濟發(fā)達地區(qū),而中介中心度排名靠后的省份經濟規(guī)模相對較小,地理位置多位于我國中西部地區(qū),說明現(xiàn)行經濟增長的發(fā)展模式下,各省經濟發(fā)展水平和地理位置等因素,對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的空間關聯(lián)關系的變化具有較強的影響。
接近中心度反映某個地區(qū)在網絡中“不受其它地區(qū)控制”的程度。地區(qū)位于網絡中心的位置,意味著該地區(qū)對其它地區(qū)的影響控制程度越強,進而接近中心度越高。接近中心度用該地區(qū)與其它地區(qū)的捷徑“距離”(即捷徑中包含的線數(shù))之和的倒數(shù)值來表示。設dij代表節(jié)點i與j之間的捷徑距離,接近中心度可表示為:
(3)
接近中心度的均值為60.43,此類地區(qū)在空間網絡中處于網絡的中心。一方面,在經濟快速發(fā)展的前提下,非稅收入作為地方政府的可控制政策工具,地方政府往往會通過非稅競爭來實現(xiàn)加快經濟增長的目標。處于邊緣地位的地區(qū)易于利用自身在經濟方面的優(yōu)勢,向經濟落后的中心省份輸出地方政府非稅收入,在空間網絡中表現(xiàn)為發(fā)出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的空間關聯(lián)關系。處于中心地位的地區(qū)利用自身在經濟政策方面強化優(yōu)勢,表現(xiàn)為邊緣省份向中心省份發(fā)出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的空間關聯(lián)關系。

表1 中國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的空間網絡中心性分析
(四)空間關聯(lián)網絡的塊模型分析
運用塊模型(Block Modeling)分析法來研究地方政府非稅收入在網絡中的角色和聯(lián)動網絡的內部結構狀態(tài)。基于地方政府非稅收入角色位置,采用CONCOR方法對空間網絡板塊關聯(lián)關系進行刻畫,選擇最大分割深度為2,集中標準為0.2,通過把全國31個省份劃分為四大板塊,通過測算得出,在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的整體關聯(lián)網絡中存在219個關聯(lián)關系(見表2)。其中,板塊內部間的關聯(lián)關系有115個,板塊和板塊間的關聯(lián)關系有104個,說明板塊間的地方政府非稅收入存在著明顯的空間關聯(lián)和溢出效應。

表2 中國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空間關聯(lián)板塊的溢出效應
為清晰揭示不同聚類之間的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空間關聯(lián)關系,文章依據(jù)聚類測算得出密度矩陣,依據(jù)已計算得出的地方政府非稅收入整體網絡密度0.2355,將密度矩陣中大于整體網絡密度的計算結果記為1,反之則認為聚類之間的關聯(lián)關系較弱(記為0),計算得出的像矩陣結果詳見表3。依據(jù)計算的像矩陣,圖4反映了不同聚類之間的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的空間關聯(lián)關系。第I板塊的溢出關系有36個,屬于板塊內部的關系有23個,接收其他板塊溢出的關系有23個;期望內部關系比例為23%,實際的內部關系比例為64%,因此第I板塊為“雙向溢出板塊”。位于第I板塊的成員有8個,分別是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這些省份主要分布在京津冀和環(huán)渤海地區(qū);該板塊成員既發(fā)出聯(lián)系也接收其他板塊較多的聯(lián)系,然而來自板塊內部成員的聯(lián)系相對較多,表明該板塊成員對板塊內部和其他板塊的地方政府非稅收入增長產生雙向溢出效應。第II板塊的溢出關系有87個,屬于板塊內部的關系有28個,接收其他板塊發(fā)出的關系有59個;期望內部關系比例為20%,實際的內部關系比例為32%,因此第II板塊稱為“凈溢出板塊”。位于第II板塊的成員有7個,分別是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河南、江西、山東,這些省份主要集中在長三角地區(qū);該板塊成員向其它板塊成員發(fā)出較多關系,對板塊內部較少發(fā)出關系且較少接收到外來關系,表明該板塊成員在在政府非稅收入上存在向其他地區(qū)進行資金溢出。第III板塊的溢出關系有87個,屬于板塊內部的關系有59個,接收其他板塊發(fā)出的關系有28個;期望內部關系比例為33%,實際的內部關系比例為68%,該板塊稱為“經紀人板塊”。位于第III板塊的成員有11個,包括福建、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海南、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這些省份主要集中在長江中游地區(qū)和成渝地區(qū);該板塊成員既對其他板塊產生溢出關系,也接收來自外部成員的溢出,然而來自板塊內部成員的聯(lián)系相對較少,在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空間關聯(lián)網絡中扮演著“中介”與“橋梁”作用。第IV板塊的溢出關系有9個,屬于板塊內部的關系有5個,接收其他板塊發(fā)出的關系有4個;期望內部關系比例為13%,實際的內部關系比例為56%,因此第IV板塊稱為“凈受益板塊”。該板塊成員在板塊內部關系較多,對其他板塊成員的溢出效應較少。第IV板塊的成員有5個,包括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該板塊成員主要由西部經濟落后地區(qū)組成,該地區(qū)主要接收來自經濟發(fā)達地區(qū)的政府資金溢出。

表3 中國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空間關聯(lián)板塊的密度矩陣與像矩陣
注:“0”表示不存在行指向列的關聯(lián)關系,“1”表示具有關聯(lián)關系。
三、中國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空間關聯(lián)網絡的影響因素分析
(一)模型構建


圖4 中國地方政府非稅收入四大板塊間的關聯(lián)關系圖
(二)QAP相關分析與回歸分析

表4 QAP相關分析結果
注:隨機置換次數(shù)選擇5000次,P≥0反映隨機置換后計算的相關系數(shù)不小于實際相關系數(shù)的概率;P≤0反映隨機置換后計算的相關系數(shù)小于實際相關系數(shù)的概率(劉軍,2014)[20]。
本部分采用QAP相關分析法檢驗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的聯(lián)動矩陣與其影響因素的相關性。表5的QAP相關分析結果。為避免解釋變量間的多重共線性,我們采用QAP回歸分析法檢驗影響因素對地方政府非稅收入聯(lián)動矩陣的影響關系。隨機置換次數(shù)選擇5000次,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調整R-squared為0.505且通過了1%顯著性檢驗,這說明區(qū)域間的財政收入分權差異、稅收收入差異、經濟發(fā)展水平差異、對外開放程度差異、城市化水平差異和產業(yè)結構差異能夠50.5%的解釋我國地方政府非稅收入聯(lián)動關系。財政收入分權的區(qū)域差異和稅收收入的區(qū)域差異與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空間溢出的回歸系數(shù)分別為-0.202和-0.135,均通過了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財政收入分權的區(qū)域差異和稅收收入的區(qū)域差異越高,意味著地方政府為了減少地區(qū)間的財力差距,財政競爭工具的可選擇集越大,地方政府間財政競爭模式從稅收競爭開始向非稅收競爭轉變,從而增加地區(qū)間在非稅收入領域競爭的可能性。經濟發(fā)展水平的區(qū)域差異對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空間溢出的回歸系數(shù)為0.015,通過了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隨著地區(qū)經濟增長,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缺口需要謀求非稅收入的支持,從而增強區(qū)域間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的聯(lián)動性。對外開放程度的區(qū)域差異對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空間溢出的回歸系數(shù)為-0.804,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地方政府和周邊地區(qū)在資源稟賦方面較為接近的情況下,制度環(huán)境成為影響投資者決策的重要因素。如果地區(qū)非稅收入規(guī)模高于周邊地區(qū),就會給投資者帶來負面的環(huán)境信號,地方政府為了獲得相對于周邊地區(qū)投資優(yōu)勢而引發(fā)非稅競爭。城市化水平的區(qū)域差異和產業(yè)結構的區(qū)域差異與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空間溢出的回歸系數(shù)分別為0.210和0.845,但是均沒有通過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在城市化和產業(yè)結構升級進程中,地方政府仍在資源配置中發(fā)揮著決定性作用。

表5 QAP回歸分析結果
四、結論與啟示
(一)研究結論
文章基于2000~2014年我國地方政府非稅收入數(shù)據(jù),根據(jù)修正的引力模型測算出中國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的空間關聯(lián)關系,并運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SNA)對中國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空間關聯(lián)網絡結構特征及其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考察。研究結論如下:(1)從整體網絡結構特征看,我國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空間關聯(lián)呈現(xiàn)出復雜的、多線程的網絡結構,網絡密度從0.2355上升至0.2484,說明中國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空間關聯(lián)網絡的網絡緊密程度逐年提高;網絡等級度維持在0.2888至0.5392之間,說明我國區(qū)域間地方政府非稅收入森嚴的等級結構被逐步打破,更多的地區(qū)脫離所在空間網絡中的從屬和邊緣地位;網絡效率維持在0.6552至0.6897之間,說明網絡中存在較多的冗余連線,網絡通達性好,網絡穩(wěn)定性高。(2)從個體空間網絡特征和核心邊緣分析結果來看,廣東、江蘇、山東等11個省份處于網絡核心位置;福建、四川、重慶等12個省份處于網絡半邊緣位置;甘肅、青海、寧夏等8個地區(qū)處于網絡邊緣位置。(3)從塊模型分析結果來看,上海、江蘇、山東等7個省份屬于凈溢出板塊,在網絡中扮演“引導”角色;福建、廣東、湖南等11個省份屬于經紀人板塊,在網絡中扮演“橋梁”角色;北京、天津、河北等8個省份屬于雙向溢出板塊,在網絡中扮演內部和外部雙向“引導”角色;甘肅、青海、寧夏等5個省份屬于凈受益板塊,在網絡中扮演“跟隨”角色。(4)QAP回歸分析結果表明,區(qū)域間財政收入分權程度差異、稅收收入差異和對外開放程度差異與地方政府非稅收入聯(lián)動矩陣呈現(xiàn)顯著負相關;經濟發(fā)展水平差異與地方政府非稅收入聯(lián)動矩陣呈現(xiàn)顯著正相關;城市化水平差異和產業(yè)結構差異與地方政府非稅收入聯(lián)動矩陣相關性并不顯著。
(二)幾點啟示
地方政府非稅收入聯(lián)動關系及其多線程網絡結構特征為推進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管理提供了新的視角與依據(jù)。第一,我國31個省份地方政府非稅收入之間普遍存在空間聯(lián)動關系,即省域間多線程的復雜網絡結構關系。基于此,國家在非稅收入的治理上,為了提升治理效果,應樹立區(qū)域協(xié)同治理理念,實施區(qū)域梯度推進策略。對于接近中心度和中介中心度較高的省份,一方面,要充分考慮這些省份地方政府非稅收入膨脹的自身傳導因素;另一方面,還要更加重視由于這些省份對其他省份的空間溢出而產生的引領或示范效應。如果這些省份地方政府非稅收入能夠得到定向調控,那么通過它們在地方政府非稅收入聯(lián)動網絡中的引領作用或中介作用則可能更好地調控其它省份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總之,地方政府非稅收入聯(lián)動關系為非稅收入空間協(xié)同調控創(chuàng)造了條件,同時也為地方政府非稅收入調控整體政策的實施增加難度,要求政府不僅要高度關注各地區(qū)自身“屬性數(shù)據(jù)”的表現(xiàn),還要充分重視區(qū)域間非稅收入的空間聯(lián)動性,地方政府非稅收入調控政策應從“點”轉向“面”、從“數(shù)量”轉向“結構”、從“局部”轉向“整體”。第二,地方政府非稅收入聯(lián)動網絡的板塊結構特征為制定差別化的區(qū)域定向調控政策提供了依據(jù)。為控制地方政府非稅收入快速增長,近年來中央及地方政府先后出臺一系列非稅收入調控政策,但調控力度還有待加強,調控效果有待提高。本文認為應充分重視地方政府非稅收入聯(lián)動網絡中板塊的空間聚類特征,以及板塊間的關聯(lián)效應和溢出效應,進而針對不同板塊特點制定區(qū)域性非稅收入調控政策。對于凈溢出板塊地區(qū),應利用其在地方政府非稅收入聯(lián)動網絡中扮演的發(fā)動機角色,以及地方政府非稅收入波動對其它板塊地區(qū)的引導作用,實施從嚴調控策略,并作為改革的先行先試地區(qū),從源頭上穩(wěn)定地方政府非稅收入。對于凈受益板塊地區(qū),因其在網絡中較多地受制于其它板塊,處于較為被動的地位,扮演著“跟隨”角色,這一板塊的地方可以作為政府非稅收入調控政策和管理改革的經驗推廣區(qū)域,在總結前期改革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穩(wěn)步推進。對于經紀人板塊地區(qū),因其在聯(lián)動網絡中扮演“橋梁”角色,直接影響整個地方政府非稅收入聯(lián)動網絡的關聯(lián)程度,所以基于這一板塊的非稅收入調控政策應充分考慮其在網絡中的傳遞作用。對于雙向溢出板塊地區(qū),基于這一板塊的地方政府非稅收入調控政策應充分考慮其內部、外部雙向“引導”作用,強調和重視改革過程中的區(qū)域聯(lián)動。第三,QAP分析結果揭示了影響地方政府非稅收入聯(lián)動關系的主要因素,指出了地方政府非稅收入變化規(guī)律背后的根源和動因,為加快非稅收入管理改革步伐、改善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管理效果提供了新的思路。分析結果印證了地方政府非稅收入聯(lián)動關系的復雜性,地方政府非稅收入增長或者說存在較大的管控難度,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既有財政分權體制安排以及稅收收入差異所帶來的地方財力差異可能提升了地方政府選擇非稅收入作為融資工具的可能性,在財政壓力的情況下,為了滿足發(fā)展地方經濟的支出需要,會賦予地方政府增加非稅收入的內在動機,由于區(qū)域間關聯(lián)性,給非稅收入管理改革的整體縱深推進帶來了阻力。為了控制地方政府非稅收入規(guī)模,消除地方政府謀求非稅收入的內在沖動,必須通過深入推進財政分權體制改革,從事權與支出責任相匹配、稅收收入的合理劃分、健全轉移支付制度等地方體制環(huán)境入手降低地區(qū)之間在財力保障上的差異,同時,應規(guī)范地方政府經濟發(fā)展競爭行為,強化非稅收入征管約束,防止非稅工具的濫用。
[1] 周瀟梟.2014年財政收入結構分析:地方非稅收入占比22%[N].21世紀經濟報道,2015-3-26(7).
[2] 張麗華,楊樹琪,孫輝.對現(xiàn)行非稅收入管理制度建設的評述和思考[J].經濟問題探索,2009,(1):121-124.
[3] 鄭建新.全面規(guī)范非稅收入管理加快建立現(xiàn)代財政制度[J].財政研究,2014,(10):24-27.
[4] 王玲.地方政府非稅收入激增的動因與條件分析[J].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10):63-66.
[5] 馮輝.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的激勵與法律規(guī)制[J].廣東社會科學,2014,(4):235-242.
[6] 白宇飛,張宇麟,張國勝.我國政府非稅收入規(guī)模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9,(5):43-47.
[7] 王志剛,龔六堂.財政分權和地方政府非稅收入:基于省級財政數(shù)據(jù)[J].世界經濟文匯,2009,(5):17-38.
[8] 白宇飛,張紫娟.地方政府非稅收入困態(tài)擺脫路徑研究[J].財政研究,2015,(9):59-63.
[9] 武玉坤.中國地方政府非稅收入汲取研究:一個財政社會學分析框架[J].貴州社會科學,2015,(10):136-142.
[10] Crowley and Sobel. Doe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Constrain Leviathan? New Evidence from Local Property Tax Competition [J]. Public Choice,2011,149(1):5-30.
[11] Brueckner J. K. Strategic Interaction among Governments: An Overview of Empirical Studies [J].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2003,26(2):175-188.
[12] 王佳杰,童錦治,李星.稅收競爭、財政支出壓力與地方非稅收入增長[J].財貿經濟,2014,(5):27-38.
[13] 陳工,洪禮陽.省級政府非稅收入競爭的強度比較與分析——基于財政分權的視角[J].財貿經濟,2014,(4):5-13.
[14] 童錦治,李星,王佳杰.非稅收入、非稅競爭與區(qū)域經濟增長[J].財貿研究,2013,(6):70-77.
[15] 孟天廣,蘇政.“同儕效應”與“鄰居效應”:地級市非稅收入規(guī)模膨脹的政治邏輯[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5,(2):165-176.
[16] Revelli F. Spatial Patterns in Local Taxation: Tax Mimicking or Error Mimicking? [J]. Applied Economics,2001,33(9):1101-1107.
[17] Devereux M. P.,Lockwood B.,Redoano M.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Indirect Tax Competition: Theory and Some Evidence from the USA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7,91(3):451-479.
[18] 童錦治,李星,王佳杰.財政分權、多級政府競爭與地方政府非稅收入[J].吉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6):33-42.
[19] 李敬,陳澍,萬廣華,付陳梅.中國區(qū)域經濟增長的空間關聯(lián)及其解釋——基于網絡分析方法[J].經濟研究,2014,(11):4-16.
[20] 劉軍.整體網分析:UCINET軟件實用指南(第二版)[M].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