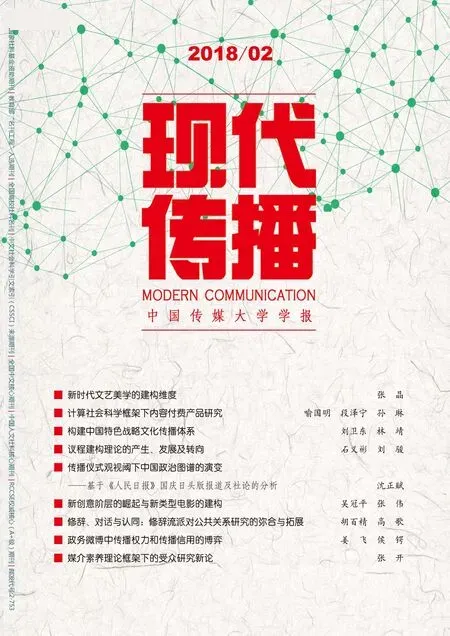修辭、對話與認同:修辭流派對公共關系研究的彌合與拓展*
■ 胡百精 高 歌
一、問題的提出
公共關系修辭流派興起于20世紀晚期,是公關理論研究的一次重要轉向,對于構建新的公關學術范式,特別是彌合行為主義取向公關研究的問題和局限具有重要意義。這一轉向發生于更開闊的三個學術和思想背景之下:哲學的語言學轉向、語言學的修辭學轉向,以及新修辭學的發展及其對話轉向。通過對這三個轉向的銜接和借用,修辭流派使公關理論建設獲得了如下拓展機會:建立公關哲學體系,以改變“公關罕言哲學”①的窘境;重返語言行為和話語實踐——公關理論研究的核心地帶,從人的存在、對話與社會互動、語言與世界的關系切入考察公關現象,并因此突破了行為主義公關研究的某些關鍵阻礙;兼顧了功能、詮釋和批判等傳統公關研究的經典路徑,提供了多元路徑相互敞開的可能性。
然而,公關學界并未善用這些機會。除了希斯(Robert L.Heath)等個別學者的成果,修辭取向的公關研究與哲學、語言學領域的新修辭學未能真正貫通。大多數參與其中的學者只是在語詞和話語分析層面搬運了新修辭學的部分概念和方法。針對上述問題,本文分別考察了新修辭學認識論和方法論、公關修辭流派理論主張和實踐路徑,在此基礎上將前者的思想資源進一步轉渡至后者,進而探討確立和拓展公關修辭范式的可能性。
二、新修辭學:語言、認同與世界
希斯、托斯(Elizabeth L.Toth)、庫姆斯(W.T.Coombs)、班尼特(W.L.Benoit)等人都承認,修辭取向公關研究的主要理論和思想來源乃新修辭學。②20世紀中前期,傳承自古希臘、古羅馬的古典修辭學在哲學、語言學領域于沉寂中被喚醒,并逐漸發展為新修辭學。新修辭學的誕生和成熟,得益于哲學的語言學轉向和語言學的修辭學轉向。
20世紀太喧囂和復雜了,這是哲學家們的普遍感受,“我們所見到的20世紀是一個充滿變革、動蕩、戰爭和沖突的時代,一個物質進步、環境惡化、自人類統治地球以來前所未有的時代”③。為了解釋人類在這個新時代的境遇,哲學家們不得不改造古典哲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把哲學研究的范疇由主體內在形而上的運思,拓展至形而下的外在世界和世俗生活,以理解新時代于外部強加給個體的復雜性——危機與繁榮、戰爭與和平、野蠻與文明、交往與沖突。在此拓展過程中,一些哲學家發現語言乃聯通主體內在與外在、形而上與形而下的媒介,故將研究焦點轉向語言。這就是后來對整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產生了普泛影響的所謂語言學轉向。
在語言研究受到重視后,索緒爾(Ferdinand Saussure)、皮爾斯(C.S.Pierce)等人發展了形式主義或曰結構主義語言學,探究語詞句法普遍共時的內在結構。雖然他們也宣稱語言是一種社會契約,但是對語言符號形式和結構的關切導致他們往往把文本當作孤立的考察對象,忽視文本的語境、修辭和意義問題。索緒爾明確提出:“意義不是符號學或結構主義語言學研究的主要任務,應該把它交給心理學或其他學科”。④而理查茲(I.A.Richards)、奧格登(C.K.Ogden)則認為,意義、修辭、文本、語境才是哲學和語言學研究的重點,“語詞不是復制生活的媒介”,它在交往者的闡釋和理解中生產意義;意義反映過去與現在、個人與社會的復雜鏈條,同時也建構了這些鏈條;語詞及其意義可能產生誤解,而修辭的目的在于達成理解。⑤
理查茲的全部論證皆圍繞兩個原初問題展開:詞語何以產生意義?交往何以消除誤解、達成理解?他給出的答案是修辭。語詞(象征或符號)與其指稱對象(所指)之間存在一個中介地帶即意義,三者構成了一個語義三角,而修辭乃搭建三角關系的表達機制和話語行為。語詞并無確定意義,所指可能抽象亦可能具象,因此意義只能來源于人的話語行為。這些行為包括編碼、解碼、對噪音的克服、對語境的適應,以及對指示(indication)、描述(characterizing)、體驗(realizing)、評價(valuing)、影響(influencing)、控制(controlling)、目的(purposing)等語言功能的綜合運用。理茲查指出,這正是一個修辭過程,人類運用符號和象征生產意義,并通過意義達成理解,建構交往者之間的共同世界。⑥在1930—1970年代,柏克(Kenneth Burke)、佩雷爾曼(Chaim Perelman)、韋弗(Richard Weaver)、圖爾明(Stephen Toulmin)、喬姆斯基(Norm Chomsky)——廣義上還包括巴赫金(M.Bakhtin)、格拉斯(Ernesto Grassi)和福柯(Michel Foucault)等學者也加入到修辭研究中來,共同推動了語言學的修辭學轉向,形成了與古典修辭學遙相呼應的“新修辭學”運動。新修辭學派總體上抱持如下主張:
一是意義乃語言和修辭的核心問題。語言是人的天賦,而此般天賦的核心價值在于創造和分享意義,使人類的溝通、理解、合作、和諧以及維系共同體成為可能。除了理查茲,佩雷爾曼、巴赫金、格拉斯等人也都特別看重語言行為——修辭的意義生產功能。譬如在格拉斯看來,人類擁有想象、工作和語言三樣天賦⑦,而正是語言使人類能夠以自身的經驗理解和表達世界,賦予存在和現象以意義,從而改造自然、教化自我、創造歷史。對意義而非形式的重視,使新修辭流派與語言學轉向中的形式主義、結構主義研究區隔開來。
二是凡表達皆修辭。柏克提出:“哪里有說服,哪里就有修辭;哪里有意義,哪里就有說服。”⑧人是象征的動物,藉由語言行為與他者和世界進行象征互動,以構建共通的意義空間,改變個體與生俱來的孤立、隔絕狀態。因此,修辭的情境是遍在的。“人一旦運用語言,便不可避免地進入修辭情境”。⑨圖爾明等人也認為修辭乃人類生活的核心問題,是人類形成和表達一切動機、實現所有交往和互動的基礎。⑩這就把修辭研究從文學、演說、辯論等狹隘領地解放了出來,將之推向人的日常存在和更開闊的社會交往空間。政治、商業、外交、傳媒、廣告、公關以及日常生活等全部人類交往活動皆可視為修辭,皆仰賴修辭而運轉。
三是語言的“反仆為主”。在傳統觀念中,語言乃人之工具。語言學的轉向拋棄了這種工具論,發現了語言反仆為主的功能——建構人和世界。索緒爾認為語言有其內在結構,并依照自身的結構編碼世界。而語言建構的世界與真實世界并非全然對應,有時簡直是兩碼事。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認為在語言運動中,不是表達者絕對主導言說,而是言說反過來建構了表達者的角色和地位。柏克明確指出:“人類主要生活在語言之中,用語言談論語言,用語言解釋語言。”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的語言觀更加激進,“人以語言的形式擁有世界”。新修辭理論認為,語言反仆為主的動力機制正是修辭,修辭不僅普遍存在,而且生產和控制意義,命名世界和建立秩序,組織和規范人類的思想與行為。
四是修辭論證與完整認識世界。在古典修辭學中,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審慎區分了辯證法和修辭論證:前者遵循形式邏輯,基于必然性和明確的因果關系實現對世界的理性認知,故可用來獲取知識;后者則奉行或然性邏輯,談論的只是某種相關性或可能性,故可用來說服聽眾。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據此認為,辯證法乃認識世界的高級手段,修辭論證則相對低劣。這種看法影響深遠,以至于知識精英尤其是科學家總是在辯論中強調自己“沒有使用修辭”。新修辭學派對高高在上的辯證法強烈不滿,指出了形式邏輯認識世界的局限。佩雷爾曼等人在考察大量政治家、道德家和律師辯論個案后提出,并非所有社會領域都奉行形式邏輯。譬如在輿論、情感、道德、審美諸領域,苛求形式邏輯上的必然性和因果律往往徒勞,甚或帶來災難性后果。而修辭論證恰可以為這些領域提供或然的理性基礎。因此,修辭論證并非低劣的認識手段,它與辯證法的相互聯合有利于人類完整地認識世界。
五是修辭的前提和目的皆為認同。新修辭學并未拋棄或顛覆古典修辭學,而是繼承、拓展了其核心思想。亞里士多德將修辭定義為“在每一事例上發現可行的說服方式的能力”,韋弗、柏克等人幾乎完全接納了這個定義。韋弗認為“語言即說教”,凡語言使用皆帶有說服性質,皆內蘊倫理問題,即修辭性的。柏克也承認,修辭即藉由話語行為影響交往者的態度和行為。那么新修辭學何以為“新”?一則如前所述,柏克等人將修辭視為遍在于人類交往活動,關系到人類如何認識自身和世界的大問題,不再像古典時期那樣將修辭局限于特定語境、文本,或風格、技巧之類的“雕蟲小技”;二則新修辭學將認同視為修辭的出發點和歸宿,認為“舊修辭學的關鍵詞是說服……新修辭學的關鍵詞是認同。”
1986年,希斯出版了他的代表作《現實主義與相對主義》(Realism and Relativism),系統介紹和批判了新修辭學特別是柏克的修辭思想。之后,希斯并未像他的學術偶像柏克那樣深耕修辭哲學,而是以其修辭學訓練投向了公共關系研究。進入1990年代,以希斯為代表的一批公關學者持續借鑒、應用新修辭流派的思想資源,逐步確立了公關修辭流派的格局和地位。自此,公關理論研究出現了管理流派、關系流派、傳播流派和修辭流派多足鼎立的新局面。
三、公關修辭流派:意義、對話與情境
希斯并非第一個行動者。1983年,克萊伯(Richard Crable)等人對里根總統的某場演說進行了修辭分析,以考察政治信仰表達中的語用資源和符號選擇;1988年,斯普盧爾(Michael Sproule)提出了新管理修辭(new managerial rhetoric)概念,將組織視為修辭者(rhetor),按修辭框架研究了組織在海報、宣傳冊、新聞稿和公告等文本中所欲傳達的組織形象(persona)和意識形態。希斯、托斯合作出版了《公共關系修辭與批判研究》(Rhetorical and Critical Approach to Public Relations),該書被認為是公關修辭流派崛起的標志。此后十余年,希斯、托斯、庫姆斯、班尼特等人相互呼應,為公關理論研究開辟了一條修辭取向的通途。
盡管加入公關修辭流派的學者越來越多,但希斯始終是旗手。他的公關修辭理論筑基于新修辭學的幾個核心概念和觀念。
一是公關即修辭。公關與修辭有著天然的聯系,二者皆屬以說服為目的的語言實踐。在管理流派、關系流派和傳播流派看來,公關與修辭乃從屬關系,后者是前者謀求說服效果的諸多手段之一。希斯則持以柏克的修辭遍在論,主張公關就是組織和公眾彼此適應的修辭過程,“組織可根據消費者和公眾的偏好采取行動、設計產品和提供服務。同樣,如果組織的某項倡導足夠有說服力,消費者和公眾也會主動采信、誠意跟隨”。希斯相信,藉由持續的動態影響、相互調整,組織和公眾能在對話中達到彼此適應的平衡。這一判斷顯然受到了新修辭學能動語言觀的影響:修辭使觀念適應人,也使人適應觀念,并建構人與人、觀念與觀念之間的平衡關系。
希斯進一步提出,公關和修辭都承認世界的未知、不確定性和矛盾性,試圖介入和解決那些存在爭議的人類事務。那些遍在的“不確定性和未知,以及(人類面對同一對象時)復雜的動機、迥異的主張乃修辭和公關得以存在的共同前提”。從此前提出發,公關致力于在多元對話中建立信任、消除誤解、達成理解,形塑程序或實效上的認同,而這正是組織以修辭者身份介入社會互動的話語行為和說服過程。從更廣泛的意義上看,公關的主體和對象——個體、組織和社群皆屬語言和修辭的存在,基于修辭和象征互動來理解、影響外部世界。
二是意義乃公關的核心問題。這是希斯從新修辭學那里直接借用的一個觀念。理查茲等人認為,修辭生產意義,并通過意義的社會建構、連接和接納,使交往者進入共同的世界。從修辭視角看,公關即組織生產意義,并期待與多元公眾構建共通意義空間的過程。這種意義中心論使公關修辭流派同盛行的管理流派區別開來。管理流派認為,公關的核心問題是力求卓越地管理傳播過程,以期實現組織與公眾在利益上的雙贏。希斯的合作者托斯指出,“管理學派的量化取向假定傳播是符合一定標準和流程的實踐行動,重視對這一過程的管理,而不是通過修辭分析研究傳播究竟實現了何種程度的意義建構。”修辭流派則更關切公關的意義生產及其達成理解和認同的可能性,而理解和認同從來不只是一個利益問題。
這就涉及到新修辭學派對認同問題的深入討論。柏克認為新修辭學對古典修辭學最大的改造是對認同的強調,“舊修辭學的重點在于說服力建設,強調語言技巧的審慎設計,而新修辭學則主張修辭是為了靠近本體層面的認同,并且重視來自本能和表達場域的無意識因素。”古典修辭學片面追求表達技巧和說服力建設,忽視了認同才是交往的基礎。柏克特別重視基于身份和無意識的“本體認同”:聽者對言者身份的認同是如此牢固,以至于有人不管講什么聽者都愿意相信,也有人縱口吐蓮花亦屬枉然;直覺、本能或無意識的心靈認同,以及宗教性的神秘認同往往也比說理更強大。因此,形塑認同較之表達技巧和溝通過程更具基礎性和優先性。同時,意義和認同不單指向理性和利益問題,而且包含了本體、直覺乃至宗教意義上的“同一性”。
三是修辭和公關的對話轉向。語言學發生修辭學轉向后,修辭學又出現了對話轉向。這場轉向至少存在三個動力來源:古典修辭學過于強調修辭的規勸、教育和支配功能,導致修辭學看起來極像一門不光彩的“統治術”,新修辭學因此強烈期待以對話、同一、認同等概念取代教化、支配和統治,以為修辭確立正當的價值觀;修辭以意義為中心,而意義乃編碼與解碼、表達與闡釋等雙向協商的產物,因此修辭和話語行為理應走向對話,“對話才是意義的真正所在”;面對20世紀復雜的社會交往實踐,尤其是民主政治和大眾社會的持續發展,旨在消除誤解、達成理解、增進和諧的修辭也要因應時勢、轉向對話。
公關研究同樣存在新修辭學派的上述三個訴求。希斯敏感地捕捉到了修辭學的對話轉向,并將之轉用于公關理論建設。人們之所以需要修辭,試圖真切、有力、靈動地表達自己,就是因為“修辭假定有多元聲音加入對話,而不是陷入獨白”。若非為了對話和認同,則修辭是不必要的。希斯引述柏克說,社會乃觀點的市場,多元主體圍繞事實、價值和公共政策爭論不止,修辭和對話使人們相互理解對方所主張的事實、價值、政策、所欲認同之物及其敘事方式,從而做出正確抉擇。專業的、良善的公關可以確保某項事業、某個產業、企業或個人加入眾聲喧嘩的觀點競爭,并在對話中彼此傾聽、達成認同。
批評者指出,修辭調適各方意見的結果未必是理想的平衡,精英總是通過操控大眾心智制造共識,最終強化了主導意識形態的統治權。希斯回應說,修辭確實可以用來做好事,也會做壞事,但是“人們只需稍加留意就會注意到,任何以信任為代價的策略,最終只會讓事情和自己的處境變得更糟”。在現代民主社會,對話的價值不僅是在多元聲音中尋求“相對較佳”的問題解決方案,而且它本身就意味著信任、開放和平等,并持續、動態地引導人們趨向認同。這也正是藉由對話取向的修辭重構公關角色和道德的原因所在。
希斯還借用了柏克提出的“辭屏”(terministic screen)概念來說明對話、合作的必要性。柏克認為語言因其呈現和遮蔽的雙重本質,同樣有攝影透鏡的“濾色”功能。人們在交往時使用的詞語,就像獨特的修辭濾色鏡,柏克稱之為辭屏。人們透過辭屏看世界,有所選擇,也有所背離(deflection)。當某一群體被描述為消費者而不是公民,表明修辭者意在選擇和凸顯其經濟屬性而非政治屬性。希斯進一步指出,“每種辭屏代表一個不同的視角”,每一視角都代表一種觀看之道。人們傾向于認同持相同視角者,信任敘事和倫理判斷與己一致的人。在高度市場化、多元化的現代社會,辭屏之間形成了鮮明比照和激烈競爭。無論人際交往還是社會互動,若欲達成認同與合作,修辭者就要持續調整辭屏、促進對話。柏克和希斯的辭屏概念也呼應了巴赫金的對話思想,后者認為多元、獨立、差異化的主體只有在對話中才能彌合各自的視域剩余,從而形成完整的理解力和判斷力。
除了前述意義、認同、對話等問題,希斯還注意到了新修辭學對結構主義語言學的一個重要指控——語境、情境研究缺位。他基于修辭學家比徹爾(Lloyd Bitzer)的情急狀態(exigency)概念,考察了公關領域的修辭困境(rhetorical problem)。所謂修辭困境,即組織在公關實踐中面臨的一種情急狀態,這種狀態揭示或激發了利益相關者對組織行為、決策及相關影響的質疑或異議,組織需要針對情急狀態制定適當修辭策略,以化解困境。此中,話語必須契應情境,情境決定了意義生產的可能性、對話與認同的有效性,以及倫理和價值觀的正當性。
庫姆斯在公關修辭情境研究方面做出了更豐富和實用的貢獻。他指出,“組織和利益相關者之間在利益協商、意義生產,乃至對事實的認知、理解和價值詮釋上存在著鴻溝”,“雙方在動機、利益的解讀、價值判斷、行為選擇以及結論等方面皆出現難以彌合的斷裂”。為此,組織要因應情境變化采取靈活的修辭策略:在危機發生階段(crisis phase),回應利益相關者對健康、安全等核心關切,不僅要提供有關核心關切的說明性信息(instructing information),還應積極開展補救行動,提供情感和精神撫恤等修復性信息(adjusting information);在后危機階段(post-crisis phase),修辭困境發生遷轉,組織要兌現對利益相關者的承諾,還要開展形象修復和聲譽管理。無論在哪個階段,組織作為修辭者的德性和信譽都直接影響危機傳播的成敗。總之,危機傳播就是一種化解修辭困境的公共話語(public discourse),組織要引導利益相關者以共同的視角理解危機,于對話中尋求認同。
班尼特是另一位深耕公關修辭研究的代表性學者。他被廣為引用的形象修復理論區分了多種危機情境,提出了針對性的修辭策略:否認事實(Denial),包括簡單否認和轉移批評;回避責任(Evasion of Responsibility),包括申明被挑戰,無力為之或不可抗,純屬意外或無心之過;淡化處理(Reducing Offensiveness of Event),包括輕描淡寫事態,提供證據顯示該事件帶來的利益和好處,進行比較、尋找差異,以及反擊對手、降低指控者的信譽,或合理補償利益受損者;修正行為(Corrective Action),制定和實施解決方案,改善自身行動,避免此類事件再次發生;誠意致歉(Mortification),表示遺憾和歉意。
一些中國公關學者也注意到了修辭研究的重要性,代表性的成果包括:張依依簡要介紹了公關修辭流派的興起,分析了該流派與傳播、管理、關系諸流派的異同;吳宜蓁將希斯、庫姆斯、班尼特的研究成果應用于危機情境,探討了危機修辭的理論框架;胡百精比較了西方新舊修辭思想同中國修辭思想,考察了柏克修辭理論在公關敘事中的應用。
四、范式創新:改造、拓展與融合
傳播流派、管理流派和關系流派是既往研究中較為成熟的三大流派,三者分別強調了公關的傳播、管理和關系維護功能。在1990年代,格魯尼格(J.E.Grunig)等人確立了卓越公關理論的主導地位,公關即傳播管理的定義深入人心,傳播流派與管理流派漸趨合流。如是,公關的經典研究取向就變成了傳播管理和關系管理兩大流派。也恰在同期,修辭流派強勁崛起,與前二者形成鼎足之勢。
公關修辭流派的崛起有其內因和外因。從理論建設的內部情況看,修辭流派大體確立了公關修辭理論的核心概念與觀念、框架與方法,扎實開展了特定公關情境的修辭策略研究。事實上,除了希斯、托斯在基礎理論和庫姆斯、班尼特在情境理論方面的探索,還有更多公關學者于微觀層面對組織話語展開修辭分析,在應用、功能和效果方面取得了豐富、精致的研究成果。譬如,一些學者基于組織即修辭者的假設,從語詞、句法、主題、動機、調性和價值觀等微觀問題切入,深入考察了包括口號、標語、公告、公共演說等多樣文本的意義生產方式和效果。可見,公關修辭流派搭建了從宏觀到中觀再到微觀層面的理論框架,初步確立了修辭取向公關研究的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
從外部情況看,修辭流派有效彌合了傳播管理和關系管理研究取向的不足,為創新公關理論范式提供了可能性。早前的公關傳播流派也重視說服,強調通過設計、控制信源、信息、信道等傳播自變量,改變信宿的認知、態度和行為等因變量,試圖構建系統的、集成的理論范式。公關之父伯內斯的看法最能代表傳播流派的主張:“包括公關專業人員在內的少數社會精英是對社會進行隱蔽治理的專家,他們以簡單的文字或圖像捕捉并馴服大眾的想象,守護進步社會的穩定秩序。”他后來雖然也主張公關是“組織與公眾之間的雙行道”,但仍是組織說服、支配公眾,而不是反過來。傳播流派在20世紀中后期的發展墮入了行為科學主義的陷阱:越來越看重傳播變量、過程和預期結果的設計,而公關的基本問題——話語建構和意義生產的核心地位卻遭弱化。譬如,麥奎爾的說服矩陣,包含了5個自變量、13個因變量,話語、意義問題湮沒于繁復的傳播要素和過程之中。這就犯下了一個吊詭的錯誤:傳播流派認為公關以說服為業,話語和意義問題卻在公關研究中邊緣化了。
管理流派將公關定義為組織的一種管理職能,有效的公關有利于組織管理戰略性公眾(strategic public),降低組織成本,構建“組織—公眾”共生的雙向開放系統。及至格魯尼格夫婦、亨特、多澤爾等人發展出卓越公關理論和雙向均衡模式(symmetrical model),公關的定義被明確為組織與公眾之間的傳播管理,旨在謀求二者雙向均衡的溝通、互蒙其惠的雙贏。作為“公關領域最具影響力的理論范式”,卓越公關理論亦存在明顯的局限:在真正的平等幾無可能的情況下,組織與公眾何以實現理想中的雙向均衡溝通?作為一種管理職能,公關可以避免零和博弈或雙輸局面而實現組織與公眾的雙贏?雖然格魯尼格強調了“公關世界觀”的重要性,但它的來源何在?是誰的世界觀?是否仍會墮入組織強加或一廂情愿施予某種世界觀的窠臼?而當我們談論公關世界觀時,公關的哲學是什么?
關系流派的一些主張在公關學術史的早期即已出現,但它的真正興起也是在20世紀80-90年代。卡塞(Shawna Casey)、里奇(James Ritchey)、萊丁漢姆(J.A.Ledingham)和白朗寧(S.D.Bruning)等人批判傳統公關模式重“公共”(public)輕“關系”(relations)的傾向,進而提出了建立“以關系問題為中心”的公關新范式。格魯尼格、多澤爾等管理流派的關鍵人物隨后也加入關系研究,流派邊界呈現了突破、融合之勢。關系流派主張建立和維護組織與公眾的長遠戰略關系,并因此確立了測試關系質量的若干指標:信任(trust)、互控平衡或曰勢力均衡(control mutuality)、關系的滿意度(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關系互動中承諾的兌現程度(relationship commitment)和目標的達成程度(goal achieved)。格魯尼格等人還提出了關系管理的六種策略:接近(access)、積極卷入(positivity)、開放(openness)、保障(assurances)建立關系網絡(networking)和任務共享(sharing of tasks)。
關系學派開啟了公關研究的新維度,更加重視公關中的信任、結構和控制等問題,但也遮蔽了其他流派的一些視域和洞見,譬如相對輕視了傳播要素、管理過程和互動情境的重要性與復雜性。以情境問題為例,關系是一個強烈受到文化和社會情境影響的交往范疇,譬如中國式關系和美國式關系分殊甚巨,以至于一些西方公關學者不得不用guanxi而非relationship來指代中國語境下的社會關系。此外,關系管理與傳播管理研究皆抱持強烈的功能主義和行為主義傾向,注重變量調節、過程管控和實效實惠,而對公關的哲學觀照、意義闡釋和批判分析則無力或無意為之。而修辭流派恰好可從這些留白或虛弱處下手,為公關理論研究拓展新的視野和空間。
托斯概括了公關修辭流派的四個基本觀點(four perspective of rhetoric):人文主義、對話、象征和批判,可以看作對前述拓展可能性的積極響應。人文主義是修辭流派與其他公關流派相區隔的核心特質之一。理論界普遍認為修辭流派所承繼的人文而非社會科學的傳統。與社會科學尤其是行為科學偏重以實證、量化方法測定傳播行為對群體產生的影響不同,人文主義取向的修辭研究不崇拜方法和工具,也不抽象地談論群體,而是明確承認個體在傳播和意義生產中認知和選擇的合理性。
對話是修辭流派的另一個核心觀點,它最大的貢獻在于打破了長期由組織主導的單向、線性話語模式,淡化了公關宣傳、教化和操縱的色彩。雖然管理流派也提出了“雙向均衡”的概念,但是修辭流派則向前一步,明確將之落實為意見交換和意義建構的多元對話。希斯反對行為科學取向的“傳者中心論”,認為修辭絕非某種語言幻術,平等、開放的對話才是修辭的應有之意。克萊伯和維博特也提出,企業的修辭過程即是各方意見交換的對話過程。
修辭流派的第三個重要特質是重視象征研究。人類世界由象征所建構,象征無處不在,修辭流派的一個獨特優勢是使公關研究真正認識到了“語詞和其他象征符號的影響”。托斯在考察修辭流派的代表性成果后發現,不同于管理流派和傳播流派重視傳播流程設計、對信息流通方向和效果的控制,修辭學者更關注信息和意見在人際間傳布、交換的深層象征本質(symbolic nature),以及多元對話和公共決策中的意義生產機制和語言策略的選擇,“修辭有關象征的研究填補了公關其他流派視域的空白”。
在兼顧功能和詮釋研究取向的同時,修辭流派的批判主義取向深度涉入了公關倫理和哲學問題。修辭具有影響、塑造人和社會的獨特價值,因此以批判的眼光檢視修辭的文本設計、策略規劃和效果達成,有利于深入評估修辭背后的動機和權力問題,并從哲學高度探討公關的倫理規范。希斯將這一過程稱為把握“社會可持續性的框架”(evaluative frameworks that give continuity to society)。他認為修辭可以撥開信息的迷霧和文本的表象,從批判的進路探知意見和意義如何創造或打破社會運行的持續性。譬如,公共決策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乃公眾是否認同決策者的倫理、責任感和價值觀,而非事實層面政策條款和風險評估所呈現的信息和數據。這就彌補了公關管理、傳播和關系流派“信息中心論”(information-centered)的不足,不唯信息至上,而是批判性地關切信息背后的倫理價值。循此向上,更可將公關、修辭對人與社會的塑造拓展至哲學層面進行考察。
總體而觀,公關修辭流派為公關理論發展和范式創新敞開了新的通路。新范式基于人文主義視角,以象征互動和意義生產為中心,從功能、詮釋和批判諸路徑出發,考察作為話語行為和對話實踐的公共關系語境、文本和效果。然而,公關修辭流派的理論建設遠未達到完善、圓滿之境。這主要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一是對新修辭理論思想資源的借鑒、轉渡仍顯表面化和碎片化,因而限制了公關修辭流派的整體解釋力和想象力。理查茲、柏克等人構建了貫通哲學、語言學和修辭學的龐大思想體系,在哲學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等層面對話語行為、象征互動和意義生產皆有復雜、深刻的討論。而除了希斯,公關修辭流派的代表人物中大多缺少語言哲學和修辭哲學的系統訓練,往往僅根據自己的論證需要挪用、嵌入某些新修辭學的概念或命題。這就導致新修辭學在一些重大和基本問題——修辭與人的存在、修辭與真理、修辭與權力、修辭與倫理等領域的厚重思想遺產,并未充分轉化、應用于公關修辭理論研究。也正因為如此,公關修辭流派并未如人們期待的那般,發展一套有完整解釋力和豐富想象力的公關哲學。譬如,公關修辭流派借鑒了新修辭學的對話概念,但關于對話何以改造交往者之間的“主體—客體”關系,以構建互為主體關系,卻未能像后者那樣在哲學認識論層面展開完整、深入的闡釋。而這個問題若得不到解決,那么所謂對話不過是一種充滿道德溫情的交往烏托邦。
二是從功能主義的視角看,新修辭學中一些經典、“好用”的理論尚未被創造性地應用于公關研究和實踐。譬如理查茲的有效溝通概念(effective communication)、圖爾明的實用辯論模式(model of practical argument)、韋弗的新柏拉圖主義(Neo-Platonism)、柏克的認同(theory of identity)和戲劇主義修辭思想(dramatism rhetoric)皆對公關理論和實踐創新有重要、直接的啟發意義,但它們在公關修辭流派的研究成果迄今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和引介。以圖爾明的論辯模式為例,該模式視辯論為“從事實出發的修辭旅行”,它由六個要素構成:主張(Claim):某人試圖在論證中證明為正當的觀點或結論;根據(Grounds):作為論證基礎的事實/證據;理由/擔保(Warrant):連接根據和結論的橋梁,確保主張合法地基于根據;支援(Backing):通過回答對正當理由的質疑而提供的附加支持;模態限定(Qualifiers):指示從根據到理由這一步的強度;反駁(Rebuttal):舉出阻礙主張實現的因素,限定主張所適用的范圍。拋開圖爾明復雜的哲學論證不談,僅從語用上看,該模式亦可為多元公關情境提供明確的修辭指南。
三是修辭、管理、傳播、關系諸流派的相互敞開、融合和共創尚處起步階段,公關修辭流派并未真正履踐自己的對話主張。如前所述,管理、傳播和關系流派的融合創新已見標志性成果,而修辭流派與其他流派的彼此開放和介入顯著不足。從現有成果看,修辭流派主要以批判視角和反思性框架干預其他流派過度的功能主義和行為主義取向。批判固然是可貴的,協同創新和價值共創更不可少。有效對話缺位至少辜負了新修辭學派有關對話的核心主張,譬如韋弗宣稱的“修辭通過把所有個體對于修辭的經驗和意義融為一體,從而成為超越個體的普遍經驗……在人們尋求文化的象征時,它能把一種共同文化的所有頭腦連接在一起”。哈貝馬斯的說法則更直接,“研究對象越復雜,用單一某個學科的方法就越難以奏效”。
五、結語
最近十余年來,已有一些學者起而行之。伯頓(C.Botan)和泰勒(M.Taylor)提出了公關的共創模式(co-creational model),試圖協調傳播、修辭和管理等不同視角,將組織和公眾視為平等的對話者,雙方皆以主體身份進入詮釋共同體,分享意義,共創價值。皮爾森、肯特和泰勒、梅森巴赫、胡百精等學者持續將對話理論引入公關研究,以之確立公關的哲學前提、倫理基礎和實踐模式,并嘗試構建多流派相互敞開的新范式。誠如巴赫金指出的那樣,對話不一定走向某種確定的結果或結論,但它至少會許諾持續的傾聽、表達、理解,只要對話得以發生和持續,超越的可能便一直存在。
注釋:
① 賴祥蔚:《公共關系學想像:社群主義觀點》,《新聞學研究》,2004年總第80期。
② 具體論述可參見本文中對希斯、托斯、庫姆斯等學者核心觀點的介紹和引用,在此不一一贅述。
③ [美]邁克·亞達斯、彼得·斯蒂恩、斯圖亞特·史瓦茲:《喧囂時代》,大可、王舜舟、王靜秋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序言第1頁。
⑤ I.A.Richards.PracticalCriticism:AStudyofLiteraryJudgement.London:Kegan Paul,Trench,Trubner.1929.p.174.
⑦ 溫科學:《當代西方修辭學理論導讀》,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258頁。
⑩ Sonja K Foss et al.(Eds.).ContemporaryPerspectiveonRhetoric.Long Grove:Waveland Press.Inc.1991.p.173-181.
(作者胡百精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執行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高歌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