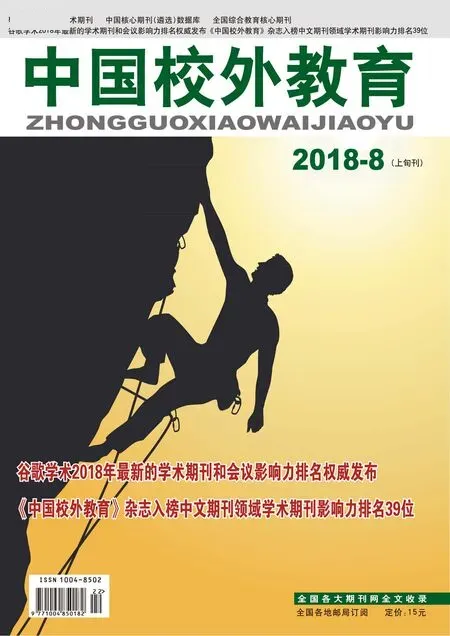論如何將生活化教育思想引申到小學語文教學中
◆孫欽艷
(山東省臨沂市莒南縣第一小學)
生活化教育思想的推崇者、中國著名教育學家陶行知先生曾經說過:生活教育是以生活為中心之教育,生活與教育是一個東西,不是兩個東西。他們是一個現象的兩個名稱,好比一個人的小名與學名……生活即教育,是生活便是教育,不是生活便不是教育。這位偉大的民主教育家還說過:生活教育的生命力特別強,它今天不是完成的東西,明天也不是完成的東西,它會永遠隨著歷史和生活的發展而發展。
一、教材講解生活化
教師照本宣科的教學方式是不負責任的表現,而教師結合實際生活對教材內容進行講解卻能夠賦予教學活動全新的、活躍的生命力,陶行知先生曾經說過:沒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沒有生活做中心的學校是死學校,沒有生活做中心的書本是死書本。由此,在語文教學中,教材講解生活化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例如,在對《快樂的節日》一文進行教學時,首先將文章背景進行講解——課文內容原是一首歌詞,作詞者是管樺,并詢問學生誰會唱,學生集體舉起了他們的小手,教師便站在講臺上以教棍為指揮棒,帶領學生對《快樂的節日》進行演唱,學生們十分興奮,一個個唱得臉蛋都紅通通的。演唱結束之后,教師趁熱打鐵帶領學生對課文當中的必會字詞進行了學習,隨后指導學生對課文進行了流利的、充滿情感的朗讀。最后,教師問學生,“同學們,通過學習《快樂的節日》這篇課文,或者說通過演唱這首歌,大家想到了生活當中哪些快樂的節日呢?”學生們再一次爭先恐后地舉起了手,“六一兒童節!”“植樹節!”“春節!”
在上述教學案例當中,教師通過帶領學生演唱《快樂的節日》這首歌,并結合課文內容聯系生活當中的節日進行生活化教學,增加了學生的學習樂趣,并加深了其對所學內容的學習與理解,最終實現了教學效率的提高。
二、寫作教學生活化
語文寫作取材于生活,而寫作學習的最終目的即運用于生活,二者息息相關,“‘教育即生活’——將教育和生活關在學校大門里面,如同一只鳥關在籠子里。‘生活即教育’——是叫教育從書本的到人生的,從狹隘的到廣闊的,從字面的到手腦相長的,從耳目的到身心全顧的。”一味地讓學生呆在教室里,如何保證其思維活躍度?如何激發其寫作靈感?又從哪里尋找寫作的源泉?與其讓學生在教室里生堆硬造,寫一些陳詞濫調,不如帶領學生走出教室感受生活,在生活當中感悟寫作、學習寫作、享受寫作。
例如,在某節語文寫作課堂上以“尋找春天”為主題,帶領學生到附近的公園踏青,讓學生在真實的生活中、在歡樂的活動中激發其內在的、自然的文字靈感,讓其自愿寫作、高效寫作,進而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與寫作水平。
三、提問方式生活化
語文教學當中存在一大通病,大多數語文教師的提問方式、提問用語以及提問內容都十分的“官方”與“教科書化”,就像是從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這使得學生回答問題的積極性下降,甚至因此對語文學習及教師產生疏離感。那么,為什么不能將課堂提問生活化呢?陶行知先生曾經說過:從定義上說,生活教育是給生活以教育,用生活來教育,為生活向上向前的需要而教育;從生活與教育的關系上說,是生活決定教育;從效力上說,教育要通過生活才能發出力量而成為真正的教育。教師在語文教學當中可以嘗試將提問方式、語氣及內容生活化,就像一個長輩用柔和的語氣在詢問孩子問題;不要脫離實際,泛泛而講、泛泛而問,而將教學內容與實際生活結合來進行提問。
例如,在對《要下雨了》這一課進行教學時,教師在課堂上結合教材內容與實際生活向學生提出了幾個問題,并以這些問題對學生實施了課堂導入:同學們,你們喜歡雨天嗎?那么大家觀察過下雨之前的天空嗎?大家還知道哪些動物能夠“預報”天氣呢?教師諄諄善誘,學生“漸入佳境”,很快進入了學習狀態,為后續教學活動順利、高效地開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與此同時,學生通過上述問題對所學內容產生了一定的了解與興趣,進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其學習的積極性及學習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