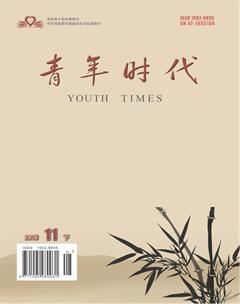譯者的適應與選擇
鄭青
摘 要:本文擬以生態翻譯學的“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為理論工具來評析譯者的兩個譯本,并結合此次翻譯實踐和翻譯批評實踐,梳理總結譯者對翻譯過程、翻譯標準和翻譯批評的認識。
關鍵詞:生態翻譯學;“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
一、前言
2010年11月初,楊金才老師布置翻譯Miriam C. Daum 2005年2月2日發表在《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上的一篇短文Nature Raises and Lowers the Curtain,并要求就翻譯的過程和結果進行分析和總結,寫出一篇2,000字左右的翻譯批評。
為了使評論言之有物、有理有據,真正起到指導和促進翻譯的作用,本人采用胡庚申教授的生態翻譯學理論,對本次翻譯活動做一個小而全的批評。
二、譯者在語言維的適應與選擇
“譯者對語言維(即語言形式)的適應性選擇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層次上進行的”(胡庚申,2004:134)。本次選譯的散文篇幅較短,英文共計486詞。整篇文章,語言準確而生動。
譯者對文章翻譯了兩次,兩次翻譯中間間隔10天左右。重譯時重點注意漢語表達的準確和地道,更注意傳達英文中直接用于描寫日出和日落的文字有280詞,占了一半以上篇幅。尤其是中間的三個明喻,以畫家作畫為喻體,既增添了文章的生動性,又起到了前后呼應的作用,使文章結構也更加緊密。這給譯者提出了較高的語言要求。
下面,本人試從語義學的角度,來分析源語和譯語在意義上的差別,以反映譯者在選擇與適應方面做出的努力:
We watched the horizon intently, trying to guess where the sun would emerge.
譯文一:我們一邊急切地望著地平線,一邊想要猜出太陽會從那里冒出來。
譯文二:我們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地平線,想猜出太陽升起的地方。
原文中“watched intently”,表示“專注地、全神貫注地注視著”,譯文一用了“急切地望著”,有“著急、不安”的聯想意義,與原文不符;且“望著”的語用意義與“注視著”相比稍不正式。譯文二用“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則與原文教貼合。從語法上看,原文的“trying”表伴隨主句同時發生的動作。譯文一用“一邊……一邊”結構表并列,忽視了漢語是重意合的語言,不用“一邊……一邊”結構反而使譯文更精煉地道。
Turning toward each other we smiled and sighed.
譯文一:我們相視而笑,都嘆了口氣。
譯文二:我和比爾轉過頭來,會心一笑,轉而又都嘆了口氣。
譯文一“我們相視而笑,都嘆了口氣”缺失了“turning”和“and”的翻譯。原文中作者和好友看日出后的片刻快樂和要返回上班的無奈,都在這一笑一嘆中。譯文一僅僅傳達語言了字面意義,言內意義和語用意義缺失。譯文二則解決了這一問題,且選擇用“會心一笑”貼合了目的語語言和潛在讀者。
“The sun moves so quickly now in the short days of winter,” I said.
“冬天晝短夜長,這太陽落得可真快,”我開口說。
原文中“in the short days of winter”,準確的理解是“冬季白天的時間變短”。如果就譯成這樣,固然讓譯文讀者在理解上沒有問題,但“晝短夜長”雖在指稱意義上比原語更大了,但言內意義和語用意義則與原語更接近,且是中文的習慣表達,更適應譯文讀者的潛在要求。
三、譯者在文化維的適應與選擇
“由于原語文化和譯語文化在性質上和內容上往往存在著差異,為了避免從譯語文化觀點出發曲解原文,譯者不僅需要注意原語的語言轉換,還需要適應該語言所屬的整個文化系統,并在翻譯過程中關注雙語文化內涵的傳遞”(胡庚申,2004:136)。
Across the lower sky were faint peach and lavender brush strokes, as if some celestial painter were experimenting and not quite sure which pigments to choose.
譯文一:低低的天空橫著幾抹如畫筆添上的迷離的桃紅和淡紫,就好像天上的丹青妙手還沒拿準用什么顏料,正試著為天空著色。
譯文二:天空低低地橫著迷離的桃紅和淡紫,如畫筆添上一般,好像天上的丹青妙手正在調色,還沒拿準選什么顏料。
原文中的“painter”和漢語里的“畫家”指稱意義和言內意義相同,但譯文中用了“丹青妙手”,后面的譯文中又用了“丹青圣手”。因為通觀全文,painter的語用意義是中性偏褒的角度,而“畫家”在漢語中語用意屬中性,沒有褒義。“丹青妙手”和“丹青圣手”的字面意義與painter稍有不同。這是譯者為適應譯語文化和讀者需要而做出的選擇。
弄清了這一點,則后面的“experimenting”和“choose”譯成“調色”和“選顏料”,就顯得自然契合。
原語所屬文化的傳遞,很多時候是遠遠超越詞匯層面的,但最終又落在詞匯和句子上。如原文的倒數第四段,比爾糾正作者說“不是太陽落,是我們人落。”這在譯文的潛在讀者看來,很可能是突兀而不容易接受的。
接著在下一段,作者作了一番闡釋,是我們看待和我們相關的事物時,慣常以自我為中心,以為“整個世界都圍繞我們旋轉”。其實這種看法是錯誤的,是我們圍繞太陽轉。但這種思維定勢,對譯文讀者來說,也同樣有可能存在。打破這種思維定勢,是原文的主旨所在。所以,對于下面這兩個短句的翻譯,就是為了更好地傳達出原語的文化內涵。
“Yes,” I said. “We are moving. And it is quite a ride.”
譯文一:“是啊,”我說,“是我們在轉動,這行程可不短。”
譯文二:“對,”我說道。“是我們西升東落,這一天的行程可夠遠的。”
譯文一表面看起來與原文字字對應,意思準確;實際上無助于原文文化內涵的傳達,且有可能誤導譯文讀者。譯文二前面用了“西升東落”這一能給潛在的譯文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的詞;后面的“這一天的行程可夠遠的”,又會使人聯想到毛澤東的“坐地日行八萬里”的著名詩句。 這是為適應原文文化和譯文讀者文化而做出的選擇。
四、譯者在交際維的適應與選擇
“譯者出語言信息的轉換和文化內涵的轉換之外,把選擇轉換的側重點放在交際的層面上,關注原文中的交際意圖是否在譯文中得以體現”(胡庚申,2004:137-138)。
原文的交際意圖主要有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通過敘述和描寫作者在工作間隙,和好友欣賞日出日落美景,向讀者傳遞出人應該親近自然、欣賞自然美景的信息。第二個層面是向其交際對象(即讀者)說明太陽不是圍繞地球轉,世界也不是圍繞我們轉的,我們不是中心。
在實現第一個層面的交際意圖時,譯文一有誤譯,譯者沒有很好地適應原文的語言的生態環境,對日出日落美景的描寫沒有達到準確生動。譯者在譯文一的基礎上,進一步加深對原文的理解,努力使譯文從語言形式到文化內涵方面適應原文、譯文和譯文讀者的生態環境,再現了原文準確生動的語言,實現了第一層次的交際意圖。
在實現第二個層面的交際意圖時,譯文一基本適應了原文的生態環境,但是沒有適應譯文的生態環境,更沒有適應譯文讀者的生態環境,從而未能實現這一層次交際意圖。譯文二為了適應譯文和譯文讀者的生態環境,創造性地使用了圓周句,如:“清晨從地平線升上來,黃昏又落下去的,事實上,是我們,地球人。”和中文習慣表達,如“晝短夜長”、“萬物皆備于我”、“西升東落”等,基本實現了第二層次的交際意圖。
五、結語
通過此次翻譯和對翻譯過程與譯文的批評,對翻譯過程、翻譯標準、翻譯批評等方面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
完整的翻譯過程應該包括理解原文、譯出譯文、修改譯文和翻譯批評四個方面。在理解原文階段,譯者應努力適應原文的生態環境,包括對語言形式、文化內涵和交際意圖等方面的適應。譯出譯文是把譯者對原文所包含的各種意義,包括指稱意義、言內意義和語用意義等,最大程度地用譯語轉化出來。
翻譯批評方面,無論自我批評還是對他人作品進行批評,無論是作為批評者還是被批評者,“和諧統一”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少有一點值得提倡,就是批評者言之有理、言之有據,“汰弱留強”(胡庚申,2009:53);被批評者對待批評應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二者都應為營造“適者生存”、“強者長存”(孫迎春,2009:5)的翻譯生態環境而努力。
參考文獻:
[1]Miriam C. Daum.Nature Raises and Lowers the Curtain.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005, January 2.
[2]胡庚申.翻譯適應選擇論[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134-138.
[3]胡庚申.翻譯生態學解讀[J].中國翻譯,2008,(6):11-15.
[4]柯平.英漢與漢英翻譯教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23.
[5]胡庚申.傅雷翻譯思想的生態翻譯學闡釋[J].外國語,2009,(3):48-53.
[6]蔣驍華.譯者的選擇性適應與適應性選擇[J].上海翻譯,2009,(4):11-14.
[7]孫迎春.張谷若與“適應”、“選擇”[J].上海翻譯,2009,(4):5.
[8]許鈞,穆雷.翻譯學概論[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