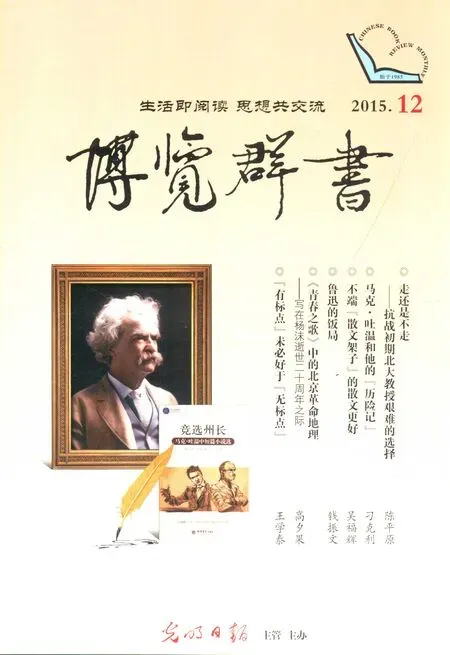回望《四鎮(zhèn)三關(guān)志》的磨礪
彭勇
地方志綜合記載一地區(qū)的自然、地理、沿革、制度、經(jīng)濟(jì)、軍事、文化、人物、生活、災(zāi)害等諸方面,或?qū)S浤骋活?lèi)史事,不僅為研究區(qū)域史者必讀,也是研究國(guó)家與社會(huì)之關(guān)聯(lián)的重要文獻(xiàn),歷來(lái)為治明清史者所重。本人研讀明清歷史30載,一直把地方志作為最重要的史料之一,長(zhǎng)期使用前輩學(xué)者、同行提供的諸如縮微膠卷、影印、整理、點(diǎn)校、校注等不同形式的方志文獻(xiàn)。這次自己主持校注《四鎮(zhèn)三關(guān)志》的重要原因,第一它是我關(guān)注十多年的一部珍貴方志,我知道它的重要價(jià)值,它值得我下功夫去做;二是我曾認(rèn)真閱讀并加以利用過(guò)這部文獻(xiàn),也曾做過(guò)初步的整理,有底氣和信心去做;三是機(jī)緣巧合,幸得中州古籍出版社馬達(dá)先生的極力促成,以及數(shù)位得力助手的分工合作,可謂天時(shí)、地利、人和。
/壹/
《四鎮(zhèn)三關(guān)志》初成于萬(wàn)歷二年(1574年),萬(wàn)歷四年刊刻、六年增修,“四鎮(zhèn)”是指薊州鎮(zhèn)、昌平鎮(zhèn)、真保鎮(zhèn)和遼東鎮(zhèn),“三關(guān)”是指居庸關(guān)、紫荊關(guān)和山海關(guān),它是自嘉靖“庚戌之變”(1550年)之后明朝北邊防御最緊要的之地——京畿、薊遼地區(qū)的專(zhuān)志,內(nèi)容主要是當(dāng)時(shí)的軍政、錢(qián)糧、兵馬、職官以及詔令奏議等官方資料,是研究明代軍事史、政治史、長(zhǎng)城史、民族史等重要的文獻(xiàn)。2001年,我在北京師范大學(xué)歷史系跟隨顧誠(chéng)先生讀博士研究生時(shí),以明代軍事制度史作為學(xué)位論文,這部志書(shū)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卷七收集的大量詔敕奏疏讓我發(fā)現(xiàn)了不少明史研究的新問(wèn)題,幫我解決了許多的迷惑,比如其中記載的“忠順營(yíng)(軍)”問(wèn)題,此前學(xué)界沒(méi)有學(xué)者關(guān)注過(guò);有關(guān)“夜不守”“撫賞銀”和“燒荒”等問(wèn)題,記載也比較詳細(xì),本人不僅在兩部專(zhuān)著《明代班軍制度研究——以京操班軍為中心》(中央民族大學(xué)出版社2006年版)和《明代北邊防御體制研究——以邊操班軍的演變?yōu)榫€索》(中央民族大學(xué)出版社2009年版)中多有引用,還發(fā)表有專(zhuān)題學(xué)術(shù)論文《論明代忠順營(yíng)官軍的命運(yùn)變遷》(《中州學(xué)刊》2009年第6期)和《明代領(lǐng)班武官敕書(shū)“坐名”試析》(《明史研究論叢(第八輯)》2010年)等。
對(duì)這部志書(shū)的初步整理,緣于2007年,我作為大型新志《中國(guó)長(zhǎng)城志》“文獻(xiàn)卷”的副主編,把《四鎮(zhèn)三關(guān)志》作為明代最重要的長(zhǎng)城文獻(xiàn)列入其中,當(dāng)時(shí)選輯了該書(shū)全部54萬(wàn)字中的30多萬(wàn)字。到2013年時(shí),中州古籍出版社的副總編馬達(dá)先生聽(tīng)說(shuō)這部文獻(xiàn)很重要,并得知以前我已做了大量的前期積累,便建議申請(qǐng)國(guó)家古籍規(guī)劃整理資助項(xiàng)目,明史專(zhuān)家邱仲麟先生、地方志專(zhuān)家張英聘研究員等都高度評(píng)價(jià)了這部文獻(xiàn),并給予熱情的鼓勵(lì)和切實(shí)的支持。此后又經(jīng)過(guò)兩年的準(zhǔn)備,經(jīng)過(guò)明史專(zhuān)家陳梧桐先生和高壽仙先生熱情推薦,在中州古籍出版社的具體組織申報(bào)下,《四鎮(zhèn)三關(guān)志校注》順利獲得“2016年度國(guó)家古籍整理出版專(zhuān)項(xiàng)經(jīng)費(fèi)資助”立項(xiàng)。
/貳/
作為一名高校教師,我平時(shí)的大部分精力是用于教學(xué)工作,科研工作也時(shí)常是圍繞教學(xué)展開(kāi)、為教學(xué)服務(wù),《四鎮(zhèn)三關(guān)志校注》也可稱(chēng)為教學(xué)與科研相結(jié)合的產(chǎn)物。本書(shū)的整理和校注工作,實(shí)際分成了四個(gè)階段,第一階段,是主編《中國(guó)長(zhǎng)城志》(文獻(xiàn)卷)時(shí)的錄入、標(biāo)點(diǎn)與校對(duì)工作,完成了30余萬(wàn)字;二是全書(shū)剩余的20萬(wàn)字正文的點(diǎn)斷工作,由我的明清史、明清歷史文獻(xiàn)學(xué)的研究生李夢(mèng)琴、李宜潔協(xié)助完成;三是對(duì)全書(shū)進(jìn)行校注,由我的博士生崔繼來(lái)、肖晴和段晉媛等分別承擔(dān)。他們每個(gè)人手中均有一套萬(wàn)歷版的底本、一套民國(guó)抄本的對(duì)校本,逐字逐句的對(duì)照,在錄入好的工作稿上標(biāo)出發(fā)現(xiàn)的問(wèn)題和疑惑。我們組建了“劉效祖”微信群隨時(shí)交流,在研究生課堂上,在讀書(shū)班上,大家時(shí)常為一個(gè)字、一個(gè)標(biāo)點(diǎn)、一個(gè)地名,去查閱大量的文獻(xiàn),師生同門(mén)在一起教學(xué)相長(zhǎng),收獲很大。
《四鎮(zhèn)三關(guān)志》是一部地方專(zhuān)志,在校注時(shí),我們也大量參考了明清時(shí)期的地方志書(shū),“校注本”出版后,在書(shū)后附錄的地方志共21頁(yè)有600種。這些地方志,又以省、府、州、縣的綜合性志書(shū)為主,以綜合性地志書(shū)去校注邊地專(zhuān)志,也讓在讀研究生得到了很好的學(xué)術(shù)訓(xùn)練。類(lèi)似的學(xué)術(shù)訓(xùn)練是我熟悉的,上世紀(jì)末,我在鄭州大學(xué)歷史學(xué)院跟隨張民服教授讀書(shū)、留校工作,當(dāng)時(shí)參加編寫(xiě)《河南通史》(明清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時(shí),便把明清時(shí)期河南地方志系統(tǒng)查閱一遍。我的博士生導(dǎo)師顧誠(chéng)先生尤其重視在研究中利用明清方志,他為了撰寫(xiě)《明末農(nóng)民戰(zhàn)爭(zhēng)史》(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84年版)和《南明史》(中國(guó)青年出版社1987年版)時(shí),是沿著明末農(nóng)民軍活動(dòng)的線路和區(qū)域,把涉及的上千部地方地全部讀完的。我當(dāng)時(shí)在研究明代班軍制度時(shí),把能找到的明代方志以及清代乾隆之前的方志全部翻閱一遍,出版時(shí)直接征引的地方志達(dá)300種。我在指導(dǎo)明清史專(zhuān)業(yè)研究生時(shí),大部分同學(xué)為撰寫(xiě)畢業(yè)論文,也都下過(guò)類(lèi)似的苦功夫。本次師生一起校注邊鎮(zhèn)專(zhuān)志,這算是學(xué)術(shù)的薪火相傳吧。
/叁/
本人的專(zhuān)業(yè)在明清史研究,這次的古籍整理與校注,頗有點(diǎn)“不務(wù)正業(yè)”,實(shí)在是考慮到這部方志的重要性。校注時(shí),我們預(yù)定的目標(biāo)有三,一是給讀者提供一版內(nèi)容精良、閱讀方便的讀本,提高它的閱讀和使用率;二是給廣大讀者提供明代長(zhǎng)城史、軍事史和邊地志書(shū)等方面專(zhuān)業(yè)的釋讀知識(shí);三是給專(zhuān)業(yè)研究者提供相關(guān)研究的方法、線索和思考的憑借。
因《四鎮(zhèn)三關(guān)志》的內(nèi)容主要集中在兵馬、形勝、錢(qián)糧、營(yíng)伍、經(jīng)略、文臣武將以及民族關(guān)系等,有一批學(xué)者和愛(ài)好者關(guān)注于此,因此我們?cè)谛Wr(shí),對(duì)涉及到的相關(guān)知識(shí),盡可能以最簡(jiǎn)潔、概括的語(yǔ)言體現(xiàn)學(xué)界最新研究成果。對(duì)廣大讀者不太容易查閱、對(duì)比和熟悉的內(nèi)容,我們做了詳細(xì)的校注,比如卷八《職官》、卷九《才賢》和卷十《夷部》的內(nèi)容,相信細(xì)心的讀者會(huì)得到有價(jià)值的研究信息和追查線索。本書(shū)對(duì)公認(rèn)價(jià)值極其的詔令奏議部分并沒(méi)有進(jìn)行過(guò)于詳細(xì)的文本對(duì)比,只是為了閱讀和利用的方便,進(jìn)行了必要的校注,原因是卷七的內(nèi)容很龐大,劉效祖當(dāng)年輯錄編撰時(shí),對(duì)許多原始奏疏做了編輯處理,而他收錄的奏議不少另有傳世,如果把不同的文本進(jìn)行逐一比對(duì),必將加大校注的分量,從史料的使用價(jià)值角度考慮,所以我們校注時(shí)僅提供了不同版本的信息,提醒專(zhuān)業(yè)研究者自行查閱。此外,民國(guó)抄本作為對(duì)校本,字跡比較清楚,對(duì)校注底本大有幫助,但抄本在抄錄時(shí)錯(cuò)漏之處實(shí)在太多,無(wú)法一一出注(這也不是我們校注的主要任務(wù)),只是在校注部分內(nèi)容,遇有底本不清,而抄本內(nèi)容或可成為一說(shuō)時(shí),兩說(shuō)并存。
這次整理,經(jīng)與出版社商議,采取繁體橫排版式印刷,“校”與“注”統(tǒng)一編號(hào),并沒(méi)有分別編號(hào),“校”的內(nèi)容以【校】提醒讀者,而“注”的部分并不標(biāo)【注】,“校”與“注”均于頁(yè)下出注,這主要基于閱讀和使用的習(xí)慣,也可以節(jié)省版面,降低成本。經(jīng)驗(yàn)告訴我這樣利用的效率會(huì)更高一些,盡管這并不是傳統(tǒng)古籍校注的處理方法。
本書(shū)的校注也留下了許多遺憾。隨著工作的展開(kāi),盡管做了充分的準(zhǔn)備,我還是低估了這項(xiàng)工作的難度。校注工作千頭萬(wàn)緒,無(wú)一處不在考驗(yàn)著我們的知識(shí)、能力、體力和耐心。比如最基礎(chǔ)的斷句是需要過(guò)硬的功夫,有時(shí)候一個(gè)字、一個(gè)典故需要花費(fèi)數(shù)小時(shí)處理。本書(shū)有大量北方民族的地名、族群名,以及長(zhǎng)城堡塞關(guān)隘名稱(chēng),限于材料和能力,都無(wú)法保證校注是準(zhǔn)確無(wú)誤的。至于校勘與注釋的內(nèi)容,如何準(zhǔn)確把握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相信讀者不難發(fā)現(xiàn)若干問(wèn)題。此外,校注的初稿,我們也使用了專(zhuān)名線,為此我們征求了多名專(zhuān)家的意見(jiàn),討論多次,以統(tǒng)一專(zhuān)名線的體例,但這部志書(shū)的專(zhuān)名線類(lèi)型太多,如果一一劃出,幾乎滿(mǎn)頁(yè)盡是專(zhuān)名線,深感影響到閱讀體驗(yàn),在決定使用橫排版之后,最終放棄了專(zhuān)名線的使用。
當(dāng)書(shū)稿幾經(jīng)推遲交出之后,我們深深體會(huì)到古籍整理之不易,確實(shí)是一份責(zé)任讓我堅(jiān)持下來(lái)。這本書(shū)對(duì)于我,是心愿的滿(mǎn)足和一件事情的終結(jié),對(duì)于同學(xué)們,也是一次難得的磨練。希望有更多、更好的明清方志能整理出來(lái)。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學(xué)歷史文化學(xué)院院長(zhǎng),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