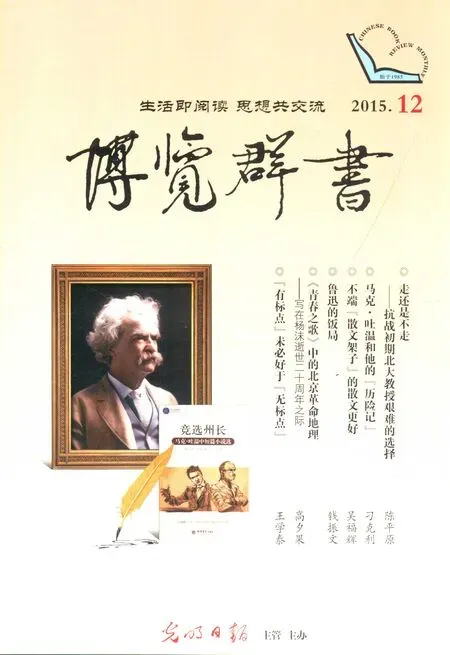“魯迅采集的植物標本”解讀
錢振文
在北京魯迅博物館一樓展廳,可以看見魯迅在杭州浙江兩級師范學堂任教時的一件植物標本木槿和魯迅1910年3月采集植物標本的記錄冊。這件展品下面的說明是:“魯迅采集的植物標本”,但這件標本左下角原有的標簽上卻有“蔣謙制藏第 號”字樣,采集地為“西湖岳墳”,采集時間為“己酉年七月”。實際上,除了這件木槿,北京魯迅博物館還收藏了另一件植物標本馬蓼。馬蓼標本的制作收藏人同樣也是“蔣謙”,但采集地為“西湖”,采集時間為“己酉年八月”。
“己酉年”是1909年,距離現在109年了。這年夏天,魯迅結束了留學生活,從日本回國。秋天新學期開始后,他到杭州浙江兩級師范學堂任教。這是魯迅從日本回國后的第一份工作。在許壽裳的《魯迅先生年譜》中有:“六月歸國,任浙江兩級師范學堂生理學化學教員。”
當然,以上所說的月份“六月”“七月”“八月”都是陰歷。雖然都沒有更具體的日期,但總之是,魯迅是在到兩級師范任教不久就開始了植物標本的采集。
對于魯迅在杭州浙江兩級師范的任職,大多數說法是擔任化學和生理學教員。魯迅自己在《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中也說:
終于,因為我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這時我是二十九歲。
我一回國,就在浙江杭州的兩級師范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
擔任化學和生理學教員的魯迅又怎么會采集植物標本呢?原來,除了擔任化學和生理學的教課,魯迅還兼任博物科植物學教員鈴木珪壽的翻譯。當時,浙江兩級師范聘請了八個日本教員,其中以博物科的日籍教員最多。這些日本教員的教課都需要課堂翻譯,魯迅、夏丏尊、楊莘耜、錢家治等留學日本的教員都曾經擔任過日本老師的翻譯。魯迅是優級師范理化科和博物科的生理學教員,為同為博物科的植物學教員做翻譯是很合適的。當然,魯迅做植物學翻譯有足夠的條件。他資料顯示,他在弘文學院學習的時候,就曾經學過植物學。甚至也有一種說法是,魯迅在兩級師范的主要工作是做日本教員的翻譯。如夏丏尊回憶說:
那時兩級師范學校有許多功課是聘用日本人為教師的,教師所編的講義要人翻譯一過,上課的時候也要有人在旁邊翻譯。我和周先生在那里所擔任的就是這翻譯的職務。我擔任教育學科方面的翻譯,周先生擔任生物學科方面的翻譯。此外,他還兼任著幾點鐘的生理衛生的教課。
再如楊莘耜在回憶中說:
在杭州兩級師范教書時,與我比室而居,朝夕相見。他做日本教師植物學翻譯,自己教生理衛生;我做日本教師動物學翻譯,自己也教生理衛生。每星期六下午他至西湖采集植物標本,我去采集動物標本(鳥類和蝴蝶),各以所得相夸示。
夏丏尊和楊莘耜是魯迅在浙江兩級師范的同事,除了做日本教員的翻譯,他們也都有自己擔任的教課。夏丏尊擔任的教課是優級公共科的日語,楊莘耜擔任的是優級史地科的生物學。現在我們不好說究竟魯迅、夏丏尊、楊莘耜他們在兩級師范的教課和翻譯哪個更重要。但顯然,不管是教課還是翻譯,魯迅從日本回國后的第一份工作和他在日本的留學經歷尤其是在仙臺醫學專門學校的學習經歷是密切相關的。日本仙臺魯迅記錄調查會的渡邊襄在《魯迅與仙臺》中說過:
魯迅在醫專一年級所學的課程中,醫學領域的重點是基礎科目和理論。因此,一二學期的主要科目側重于副課,有化學、物理學、德語、倫理學、體育等,占全部課程的三分之二。與醫學有關的是藤野、敷波兩位教授的解剖學、組織學和第三學期的生理學。弘文學院的課程,除日語之外,有動物學、植物學、理化學等相當于舊制初中的課程。
由此可見,他在浙江兩級師范的教課化學和生理學都是他在仙臺醫專學習過的課程。雖然他在仙臺醫專沒有畢業,但化學和生理學都是他在第一學年就已經圓滿完成了的課程。更何況,早在南京礦路學堂學習采礦專業的時候,魯迅就學習過化學。因此,從學科出身來講,教化學、生理學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但魯迅在仙臺醫專讀到二年級的時候興趣志向發生了轉變,即大家都知道的“棄醫從文”。的確,從1906年魯迅離開仙臺后回到東京,一直到1909年夏天到浙江兩級師范任職前,他都在“弄文藝”。后來人們把他在東京的這段時間和到北京教育部任職后的最初幾年,都作為魯迅文學的準備期。如周作人說:
魯迅在東京的日常生活,說起來有點特別,因為他所說是留學,學籍是獨逸語學會的獨逸語學校,實在他不是在那里當學生,卻是在準備他一生的文學工作。這可以說是前期,后期則是民初在北京教育部的五六年。
但是,在這個東京的“前期”和北京的 “后期”之間有一段時間的插曲,就是從1909年夏天回國到1911年底離開紹興的兩年半,按照許壽裳撰寫的《魯迅先生年譜》,在這段短暫的時間里魯迅的主要事跡可以列表如下:
宣統元年(1909)二十九歲
六月歸國,任浙江兩級師范學堂生理、化學教員。
輯印《域外小說集》二冊。
宣統二年(1910)三十歲
上季仍任兩級師范學堂教員。
下季(八月起)改任紹興府中學堂教員兼監學。
宣統三年(1911)三十一歲
上季仍任紹興府中學堂教員兼監學。
九月紹興光復,任山會初級師范學堂監督。
這段時間的魯迅,看起來像是接續上了幾年前在仙臺時候比較枯燥的理科學術生活。在東京研究文學的那些年當然閑散舒適,但是回國謀職的話,能夠拿得出手的學歷還是仙臺醫專的肄業證,為了謀生,他也只能撿起來化學、生理衛生這些曾經讓他感到“莫遐應接”“腦力頓疲”的功課。植物學不是魯迅的專業,但卻是他的興趣所在。在《藤野先生》中,“我”對“藤野先生”說的“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還有用的”是有一定緣由的。雖然作者接著說,其實他并沒有決意要學生物學,這只不過是安慰藤野先生的謊話。但魯迅對生物學的興趣卻是真實的。
在杭州和紹興,學堂里的植物學課程讓魯迅有機會實現自己一直就有的愛好植物的“趣味”。我甚至有些懷疑,魯迅在杭州做植物學教師鈴木珪壽的翻譯是他自己主動爭取的。
那么,在植物標本左下角標簽上的“蔣謙制藏第號”是什么意思?“蔣謙”又是何許人呢?
裘士雄在一篇關于魯迅在浙江兩級師范學堂的一個學生陳士遺的文章《陳士遺與魯迅》中提到了蔣謙其人:
陳士遺生于一八七四年二月二十九日,早年是前清第三名優稟生。……不久,陳士遺再次違抗父命,私奔杭州投考浙江兩級師范學堂。因榜列前茅,他被編入優級史地科,與蔣謙(庸生)、宋崇義(知方)等為同班同學。
蔣庸生在魯迅日記中出現過三次。1913年和1916年魯迅兩次回紹興省親,與蔣庸生都有來往。2013年6月30日魯迅日記有:“上午錢錦江、周子和、章景鄂、葉譜人、經泰來、蔣庸生來。”和蔣庸生一起到周家拜訪魯迅的錢錦江、周子和、章景鄂、葉譜人、經泰來和蔣庸生一樣都是紹興第五中學的職員,紹興第五中學的前身就是魯迅曾經工作過的紹興府中學堂,這幾人中的錢錦江當時是第五中學的校長,葉譜人和經泰來是魯迅在紹興府中學堂工作時的老同事。7月5日日記中有:
午后同二弟、三弟往大街明達書莊買會稽章氏刻本《絕妙好詞箋》一部四冊,五角六分。又在墨潤堂買仿古《西廂十則》一部十本,四元八角。并購餅餌、玩具少許。由倉橋街歸,道經蔣庸生家,往看之。
從這則日記可以看出,蔣庸生和魯迅是地地道道的同鄉,魯迅上街購物順便就走到了蔣庸生家。《魯迅全集》“人物注釋”部分有詞條“蔣庸生”:“蔣庸生(1885-1966)名謙,字庸生,亦作蓉生,浙江紹興人。魯迅在杭州浙江兩級師范學堂任教時的博物科學生,當時任紹興第五中學植物學教員。”這個詞條和裘士雄文章中的說法略有不同。按照裘文的意思,蔣謙與陳士遺是同班同學,就應該與陳士遺一樣都是史地科,但魯迅擔任的課程在理化科和博物科,因此,《全集》詞條的說法當更為合理。
周芾棠在《鄉土憶錄——魯迅親友憶魯迅》一書中寫到了蔣謙,在周芾棠的書中蔣謙的名字是蔣蓉生。周芾棠采訪蔣謙的時候是1964年,那年蔣謙虛歲八十整。周芾棠寫道:
據魯迅先生在兩級師范時的學生、1964年尚健在但已有八十高齡的蔣蓉生老先生告訴我說:
我們到魯迅先生房里去,魯迅先生是一點架子也沒有的,有時他就躺著邊抽香煙,邊用紹興土話和我們這些紹興籍的學生談天,談的更多的是他在日本的見聞。魯迅先生的案桌上,放的多是一些文學書,除中文外,還有日文、德文版的世界文學名著。
蔣老先生當時又曾對我說:“魯迅先生在兩級師范每周任二十幾節課,是很忙的。除備課、編寫講義、批改學生作業和自學外,他每逢星期六下午,還常和鈴木珪壽先生帶領我們同到錢塘門外的孤山、葛嶺、岳墳、北高峰一帶去采集植物標本。來來去去,魯迅先生都是走的,鈴木珪壽先生回校是坐轎的。當時學生每人都背一只狹長圓口的馬口鐵標本箱,并隨身攜帶一把剪刀、一把鐵鍤。植物總是采比較少見的,一般都連根掘,也有的不連根,只用剪刀剪。植物采回后,魯迅先生和鈴木珪壽先生就指導學生用標本夾一一壓平壓干,然后再填寫科目、采集地點和時間。”這些由魯迅先生指導制作的標本,蔣老先生還有十幾張保存下來,解放后他已分送給紹興魯迅紀念館、杭州市第一中學魯迅紀念室陳列和收藏。給杭一中魯迅紀念室的幾張標本,是我經手送去的。當時杭一中還出了收據并寫了感謝信,由我親手交給蔣蓉生先生。
《魯迅生平史料匯編》第二輯中有蔣蓉生送給杭州第一中學的兩件植物標本的照片,這兩件植物標本的說明是“魯迅帶學生制作的標本:這是1909年(己酉年)魯迅帶領學生采集制作的植物標本,由魯迅的學生蔣謙保存下來,于1964年送給杭州第一中學。”
這樣看來,北京魯迅博物館保存的這兩件植物標本應該和蔣老先生送給紹興魯迅紀念館和杭州市一中的十幾張標本一樣,都應該說是魯迅帶領學生采集制作的而不應該簡單說是魯迅采集制作的。
在這件木槿標本邊上還有一件魯迅當年采集植物標本的記錄手稿,魯迅博物館展出的是手稿的復制件,原件保存在國家圖書館。這份記錄是1910年3月采集植物的時間、地點和種類。采集的時間地點和采集的種類數量羅列如下:
三月一日,孤山,一種;
三月八日,錢塘門內,二種、門外,五種;
三月八日,棲霞嶺,十種;
三月十三日,孤山,八種;
三月十四日,靈隱,十六種;
三月十五日,師范學堂內,一種;
三月十六日,吳山,一種;
三月二十日,本學堂,一種;
三月二十二日,孤山,四種;
三月二十七日,棲霞嶺,十三種;
三月二十八日,玉皇山,一種;
三月二十九日,棲霞嶺及葛嶺孤山,十種。
三月總共采集七十三種。
從以上羅列看,魯迅在1910年3月采集植物標本的次數達到11次,并不是“每逢周六下午”才出去。當然,并不是每次采集活動都去野外,有兩次采集就是在師范學堂里邊完成的。從這份記錄上看,魯迅在杭州開展的植物采集活動,采集的地點都是西湖周邊風景如畫的地方,但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卻說:
魯迅極少游覽,在杭州一年之間,游湖只有一次,還是因為應我的邀請而去的。他對于西湖的風景,并沒有多大興趣。“寶淑塔如美人,雷峰塔如醉漢”,雖為人們所艷稱的,他卻只說平平而已;煙波千頃的“平湖秋月”和“三潭印月”,為人們所流連忘返的,他也只說平平而已。
這看起來有點矛盾和不好理解。許壽裳在另一篇文章中也說到了魯迅在杭州的植物學研究和標本采集:
他在杭州時,星期日喜歡和同事出去采集植物標本,徘徊于吳山圣水之間,不是為游賞而是為科學研究。每次看他滿載而歸,接著做整理,壓平,張貼,標名等等工作,樂此不疲,弄得房間里堆積如丘,琳瑯滿目。
從許壽裳的回憶可以看出,魯迅當年不光是指導學生制作植物標本,而是自己親自“做整理,壓平,張貼,標名等工作”。
現在,我們大體上理清了魯迅博物館收藏的兩件植物標本的來龍去脈,但疑慮還是不少:這兩件植物標本是在什么時候、從什么地方流轉到北京魯迅博物館?如果說這批標本都是由蔣謙在魯迅指導下制作的,那么魯迅自己制作的植物標本又散落在何處了呢?還是這件標著“蔣謙制藏”的標本其實就是魯迅制作或參與制作的?這一切還有待深入的探討。
(作者系北京魯迅博物館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