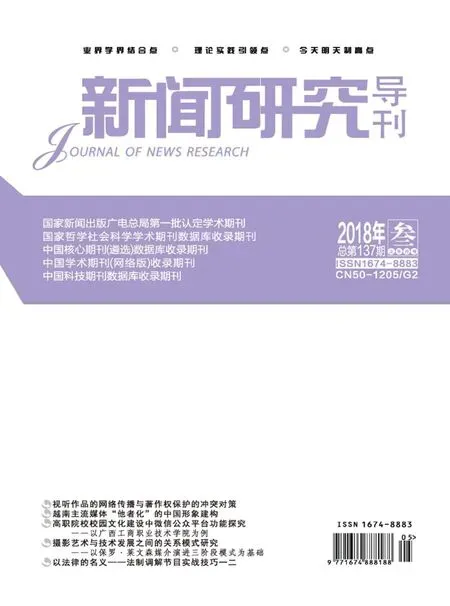短視頻社交軟件的受眾心理研究
——以抖音APP為例
馬海燕
(山東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0)
一、受眾心理研究
抖音自上線以來,就有褒貶不一的評價,贊同主要是因為它滿足了受眾在碎片化時間的娛樂需求,出現質疑的聲音主要原因在于其對受眾行為產生的不良影響。抖音將受眾群體定位于年輕人,其表現的共同興趣點及對事物認知的一致性,使受眾在信息接收方面存在一致性。因此,本文結合傳播學理論分析受眾觀看抖音短視頻的心理。
(一)從眾帶來的效仿
日本社會學家?guī)r原勉認為,群體是指“具有特定的共同目標和共同歸屬感、存在著互動關系的復數個人的集合體”。[1]可以說,我們每個人都屬于一個群體,而且每個人都或多或少會受到群體的影響。從心理學上看,所謂的從眾心理,即個人在群體的影響下,由于各種原因或壓力選擇或做出了與群體中大多數人一樣的行為。
如果群體中或圈子里一部分人在使用抖音,這一部分人對抖音上的“梗”、段子等會有共同理解和共同語言。作為群體中的個人,一方面怕由于沒有共同語言被邊緣化,另一方面作為聽眾的個人會產生強烈的好奇,在這種驅動下,很多人就開始下載抖音并觀看上面的視頻。
從眾心理驅使受眾下載和接觸抖音,而使用后受眾對抖音表現出來的沉迷和喜愛則是由于素人創(chuàng)作引發(fā)的情緒共鳴。抖音的拍攝者幾乎都是普通網民,場景也比較生活化,再加上具有情緒感染力的音樂,很容易使觀看者產生情感共鳴。不少用戶表示只要打開抖音就停不下來,這也說明抖音已經有了較高的用戶黏度。這種黏度僅靠從眾心理是不可能獲得的,真正能留住用戶的是平臺本身的作品質量。
(二)受眾選擇性心理驅動的自主選擇
受眾并不是像“魔彈論”中所說的那樣可以輕易地被信息一擊即中。選擇性接觸假說認為,受眾在接觸大眾傳播的信息時并不是不加選擇的。在互聯網時代,受眾的選擇性表現得更加明顯,受眾在媒體傳播的信息面前并不是完全被動的,他們具有能動性,可以選擇自己感興趣的內容,同時也可以忽略自己不感興趣和并不認同的信息。
這種選擇性心理,在觀看抖音APP時有明顯的表現。受眾在觀看一條抖音視頻時,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選擇上滑不看或者雙擊點贊。在這個過程中,受眾是完全遵從自己的內心選擇的。對于視頻內容,不同層次、職業(yè)、年齡的人會有不同的理解,抖音視頻內容的重復性可以加深受眾的印象。
前一段時間,一篇《人民不需要“讓水變油”的抖音》引起爭議。文章中表示,“讓水變油”對受眾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誤導,抖音成為傳播謊言的平臺。事實上,一方面就其點贊和轉發(fā)量來看,這條“水變油”的視頻并沒有引起多少人的關注;另一方面,文章忽視了受眾自身的選擇性,受眾在觀看視頻時并不是完全被動的,他們會有自己的是非判斷和選擇性接受。
(三)“使用與滿足”帶來的滿足感
“使用與滿足”理論把受眾看作有特定需求的個人,把他們的媒介接觸活動看作基于特定需求動機來使用媒介,從而使這些需求得到滿足。
可以說,受眾從一開始的接觸行為到后來的接受與熱衷,都是因為抖音滿足了他們特定的需求。現今快節(jié)奏的生活中,人們覺得無法釋放巨大的工作、學習壓力,而抖音恰好能滿足受眾利用碎片化時間娛樂和休閑的需求。
抖音是音樂短視頻社交軟件,音樂本身就能使人們放松心情,再加上所配視頻多為美好的風景、人物,或是搞笑的段子和游戲,這一切都能讓受眾在緊張的生活中抽離出來,得到暫時的放松。
而作為視頻拍攝者的受眾在使用抖音時,會獲得強烈的被認同感和滿足感。尤其表現在被人關注、點贊之后,拍攝者在產生愉悅感的同時會更加認可這一軟件,繼續(xù)上傳自己的視頻以獲得關注。在用戶相互評論和點贊、關注的時候,就形成了互動,在一定程度上讓受眾獲得了人際交往的滿足感。
受眾不管是作為觀看者,還是視頻制作者,在使用抖音期間都獲得了滿足感。抖音滿足了受眾對娛樂、休閑、社會互動和認同等的需求。盡管這些滿足感可能轉瞬即逝,但這并不妨礙受眾繼續(xù)使用抖音以獲得更多的滿足感。
(四)“狂歡”下的自我釋放
狂歡化是對現實生活的一種反叛,巴赫金的“狂歡理論”認為,那種狂歡廣場式的生活是在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起完全“顛倒的世界”,這是平民大眾的世界,打破了階級、財產、等級、身份的區(qū)分與界限……人們平等而親昵地交往、對話與游戲,盡情狂歡。巴赫金認為,對于平民來說,這是“暫時通向烏托邦世界之路”。[2]巴赫金的“狂歡理論”契合了當前短視頻社交平臺中人人都是傳播者的現象,它們都是在虛擬的世界中建立起來的平等、自由的全新社交舞臺。
在抖音里,人們既可以作為一個觀看者,也可以作為一個傳播者自己錄制視頻上傳到平臺。在觀看視頻的過程中,受眾可以通過評論等進行互動,受眾的身份、職業(yè)、地位、年齡等可能大不相同,但在抖音平臺上可以實現平等互動與交流,打破了現實中可能存在的貧富、階級、身份等的界限。
快節(jié)奏的生活使人們一般都處于精神壓力增大的狀態(tài),在抖音上人們可以盡情地釋放自我,不必在乎現實世界的地位、等級與身份,身份迥異的兩個人可以平等交流,無障礙地對話。在這個被建構起來的“烏托邦”世界里,人們追求自由和釋放自我。
(五)求知欲驅動的探索與求知
在生活和學習中,人們會遇到很多障礙或困難,當感覺到自己的相關知識不足或已有知識無法解決相應問題時,就會產生探究新知識的認知傾向。久而久之,這種認知傾向就會轉化為內在強烈的認知欲望,也就是求知欲。在互聯網不發(fā)達的時候,人們普遍會選擇翻閱書本來滿足自己的求知欲。互聯網時代,人們更傾向于在網絡上汲取知識,這種知識涉及方方面面。
在抖音平臺上,比較受用戶喜愛的不僅是它的搞怪、寵物和美女視頻,還有生活小貼士類的視頻。受眾比較熱衷的“抖音蝦”,讓受眾學會了怎樣在最短的時間內做出別有一番風味的大蝦;“反差加閃光燈”的拍照方式,讓受眾打開了自拍道路上的新大門;快速哄孩子睡覺法,給不少家長減輕了帶娃的壓力。除此之外,還有快速去除車輛劃痕、清理洗衣機等各種生活小貼士也備受推崇。
但是,求知欲帶來的效仿也曾一度給抖音帶來了爭議。前段時間,一則“爸爸學抖音動作失手,致娃脊髓受傷”的新聞在網絡上傳播,此新聞引起了很多爭議。在抖音上,該動作是推送較多的內容,也是被模仿最多的。目前,抖音已經對此類會讓未成年人陷入危險的視頻進行了下架處理,之前很多人發(fā)布的內容也看不到了。
受眾的求知欲促使受眾汲取視頻中的信息,這種信息可能彌補受眾自身的某些短板,使自己得到提升。同時,受眾自身要有能力辨識平臺發(fā)布內容的可行性。
二、基于受眾心理對短視頻社交軟件發(fā)展的建議
受眾的年齡、層次等參差不齊,我們說受眾有自己的判斷力,具有選擇性心理,但在很多未成年人身上,這種選擇能力和判斷能力有時并不足以判斷出視頻所傳達的內容是否正確。如果視頻傳達了不正確的導向、危險的行為,很容易造成誤導,引起爭相模仿會帶來一定的危險。對于受眾來說,短視頻社交軟件只有在滿足人們需求的前提下才可以存活下去。
(一)嚴格審核
自媒體時代,人人都可以扮演傳播者的角色,傳播者所傳播的信息也是魚龍混雜。國家對此出臺了很多法律法規(guī),各大互聯網平臺也紛紛開始實行實名制。審核就如同一個過濾器,篩選出適合傳達給大眾的信息,摒棄黃、賭、毒以及各種違法違規(guī)的信息,以保證受眾接收健康、綠色的信息。
目前,市場上出現的各種短視頻社交軟件的審核機制和審核原則各不相同。面對不同的市場,它們的審核嚴格程度也存在差別。但不管是什么樣的市場定位和受眾定位,各大短視頻社交平臺都應該有自己的底線,一定不能出現違法違規(guī)的內容。4月4日,國內短視頻社交軟件快手、火山小視頻兩家平臺因為被曝存在大量“低齡媽媽”走紅視頻而被廣電總局約談。與此同時,快手APP開始在招聘網站上招募內容審核員,以期對上傳的視頻進行更加嚴格的審核。這足以說明各大短視頻社交軟件只有保證正確的導向和嚴格的審核才能生存下去。
現在,短視頻社交軟件的審核基本上都是采取計算機算法審核和人工審核相結合的方法對上傳的各種視頻進行審核。“算法”可以節(jié)省人力、提高效率,但絕不能代替人工,因為正確的價值觀和導向都需要人來賦予和選擇。
(二)內容優(yōu)化,避免同質化
傳統(tǒng)媒體時代講究“內容為王”,要想有好的受眾市場就要提高內容質量。自媒體時代更是如此,人們有了更廣闊的選擇空間。要想在市場上存活,短視頻社交軟件在加強自身營銷的同時,提高內容質量才是關鍵。
短視頻社交軟件在滿足人們在碎片化時間娛樂和休閑的需求之外,可以更多地推送傳達生活技巧、生活貼士類的內容。這樣一方面可以滿足人們的求知欲,另一方面可以提升軟件格調。
另外,避免內容同質化也是相當重要的。以抖音為例,作為音樂短視頻社交軟件,用戶多是在音樂背景下進行創(chuàng)作、表演。音樂的同質化也導致用戶上傳內容的同質化。某一音樂走紅后,會吸引更多人用此音樂創(chuàng)作,創(chuàng)作內容也相差無幾,受眾在抖音推薦功能下看到的視頻可能也都是類似內容,久而久之會產生審美疲勞,這就要求平臺在推薦功能上作出調整,盡量避免內容重復。
三、結語
我們不能否認短視頻社交軟件的發(fā)展?jié)摿蛷V闊前景,它的興起是自媒體時代的一大趨勢。抖音APP之所以擁有這么多的高黏性用戶,除了它自身的營銷推廣外,還依賴于內容的吸引力。保持吸引力的訣竅就是嚴格的審核和內容的多樣性。短視頻社交軟件要想存活下去,必須契合受眾心理,保持內容的多樣性、趣味性。而要想長久地生存下去,就必須擁有社會責任感,不要為了迎合部分受眾的低級趣味選擇推送違法違規(guī)的內容,保持品牌調性才是最重要的生存之道。
[1]見田宗介(日),等.社會學事典[M].東京:弘文堂,1988:439.
[2]巴赫金(俄).巴赫金全集(第六卷)[M].錢中文,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17-321.
[3]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78-83,165-168.
[4]于海航,張維剛.新媒體原創(chuàng)短視頻的受眾心理分析及發(fā)展建議[J].現代視聽,2017(12):54-57.
[5]田高潔.互動儀式鏈視角下的音樂短視頻研究——以抖音App為例[J].新媒體研究,2018(4):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