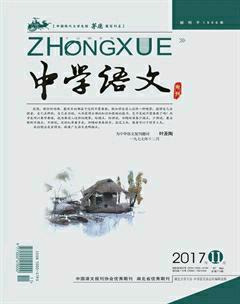論納蘭眭德詩詞的審美特質
段樹發
清初杰出詞人納蘭性德,生于順治十一年(1655)臘月十二日,卒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五月三十日,原名成德,字容若,號楞伽山人。他精于詞道,且詩、文、賦俱佳,留下了卷軼浩繁的著述,而尤以詞名世。
選擇意象、組合意象的過程,就是在寫作構思時作者頭腦中所形成的生活圖景和要表現的主觀思想感情融合一致的形象化的思考過程。一個詩人有沒有獨特的風格,在一定程度上即取決于他是否建立了他個人的意象群。納蘭性德就是這樣的一位詩人,他在意象選擇上有著獨特鮮明的審美傾向性,主要表現在:
一是自然意象在他的詩詞作品中占的比例很高。納蘭性德是一個“純任性靈,纖塵不染”的“翩翩濁世佳公子”,追求真景、真情、真性。王國維評價他是“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他筆下常用的意象有:凄風、苦雨、冷月、落花等。如:“冷雨凄風打畫橋。”“想天涯只影,凄風苦雨。”“一宵冷雨葬名花。”“宵來涼雨咫庵。”“凄涼煞,五枝青玉,風雨飄飄。”……這樣的風雨意蘊實際上是深深打上了詞人人生體驗的烙印。月亮意象常常和團圓、和平、寧靜、安詳等意蘊相連,而納蘭詞中的月則是:“相思何處說,空有當時月。”“月似當時,人似當時否?”“月淺燈深,夢里云歸何處尋?”月的那種皎潔、明凈而又清冷的意味其實正是詞人主體生命的內涵。落花也是詞人鐘愛的意象,“一別如斯,落盡梨花月又西。”“落花如夢凄迷。”“西風惡,夕陽吹角,一陣槐花落。”“倚著閑窗數落花。”……這些落花意象是對美的留戀,是惆悵與無奈,是對命運的感傷。
二是納蘭性德詩詞在意象的選擇上呈現出低回向下的特點,其情感指向是悲涼、落寞、感傷的。意象的選擇是和詞所表現的情感是一致的,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說:“如果作家所感受的情感活動的性質是消極否定的,其情感作用方向是消極向下的,那么最終形成的意象,其力的作用方向也應該是低回向下的。”納蘭詞中很少選擇具有亮麗色彩的意象,他所選擇的意象往往蘊含著悲涼、落寞、感傷的基調,籠罩著一層暗淡的色彩,以傳達內心孤獨抑郁和愁苦。夜在納蘭詞中出現91次,“夜寒驚被薄,淚與燈花落。”“夜雨做成秋,恰上心頭。”秋在納蘭詞里出現了75次,頻率也很高,呈現的是悲涼、凄切,滲透了詞人主體的身世之感。“晚秋風景倍凄涼。”“已是深秋兼獨夜,凄涼。”“香消被冷殘燈滅,靜數秋天。”淚在納蘭詞里出現了62次,“又到斷腸回首處,淚偷零。”“紅淚偷垂,滿眼春風百事非。”“黃昏清淚閣,忍便花漂泊。”在淚水中,是詞人的追懷與無奈,那是他生命中最刻骨的體驗。
三是喜歡選擇一些殘缺狀態的意象。這些殘缺狀態的意象其實是作者孤獨寂寥生活在心靈中的投射。如他經常使用殘紅意象,“催花未歇花奴鼓,酒醒已見殘紅舞。”“索性不還家,落殘紅杏花。”“飄零心事,殘落花知。”等等,殘紅花落映襯著作者孤寂的身影。再如寫日月,在納蘭性德筆下也很少展示出圓滿光輝的氣勢,而總是以殘缺示人。如“一半殘陽下小樓。”“剛剩秋裊一半,擁透簾殘月。”“一鉤殘照,半簾飛絮,總是惱人時。”“乳鶯殘月啼。”“一樣曉風殘月,而今觸緒添愁”等。此外象說香“殘香細裊秋情緒。”“無那殘香半縷惱多情”;說燈“殘燈落碎花。”“香雪被冷殘燈滅”;說夢“奈卷地西風,驚回殘夢,幾點打窗雨。”“一種曉寒殘夢”等等。納蘭性德詩詞意象選擇的審美傾向也表現了他獨特的藝術風格和審美價值追求。作為婉約詞家,他給讀者提供的主要是一些“柔性”的美感,即“哀感頑艷”的美感特色。種種意象在作者筆下大都蒙上了一層憂傷的暗影,染上了一種凄清的色彩,透露出悲涼傷感的情緒。美的事物常常被摧殘,賦予其悲劇氛圍。如“平原草枯”“梨花零落”“芳菲寂寥”“西風斷雁”“雨剪芭蕉”“塞煙衰草”等等,這些意象凄迷低徊,令人讀之蕩氣回腸。
作為詞界高手,納蘭詞的意象蘊含的情感是十分豐富的。他也正是用這些意象構成詞的基本材料來唱出自己心靈的悲歌。他雖出生于貴族之家,但也體味了人生的苦澀。他的摯友顧貞觀在祭文中說:“吾哥所欲試之才,百不一展;所欲建之業,百不一副;所欲遂之愿,百不一酬;所欲言之情,百不一吐。”他自己也說:“予生未三十,憂愁居其半。心事如落花,春風吹已斷。”(《擬古》)妻子的早逝,引發他對世間萬物終將消逝的悲愁,其淡泊功名富貴的天性,又使他厭倦了扈從入值的仕宦生活,他內心深處積郁著一層難以言狀的隱怨深悲,他把這種對人生的遺憾、失望、哀傷和悲痛全部重重融合在詞作中,使詞中的物象融入了某種典型性的主觀情味,也使他的詞作總是繚繞彌漫著一片凝重的、難以掩抑的、剪不斷、理還亂的傷感意緒,因此他始終以悲眼觀物,無論是自然景觀,還是世路人情,似乎都融進了他的人生嘆息與不盡的家國身世之感,使他詞作的意象所表達的感情更加悲凄。
如《采桑子》:“誰翻樂府凄涼曲,風也蕭蕭。雨也蕭蕭,瘦盡燈花又一宵。不知何事縈懷抱,醒也無聊。醉也無聊,夢也何曾到謝橋。”蕭蕭雨夜,孤燈無眠,風聲雨聲和著凄涼的樂曲聲伴著寂寞難耐的心情,由這些意象組合成的意境,顯得凄惋悱惻。哀怨動人,有人認為這是一首愛情詞,而梁啟超先生卻認為此詞有“時代哀音”“眼界大而感慨深”。即使是他的塞上曲也是如此。
如《長相思》:“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關那畔行,夜深干帳燈。風一更,雪一更,聒碎鄉心夢不成,故園無此聲。”邊塞的風雪、聒碎鄉心的邊塞之聲及壯觀的干帳燈火,幾個意象構成的壯闊場景,顯得無比凄清與悲壯,正如嚴迪昌《清詞史》所評:“夜深干帳燈是壯麗的,但干帳燈下照著無眠的萬顆鄉心,又是怎樣的情味?一暖一寒,兩相對照,寫盡了一己厭于扈從的情懷。”這說明在表面的“千古壯觀”之外,還蘊含他的深層傷感痛苦的內心世界。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