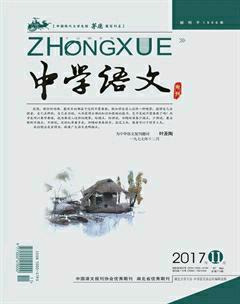讓孩子站在最中央
左衛勝
劉可欽在《教育其實很美》一書中寫道:“面對不同的學生,我們的教育是包容的而不是排斥的;面對學生的問題,我們的態度是接納的而不是指責;面對學生的發展,我們的教導是支持的而不是批判性的。要讓學生站在正中央,讓每一個學生獲得成長的自信!”
是的,要讓孩子站在最中央,摒棄“標準”,注重個性發展,讓他們在同一片藍天下創造出不同的精彩,乃當務之急!
1.標準答案
究竟是從什么時候開始,語文教育也有了整齊劃一的標準答案。所謂“語文”,它與人類文化密不可分,它應當是充滿活力的、充滿生機的;它應當是生生不息的、博大精深的;它應當是日新月異的、與時俱進的,何來標準答案這一說啊。
曾經不止一次有過家長向我抱怨,現在的孩子作業太多,除了書面作業,還要背誦閱讀理解答題標準,每周還要背誦一篇標準范文,孩子們太累了……我十分贊同家長們的觀點,也想方設法地去改變,但好像又有什么羈絆,使得我依然無法將傷害降到最低,為了升學,我還必須要求著他們夜以繼日地復習背誦。他們的叫苦連天讓我沒有一刻不在思考反省:語文教育真的也要像數理化一樣用標準答案約束著嗎?真的也要用分數高低來評判孩子的文學情操嗎?
2.得分要點
記得某一次期中考試,班上一位同學拿著試卷質問我,為何一道4分題他一分沒得。這是一篇關于《父親的愛》的閱讀,其中有一題是“請畫出文章中讓你最感動的一句話,并進行賞析”。他的答案“這句話體現出了父親對孩子的愛”。閱卷老師把4分全扣了。面對孩子的不甘眼神,我只能耐心教育他說,這種題目,是有模式的,比如“運用……的修辭手法,通過對……描寫,體現了……的情感,也飽含作者……的情感,使讀者感到……”其實說完之后,我覺得4分全扣是不對的,起碼能給一分吧!但又細細想想,我們平時不就是這么教孩子背誦標準答題模式的嗎?此刻嚴厲一點,更利于孩子得高分吧!
是啊,孩子認為某一句話是感人的并作出中肯的評價,教師卻要全盤否定。所謂感悟與情操,我實在是想不出何來對錯之分,不過是孩子與答案命題人所想的不一樣罷了。如果真的是千篇一律的答案,所有孩子都說著同樣的語言表達著同樣的情感,我想這才是真正的錯誤結果吧!
3.范例作文
孩子回家告訴我,上周老師布置了一篇作文,他有認真寫完并且字數要求達到了,可是老師只給了他85分。班里有個孩子得了93分,老師讓她在全班宣讀,還復印出來貼在了教室后面的墻上,以供其他同學參考模仿,老師明確告訴他們,作文這樣寫才能得高分。兒子很委屈,因為他寫的十分用心卻沒有得到一個高分,甚至連支持與鼓勵都沒有。這樣一來,當兒子再次寫作的時候,我明顯感覺到他的熱情不如之前了,下筆也沒有上一次的自信了,真的開始模仿起老師所說的“范例作文”的結構與語言了,他這樣做大概是企圖可以獲得一個高分和肯定吧!
然而我卻感到悲哀。我始終認為,語文是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繼承并發揚傳統文化的感性學科,其本質應該是豐富情感,陶冶情操,而作文作為語文學習中自我感悟的表達,不該受到條條框框的約束,也不該有模板有范例。如此教法,這一代孩子成長起來,往后還會不會有下一個魯迅,下一個莫言,下一個陳忠實?
這是教育的悲哀,更是文學的悲哀。作為一名語文“教書匠”,我從來不相信閱讀理解、文言文閱讀以及作文這樣的主觀性極強的題目,也可以通過大量做題反復背誦來實現提高。我堅持以為,這些題目是取決于閱讀與情懷,應該是“多讀書讀好書”并且要真的用心體會。如果孩子不能站在教育的最中央,換來的是習題與分數最得人心,也就是專業上稱之為“教育影響”的物質化要素,如此發展,恐怕真的是要“誤盡天下蒼生”!
4.五段式教學
在我大學實習期間,導師就曾經說過,“五段式教學”即“文章背景、作者生平、劃分段落、概括段落大意以及思想升華”不能說不好但也確實缺乏新意,早在近三十年前“關于《紅領巾》教學大討論”中就指出傳統語文教學的不足,并且純填鴨式地教學不是文學該有的形態。
但可惜的是,今天的我們從事語文教育依舊在孜孜不倦地研究“五段式教學”,真真切切做成了“長大以后,我就成了你”。改變與改革確是刻不容緩,就應該從這一代開始了。課堂與課文的主人都應該是孩子,沒有“五段式”,沒有“填鴨式”,而應該是孩子自由的用心去感悟,想其所想,用其所有。
5.讓孩子站在最中央
十八世紀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奇提出“教育心理學化”,他指出我們應該“熱愛孩子,尊重孩子”;而盧梭倡導的自然教育同樣是出于對孩子的尊重,他所保護和張揚的是人最可貴的自然精神和自由權利,自然的教育應該是順應孩子天性的教育,應該是遵循孩子身心發展規律的教育。
可是正如薛毅老師所說,我們為了分數和升學實際要求孩子的種種應該還是現代中小學語文教育的悲哀,我們不得不努力更努力地靠近標準答案,語文作為一門高分值的語言類學科,卻也已經無異于數理化這樣的計算學科。
面對現實與理想之間的差距,面對成千上萬的孩子們正在淪失著屬于自己的自然的自由的情感與思考,我們作為教育的踐行者已經是不得不付諸實踐,樹立起正確的“學生觀”,真正做到讓孩子站在最中央。就像柳宗元在《郭橐駝傳》中提到“順木之天,以致其性”,順應每個孩子不盡相同的天性,堅持人性關懷,不要以所謂的“標準模式”“標準答案”“標準感悟”“標準作文”來衡量孩子。在每個孩子不同的想法與答案出現時,只要不涉及原則問題上的偏離,我們都應該予以肯定和引導,這應該是我們每一個教育工作者努力的目標。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