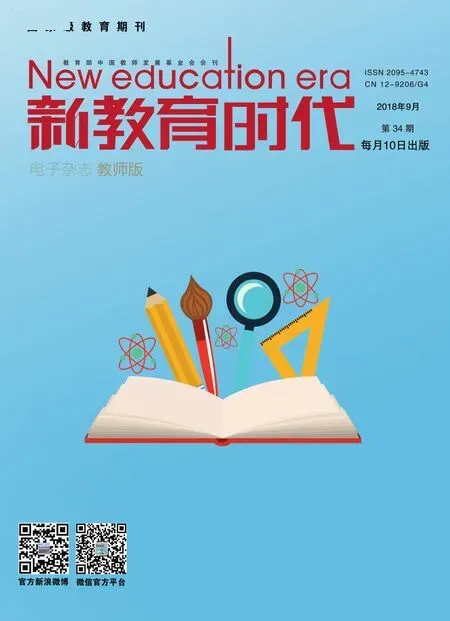關于基于任務驅動的建構主義高中生物教學的一點思考
(哈爾濱市中實學校 黑龍江哈爾濱 150008)
筆者在教學實踐中發現,受應試教育和傳統教育理念的影響,許多高中學生和生物老師認為生物學科偏向文科,所以在教學過程中和學法指導中仍然以講授和識記為主,難以實現提高學生能力和發展生物學科素養的目標。而“任務驅動法”是建立在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基礎上的教學法,是學科教學與現代信息技術整合的結果。其根本特點就是“以任務為主線,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改變了以往“教師講,學生聽”,以教定學的被動教學模式,創造了以學定教的新型學習模式。建構主義學習理論認為:學習活動必須是學習者在原有知識經驗的基礎上,在一定的環境中,主動對新信息進行加工處理,建構知識表征的過程。因為學習者具有差異性,所以建構學習也具有特異性。建構主義教學是注重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學生是信息加工的主體,是知識表征的主動建構者,而不是外界刺激的被動接受者和被灌輸的對象。因此建構主義指導下的教學要注重在實際情景中進行教學,讓學習活動與任務或問題相結合,以探索問題來引導和維持學生的學習興趣、學習動機,讓學生擁有學習的主動權。
這讓我想到一則寓言故事“盲人摸象”。“盲人摸象”原本是一則來自佛經的成語故事。說的是古印度一個國王召集一群沒見過大象的盲人來到大象身旁,要求他們站在固定位置用手觸摸大象的身體,然后回答侍臣的提問:“摸完后各自說說大象是什么樣子的?”盲人們自然回答得五花八門:“大象長得像一堵堅實墻壁。”“大象長得像一把巨大扇子。”“大象長得像根軟軟長長的管子。”“大象長得像又長又光的牛角。”“大象像一根粗大的石柱。”“大象像一根細細的麻繩。”一群盲人各持己見,爭論不休,都說自己正確而別人說的不對……這個故事傳頌了很多年,讓不是盲人的我們嘲笑了很多年。創作這個故事的人和傳播這個故事的人,其本意可能是想告訴人們這樣一個哲理:看事物一定要全面地觀察、分析,假如我們把對于事物的認識建立在一知半解或淺嘗輒止的局部經驗基礎上,往往就容易導致以偏概全的錯誤。可是,不論是盲人,或者如我們一樣有一雙明亮眸子的人,在觀察和學習一個新事物或概念的時候,事實上很多時候一開始是不全面的,因為我們缺乏一個好的,全面的,實際的情境,有時候還缺乏充分的資源和信息條件,那么這個觀察和學習的過程就如盲人摸象,但如果我們能注重協作與交流,那么你感覺到了這一點,我體會到了那一點,大家將這一點點認識匯聚起來,相互分享,探討,然后逐漸形成一個接近真相的概念,模型或理論。這才是我們提倡的有效的教學過程。
我們教師很多時候墨守的教學規則就是老師或教材必須清晰地準備好講授的概念,清楚地告訴學生們什么樣的概念,學生們才會照著這樣的概念學習、背誦、記憶、答題。如果不給出準確的概念,學生依據什么完成這一連串的學習?如何才能通過測評(考試)檢測學生學到了、掌握了這部分知識?而這種閱讀教材,標注概念,直指結果的學習內容,只是生物學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基本規律和基本觀念及其內在聯系,即所謂的必備知識,完全可以并且應該由學生獨立完成。如果一味地追求學生自主學習的課堂形式,沒有領會新課改的精髓,只模仿形式,給人的感覺很可能是:要么這個老師是無能的,要么這樣的教學是沒有真正效果的。
那么,在培養學生學習生物學知識及運用所學知識解決與生物學有關的實際問題的各種能力,以及綜合的學科素養時,不論教師手頭有多少概念,掌握了多少知識真理,在促進學生學習時,需要發展和改造“盲人摸象法”,努力創設合理真實的情境,讓學生親自感覺“象”是什么,讓他們說出自己的感覺,其中必然就有如“盲人摸象”故事里的混亂和幼稚,但正因為有這樣一個混亂和幼稚的過程,學生才會真正開啟思維的大門,才會進入動腦學習的狀態。如果一開始就直端端的告訴學生,“象”是什么,“象”的準確概念表述是什么,學生就失去了學習體驗的過程,學習也就變成了記憶,教學也就變成了灌輸。
本人認為,基于問題驅動的建構主義教學可以分為以下環節:
第一,“摸象”,讓學生在已有知識基礎上親身體驗與認識,反復實踐和積累深化。這需要教師給始終以學生為學習活動的主體,設置一個探究的場景或問題,有意識地避免灌輸式的“傳授”。既要激發學生的濃厚興趣,又要考慮學生的能力范圍,選擇適合的難度和范圍。
第二,“談象”,由教師引導、創設活躍開放而又嚴謹明確的互助氛圍,鼓勵學生進行充分的交流和討論,提供學生多種學習資源或者指導學生開展多種學習方法,充分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將課堂真正交給學生。
第三,“抽象”,通過以上兩步知識的獲取、集合和梳理的過程,完成知識的建構,由點到面,由局部到整體,在此基礎上將學生的體驗式成果抽象概括為初級概念,當然這個過程還需要教師的修正,教材等權威的統一。只有通過這些環節的循序漸進,才能把未知變已知,外在變內化,進而表現在解決問題的能力,和科學素養的提高。那么,概念的準確再現、辨析,知識網絡的聯接和問題的優化解決遲早都能熟能生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