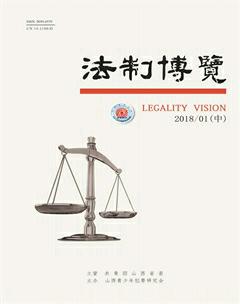環境侵權原因行為的法典化探析
摘要:環境侵權是環境法與民法典對接的重點領域,在民法典編纂過程中應完善環境侵權的相關規定。現行《侵權責任法》第八章環境污染責任不包括破壞生態責任,第65條的“污染環境造成損害”并不包括“破壞生態造成損害”,在編纂民法典時在侵權責任中應增加破壞生態的有關規定。
關鍵詞:污染環境侵權;破壞生態侵權;必要性;法典化
中圖分類號:D922.6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4379-(2018)02-0161-02
作者簡介:毛爽妍(1994-),女,漢族,吉林吉林人,北京理工大學,2016級法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環境法。
一、關于《侵權責任法》第65條行為適用的現有爭議
《侵權責任法》第65條是否適用于破壞生態造成損害的情形,無論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存在爭議。主流觀點認為“環境污染責任”是狹義的,并不包括破壞生態侵權責任。學界上,不少教授等也持此觀點。王利明教授認為從第八章的標題和具體表述以及比較法上來看,該章調整的僅是因污染環境而導致的侵權責任關系,目前很多國家的侵權法并沒有將生態損害納入保護范圍,主要借助公益訴訟來救濟。呂忠梅教授認為“排放”是兩種行為最為明顯的區別,并且從環境法學理上講,原因行為上污染行為和破壞行為的二分,是環境侵權行為類型化的基礎。張新寶教授曾建議增加破壞生態侵權責任規則。羅麗教授雖然在二分法上有分歧,她認為原因行為應分為污染環境侵權行為與破壞環境侵權行為,但是也認為侵權法第八章僅包括污染環境侵權責任。司法實踐上,最高人民法院也認為環境污染責任糾紛中不含有破壞生態導致的糾紛,主張二分式立法。
對此也有人持反對觀點,全國人大法工委相關人員及環境資源審判庭相關人員認為“環境污染責任”是廣義的,包括破壞生態環境行為。還有學者認為《侵權責任法司法解釋》第110條明確寫明“環境”包括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試圖用立法解釋的方法來表明自己的觀點的正確性。但是即使假定65條中“污染環境”包括污染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該條原因行為也只是“污染行為”,并不能得出包括“破壞行為”的結論。
二、爭議解決的關鍵
筆者認為第65條的現有規定不包括破壞生態行為,二者是相關但不同的行為,解決這一爭議的關鍵在于明確兩種原因行為的范圍和造成損害的表現的差別。就原因行為而言,環境污染行為強調利用資源的不合理性;生態破壞行為強調開發和適用資源的過度性。從損害的表現上看,前者造成環境污染,后者造成生態破壞。環境污染強調有害或有潛在威脅的物質的過量排放,產生了不利于人類及其他生物正常生存和發展的物理、化學等性質的變化;生態破壞強調開發環境的過度性,以致破壞或降低其環境效能而危及人類和其他生物的生存與發展。
三、引入生態破壞侵權責任的必要性探析
(一)立足環境基本法
目前的《環境保護法》第64條明確規定了破壞生態侵權責任,但并沒有細化規定,而是規定援用《侵權責任法》的相關規定處理類似問題。但是關于破壞生態侵權責任的具體處理規則并不能在《侵權責任法》中找到答案。此外,立足于現有環境法的相關條文,我國現有的環境立法的首要目標均是預防損害,缺乏恢復與填補生態損害的有關規定。顯而易見,以預防為首要目的的環境法無法有效應對發生的生態損害事件,更無法減少此類事件的發生。在生態損害事件發生后,運用現有的環境法難以對環境侵害人進行歸責,更無法救濟所造成的生態損害。而對于侵權法的功能雖有不同觀點,但都包含了“賠償填補損害”這一重要功能。筆者贊同“多重功能說”,核心功能是預防功能與填補損害。目前大部分國家的侵權責任法都體現出了上述的兩大重要功能,即填補損害和預防損害。并且,生態損害的救濟方式主要包括預防與填補兩種。可以說,侵權責任法的預防與填補損害這兩個核心功能會極大促進與之對應的目標的實現,是功能與目標的重合,可以配合環境法的適用更好地實現環境法的目的。因而,在《侵權責任法》第八章引入破壞生態侵權責任制度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二)立足民法典
《民法總則》第9條將“保護生態環境”規定為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遵循的原則。從中可以看出民法法典化過程中“生態環境”的重要性。而對生態環境的侵害不僅僅只有污染,還有破壞行為。王利明教授就認為從發展趨勢來看,在法典化過程中侵權責任法有必要將其保護范圍進行擴張,將生態環境納入到其保護范疇,以更好地救濟有關生態環境本身的損害。
(三)立足司法實踐
各類環境侵權糾紛日益復雜化、多樣化,生態破壞帶來的損害已經危及到人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而傳統的公力救濟方式已不能滿足人們的利益訴求,公力救濟渠道有較大的滯后性。而最高人民法院并沒有將破壞生態致人損害的民事責任糾紛案件納入環境污染侵權責任糾紛這一類之中,可見立法上對該原因行為規定的模糊已造成了司法實踐上環境侵權糾紛案件受理范圍的狹隘。此外,面對日益增多的破壞生態造成損害引發的求償案件,基層法院在辨析污染環境行為與破壞生態行為以及適用相應規則時,缺乏明確的立法支撐,只能以個案司法解釋去盡力維護實質公平。這種尋求個案司法解釋來解決現實問題的司法困境出現的直接原因在于第65條規定的污染環境行為不能包含破壞生態行為。
最后假設若不在第八章中明確規定破壞生態行為,按此理解,第65條乃至第8章都不包括破壞生態行為,這勢必會完全割裂污染環境行為和破壞生態行為,分別適用侵權責任法下特殊與一般的規定。在這種情況下,不僅是對環境侵權行為本質特征的背離,還會影響環境侵權民事責任功能的有效發揮,不利于實現救濟受害人的目的。由于環境污染行為與生態破壞行為具有相關性,嚴重的環境污染無疑會打破生態的衡平,而如果生態環境被破壞了,反過來又會使環境的自凈能力下降,環境的污染會會更加惡劣。二者在基本框架上的適用應是相同的,只是在細化時會有不同。因此,在侵權法法典化過程中,引入并構建破壞生態侵權責任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參考文獻]
[1]王利明.論我國侵權責任法分則的體系及其完善[J].清華法學,2016(1):125.
[2]呂忠梅.侵害與救濟:環境友好型社會中的法治基礎[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66-69.
[3]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民法室.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解讀[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2:325.
[4]竺效.論環境侵權行為的立法拓展[J].中國法學,2015(2):251-260.
[5]殷鑫.論生態損害的侵權責任法救濟機制[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5):54-55.
[6]岳紅強.我國民法典編纂中綠色理念的植入與建構[J].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4):60.
[7]王利明.論我國侵權責任法分則的體系及其完善[J].清華法學,2016(1):125.
[8]羅麗.再論環境侵權民事責任—評<侵權責任法第65條>[J].清華法治論衡,2011(1):256.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