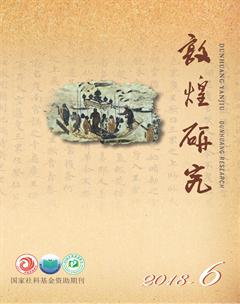以“舊問題”治“新材料”的新高度
蔡淵迪
內容摘要:放置到整個百年學術史的大語境中,許建平先生的經學研究特色可以說是以傳統經史小學這一舊的問題意識來攻治敦煌文獻等新的文獻材料,其新著《敦煌經學文獻論稿》則標定了這種研究路數的新高度。該書至少有三個方面的學術特色:鉤貫群經、精通小學和尊重成說。
關鍵詞:經學;小學;敦煌;異文
中圖分類號:K87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18)06-0177-05
中國敦煌學在發端肇始之時是帶有濃厚的舊問題意識的,即以經史小學和金石學這類有清三百年最為發達的舊學問來研治敦煌文獻這堆新材料,可以說是以“舊問題”治“新材料”。無論是羅振玉對于敦煌寫卷的拚命刊布,還是劉師培對寫卷異文的精細考訂,都是如此。大約在上世紀20、30年代,中國的敦煌學經歷了一次急劇的轉型,從此轉向了對變文、胡語文獻、夷教文獻、經濟文書乃至壁畫藝術等“新問題”的探討,先前的“舊問題”則被冷落下去,直至今日,這一大趨勢仍未見改變的跡象。因此,自上世紀30年代至今,在整個敦煌研究的大格局中,敦煌經學文獻研究所占比重偏小,其中論斷精確、質量上乘者更是少之又少,許建平先生卻是這其中的佼佼者。自上世紀末以來,許先生一直埋首于敦煌經籍寫卷的整理與研究,二十余年艱辛,換來數百萬字的著述,這其中,無論是“最全面、最準確、最簡潔”的《敦煌經籍敘錄》①,還是煌煌五巨冊的《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群經類及小學類群經音義之屬),以及本文將要著重論述的《敦煌經學文獻論稿》,皆足以標定許先生在敦煌學界之地位,亦足以標定敦煌經籍文獻研究在整個敦煌學史上的新高度。
《敦煌經學文獻論稿》(以下簡稱《論稿》)于2016年4月出版,收錄許先生自2000年以來已發表論文21篇,外加學術自述《我與敦煌學研究》一篇,乃許先生有關敦煌經學方面研究成果的最新結集。筆者自去年9月始獲此書,反復翻讀,深覺汲深綆短。鉆堅仰高之余,每有心得,輒隨筆記之。愚見所及,是書特色,略有三端:一曰鉤貫群經,二曰精通小學,三曰尊重成說,茲各舉數例,分述如下。
一 鉤貫群經
自來治經之途不外兩端,或窮治一經以通群經,或泛覽群經而歸宗一經。這兩者在本質上并無區別,都是對治經者提出了通貫群經的要求。許先生之研治敦煌經籍,也照樣做到了鉤貫群經。具體到《論稿》本書,其鉤貫群經之處亦自有特點,大約有如下三端。
第一是對于群經字面的貫通。經典字面,常有諸經參見,因此,對某經中一字之考查,往往需要鉤貫他經中之對應諸字。如《唐寫本〈周易經典釋文〉校議》中,為論證“勞謙匪解”之“解”字乃“佳賣反”而非“佳買反”,許先生將經典中凡出現過之“解”字全部摘出,即征引到《易》《詩》《周禮》《禮記》《公羊傳》五經,共出“解”字十條,其中讀為“懈”、作懈怠義解者計七條,《釋文》無一例外皆讀去聲卦韻;作說解、解脫等義解者三條,《釋文》又無一例外皆讀上聲蟹韻,是知《釋文》于“解”字上、去讀音分別甚嚴,而“勞謙匪解”之“解”顯然作懈怠義解,故當讀去聲。然則宋本《釋文》之作“佳賣反”者正確,而P.2617《易釋文》寫卷之作“佳買反”者誤,蓋誤“賣”作“買”。許先生于下文論證“買”、“賣”二字之易混淆致誤,又例舉書證四條,其中兩條是經部文獻[1]。
第三是對經理的通解以及對群經體例的把握。清代樸學家的長處在“一字不肯放過”,即于經籍中一字一詞必推尋到底,隨之帶來的流弊則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于經籍大意反而疏忽了。許先生在步趨清儒的同時,卻避免了這項流弊。《論稿》中亦有以經典理論來解決問題者。如《關于傅斯年圖書館所藏〈周易正義〉寫卷》一文中,其證明《賁》卦下孔疏“坤之上六,何以來居二位不居于初三;乾之九二,何以分居上位不居于五者”之“初”字為衍文,便全憑《周易》象數變化的理論來解決。其文不長,且抄如下:
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荀爽曰:“此本《泰卦》。”《賁卦》自《泰卦》來,《泰卦》下乾上坤,其上六來居二位,二位而居上六(引者案:此作“九二而居上位”似更合適),則成《賁卦》。坤之上六,坤卦之極,其對應之爻乾三也;乾之九二,其對應之爻則坤五也。今坤之上六下居乾二而不居乾三,因“坤性柔順,不為物首”也;乾之九二不居于坤五而居于上六,因“乾性剛亢”也。“初”字當是衍文。若該句作“何以來居二位不居于初三”,則下句為何不作“何以分居上位不居于四五”也?寫卷無“初”字,是也。[1]82
五經中數《易》最難,以象數解《易》難之尤難。許先生此處解《泰卦》、《賁卦》演化消息略無疑滯,其于他經經理之熟稔更無待論矣。此是通解經理之例。
《唐寫本〈周易經典釋文〉校議》第2條,其舉證多方,周詳往覆,以發明《易釋文》“卦末注同”之例,從而知P.2617號寫本《易釋文》中“烏路反注同”句脫“卦末”二字(在“注同”前),而“所惡烏故反”為后人妄添。此是把握經籍體例之例。
二 精通小學
既然群經異文極其豐富,而這些異文間的關系又極為復雜,或此為本字,彼為借字;或此為古字,彼為今字;或此為正字,彼為俗訛;或一正一誤,或字可兩存,不一而足,那么,在對種種異文作出取舍判斷時,便要求學者必須精通小學。因此,清代經師無不精通小學者,王國維謂有清一代學術“所以超絕前代者,小學而已”[2],可謂一語中的。
許先生既步趨清儒,其于小學自然十分注意。在《整理敦煌文獻時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一文中,他特別指出:
在異文錄校時,存在問題最多的是關于古今字、通假字、異體字的判定。很多論著在碰到這一類的異文時,往往不作考察,就簡單地賦予“通假”二字,不僅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反而產生了新的訛誤。正確地判定它們的關系,對于考證寫卷價值有重要的作用。但這要求整理者必須具有文字、音韻、訓詁方面的一定功底,否則就會得出錯誤的結論。[1]38
就《論稿》所見,許先生之長于小學大約有三方面之特色。
一是精熟《說文》。《說文解字》乃治小學之第一要籍,自段玉裁為之作注,所謂“創通條例、開發奧窔”[2]卷27(19A),此后,有關《說文》之著作可謂汗牛充棟。許先生于清人有關《說文》著作的掌握簡直到了叫人驚嘆的地步。所謂“四大家”之著作自不必論,煌煌數百萬字的《說文詁林》也常在引用之列,甚至于《續修四庫全書》及《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所收錄的清人《說文》著述也幾乎被許先生爬抉殆盡。清人以外,近百年來續出有關《說文》之要籍若馬敘倫《說文解字六書疏證》、張舜徽《說文解字約注》、季旭升《說文新證》等也常在引用之列。
三是長于音韻。古音學在先秦經籍文獻研究中的重要性早經前輩名家指出,今日已是眾所周知,不必贅引。然音韻學向稱絕學,今日學者大多更是視為畏途。許先生于音韻方面卻特別擅長。論稿收論文21篇,其中專門研究音義寫卷者即有7篇,論篇目,占全書三分之一,論篇幅,卻幾乎占了全書之半。應該說,這7篇文章是全書中最能代表許先生治學特色、發明最多,同時也是最難讀的文章。不過,必須指出的是,這些文章雖然都是研究音義寫卷,卻并不討論音韻本身的問題,許先生只是將音韻作為工具,最終的落腳點仍然是文獻本身,這一路徑與清儒毫無二致。
在這些文章中,我特別要提請讀者注意的是《“又音”考》一文。此文所考者不過21條音切材料,卻竟然寫成了上萬字的論文,其功力可以想見。而其中第14、15兩條更是幾乎在一空依傍的情況下(沒有直接文獻材料,僅據音切以及旁證),憑空考出了兩條以前經學家都未見過的異文:一是《詩經·大雅·皇矣》“攘之剔之”之“剔”字,據許先生所考,六朝時當別有作“鬀”之本;一是《大雅·生民》“載謀載惟”句鄭箋“則諏謀其日”之“諏”字,據許先生所考,六朝時當別有作“掫”之本。說這兩個異文“一字千金,驚心動魄”,殆不為過。
三 尊重成說
尊重先賢成說也是《論稿》之一大特色。許先生在談及整理敦煌文獻時需要注意的問題時,特別強調了當下的敦煌文獻整理對清人的研究成果不夠重視[1]41。這顯然可以反證,許先生本人是極其重視既有研究成果的。《論稿》中引用清人以及近人著作者比比皆是。隨手舉例,如考今本《谷梁傳·莊公二十年》“冬,齊人伐我”之“我”乃“戎”之誤,即引趙坦、鐘文烝之說;考今本《毛詩·豳風·破斧》“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傳“隋銎曰斧”下脫“方銎曰斨”又迭引阮元、陳奐及潘重規之說[1] 12-16。
書中有好多地方,往往是引了前賢成說后,便得出結論,許先生自己的意見一點也不摻雜進去,乍看“殆同抄書”。實則匯集前人學說并抉擇之,又談何容易?抄哪些,不抄哪些,實有自家見地在。同樣是清人的見解,《論稿》第14頁于王先謙之說不就果斷拋棄了嗎?顯然,這樣的抄書,不是隨隨便便就能抄得好的。眾多前賢成說經過研究者的含英咀華,最終匯集在一起,這對于后來學者而言更有意義。王重民先生《敦煌古籍敘錄》是敦煌學史上不刊的名著,其中好多地方王先生也只是匯集成說,而并不提出自己的意見,許先生卻評價說:“能將散見各處的研究成果匯為一編,為后人利用這些成果提供方便,其功可謂至大。”[1]110這一評價也未始不可移用于《論稿》中的很多條目。
具體來講,許先生之重視前人成果亦有其特色,大約三條:一、特重清人成說;二、于臺灣、日本著述之搜羅不遺余力{1};于未公開發表的著述也不輕易放過{2}。
也正因為這份敬業,這份認真嚴謹,許先生于那些學術質量低劣以及學術不端的行為絕不寬貸。且看《敦煌出土〈尚書〉寫卷研究的過去與未來》一文中對吳福熙《敦煌殘卷古文尚書校注》一書的批評[1]113-114,那真是拳拳到肉、針針見血,讀來虎虎有生氣。如此是非分明,在今日“一團和氣”的學術界難能可貴。
筆者愚鈍,所見《論稿》之學術特色主要便是如上這些,或許隔靴搔癢,說不到要害,那便要請許先生及讀者諸君見諒。
至于該書也存在著一些小小瑕疵,卻無傷大雅,讀時順手摘出,或便于許先生日后之修訂。如下:
第71頁注③“(明)毛居正”,“明”當標作“宋”,毛居正為南宋人。
第78頁第11行、第84頁正文倒數第5行“1917年”乃“1919年”之誤。考許先生所引羅振玉致王國維信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中編為第617號[3],是信原書考訂為1919年所作,綜合前后各信,其作于1919年者當不誤。
第108、110頁兩處“胡士鑒”皆為“吳士鑒”之誤。
第209頁正文倒數第1行“P.2729”乃“S.2729”之誤。
參考文獻:
[1]許建平.敦煌經學文獻論稿[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88-90.
[2]王國維.殷虛書契考釋后序[C]//王國維.觀堂集林.上海:商務印書館,1940:卷27(18B-19A).
[3]王慶祥,蕭文立.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470-4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