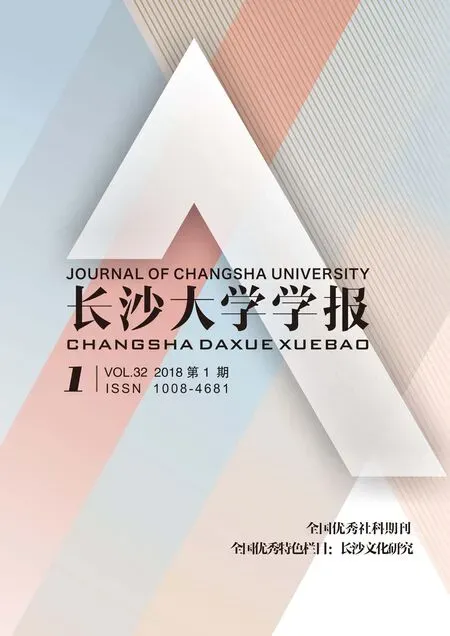萍瀏醴起義水陸洲籌備會議蔣翊武選擇運動新軍的原因探析
周 勇
(長沙師范學院思政課部,湖南 長沙 410100)
蔣翊武這位唯一被孫中山譽為“中華民國開國元勛”的資產階級革命家,卓越地領導了辛亥年間對湖北新軍的革命化改造,為武昌首義的成功從而也為推翻清王朝的統治奠定了堅實基礎。1906年5月在長沙水陸洲召開的萍瀏醴起義首次籌備會議(又稱水陸洲籌備會議),是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從發動會黨轉變到發動新軍的重要節點。蔣翊武在會上選擇承擔運動新軍的任務,從此開始了對新軍開展革命化改造的探索歷程。現有關于水陸洲籌備會議的研究還只掌握了會議的大體時間、內容以及蔣翊武等人選擇運動新軍這些基本史實,對于蔣翊武在會上選擇運動新軍的原因尚未涉及。弄清楚蔣翊武在水陸洲籌備會議上選擇運動新軍的原因,不僅有助于梳理資產階級革命黨人開展新軍革命化改造的整體線索,也有助于推動關于蔣翊武的研究。
一 水陸洲籌備會議上蔣翊武選擇承擔運動新軍的基本情況
1906年底爆發的萍瀏醴起義是同盟會成立后發動的第一次武裝起義,它是此前華興會長沙起義的延續和發展。同盟會建立時的成員多數為原華興會會員,而萍瀏醴起義的主要依靠力量則是湘贛交界地帶的哥老會勢力,即華興會長沙起義的會黨領袖馬福益的部下和會眾。參加萍瀏醴起義的會眾舉白旗、裹白布的做法就有為馬福益披麻戴孝、報仇雪恨之意[1]。
1906年春,劉道一奉黃興之命從日本返回上海,此時蔣翊武正在上海中國公學就讀。蔣翊武不僅曾是華興會會員,還曾協助宋教仁籌劃在常德響應甲辰長沙起義,并具體負責發動常德的進步學生響應。起義失敗后馬福益準備在湘西再舉,派人前來聯系,于是蔣翊武又與劉復基、胡幻安等人在常德建立機關、聯絡會黨,準備響應。據蔣翊武生前好友萬武回憶,1898年春蔣翊武赴長沙報考時務學堂之時,“善化陳其殷創自立黨,蔣翊武、李虎村、何鐵笛、劉道一、蔡佩珊、蔡樹珊昆季及余均加入。彼此志同道合,情逾骨肉”[2]。因此,蔣翊武參加萍瀏醴起義,很有可能就是劉道一從日本返回上海時邀請的。
1906年5月,萍瀏醴起義首次籌備會議在長沙水陸州的一艘船上召開,劉道一、蔣翊武、龔春臺、劉重、劉崧衡等40人與會。劉道一在會上傳達了黃興關于起義的指示,明確本次起義“以軍隊與會黨并舉為上策”,而以“會黨發難,軍隊急為響應”為次策[3]。在分析了湘、贛兩省的政治形勢以及哥老會的分布情況后,會議對與會人員的任務進行了分工。蔡紹南、龔春臺、劉重、張堯卿等負責聯絡巡防營,布置會黨;蔣翊武、劉岳峙、覃振、劉承烈等人則“愿負運動新軍責任”[4]。分工確定以后,會議約定“一俟軍隊運動成熟”,將“于清吏封印時舉事。”[5]
二 從與會人員構成看蔣翊武選擇運動新軍的客觀原因

表1 水陸洲會議參加人員情況統計(負責運動會黨者)
注:本表由作者根據相關資料編制
值得注意的是,萍瀏醴起義之前蔣翊武兩次參與籌備的武裝起義,都是發動會黨。然而,萍瀏醴起義水陸洲籌備會議上,蔣翊武卻選擇承擔運動新軍的責任,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至于蔣翊武此時為何選擇運動新軍而不是此前他比較熟悉的發動會黨,目前沒有資料能夠直接說明。然而,如果深挖現有的資料我們仍能發現,蔣翊武此舉是經過反復思考后主動選擇的,而不是會議主持者的安排。上述關于水陸洲會議分工的記載也能夠體現這一點,該記載在描述蔣翊武等人選擇運動新軍時使用了一個“愿”字,即蔣翊武等人“愿負運動新軍之責”。
蔣翊武作為一位革命活動家,雖然所辦報刊不少,但著述不多,加之英年早逝,因而很多問題只能依靠對現有材料的深挖,才能找到線索。為了清楚說明蔣翊武選擇運動新軍的原因,厘清其思想發展歷程和歷史活動軌跡,筆者經過長期努力對水陸洲會議與會人員(劉道一除外)的相關情況作了統計。表1是負責發動會黨者的情況統計,表2是負責運動新軍者的情況統計。通過對表1與表2的對比,可以梳理出水陸洲會議任務分工的相關線索。
(一)運動新軍者與發動會黨者在身份閱歷上形成明顯分野
負責發動會黨者除了會黨首領之外,學生出身的革命黨人多數與會黨有歷史淵源,而負責運動新軍者多數為學生出身的革命黨人。由表1可知,在負責發動會黨的19人中,除5人目前尚不清楚身份之外,其余的14人中會黨首領有龔春臺、張堯卿、瞿光炆、李九、鄧玉林等5人。此外,已知身份的7位革命黨人多半也與會黨有淵源。蔡紹南是參加這次會議的唯一一位外省人,但正好是江西萍鄉人。1905年8月,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蔡紹南在“分任聯絡防營,布署會黨”的十九人中名列第二[6]。華興會長沙起義期間,劉重經黃興介紹加入華興會負責聯絡會黨的外圍組織“同仇會”,與馬福益結為莫逆之交,后經馬介紹加入哥老會,負責華興會與哥老會之間的聯絡工作[7]。萍瀏醴起義前,周果一就曾結識很多洪江會的朋友。1911年10月31日,周又發動會黨起義,光復衡陽[8]。黃人漳曾在日本橫濱與劉道一、秋瑾等人組成十人團,研究各派會黨的特點和聯絡方法,并且投身其中以發動革命。凌漢秋為長沙巡防營統領,與劉揆一、劉道一兄弟交往甚密,并受邀加入同盟會。1911年,凌漢秋帶領營兵,在長沙小吳門打開城門迎接革命軍入城。因為巡防營中哥老會組織密布,革命黨人對巡防營的發動也多半通過會黨發動,所以水陸洲會議將發動巡防營與發動會黨并列起來,二者整體上都屬于發動會黨的范疇。

表2 水陸洲會議參加人員情況統計(負責運動新軍者)
注:本表由作者根據相關資料編制
反觀表2,負責運動新軍的20人中,除2人身份尚不確知外,其余18人皆為學生出身的革命黨人。這一點與黃興“新軍兵精械良,官佐皆學生出身,多與吾輩通聲氣者,運動較易”[9]的觀點相符合。蔣翊武雖然未能赴日留學,此時也未投身新軍,但先后在西路師范學堂和中國公學就讀,與新軍中學生出身的官佐有一定的聯系,因而選擇運動新軍于革命發動更為有利。值得注意的是,蔣翊武在西路師范的同學好友黃貞元,此時已投身湖北新軍[10],這是目前唯一確知的水陸洲會議與會者身在新軍的史實。這一過去為人們所忽視的史實,包含了蔣翊武在會上選擇運動新軍的重要原因。盡管受史料的限制,上述20位水陸洲會議上選擇承擔運動新軍的與會者,在萍瀏醴起義中參與發動新軍的情況尚不清楚,但可以從他們在起義后的革命軌跡中窺見一斑。如表2所示,易本羲在萍瀏醴起義失敗后,于1907年與蔡鍔等人在桂林組織陸軍隨營學堂,準備伺機起義。胡國梁曾奉黃興之命考入廣州巡警教練所,以便在黃花崗起義爆發的時候作為內應。
(二)運動新軍者與發動會黨者在籍貫上形成明顯分野
負責發動會黨的19人中,有13人已確知籍貫。其中,蔡紹南(萍鄉)、龔春臺(瀏陽)、瞿光炆(醴陵)、陳顯龍(醴陵)本身就來自萍瀏醴地區,且很有代表性。張堯卿作為會黨首領,雖然不在萍瀏醴,但其籍貫所在地長沙卻是本次起義的目標所在,凌漢秋作為巡防營管帶也是長沙人。此外,其他已確知籍貫的7人中,劉重為郴州永興縣人,彭邦棟為郴州宜章縣人,李國柱為郴州嘉禾縣人,劉崧衡為衡陽縣人,黃人漳為湘潭縣人,周果一為衡陽衡山縣人。不難發現,上述7人的籍貫地都處于湘南地區,且與萍瀏醴地區相距不遠。負責運動新軍的20人中,已有17人確知籍貫。其中屬于湘北地區的8人,蔣翊武(常德澧縣)、黃貞元(常德澧縣)、覃振(常德桃源)、楊熙績(常德縣)、劉承烈(益陽桃江)、荊嗣佑(懷化溆浦)、禹瀛(懷化靖州)、胡國梁(岳陽汨羅);屬于長沙周邊的5人,成邦杰(長沙寧鄉)、向瑞彝(長沙寧鄉)、易本羲(湘潭湘鄉)、唐支夏(湘潭湘鄉)、曹武(湘潭湘鄉);屬于萍瀏醴周邊或湘南地區5人,劉岳峙(衡陽衡東)、柳繼貞(株洲攸縣)、葛天保(邵陽縣)、文斐(株洲醴陵)。
這種地緣上的分野也與起義的形勢有關,因為本次起義所依靠的會黨力量集中萍瀏醴地區,衡陽、郴州、株洲等地與之在地理和文化上較為接近。負責運動新軍的與會者則多集中在湘西北、湘北以及長沙周邊,也有某種地緣因素的客觀影響。蔣翊武、楊熙績、黃貞元等人在華興會起義的籌備過程中雖曾有過較豐富的發動會黨經驗,但他們主要是發動沅澧流域的會黨。本次起義改變了華興會五路舉事的做法,集中力量于萍瀏醴地區,因此,蔣翊武等人即使有豐富的會黨經驗,但要發動地處湘贛邊界的萍瀏醴地區的會黨,在語言、習俗和人脈等方面沒有優勢。當然,在負責運動新軍的與會者中,也會有萍瀏醴地區的與會者選擇發動新軍,因為他們具備具有發動新軍的有利條件。比如:文斐是株洲醴陵人,但其與新軍的關聯更多。1911年10月,文斐配合焦達峰、陳作新聯絡長沙新軍響應武昌起義,隨后擔任湘軍第二鎮參謀長。武漢戰事危急時,曾奉調參加湘軍援鄂的戰斗。
三 水陸洲籌備會議蔣翊武選擇運動新軍的主觀原因
蔣翊武在水陸洲籌備會議上選擇運動新軍,不僅有與會人員構成所產生的客觀原因,也有其主觀原因。現有資料顯示,水陸洲會議召開時,蔣翊武已對當時上海和湖北的新軍有一定的了解,從而對于革命的依靠力量有了新認識,選擇運動新軍正是基于這種新認識的一種嘗試。蔣翊武此時對新軍的了解,主要通過以下兩條途徑:
(一)通過楊卓林、楊瑾等人對上海新軍有所了解
在中國公學就讀期間,蔣翊武結識了一些進步的革命黨人,并通過與他們的交流對上海新軍有所了解。其中,最重要的是楊卓林和楊瑾。
1876年出生的楊卓林曾在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作為清軍江南福字營的一員,與侵略軍激戰。受傷后機智逃脫,遍游各省,廣泛結交江湖豪杰。然而,楊卓林逐漸認識到會黨雖然具有革命性的一面,但又具有落后散漫的一面,“不足與有為,遂專心轉學陸軍”[11],先后在隨營武備學堂和江南將弁學堂學習軍事。楊卓林進軍校深造,不是為了替清王朝保駕護航,也不是為了個人升遷,而是要“從清軍內部多去軍權,實行反清革命”[12]。1905年秋,楊卓林東渡日本,由黃興介紹加入同盟會,因為具備深厚的軍素養而深受孫、黃器重,孫中山曾多次向其詢問革命軍起事戰術等軍事問題。蔣翊武在上海期間與楊卓林關系較好,時人的傳記中既有“善楊卓林”的記載[13],也有“甚是交好”的表述[14]。在與楊卓林的交流中,蔣翊武肯定有機會將會黨與新軍進行比較,從而對依靠新軍發動革命形成初步的認識。關于這一點,從蔣翊武進入中國公學不久在一次革命黨人聚會上的講話中,可以窺見一斑。在這次講話中,蔣翊武論及清末政治腐敗、士大夫“酣睡如故”時,強調“雖以克虜伯之巨炮不能驚醒其幻夢”[15]。“克虜伯之巨炮”顯然不是會黨舉事時使用大刀長矛外加少數長短槍支的情形,而是按照近代化標準建立的清末新軍才有的武器配置。蔣翊武的這個講話能很自然地使用這個概念,顯示出其對新軍已有一定的了解。
楊瑾既是蔣翊武的同鄉,又是蔣翊武加入同盟會的介紹人之一。楊瑾當時除了在中國公學任職之外,還兼任上海新軍教練,以同盟會會員側身其間,借此發動和積蓄革命力量。武昌首義爆發前,楊瑾曾隨程潛從四川赴武昌采辦軍械,程后來在其回憶錄中稱其為蔣翊武的“舊識”[16]。蔣、楊兩人關系之深,可見一斑。在與楊瑾的交往中,蔣翊武同樣能獲得不少關于上海新軍的信息,其中自然包括楊瑾在新軍中進行革命發動的相關情況。
(二)通過黃貞元、楊載雄等人對湖北新軍有所了解
參加水陸洲籌備會議之前,蔣翊武不僅對上海新軍有所了解,而且對湖北新軍也有所了解。蔣翊武在常德求學期間的同學好友黃元貞與楊載雄,此時均已投身湖北新軍,蔣翊武對湖北新軍的了解主要是通過黃、楊二人實現的[17]。黃貞元在華興會起義失敗以后,“被開除學籍,嗣往投武昌湖北新軍”[18],蔣翊武與其多有書信聯系[19]。需要指出的是,黃貞元在華興會長沙起義失敗以后不久,即離開西路師范去武昌加入湖北新軍。蔣翊武則在起義失敗后,與劉復基在校外的祗園寺設立革命機關,聯絡會黨,準備響應馬福益在湘西北發動的會黨起義。直到馬福益籌劃的這次起義失敗以后,蔣翊武才與劉復基離開常德同赴上海,投考中國公學。據蔣翊武的嗣子蔣宗策回憶,蔣翊武考中國公學的經費就是由“黃貞元津貼”[20]。資助蔣翊武投考上海中國公學時,黃貞元已在湖北新軍服役了一段時間。黃貞元是自耕農出身,家境并不富裕,資助蔣翊武投考中國公學的經費顯然來自其在湖北新軍的軍餉。由此可見,黃貞元投身湖北新軍以后確與蔣翊武保持了較多的聯系,而蔣翊武正是通過這種聯系對湖北新軍有所了解。不僅如此,黃貞元被約集參加水陸州會議很有可能就是蔣翊武促成的。水陸洲會議后,為發動湖北新軍響應萍瀏醴起義,蔣翊武曾于1906年5月前往武漢聯絡同志,拜訪湖北軍中革命組織日知會的負責人劉靜庵,并且有革命黨人回憶蔣翊武名列日知會之中[21]。
[1][5]饒懷民.同盟會與萍瀏醴起義[M].長沙:岳麓書社,1994.
[2]萬武.蔣翊武死難紀實[A].蔣漫征,編.蔣翊武研究資料匯編[M].長沙:岳麓書社,2013.
[3][4][9]劉揆一.黃興傳記[A].辛亥革命(4)[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6]熊瑛.江西蔡紹南:萍瀏醴起義發起人 受派遣回國策動革命[N].江西晨報,2014-08-31.
[7]饒懷民.劉重傳[A].三湘英烈傳(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卷3)[C].長沙:國防科技大學出版社,2003.
[8]成賽軍.周果一傳[A].三湘英烈傳(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卷4)[C].長沙:國防科技大學出版社,2005.
[10][18]高守泉.蔣翊武身邊的九澧人杰[A].湖南省歷史學會,湖南省政協文史委.蔣翊武與辛亥革命[C]. 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
[11]馮自由.楊卓林事略[A].革命逸史(第2集)[C].北京:中華書局,1981.
[12]饒懷民.楊卓林[A].三湘英烈傳(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卷2)[C].長沙:國防科技大學出版社,2001.
[13]王建中.湖北文學社首領蔣翊武[A].蔣翊武研究資料匯編[C].長沙:岳麓書社,2013.
[14][15]佚名.武昌首義首領蔣翊武事略[A].蔣翊武研究資料匯編[C].長沙:岳麓書社,2013.
[16]程潛.辛亥革命前后回憶片段[A].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集)[C].北京:中華書局,2010.
[17][19]饒懷民.蔣翊武與辛亥武昌首義[J].武陵學刊,2012,(2).
[20]蔣宗策.清末中國同盟會會員情況調查表·蔣翊武[A].蔣翊武研究資料匯編[C].長沙:岳麓書社,2013.
[21]郭欽.蔣翊武史跡系年初編[A].湖南省歷史學會,湖南省政協文史委.蔣翊武與辛亥革命[C].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