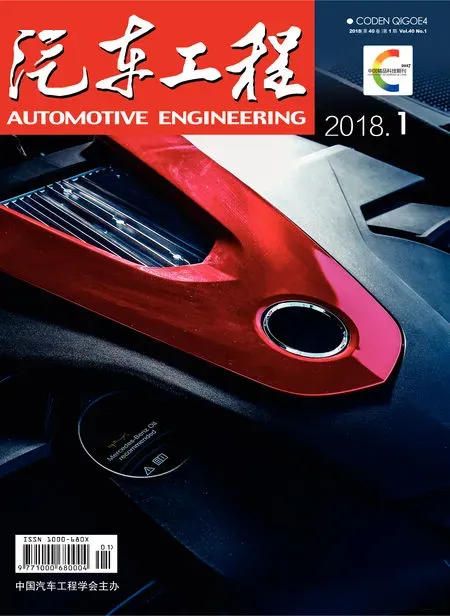基于仿生的A柱 后視鏡區域氣動降噪研究?
陳 鑫,李延洋,沈傳亮,吳元強,馮 曉,謝 沖,楊昌海
(吉林大學,汽車仿真與控制國家重點實驗室,長春 130025)
前言
隨著我國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汽車作為陸地上方便快捷的交通工具已走進了千家萬戶。但是隨著汽車保有量不斷增多,車速不斷加快,隨之產生的空氣動力噪聲也變得越來越明顯,因此,對于汽車空氣動力學特性的研究就愈加迫切。汽車氣動噪聲是汽車空氣動力學性能的重要參數之一,研究發現[1-2],當汽車以100km/h以上的速度行駛時,氣動噪聲在中頻和高頻范圍內的貢獻最為突出,所以它將直接影響一輛汽車的舒適性和整車品質。高速氣流流經汽車外表面時,由于汽車表面存在不規則的曲面和結構,導致氣流發生嚴重的分離,形成復雜的湍流結構,進而引起很高的氣動噪聲[3]。汽車高速行駛時車外存在多個氣動噪聲源,其中最主要的氣動噪聲源來自A柱-后視鏡區域[4],因此研究A柱-后視鏡區域的流場和聲場對降低整車的氣動噪聲具有積極的意義。
目前,國內外在汽車A柱-后視鏡區域的氣動特性研究有了一定進展和成果。A柱方面,文獻[5]中利用簡化模型,對幾種不同的A柱模型(橢圓、半角和直角模型)進行風洞實驗,分析前風窗和A柱的幾何形狀對汽車流場和氣動噪聲的影響。后視鏡方面,文獻[6]中采用簡化的后視鏡模型,將其固定在一個平板上,并進行風洞實驗,為研究鈍體氣動噪聲奠定了可靠的實驗基礎。文獻[7]和文獻[8]中對后視鏡尾部的流場進行研究,結果表明后視鏡尾部會有交替出現的渦團,這些渦團隨著氣流方向向后推進并逐漸減弱,在后方區域形成一個長長的湍流結構而產生噪聲。在仿生降噪研究領域,文獻[9]中將貓頭鷹的尾緣鋸齒結構應用在翼型上,對比直尾緣翼型和鋸齒尾緣翼型的流場和聲場發現,鋸齒尾緣可明顯降低翼型中低頻范圍內的噪聲。但目前國內外在汽車仿生氣動降噪方面的研究不多,尤其在A柱-后視鏡整個區域的仿生氣動降噪方面研究就更少。本文中采用仿生學原理,將仿生凸起和凹坑結構應用到A柱-后視鏡區域,通過數值仿真,考察了不同仿生模型對流場和聲場的影響,旨在研究整個A柱-后視鏡區域的仿生降噪。
1 氣動噪聲和仿生學理論
1.1 氣動噪聲理論
最早對汽車氣動噪聲進行理論研究是通過Lighthill方程[10]。它是專門研究運動的物體和固體相互作用而引發噪聲的方程,是研究流場和聲場的基礎和橋梁。它以四極子聲源為研究對象,適用范圍主要為高湍流為主的噪聲情況。數學表達式為

式(1)右邊是與流場相關的項,左邊則是與氣動噪聲相關的項。式(2)中,Tij為Lighthill張量,ui和uj為速度分量,(p-p0)為脈動壓力脈動值,(ρρ0)為流體密度的差值,δij為單位張量,c0為聲速。
Curle方程[10]用固體邊界上分布偶極子聲源來代替固體壁面的影響,成功解釋了類似湍流中靜止物體發聲的問題。該方程表達式為

式中:n為固體表面法向向量;r為從固體表面指向監測點的向量;S為固體表面。
FW-H方程[10]在Curle方程的基礎上進一步將研究范圍擴大,可以研究運動物體邊界的發聲問題,其表達方程式為

方程右邊第1項是Lighthill聲源項,表示流體運動引起的四極子聲源;第2項是脈動壓力聲源項,表面作用流體上的力引起的偶極子聲源;第3項是加速度導致的聲源項,表示容積移動效應的單極子聲源。
汽車在實際行駛過程中屬于低馬赫數狀態,偶極子聲源是主要的氣動聲源,所以在A柱-后視鏡區域氣動特性研究中主要考慮偶極子聲源,可以忽略其他聲源。
1.2 仿生學理論
仿生學就是人類借鑒大自然中生物的某種特殊功能,結合人類自身的實際需求,創造出新的產品或者設備等。目前仿生學研究內容和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功能仿生、結構仿生、形態仿生、材料仿生、構型仿生和耦合仿生。
生物表面所具有的凸起和凹坑結構,比如蜣螂頭部凸包和黃緣真龍虱背部凹坑,如圖1和圖2所示,能起到降低自身運動阻力和噪聲的作用,加上已有的一些成功案例,比如橄欖球的凸起和高爾夫球的凹坑都很好地起到了降低飛行阻力和噪聲的效果,因此本文中以蜣螂頭部凸包和黃緣真龍虱背部凹坑為依據,結合實際需要,在A柱-后視鏡區域采用仿生半球凸起和凹坑結構,以研究仿生結構對該區域氣動噪聲的影響。

圖1 蜣螂頭部凸包局部放大圖

圖2 黃緣真龍虱背部凹坑局部放大圖
2 建立模型和確定計算域
氣動噪聲的產生與其邊界層及其厚度有關[11],凸起凹坑結構對表面流場的影響是在整個邊界層內部[12],所以凹坑凸起結構的尺寸要小于邊界層的厚度。
利用CATIA軟件在某SUV的A柱、后視鏡和A柱-后視鏡區域建立了3種仿生凸起模型和3種仿生凹坑模型,命名為模型1~模型6,如圖3所示。由于本文中模擬邊界層流場厚度為5mm,建立仿生凸起和凹坑結構半徑為3mm的半球,相鄰凸起和凹坑的間距為15mm。

圖3 仿生模型
本文中建立了長寬高分別為10倍車長、5倍車高、11倍車寬的長方體模擬風洞模型。其中,仿真SUV模型前端距離模擬風洞氣流入口4倍車長,后端距離模擬風洞出口5倍車長,并且仿真SUV模型在左右方向相對于模擬風洞對稱,如圖4所示。
3 劃分網格和仿真計算

圖4 模擬風洞示意圖
采用三角形-三棱柱-四面體的網格劃分[13],這樣既可保證網格的質量,又可降低網格生成的難度,為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在A柱-后視鏡區域采用1~2mm的精細網格進行劃分,保證仿真結果的精確度和可靠性;緊接著采用網格由小到大的方法向其他區域進行過渡劃分,其中SUV底部網格最大達到25mm,計算域網格最大達到150mm。劃分體網格時,以三角形面網格為底拉伸出三棱柱單元組成邊界層區域。采用等差增長的邊界層生成方式,第一層單元的高度為 0.05mm,增幅為0.1mm,共10層,最終得到總高度為5mm的邊界層。圖5為邊界層的局部放大示意圖。

圖5 邊界層局部放大示意圖
邊界層的網格生成后,再對邊界層到計算域的剩余空間進行四面體網格劃分。其中,四面體是以三角形和三棱柱上下底面為依托生成的,整個模擬風洞的網格總數大約為1 000萬。
穩態計算選用SST k-ω湍流模型[14],此模型不僅能真實地模擬壁面附近的流體情況,而且還能反映出遠離壁面的流體形式。風洞模型的入口和出口分別設置為速度入口和壓力出口,湍流強度為2.5%。表1為邊界條件設置。

表1 邊界條件設置表
進行穩態仿真計算,考慮到該SUV和整個模擬風洞的網格數量較大,故將穩態計算步數設置為3 000,計算精度設置為0.000 1。瞬態計算采用大渦模擬(LES),以穩態計算的數據作為初始值,為獲得該SUV側窗11個監測點的聲壓級數據,在進行瞬態計算前引入FW-H聲學模型,并在監測模塊中創建待監測的11個前側窗監測點。瞬態計算階段共設置了5 000步,時間步長為0.000 1s,保證采樣時間不小于兩倍流場特征周期,又能最大限度地縮短計算時間,提高仿真效率和準確性。
4 仿真方法驗證
實驗在吉林大學風洞實驗室進行。實驗本體由特定尺寸的圓形管道組成,由動力裝置產生可調節的氣流并在管道中不斷循環流動,以達到模擬汽車實際行駛時氣流流動的效果。
在某SUV的原模型側窗表面選取11個壓力系數監測點,分別對它們進行壓力系數測量。圖6為該SUV側窗表面11個監測點的分布示意圖。圖7為PSI多點壓力掃描測量系統,用來進行壓力測量。圖8為監測點壓力系數實驗與仿真結果對比。由圖可見,數據的吻合度相當高,證明了穩態數值仿真方法的正確性。

圖6 某SUV側窗壓力系數實驗示意圖

圖7 PSI多點壓力掃描測量系統
對11個監測點進行聲壓級測量。圖9為某監測點實驗與仿真的1/3倍頻程聲壓級曲線。由圖可見,兩條曲線趨勢一致且誤差很小,證明該瞬態仿真方法是可行的。

圖8 監測點實驗與仿真結果壓力系數對比

圖9 某監測點實驗與仿真結果對比
5 計算結果與分析
5.1 流場分析
對6種仿生模型的流場進行計算,發現它們對于A柱-后視鏡區域的流場均起到了一定的改善作用。選擇仿生模型1(A柱仿生凸起模型),與原模型進行對比,分析其對A柱-后視鏡區域流場的改善效果與機理。
為分析仿生模型1不同位置流場的影響,建立了與xy面平行的幾個平面,如圖10所示。

圖10 與xy面平行的平面示意圖

圖11 原模型與xy面平行的面上流線圖

圖12 仿生模型1與xy面平行的面上流線圖
圖11 和圖12分別為原模型和仿生模型1在A柱-后視鏡區域上3組典型的xy平面流線圖。對比圖11與圖12可見:z=0.8m平面上,后視鏡后方存在明顯渦流,但與原模型相比,仿生模型1渦流明顯減小;z=0.9m平面上,后視鏡后方存在渦流主旋渦和二次渦,但與原模型相比,仿生模型1在旋渦中心上方區域少了一片流線形成的二次渦,說明該區域幾乎沒有流場流過;z=1.0m平面已在后視鏡上方,故不存在渦流。但與原模型相比,仿生模型1流線比較光順,對流線具有梳理作用。在A柱-
后視鏡區域,渦流會使氣流流動極不穩定,容易誘發強大的壓力脈動,從而形成較高的氣動噪聲[15]。通過對比分析,仿生模型1使渦流明顯減小,且對流線具有梳理作用,可預測側窗附近的氣動噪聲將會降低。
5.2 氣動噪聲分析
通過聲場計算得到原模型與6種仿生模型11個監測點的1/3倍頻程聲壓級數據,并繪制成相應的折線圖。選取A柱-后視鏡側窗表面具有代表性的 1,5,7,9 監測點進行對比,結果見圖 13~圖 16。
由圖13~圖16可見,除了監測點9上,模型5聲壓級有小幅度增加外,6種仿生模型在各監測點上都有不同幅度的降噪效果。在監測點1上,模型2和模型5都取得了良好的降噪效果,在中頻1 000~2 500Hz上,降噪效果更明顯,其中模型5最大降幅達到20dB。在監測點5上,6種模型都有降噪效果,其中模型6降噪效果更明顯,在高頻段2 500~4 000Hz平均降噪效果達到20dB。在監測點7上,模型3降噪效果不明顯,模型1、模型5和模型6在中高頻段1 000~4 000Hz具有良好的降噪效果。在監測點9上,模型1在中頻段1 000~2 500Hz取得良好的降噪效果,其他模型降噪效果不明顯,這是因為監測點9遠離A柱-后視鏡區域,仿生結構對于氣流的改善效果隨著距離的增大而逐漸削弱。綜上所述,仿生模型具有不同幅度降噪作用,在人耳敏感的中高頻域降噪效果更明顯。

圖13 監測點1聲壓級頻譜圖

圖14 監測點5聲壓級頻譜圖

圖15 監測點7聲壓級頻譜圖

圖16 監測點9聲壓級頻譜圖
為直觀和清楚地分析仿生模型對氣動噪聲的改善情況,將原模型和6種仿生模型監測點的總聲壓級進行對比,結果如圖17所示。

圖17 原模型和6種仿生模型11個監測點總聲壓級對比圖
由圖可見,6種仿生模型側窗表面11個監測點的總聲壓級變化規律與原模型基本一致。其中,模型1~模型3除了在監測點2和監測點3靠近后視鏡的上部區域總聲壓級與原模型基本接近外,在其他區域監測點的總聲壓級均小于原模型。模型1~模型3的最大降噪效果在不同的監測點上,最大降幅都在6dB左右,表明仿生凸起結構能夠在某一區域達到更大的降噪效果;模型4~模型6側窗上11個監測點的總聲壓級均小于原模型,整體降噪效果比較均勻,最大降幅為5dB,略小于前3種模型,表明仿生凹坑結構能產生更加均勻和廣泛的降噪效果。從模型3和模型6與其他模型對比可以看出,在A柱-后視鏡整個區域上采用仿生結構雖能取得一定的降噪效果,但其降噪幅度小于只在A柱或者后視鏡上采用仿生結構的模型,其原因是由于A柱上的仿生結構和后視鏡上的仿生結構對流經A柱-后視鏡區域氣流產生了一定的干擾。
6 結論
(1)汽車行駛時,A柱-后視鏡區域會產生渦流和二次渦,從而在側窗產生強烈的噪聲。在A柱-后視鏡區域建立仿生凸起和凹坑結構能降低渦流強度,并對流線具有梳理作用,從而降低氣動噪聲。
(2)仿生凸起和凹坑模型應用在A柱-后視鏡區域,使該區域氣動噪聲降低,尤其在中高頻域降噪效果更為明顯。由于人耳對中高頻噪聲反應敏感,該仿生結構的應用改善了汽車的乘坐舒適性。
(3)將仿生模型應用在整個A柱-后視鏡區域的降噪效果小于只在A柱或者后視鏡上采用仿生模型的降噪效果,說明仿生模型在這兩個區域的建立對流經該區域的氣流產生了干擾,這為以后該區域仿生降噪提供了指導。
(4)總聲壓級的對比表明,仿生凸起模型局部降噪效果明顯,仿生凹坑模型降噪效果均勻,說明兩種仿生結構降噪機理不同,這種不同的降噪機理是下一步研究的重點。
[1] LI Ye,KASAKI N,NOUZAWA T,et al.Evaluation of wind noise sources using experimental and computational methods[C].SAE Paper 2006-01-0343.
[2] BEIGMORADI S, JAHANI K, KESHAVARZ A, et al.Aerodynamic noise source identification for a coupe passenger car by numerical method focusing on the effect of the rear spoiler[C].SAE Paper 2013-01-1013.
[3] CHRISTIAN P,SIMON W,ELIZABETH L.Wind turbulence effects on aerodynamic noise with relevance to road vehicle interior noise[J].Journal of Wind Engineering and Industrial Aerodynamic, 1997, 69-71:423-435.
[4] JEONG-HYUN K,YONG O H.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wake structure around an external rear view mirror of a passenger car[J].Journal of Wind Engineering and Industrial Aerodynamics, 2011,99(12):1197-1206.
[5] ALAM F, WATKINS S, ZIMMER G.Effects of vehicle A-pillar shape on local mean and time-varying flow properties[C].SAE Paper 2001-01-1086.
[6] YOSHIHIRO K,IGOR M,YOSHIAKI N.Aeroacoustics simulations around automobile rear-view mirrors[J].Journal of Flui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8, 3(7):892-905.
[7] KHALIGHI B,CHEN K H,JOHNSON J P,et al.Computational and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the unsteady flow structures around automotive outside rear-view mirror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utomotive Technology, 2013, 14(1):143-150.
[8] JEONG-HYUN K,YONG O H.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wake structure around an external rear view mirror of a passenger car[J].Journal of Wind Engineering and Industrial Aerodynamics, 2011,99(12):1197-1206.
[9] 仝帆,喬渭陽,王良鋒,等.仿生學翼型尾緣鋸齒降噪理[J].航空學報,2015,25(9):2911-2922.
[10] 胡興軍.汽車空氣動力學[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14.
[11] 謝超,谷正氣,楊振東,等.不同RANS/LES混合模型的汽車氣動噪聲分析[J].汽車工程,2015,37(4):440-445,459.
[12] WILLIAMS J C.Alternate materials choices-some challenges to the increased use of Ti alloys[J].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A,1999,263:107-111.
[13] 陳鑫,汪碩,張武,等.某SUV外部后視鏡尾流區域氣動特性研究[J].汽車工程,2016,38(6):698-704.
[14] 胡朋,李永樂,廖海黎.基于SST k-ω湍流模型的平衡大氣邊界層模擬[J].空氣動力學學報,2012,30(6):737-743.
[15] 陳鑫,王懷玉,高長鳳,等.后視鏡罩邊緣結構對流場和氣動噪聲的影響[J].航空動力學報,2014(5):1099-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