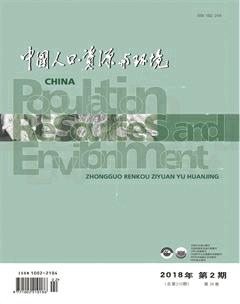碳強度約束對城鄉居民福利水平的影響:基于CGE模型的分析
董梅+徐璋勇+李存芳
摘要中國政府承諾到203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基于碳強度約束的行政型減排措施是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主要手段之一,分析碳強度約束對城鄉居民福利水平的影響,是碳減排機制設計的重要內容。本文構建31個部門的經濟-能源-碳排放動態CGE模型,模擬2012—2030年在碳強度約束和非化石能源比重提高的情景下,城鄉居民福利水平、消費結構以及CO2排放等指標相比基準情景的變化情況。結果表明:①城鄉居民收入無顯著變化,生活總消費略有下降。其中,農村居民生活總消費的降幅超過城鎮居民。②居民能源消費和CO2排放大幅下降,農村居民的降幅超過城鎮居民。③居民對煤炭、成品油和天然氣的消費大幅降低,電力消費顯著上升,部分資本密集型商品的消費小幅增加。其中,城鄉居民的煤炭消費降幅最大,農村居民對成品油和天然氣的消費降幅遠超城鎮居民,對電力、專用設備、通用設備、金屬制品等商品的消費漲幅超過城鎮居民。④碳強度約束使城鄉居民福利小幅下降。其中,農村居民的福利等價變化降幅超過城鎮居民。根據實證結果,得出以下結論:一是碳強度約束對居民生活減排起到積極作用;二是這一政策使城鄉居民福利小幅下降,但不會對居民生活產生強烈沖擊;三是對農村居民能源消費的負向影響超過城鎮居民。總體而言,政府在碳強度約束政策的基礎上,首先,應增加對農村居民的轉移支付,提高農村居民收入增幅,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其次,增加農村清潔能源的供給;再次,提高對農村居民使用清潔能源的補貼力度,從而降低應對氣候變化政策對農村居民的負向影響。
關鍵詞碳強度約束;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居民福利;動態CGE模型
中圖分類號X24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18)02-0094-12DOI:10.12062/cpre.20171017
氣候變化是當今各國面臨的全球性問題,應對氣候變化已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自2009年起,中國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基于單位國內生產總值CO2排放(以下簡稱碳強度)約束的減排目標。在國際上,中國政府承諾到2030年碳強度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以下簡稱非化石能源比重)達到20%左右。在國內,中長期發展規劃中提出到2020年,碳強度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比重達到15%左右。而現階段,中國經濟增長進入“新常態”,有效提升居民消費水平是實現經濟內生增長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此背景下,碳強度約束是否會對居民福利水平產生抑制?是否會影響居民消費水平和結構?城鎮和農村哪個居民群體受到的沖擊更大?通過明確這些問題,有利于中國提高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緩解碳減排措施對城鄉居民福利水平的不利影響。
1文獻綜述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碳減排約束的影響進行了較全面的分析。依據不同研究角度,可劃分為以下三個層次:
第一層,碳減排目標和政策措施的種類。在污染治理中,碳減排目標分為總量減排目標和強度減排目標。其中總量減排目標是指在政策期內對碳排放總量進行約束,有效實施該目標可以促使實際碳排放下降。
強度減排目標是在政策期內對單位經濟總量的碳排放進行約束,在為經濟增長留有余地的同時靈活調整碳排放量,當碳排放強度下降的速度超過經濟增長速度時,實際碳排放總量會減少。張友國[1]認為這兩種減排目標的差異體現在成本有效性、環境效益和政策可接受性三個方面。對于發展中國家,強度目標更穩定和公平,無論出現始料不及的經濟繁榮或蕭條都不會改變目標實現的難度;若采用總量減排目標,則經濟增長超過預期的國家需要付出額外的減排成本,相當于對這些國家(如中國和印度)實施懲罰或征稅。因此,發達國家主要承諾總量減排目標,而發展中國家主要承諾強度減排目標。基于以上兩種碳減排目標,Fischer[2]等人認為有兩類政策措施分別與之對應:第一類是市場型措施,包括碳排放權交易和碳稅政策,發達國家通常采取該類措施實施碳排放總量控制;第二類是行政型措施,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現階段主要采用該類措施控制碳強度。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碳減排政策正在積極的由行政型向市場型轉變,以期未來在碳排放權交易和碳稅等多種措施下,形成更長效的減排機制。然而,市場型措施的建立和有效運行需要經歷和調整很長一段時期。目前,中國尚未實施碳稅政策,全國性碳交易體系已啟動,但仍處于體系建設階段,“十三五”時期的碳強度目標仍通過行政措施分解到各省和各行業來實現。
第二層,模擬碳減排目標約束的政策影響。碳減排約束會傳導為對能源供給和消費的約束,從而影響整個經濟系統,眾多學者采用可計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模擬碳減排政策的影響。張友國[3]、周縣華[4]等人對碳強度約束和總量約束進行比較,認為碳強度約束更適合中國的碳排放控制。林伯強[5-7]、張友國[8]等人認為碳強度目標約束對煤炭消費和碳排放起到顯著抑制作用,但對宏觀經濟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其中,碳密集部門所受到的沖擊較大。Dai[9]、Yuan[10]、劉小敏[11]等人模擬得出2020年中國的碳強度目標是可以實現的。張曉娣[12]、范慶泉[13]等人更多關注社會福利的變化,認為碳強度約束使社會福利的損失較小。
另外,由于中國各省碳強度目標約束不同,Zhang[14]認為各省受到的經濟影響差異很大,Springmann[15]認為碳排放有從中國東部省份向西部省份轉移的現象。
第三層,影響碳減排效果的因素探討。在以上碳減排目標約束的模擬中,有三類因素顯著影響碳減排效果:第一類是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Dai[9]、何建坤[16]等人認為碳強度的下降速度取決于能源強度下降速度和能源排放因子下降速度的疊加,而非化石能源比重提高,可以有效降低電力對應的排放因子,使碳排放的降幅超過能源消費的降幅。第二類是技術進步。Wang[17]、Li[18]等人認為技術進步可以確保經濟增長的同時降低碳強度,這是實現碳強度目標的重要保證。第三類是碳稅政策的合理設置。張曉娣[12]、婁峰[19]等人認為在碳稅政策制定中,若政府保持稅收中性,將所得碳稅收入返還給企業和居民,可以增加社會福利水平,實現經濟增長和環境改善的“雙重紅利”。endprint
通過梳理以往文獻,發現碳強度約束對經濟影響的相關研究存在兩個特點;①研究重點關注碳稅和碳交易情景下是否能夠實現中國碳強度目標,并不關注行政型減排措施的影響。②研究重點關注碳減排政策對宏觀經濟層面的影響,而對居民福利層面關注很少,且與居民相關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模擬碳稅政策下“雙重紅利”是否實現,不探討行政型減排政策對居民消費的沖擊,也不區分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影響差異。中國通過行政型措施約束碳強度,會對城鄉居民的福利水平以及消費結構產生何種影響?以上文獻并未給出答案。基于此,本文在借鑒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擬將研究聚焦于行政型碳強度目標約束,即假設2012—2030年,中國在保持經濟適度增長的同時,通過行政型措施實施碳強度目標約束,并實現非化石能源比重的增長目標,利用動態CGE模型,評估城鄉居民的福利變動,以及與之相關的消費、碳排放等變化情況。
2碳強度約束對居民福利的影響機理
碳強度目標約束對居民消費產生影響,進而使居民福利發生變化,該過程可以從供給和消費需求兩個角度進行分析。需要說明的是,碳強度約束和碳排放總量約束是不同的,碳強度約束允許碳排放隨著經濟總量的變化而變化,從而降低經濟增長帶來的不確定性。就經濟增長而言,眾多學者和機構預測中國經濟在未來10—20年將持續穩定增長。因此,在預測未來經濟增長的基礎上可將碳強度約束轉化為碳排放總量約束(見圖1)。
從供給角度來看,碳強度目標對生產者的生產決策產生約束,調整能源供給,改變了居民的消費束,居民福利受到影響。其影響過程為:①行政型碳減排,是將碳強度目標分解到各省和各行業,使生產者進行生產決策時,將其作為生產約束,在成本最小化條件下制定生產方案;其中,能源生產者在碳強度約束下,預測未來市場的能源需求量,選擇成本最小的供應方式,使部分能源供給減少。②由于各能源的排放因子不同,碳強度約束對排放因子較大的能源(如煤炭)產生的約束也較強;而隨著非化石能源比重提高,清潔電力供應不斷增加。③在中國工業化階段,能源需求具有剛性特征,價格對能源需求的影響不大,因此能源供給的變化會助推部分能源價格上漲(主要是碳排放因子較大的化石能源),使能源投入較多的生產部門增加生產成本,影響這類部門的生產決策;因此,碳強度約束會對應理論上的最優能源結構,該能源結構下,生產部門對化石能源的消費減少,特別是對煤炭的依賴度下降,使碳排放得到有效控制。④由于包括能源商品在內的各種商品價格和供給量都會發生變化,改變了居民的消費束,使居民福利受到影響。
從消費需求角度來看,碳強度約束會從消費成本和消費習慣這兩個方面對居民消費產生影響。①就消費成本而言,一方面,由于碳強度約束使部分能源價格上升,增加了居民能源消費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能源投入較多的生產部門所提供商品的價格也會發生變化,因此,居民在效用最大化的條件下調整能源商品和其他商品的消費數量,形成最優的商品消費結構。②就消費習慣而言,為配合碳強度約束,政府會不斷推廣和普及低碳消費觀念,使居民的低碳意識逐漸增強,越來越多的居民主動調整能源消費結構,在生活中節約能源和更多選擇清潔能源。需要說明的是,在本文的模型構建中,暫未加入居民主動改變消費習慣的因素。
3模型構建與情景設計
3.1SAM表的編制及數據來源
本文以《2012年中國投入產出表》中的42部門基本流量表為基礎,結合其他相關統計年鑒數據,對部門適當合并,最終編制出2012年中國宏觀SAM表,以及細分31個部門的微觀SAM表。由于數據來源不一,數據統計口徑不一致,使SAM表行列加總不相等,因此本文采取交叉熵法(CE法),借助GAMS軟件對SAM表做平衡處理,以平衡后的SAM表作為CGE模型建立的基礎。由于數據限制,本研究不涉及中國港澳臺地區。
3.2動態CGE模型設計
本文以張欣[20]的CGE經濟模型為基礎,構建包含生產模塊、貿易模塊、國內經濟主體模塊、能源-碳排放模塊、動態機制模塊和宏觀閉合模塊在內的六大模塊。模型中的各種替代彈性系數在參考國內外同類文獻后做適當調整。因篇幅所限,以下給出居民主體模塊、能源-碳排放模塊、動態機制模塊的方程形式,其他模塊的方程均在張欣的模型基礎上做小幅改動,未詳細列出。
3.2.1生產模塊的設計
為了體現各能源之間的可替代性,生產模塊采用六層嵌套的結構(見圖1)。其中,中間投入部分僅包含26個非能源部門,采用列昂剔夫函數形成中間投入。形成國內總產出的其他各層嵌套均采用不變替代彈性(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CES)函數。
3.2.2貿易模塊的設計
貿易模塊體現了國內總產出與國外部門在商品貿易過程中的替代關系。其中,國內總產出以CET(Constant elasticity of transformation)轉換函數形式分配為內產內銷商品和出口商品,而內產內銷商品和進口商品在阿明頓(Armington)假設基礎上形成了國內銷售商品。
3.2.3國內經濟主體模塊的設計
國內經濟主體包括居民、企業和政府,該模塊包含三
個假定:①居民的效用函數為柯布-道格拉斯函數形式;
②政府收入由非稅收入、稅收和國外對政府的轉移支付共同構成。③投資總額和政府支出由外生給定。其中,居
民的收入和消費方程分別為:
YHh=WL·shifh-l·QLStot+WK·shifh-k·QKStot+transfh-ent+transfh-gov+transfh-row(1)
PQc·QHch=shrhch·mpch·(1-tih)·YHh(2)
式(1)中,h取HR和HU,分別對應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YHh是居民h的收入,WL和WK分別為勞動力價格和資本價格,shifh-l和shifh-k分別為居民h所占的勞動力份額和資本收入份額,QLStot和QKStot分別是勞動力和資本的總供給,transfh-ent、transfh-gov和transfh-row分別為企業、政府和國外部門對居民h的轉移支付。式(2)中,c=1,2,…31表示商品集的31種商品,與生產部門一一對應,但居民僅對包括能源商品在內的24種商品產生消費(見圖2)。PQc為商品價格,QHch和shrhch分別是居民h對商品c的消費量和消費份額,mpch和tih分別為居民h的邊際消費傾向和個人所得稅稅率。endprint
碳強度約束對居民福利水平的影響,可采用希克斯等價性變化(Hichs equivalent variation,EV)進行測算,公式如下:
UHbh=∏c(QHbch)shrhch(3)
UHsh=∏c(QHsch)shrhch(4)
∑cshrhch=1(5)
EV=e(PQbc,UHsh)-e(PQbc,UHbh)
=(UHsh-UHbh)·∏cPQbcshchchshchch(6)
式(3)~(6)中,UHbh和UHsh分別為政策實施前后居民h的效用,QHbch和QHsch分別為政策實施前后居民h對商品c的消費量,PQbc是政策實施前商品c的價格,EV是福利變動的等價性變化量。
3.2.4能源與碳排放模塊的設計
在以上CGE模型的構建基礎上,需要將能源、碳排放與經濟系統關聯起來。其中,碳排放的方程如下:
TGHGCO2=∑ce[λce·(∑aQINTce.a+∑hQHce.h)·PQce](7)
式(7)中,TGHCCO2為碳排放總量,ce=coal,crude,prod,gas,ele,分別表示煤炭、原油、成品油、天然氣和電力。a=1,2,…31表示生產集的31個部門,由于2012年SAM表沒有政府能源消費的數據,因此能源消費環節的碳排放僅對應居民主體。QINTce.a和QHce.h分別是a部門生產過程中能源ce的投入量和居民h對能源ce的消費量,PQce是能源ce的銷售價格,λce為能源ce的CO2排放系數(以下簡稱碳排放系數),由于SAM表內的數據是價值量(億元),因此碳排放系數也需轉換為價值型。本文采用《2006年IPCC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提供的“方法1”,估算出2012年各能源及總的碳排放量,再與SAM表中各能源最終需求總量相除,從而獲得價值型碳排放系數(見表1)。
3.2.5動態機制模塊和宏觀閉合模塊的設計
模型的動態機制主要考慮資本要素積累、勞動力增長和技術進步,并采用遞歸形式實現動態化。受此影響,CGE模型中所有的內生變量全都增加了時間維度。其中,資本要素積累的遞歸公式如下:
QKDta=QKDt-1a·(1-ηa)+It-1a(8)
Ita=It-1a·(1+gIa)(9)
QKSttot=∑aQKDta(10)公式(8)~(10)中,QKDta和QKDt-1a分別表示a部門t期和t-1期的資本需求量,t=2012,2013…2030,ηa是各部門資本折舊率,由于各部門生產特點不同,本文采用的各部門折舊率在3%~5%之間。Ita和It-1a分別是各部門t期和t-1期的新增投資,gIa為各部門新增投資增長率,結合產業發展政策,本文采用的各部門新增投資增長率在2%~23%之間。QKSttot是t期的資本總供給,在動態機制中將該指標設置為外生參數。
QLDta=QLDt-1a·(1+gLa)(11)
QLSttot=∑aQLDta(12)
公式(11)~(12)中,QLDta和QLDt-1a分別表示各部門t期和t-1期的勞動力需求量,gLa表示a部門的勞動力增長率,依據中國人口增速和產業發展預期,本文設煤炭和原油部門為0.1%,農業部門為0.25%,其他行業為0.33%,其余部門均為0.3%。QLSttot是t期的勞動力總供給,將該指標在動態機制中設置為外生參數。
αq.ta=αq.t-1a(1+gna)(13)
式(13)表示技術進步逐年增加,其中,αq.ta和αq.t-1a分別為t期和t-1期總產出的技術進步參數,gna為各部門技術進步的增長率,由于中國原油的可采儲量相對較低,本文設原油gna的為1%,其他行業設為2.5%,其余部門均設為2%。
在模型的宏觀閉合模塊設計中,首先,考慮各市場均衡,包括資本和勞動力要素市場均衡、商品市場均衡、國際收支平衡、儲蓄與投資平衡;其次,采用新古典主義宏觀閉合形式,即資本、勞動力和商品的價格內生決定,資本和勞動力數量外生給定,勞動力市場充分就業;最后,假設匯率固定。
將以上動態CGE模型作為基準情景,可衡量在沒有碳強度目標約束情景下,居民福利等相關指標的發展趨勢。
3.3碳強度目標約束的情景設計
為了模擬2012—2030年碳強度約束對城鄉居民福利的影響,本文將碳強度目標約束轉換為各年碳排放約束,并考慮非化石能源比重提高下電力碳排放系數的變化。相關目標約束推導步驟如下:
第一步,確定各年實際GDP。將2005—2015年作為歷史期,2016—2030年作為預測期。首先,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獲得歷史期的GDP,并換算為2005年價格的實際GDP。其次,計算預測期的實際GDP。由于中國經濟呈現出“新常態”,經濟增長由高速逐漸轉為中高速,在此背景下,以林伯強[6]對2020年中國經濟增長率的預測,以及張友國[8]對2030年中國經濟增長率的設定為參考,本文設2016—2020年實際GDP年均增速為6%,2021—2030年實際GDP年均增速為5%,以此可確定預測期的實際GDP(見表2)。
第二步,估算歷史期碳排放,確定2005年碳強度。首先,估算歷史期碳排放數值,即2005年的碳排放為57.456億t,2015年碳排放為94.839億t。其次,計算歷史期的碳強度。2005年的碳強度為3.067 t/104元,這一數值是中長期碳減排目標約束的參照基礎。雖然中國目前尚未公布碳排放數據,但本文估算的歷史期各年碳強度下降幅度與《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歷年報告中的相關指標基本一致,因此估算結果是可信的。再次,計算歷史期碳強度的累計增長率,得到2015年的碳強度比2005年累計下降33.863%。endprint
第三步,計算預測期2005年價格的碳強度。首先,確定預測期各年碳強度的累計增長率,設碳強度勻速下降,即碳強度累計增長率由2016年的-33.863%勻速下降至2020年的-40.001%,再勻速下降至2030年的-60.002%。其次,依據碳強度下降率,推算預測期碳強度數值,可得2030年的碳強度為1.227 t/104元。
第四步,推算預測期碳排放的約束值。依據預測期2005年價格碳強度和實際GDP,推算2016—2030年碳排放的約束值,可得碳排放由2016年的98.785億t逐漸上升至2030年的123.846億t。在保持經濟適度增長的基礎上,當各年碳排放不超過該約束值,則碳強度的降幅符合目標約束。本文將碳排放約束值作為目標情景的外生變量。
第五步,計算預測期電力的價值型碳排放系數。非化石能源主要用于電力生產(例如風電、水電、太陽能發電等),隨著非化石能源比重的提高,電力的碳排放系數逐漸下降,即生產等量電力而產生的碳排放逐漸減少。依據電力消費預測和碳排放約束,可得出電力的碳排放系數由2012年的8.631 t/104元,逐漸下降到2030年的4.151 t/104元,并將該系列數值作為參數加入動態CGE模型。
在基準情景的模型構建上,對公式(3)進行改動,并添加時間維度,形成目標情景公式:
aim_TGHGtCO2=∑ce[λtce′·(∑aQINTtce.a+∑hQHtce.h)·PQtce](14)
式(14)中,aim_TGHGtCO2是t期碳排放的約束值,即取表2中碳排放列2012—2030年的數值。λtce′是能源ce在t
期的碳排放系數,其中,煤炭、原煤、成品油和天然氣的碳排放系數不隨時間變化,而電力t期的碳排放系數取表2中的動態值。QINTtce.a、QHtce.h和PQtce分別是t期ce能源的生產投入數量、居民h的消費數量和銷售價格。將模型調整為目標約束情景,可分析碳強度約束下城鄉居民福利等相關指標變動情況。
4碳強度約束對城鄉居民福利水平的影響
動態CGE模型設置以居民效用最大化為目標函數,通過GAMS23.8.2軟件的PATHNLP求解器對模型系統進行計算,分別模擬2012—2030年基準情景和目標約束情景,可獲得居民福利等相關指標變動情況。
4.1碳強度約束對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影響
4.1.1基準情景下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及相關指標的預測
在基準情景下,2012—2030年居民的收入、生活總消費、能源消費和碳排放穩步增長(見表3)。居民收入增長是提升居民消費水平的前提,城鎮和農村居民的收入幾乎同步增長,年均增速分別為5.002%和5.006%,到2030年兩個居民群體的收入分別達到66.749和17.28×1012元,在預測期內,城鎮與農村居民的收入之比穩定在3.86,城鄉收入差距基本不變。就居民生活總消費而言,城鄉居民的消費都穩定增長,且消費增速略高于收入的增速。其中,農村居民的年均增速比城鎮居民高0.187%,這與城鄉居民的消費結構差異有關。王曉華[21]等人認為在“十二五”期間,農村居民仍以基本生活需求型消費為主,即食品、衣著、居住和交通通信的消費比重較高,而城鎮居民已具有發展與享受型消費的特點,即家庭電器設備、文教娛樂、醫療保健等消費比重較高,但隨著農村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其消費升級(即由基本生活需求型消費過渡到發展與享受型消費)的空間很大,因此基準情景預測的農村居民的消費增速略高于城鎮居民。
依據李艷梅[22]對居民能源消費和碳排放的劃分,本文僅研究直接能源消費和由其產生的碳排放,即居民用于炊事、取暖、電器及私家車等活動而直接消費能源商品并產生的碳排放。表3顯示居民的能源消費持續增加,且增速略高于生活總消費的增速,城鎮和農村居民的能源消費年均分別上漲5.276%和5.916%,到2030年,兩個居民群體的能源消費價值量將分別達到1.448和0.288×1012元。由居民生活能源消費帶來的碳排放年均增速分別為5.286%和5.883%,到2030年,城鎮和農村居民的碳排放將分別達到10.247和2.295億t,可以看出,若沒有碳強度約束,居民生活消費所產生的碳排放會快速增長,且農村居民的碳排放增速高于城鎮居民,居民生活消費引起的氣候變化壓力不容忽視。
4.1.2碳強度約束下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及相關指標的變動
在碳強度目標約束下,居民的收入、消費及碳排放等指標相對于基準情景的變動如表4所示。就居民收入而言,城鄉居民收入的變動很小,就生活總消費而言,居民消費在2021年前小幅下降,2022年后略有上升,這是由于生產部門,將碳強度目標作為生產約束,使部分能源(主要指化石能源)供給減少而推動價格上升,能源投入密集的其他生產部門也增加生產成本。因此,能源商品和其他商品的供給和價格都發生變化,影響到居民消費束,導致居民生活總消費略有下降。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居民以效用最大化為原則逐漸調整消費結構,在預測期后半段,居民消費小幅回升。但農村居民消費降幅略高于城鎮居民,這與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差異有關,城鎮居民對商品的選擇更多元,且對服務類商品的消費比重更高,因此所受影響略小一些。
碳強度約束對居民能源消費和碳排放的抑制作用較強,農村居民的能源消費和碳排放下降幅度超過城鎮居民。其中,到2030年,城鎮居民能源消費比基準情景下降了12.026%,碳排放也下降36.433%。與之相比,農村居民的能源消費和碳排放的下降幅度更大,多數年份的能源消費降幅都超過10%,到2030年,農村居民的能源消費下降了16.613%,碳排放下降了56.173%。以上特征的原因有:①碳排放的降幅超過能源消費的降幅,是由非化石能源比重上升帶來的疊加效應。②城鄉之間的能源消費和碳排放變動的差異,與城鄉能源供給、消費模式和城鄉收入差距密切相關。城鎮的能源供給和消費模式相對集中、多元和先進,由此產生了規模效益和集約效益,能源成本相對較低,另外,城鎮居民收入水平較高,能源價格上升對其能源消費的影響并不大。而對農村居民來說,一方面,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農戶使用電力的比重不斷增加,且電力的碳排放系數持續下降,因此農村居民碳排放endprint
的降幅超過城鎮居民,這符合Hosier[23]的“能源階梯”(Energy Ladder)理論,即農村能源結構演進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農戶主要依賴生物質能源;第二階段,隨著收入水平逐漸提高,農戶轉向使用煤和木炭等過度型能源;第三階段,隨著收入水平的進一步提高,農戶更多的使用電力。現階段中國農村居民已處于“能源階梯”的第三階段,電力消費增加對降低農村碳排放有積極作用。另一方面,農村的能源供給比較單一和分散,能源利用效率不高,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農村居民的能源效率提高空間很大,這使得農村居民的能源消費和碳排放下降的空間也更大。
4.2碳強度約束對城鄉居民消費結構的影響
在基準情景下,城鄉居民的消費結構有顯著差異(見圖2)。在基本生活需求消費方面,農村居民消費比重顯著高于城鎮居民;在發展與享受的消費方面,城鎮居民的消費比重顯著高于農村居民。以上差異與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差距密切相關。其中,城鄉居民消費比重最高的商品是其他行業(包括金融、房地產、居民服務、教育、衛生、文化、公共管理等與居民生活密切相關的子部門),城鎮和農村居民對該商品的消費比重分別占總消費的34.5%和28.7%。農村居民消費比重排第二和第三的分別是食品和煙草(22.2%)、農林牧漁產品和服務業(17.2%),其消費比重均顯著高于城鎮居民。與食品相關的這兩類商品的消費比重之和,相當于依據SAM表計算的恩格爾系數,即由于農村居民收入水平低于城鎮居民,其用于食品支出的比重高于城鎮居民。除以上三類商品外,城鄉居民對批發、零售業和住宿、餐飲業,紡織服裝鞋帽皮革羽絨及其制品的消費比重都超過5%。就能源消費而言,居民消費比重最高的是電力,均占城鄉居民消費的1.4%;其次,城鎮和農村居民對成品油的消費比重分別為1.3%和0.4%,對天然氣的消費比重分別為0.8%和0.2%;再次,城鎮和農村居民對煤炭消費的比重分別僅為0.04%和0.02%,可見居民生活消費中對煤炭的需求極少。
在碳強度約束下,城鄉居民的消費結構都發生變化,其變化如圖3所示。
就各商品消費的總體變動而言:①消費比重變化較大
的商品恰好對應基準情景下消費比重較低的商品,這是由于基準情景下消費比重較高的商品與居民生活密切相關,其效用的權重較大,即使這類商品的價格發生變動,其消費比重也保持穩定。與之相反,基準情景下消費比重較低的部門,其效用的權重較小,居民可以充分調整對這類商品的消費結構,以滿足效用最大化。②煤炭、成品油和天然氣消費大幅下降,而電力消費顯著上升。由供給角度分析可知,碳強度約束使部分能源價格上升,提高了居民獲得該類能源的消費成本,致使需求量大幅降低;而電力所受的影響較小,且對其他能源的替代性較強,因此居民增加對電力的消費以滿足能源需求。③資本密集型商品(專用設備、通用設備、金屬制品、非金屬礦物制品和儀器儀表等)在生產中的能源投入較小,所受碳強度約束的影響也較小,因此居民增加了對該類商品的需求。
就城鄉居民消費變動的差異而言:①城鎮與農村居民對煤炭、成品油和天然氣的消費變動差異較大。首先,碳強度約束對煤炭消費的抑制作用最強,城鎮和農村居民的煤炭消費分別下降了81.85%和79.53%,這是由于居民對煤炭的需求極少,且煤炭在生活中的炊事和取暖功能容易被其他能源替代,因此煤炭的需求價格彈性相對較高,其價格上漲會顯著抑制居民對煤炭的消費。其次,農村居民對成品油的消費降幅(71.01%)遠超城鎮居民(19.17%),這與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差異有關。《中國統計年鑒2016》顯示,2015年城鎮和農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3.12萬元和1.14萬元,在動態CGE模型的預測期,城鄉收入差距基本不變,因此,成品油的互補品——私家車對農村居民而言更接近奢侈品,該能源對農村居民的需求價格彈性遠高于城鎮居民,碳強度約束使農
村居民的成品油消費大幅下降。再次,農村居民對天然氣的消費降幅(39.9%)也遠高于城鎮居民(4.57%),這與農村的天然氣普及率過低有關。2015年城鎮居民天然氣消費達到358.38億m3,而農村均僅為1.43億m3,由于普及率很低,
使農村居民對天然氣的消費習慣還不穩定,天然氣價格上漲會使這些農村居民轉而使用電力或生物質能源,因此農村居民天然氣消費降幅超過城鎮居民。②農村居民電力消費漲幅(24.87%)高于城鎮居民(10.91%)。由于非化石能源比重增加,電力的碳排放系數持續下降,居民可增加電力消費來滿足能源需求;基于“能源階梯”的角度來看,農村居民收入增加,也使其電力消費大幅上升。③農村居民對部分資本密集型商品的消費增幅高于城鎮居民,這一差距與農村居民經營性收入比重較高有關。2015年的農村與城鎮居民人均經營性收入分別占各群體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9.43%和11.14%,在消費中,農村居民也更傾向于農業生產方面的消費支出,以期待增加經營性收入,農村居民對專用設備(包括食品和飼料專用設備、農林牧漁專用設備等)的消費上漲了28.28%,而城鎮居民對該部門的消費僅上漲了5.52%。此外,農村居民對通用設備、金屬制品(包括搪瓷制品、金屬制日用品等)、儀表儀器(包括鐘表與計時儀器、眼鏡等)和非金屬礦物制品(包括磚瓦、石材、玻璃制品、陶瓷制品等)的消費增幅也略高于城鎮居民。
4.3碳強度約束對城鄉居民福利水平的影響
受居民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的影響,居民福利水平也發生變化。根據式(6)得到的各年城鄉居民福利等價性變化EV如圖4所示,可以看出,在碳強度約束下,城鄉民福利均有小幅下降。由于動態CGE模型的擬合結果在居
不同年份產生振蕩,城鎮和農村EV的波動較大。為了厘清城鄉居民福利變動的規律,消除模擬數據震蕩的影響,分別對城鎮和農村EV進行線性擬合,可看出農村居民EV趨勢線的下降幅度超過城鎮居民,2012—2030年間,農村居民EV每年下降139.57個效用單位,對應效用水平每年下降0.121%,而城鎮居民EV每年下降87.343個效用單位,對應效用水平每年下降0.023%。可見碳強度約束對農村居民福利的負效應超過城鎮居民。雖然中國農村居民消費在相對較低的水平上不斷提升,其消費結構也發生變化,但由于農村居民收入水平仍然較低,導致消費結構不合理,消費升級相對遲緩,碳強度約束對農村居民的負向影響較大。endprint
5結論
本文基于2012年中國投入產出表,構建包含31個部門的經濟—能源—碳排放動態CGE模型,并將碳強度約束和非化石能源比重提高作為目標政策,模擬中國在2012—2030年保持經濟適度增長的同時,城鄉居民福利及相關指標受到的影響。研究的主要結論如下:
(1)碳強度約束對居民收入無顯著影響,居民生活總消費小幅下降,但不會對居民生活產生強烈沖擊。其中,農村居民生活總消費的降幅略高于城鎮居民。在中國經濟增長進入“新常態”的特征下,提高居民消費水平,特別是提升農村居民消費水平是保持經濟增長的重要著力點。因此,政府應當通過增加對農村居民轉移支付和精準扶貧等措施,使農村居民收入增幅高于城鎮居民,不斷縮小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努力降低碳強度約束對農村居民的負向影響。
(2)碳強度約束使居民能源消費和碳排放大幅下降,到2030年,城鄉居民的能源消費分別比基準情景下降了12.026%和16.613%,城鄉居民的碳排放分別下降了36.433%和56.173%。從供給角度而言,碳強度約束影響生產者的生產決策,使化石能源的價格上升;從消費需求而言,化石能源的價格上升抑制居民能源消費,促使電力消費增加。為保障居民能源需求,首先,政府應增加清潔能源供給,特別是繼續擴大農村地區沼氣、太陽能等清潔能源的推廣普及;其次,應該積極引導居民優化能源消費結構,重點引導農村居民對清潔能源的消費,增加對農村居民戶用沼氣建設、太陽能設備購置、節能家電產品購置的補貼,減少碳減排政策對農村居民的約束。
(3)碳強度約束使居民對部分資本密集商品的消費小幅增加。其中,農村居民對專用設備、通用設備、金屬制品等商品的消費漲幅超過城鎮居民,這是由于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速度相對緩慢,導致消費結構不合理,使農村居民對生產經營性消費的投入較多。從長遠來看,要不斷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在農民收入增幅不斷上升的前提下,引導其消費升級,降低基本生活消費和生產經營消費的比重。
(4)碳強度約束使城鄉居民福利水平略有下降。其中,農村居民福利的降幅超過城鎮居民。2012—2030年間,農村居民EV每年下降139.57個效用單位,對應的效用水平年均下降0.121%,而城鎮居民EV每年下降87.343個效用單位,對應的效用水平年均下降0.023%。但總體而言,碳強度約束下,城鄉居民的福利降幅較小,不
會對居民生活產生強烈的負向沖擊,但政府仍需完善農村集約和多元的能源供給,降低碳強度約束政策對農村居民福利的負向影響。
(編輯:于杰)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
張友國.總量還是強度:碳減排目標之爭[J].學術研究,2015(9):76-80,122.[ZHANG Youguo. Total carbon emission or carbon intensity: the controversy about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J]. Academic research, 2015(9): 76-80,122.]
[2]FISCHER C, SPRINGBORN M. Emissions targets and the real business cycle: intensity targets versus caps or taxe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 management, 2011, 62(3): 352-366.
[3]張友國.碳強度與總量約束的績效比較:基于CGE模型的分析[J].世界經濟,2013(7):138-160.[ZHANG Youguo. Comparison of carbon intensity constraint and total carbon emission constraint: an analysis based on CGE model[J]. 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2013(7): 138-160.]
[4]周縣華,范慶泉.碳強度減排目標的實現機制與行業減排路徑的優化設計[J].世界經濟,2016(7):168-192.[ZHOU Xianhua, FAN Qingquan. Mechanism of carbon intensity reduction and optimization design of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in industries[J]. 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2016(7): 168-192.]
[5]林伯強,姚昕,劉希穎.節能和碳排放約束下的中國能源結構戰略調整[J].中國社會科學,2010(1):58-71,222.[LIN Boqiang, YAO Xin, LIU Xiying. The strategic adjustment of Chinas energy use structure in the context of energysaving and carbon emissionreducing initiatives [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0(1): 58-71,222.]
[6]林伯強,孫傳旺.如何在保障中國經濟增長前提下完成碳減排目標[J].中國社會科學,2011(1):64-76,221.[LIN Boqiang, SUN Chuanwang. How can China achieve its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 while sustaining economic growth?[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1(1): 64-76,221.]endprint
[7]林伯強,李江龍.環境治理約束下的中國能源結構轉變——基于煤炭和二氧化碳峰值的分析[J].中國社會科學,2015(9):84-107,205.[LIN Boqiang, LI Jianglong.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nergy structure unde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onstraints: a peak value analysis of coal and carbon dioxide[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5(9): 84-107,205.]
[8]張友國,鄭玉歆.碳強度約束的宏觀效應和結構效應[J].中國工業經濟,2014(6):57-69.[ZHANG Youguo, ZHENG Yuxin. Macro effect and structural effect of carbon intensity constraint[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4(6): 57-69.]
[9]DAI H, MASUI T, MATSUOKA Y, et al. Assessment of Chinas climate commitment and nonfossil energy plan towards 2020 using hybrid AIM/CGE model[J]. Energy policy, 2011, 39(5): 2875-2887.
[10]YUAN J, HOU Y, XU M. Chinas 2020 carbon intensity target: consistency, implementation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J].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2012, 16 (7):4970-4981.
[11]劉小敏,付加鋒.基于CGE模型的2020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目標分析[J].資源科學,2011, 33(4):634-639.[LIU Xiaomin, FU Jiafeng. Analysis of the scenarios of Chinas carbon intensity reduction in 2020 based on the CGE model[J]. Resources science, 2011, 33(4): 634-639.]
[12]張曉娣,劉學悅.征收碳稅和發展可再生能源研究——基與OLGCGE模型的增長及福利效應分析[J].中國工業經濟,2015(3):18-30.[ZHANG Xiaodi, LIU Xueyue. Study on carbon taxation and developing renewable energy: growth and welfare effects analyses base on OLGCGE model[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5(3): 18-30.]
[13]范慶泉,周縣華,劉凈然.碳強度的雙重紅利:環境質量改善與經濟持續增長[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5, 25(6):62-71.[FAN Qingquan, ZHOU Xianhua, LIU Jingran. Double dividend of carbon intensity: environmental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5, 25(6): 62-71.]
[14]ZHANG D, RAUSCH S, KARPLUS V J, et al. Quantifying regional economic impacts of CO2 intensity targets in China[J]. Energy economics, 2013, 40(2): 687-701.
[15]SPRINGMANN M, ZHANG D, KARPLUS V J. Consumptionbased adjustment of emissionsintensity targets: an economic analysis for Chinas provinces [J]. Environmental & resource economics, 2015, 61(4): 615-640.
[16]何建坤.我國自主減排目標與低碳發展之路[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 25(6):122-129,157.[HE Jiankun. Chinas voluntary mitigation target and low carbon development pathway [J].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0, 25(6): 122-129, 157.]
[17]WANG K, WANG C, CHEN J.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 impact of different Chinese climate policy options based on a CGE model incorporating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 Energy policy, 2009, 37(8): 2930-2940.endprint
[18]LI A J,LI Z.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for energy intensity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in China[C]//Proceedings of the 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ergy,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ClausthalZellerfeld:Trans Tech Publications,2012:347-353,1093-1097.
[19]婁峰.碳稅征收對我國宏觀經濟及碳減排影響的模擬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4(10):84-96,109.[LOU Feng. Simulation study on the carbon tax impact on Chinas macro economy and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J]. The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 2014(10): 84-96,109.]
[20]張欣.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基本原理與編程[M].上海:格致出版社,2010: 204-216.[ZHANG Xin. The basic principle and programming of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M]. Shanghai: Gezhi Press, 2010: 204-216.]
[21]王小華,溫濤.城鄉居民消費行為及結構演化的差異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5(10):90-107.[WANG Xiaohua, WEN Tao. The evolution of differences about consumption behavior and consumption structur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J]. The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 2015(10): 90-107.]
[22]李艷梅,楊濤.城鄉家庭直接能源消費和CO2排放變化的分析與比較[J].資源科學,2013, 35(1):115-124.[LI Yanmei, YANG Tao. Comparison of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 direct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O2 emissions [J]. Resources science, 2013, 35(1): 115-124.]
[23]HOSIER R H. Energy ladder in developing nations [J]. Encyclopedia of energy, 2004(2): 423-435.
AbstractChinese government pledged to cut its CO2 emissions per unit of GDP by 60% to 65% from 2005 levels by 2030. Administrative emission reduction measures based on carbon intensity restriction are one of Chinas major means of coping with climate change.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carbon intensity restriction o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welfare is a significant content of th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mechanism design. This paper builds a dynamic CGE model of economyenergycarbon emission based on 31 sectors to simulate changes i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welfare and consumption structure as well as CO2 emission under the context of carbon intensity restriction and increased share of nonfossil energy from 2012 to 2030. Results are listed as follows: ① Theres no obvious change i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come and the general living consumption slightly drops. The decrease of rural residents living consumption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urban residents. ② Residents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O2 emission experience a dramatic fall with greater decrease on the part of rural residents. ③ A sharp decline is shown in the consumption of coal, refined oil and natural gas; an obvious increase can be witnessed in electric power consumption and the consumption of some capitalintensive sectors goes through a minor increase. The coal consump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decline in consumption of refined oil and natural gas of rural residents far exceeds that of urban residents. Besides, their increase in consumption of electric power, special purpose machinery, general purpose machinery and metal products surpasses that of urban residents. ④ Carbon intensity restriction brings about a slight drop i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welfare but its a small range. The fall in the Hicks equivalent variation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urban resident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reached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results: first, carbon intensity restriction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household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second, the policy makes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welfare decline but it wont have strong impact on residents life; third, rural residents receive greater adverse influences on energy consumption than urban residents do. Generally speaking,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perly increase the transfer payment for rural residents on the basis of carbon intensity restriction, and increase th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to narrow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Besid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more clean energy for the rural area, and increase subsidies for rural residents using clean energy, thus reducing negative influences of the climate change policy over rural residents.
Key wordscarbon intensity constraint;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structure; welfare of residents; dynamic CGE model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