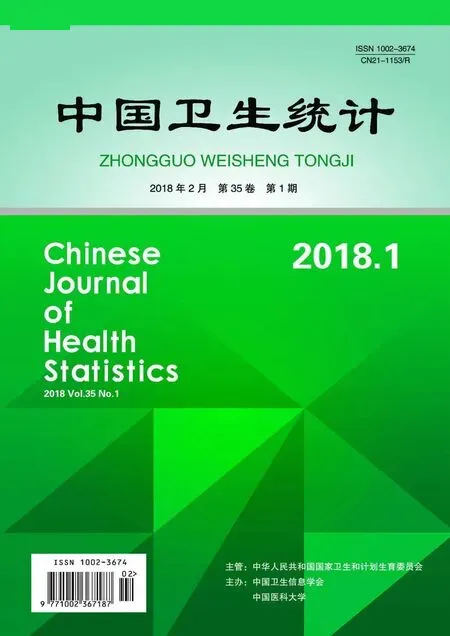應對方式在腦卒中照護者自我效能與照護能力間的調節和中介效應
石河子大學醫學院(832002) 楊 雪 王玉環 王文婷 馬文娟
腦卒中是一種常見的心腦血管疾病,具有高發病率、高死亡率和高致殘率的特點[1]。多數患者在醫院經過初期治療,病情穩定后回到家庭由家屬承擔康復及日常生活照料。居家照護者缺乏相關的知識、技能和信心,會導致照護者照護能力降低,從而使患者的康復期延長,再入院率增高[2]。因此,在腦卒中患者出院前,對其照護者進行照護能力的評估及干預可提高照護者照護質量。自我效能是個體對自己能否從事某種活動以及對此活動做到的完善程度的主觀評價。相關研究表明,自我效能與照護者照護能力呈正相關,照護者自我效能越高,其照護能力越高[3]。同時也有研究指出,照護能力與應對方式密切相關[4]。照護能力與自我效能、應對方式間如何作用機制尚不明確,也未見相關文獻報道。本研究假設①腦卒中照護者的應對方式在照護者自我效能與照護能力間起到調節效應;②腦卒中照護者的應對方式在照護者自我效能與照護能力間起到中介效應。本研究將對假設進行驗證,探索三者間的關系模型,為提高照護者照護能力干預提供理論指導。
對象與方法
1.對象
研究對象采用便利抽樣法,選取2016年10月-2017年5月在新疆石河子大學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及第三附屬醫院、重慶第三軍醫大學附屬醫院共三所三甲醫院的神經內、外科,出院前3天并符合納入標準的腦卒中患者的照護者進行現場調研。患者納入標準:①符合1995年全國第四屆腦血管病的診斷標準[5],經顱腦CT或MRI確診為腦卒中的患者;②ADL>16分,部分或全部依賴他人照料;照護者納入標準:①照護者是患者家屬或有親緣關系,提供不計報酬的照護服務;②患者的主要照護者;③照護者年齡≥18歲;④意識清楚,言語正常,有聽說能力,對調查知情同意并能夠配合調查。本次調查共收集問卷420份,有效問卷396份,有效問卷回收率94.3%。
2.工具
(1)日常生活活動能力量表(katz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scale,KatzADL)[6]
該量表由美國的Lawton氏和Brody制定,用于評定被試者的日常生活能力,評分為1~4分4個等級:完全可以做、有些困難、需要幫助和自己完全不能做,總分低于16分,為完全正常,大于16分有不同程度的功能下降,Cronbach’s α系數為0.88。
(2)家庭照護者照護能力量表(family caregiver task inventory,FCTI)[7]
該量表由李麗棠翻譯成中文,共25個條目,每個條目得分有三個等級,分別為不困難(0分),困難(1分),極困難(2分),得分越高,照護能力水平越低,Cronbach’s α系數為0.93。
(3)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8]
該量表中文版由張建新和 Schwarzer 研制,共有10 個條目,采用 Likert 4 點量表形式,得分越高,自我效能越高,Cronbach’s α系數為0.87。
(4)簡易應對方式問卷 (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9]
該量表由積極應對和消極應對兩個維度組成,包括20個條目。積極應對維度由條目1~12組成,消極應對維度由條目13~20組成。采用多級評分,“不采用”到“經常采用”依次計0~3分。積極應對方式Cronbach’s α系數為0.89,消極應對方式Cronbach’s α系數為0.78。
3.統計方法
使用SPSS 17.0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主要包括相關性分析和回歸性分析。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1.一般情況
396名腦卒中患者照護者中,男性96人,女性 300人,年齡28~86歲,平均年齡(54.93±11.17)歲。照護能力平均分(12.65±5.13),與國內常模得分(12.96±2.86)相比[7],無顯著性差異;腦卒中照護者自我效能平均分(25.33±6.48),標化后平均分(2.53±0.65)低于國內常模(2.86±0.67)[8];積極應對方式平均分(24.46±6.81),標化后得分(2.04±0.57)高于國內常模(1.78±0.52)分;消極應對方式平均分(12.61±4.25),標化后平均分(1.58±0.53)與國內常模(1.59±0.66)無顯著性差異[9]。
2.各變量的相關分析
Spearman相關分析顯示,照護者自我效能總分、照護能力總分和積極、消極應對方式總分的相關均達到顯著性水平,其相關系數見表1。

表1 應對方式與自我效能和照護能力的相關
*P<0.05,**P<0.01,***P<0.001,下同
3.調節效應檢驗
應用層次回歸分析對應對方式在自我效能與照護能力間的調節效應進行檢驗:將照護能力作為因變量,第一步納入控制變量,為減少多重共線性給結果帶來的偏差[10-11],第二步將自我效能、應對方式得分(積極應對方式、消極應對方式)進行中心化處理[12-13],并做照護能力對自我效能和應對方式(積極應對方式、消極應對方式)的回歸,第三步做照護能力對自我效能×應對方式(積極應對方式、消極應對方式)乘積項的回歸。若交互作用項回歸系數顯著,則調節效應存在。由表2可知,模型3中,自我效能×積極應對方式加入后方程的總解釋力仍然顯著,乘積項標準化回歸系數為0.128(P<0.01),表明積極應對方式在腦卒中照護者自我效能與照護能力間具有顯著的調節效應。
消極應對方式的調節效應見表3,模型6中,自我效能×消極應對方式加入后方程的總解釋力仍然顯著,乘積項標準化回歸系數為-0.216(P<0.001),表明消極應對方式在腦卒中照護者自我效能與照護能力間具有顯著的調節效應。假設1得到驗證。

表2 層次回歸分析結果(n=396)

表3 層次回歸分析結果(n=396)
4.中介效應檢驗
根據溫忠麟[14]等人總結的中介效應檢驗程序,建立三個回歸方程:(1)Y=cX+e1;(2)M=aX+e2;(3)Y=c’X+bM+e3,依次檢驗方程系數c,a,b和c’是否顯著,積極應對方式在自我效能與照護能力間的中介效應見表4。積極應對方式的中介效應顯著,回歸系數c’達到了顯著水平,且ab與c’同號,說明積極應對方式屬于部分中介效應。積極應對方式的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比例為a*b/c=62.54%,即自我效能對照護能力的效應中,有37.46%是直接效應,另有62.54%是通過中介變量積極應對方式起作用的。

表4 積極應對方式的中介效應檢驗(n=396)
*:Y為照護能力,X為自我效能,M為積極應對方式
消極應對方式在自我效能與照護能力間的中介效應見表5。結果表明消極應對方式的中介效應顯著,且消極應對方式的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比例為a×b/c=22.42%,即自我效能對照護能力的效應中,有77.58%是直接效應,另有22.42%是通過中介變量消極應對方式起作用的。假設2得到驗證。

表5 消極應對方式的中介效應檢驗(n=396)
*:Y為照護能力,X為自我效能,M為消極應對方式
討 論
應對方式的調節效應檢驗結果顯示,腦卒中照護者應對方式能夠影響其自我效能與照護能力關系的強弱,即照護者自我效能一定的情況下,采取積極應對方式組的照護者照護能力高于消極應對方式組的照護能力。采用積極應對方式一方面可以調動照護者內在的主觀能動性,使其更好地適應照護者角色;另一方面幫助照護者充分利用周圍資源,積極尋求他人的支持和幫助,從而促進自我效能對照護能力的影響;本研究中采用消極應對方式的照護者具有患者失能程度重、與被照護者關系是配偶、自評健康狀況差的特點。患者失能程度越重,需協助的日常活動越多,耗費的時間與精力越多,過于沉重的照護任務會讓照護者逃避甚至放棄照護行為。而照護者為配偶時,與其子女照護者相比年齡大,可獲得幫助的資源不如子女多[15],從而導致其在照護患者時缺乏主動性和進取性。身體狀況差的照護者更容易身心疲憊、力不從心,采用“依靠別人解決問題”等消極應對方式。
應對方式的中介效應結果顯示,腦卒中照護者應對方式在自我效能與照護能力間起到部分中介效應,即照護者自我效能一方面直接對照護能力起作用,另一方面通過影響應對方式起作用。可能的原因是自我效能高的照護者對照護行為信心也較高,不僅能積極進行照護行為的改善,面對困難時也更愿意采取多種途徑有效解決問題,其照護能力也高;而自我效能低的照護者,擔心自己不能勝任照護任務,可能出現照護態度“消極化”、照護行為“退縮化”,這些都會妨礙照護者在照護活動中的功能發揮,使得照護能力不佳。
綜上所述,應對方式的調節效應結果提示醫護人員對腦卒中照護者照護能力進行干預時,不應忽視個體應對方式這一指標的重要性。應對方式的中介效應結果提示醫護人員針對自我效能高的腦卒中照護者,應鼓勵、肯定其積極應對行為,使之固化,從而提高照護能力;針對自我效能低的照護者應制定容易實現的目標,循序漸進,提高其照護信心,從而產生積極應對行為,最終提高其照護能力。
[1] Stroke Association.About stroke.http://www.strokeassociation.org/STROKEORG/AboutStroke/Impact-of-Stroke-Stroke-statistics_UCM_310728_Article.jsp#.Wd7mfrEYxQ9/index.html
[2] 李香風,趙紅.老年人家庭照顧者及其照顧能力研究現狀.中華護理雜志,2009,44(11):1051-1053.
[3] Márk-Ribiczey N,Miklósi M,Szabó M.Maternal Self-Efficacy and Role Satisfaction: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2016,25(1):189-197.
[4] Lau BH,Cheng C.Gratitude and coping among familial caregivers of persons with dementia.Aging & Mental Health,2015(1):445-453.
[5] 王新德.各類腦血管疾病診斷要點.中華神經科雜志,1996(6):379-380.
[6] Lawton MP,Brody EM.Assessment of older people:self-maintaining and 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The Gerontologist,1969,9(3):179-186.
[7] Lee RL,Mok ES.Evaluation of th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a modified Chinese version of the Caregiver Task Inventory-refinement and psychometric testing of the Chinese Caregiver Task Inventory:a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2011,20(23-24):3452-3462.
[8] 王才康,胡中鋒,劉勇.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研究.應用心理學,2001,7(1):37-40.
[9] 解亞寧.簡易應對方式量表信度和效度的初步研究.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1998(2):114-115.
[10] 楊梅,肖靜,蔡輝.多元分析中的多重共線性及其處理方法.中國衛生統計,2012,29(4):620-624.
[11] 方杰,溫忠麟,梁東梅,等.基于多元回歸的調節效應分析.心理科學,2015(3):715-720.
[12] 溫忠麟,侯杰泰,張雷.調節效應與中介效應的比較和應用.心理學報,2005,37(2):268-274.
[13] Aiken LS,West SG.Multiple regression:testing and interpreting interactions.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1991.
[14] 溫忠麟,葉寶娟.中介效應分析:方法和模型發展.心理科學進展,2014,(22):731-745.
[15] Friedemann ML,Buckwalter KC.Family Caregiver Role and Burden Related to Gender and Family Relationships.Journal of Family Nursing,2014,20(3):313-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