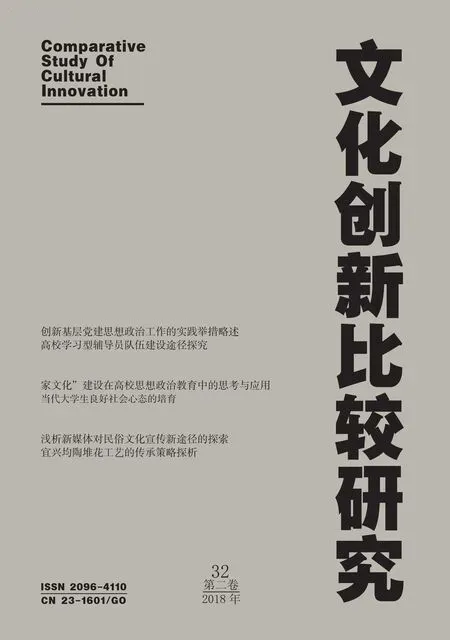《牡丹亭》舞臺(tái)劇在日本成功傳播的原因探析(上)
賈軍芹
(浙江麗水學(xué)院民族學(xué)院,浙江麗水 323000)
1 近現(xiàn)代《牡丹亭》在日本舞臺(tái)傳播過(guò)程
早在1646年,《牡丹亭》的文本已經(jīng)傳入日本,并在學(xué)界引起研讀熱潮。但是作為昆曲藝術(shù)上的一顆璀璨明珠,它的舞臺(tái)劇進(jìn)入日本要始于20世紀(jì)20年代。1919年5月24日,梅蘭芳在日本進(jìn)行訪問(wèn)演出,當(dāng)時(shí)在神戶俱樂(lè)部演出了《洪洋洞》《監(jiān)酒令》《春香鬧學(xué)》《游園驚夢(mèng)》等曲目,觀眾對(duì)《牡丹亭》等昆曲劇目的反響遠(yuǎn)遠(yuǎn)不及他的主要京劇代表作《貴妃醉酒》。到了當(dāng)代,將《牡丹亭》成功帶入日本的當(dāng)屬著名昆曲表演藝術(shù)家張繼青。她的影響力甚至超過(guò)了梅蘭芳。1986年5月2日,張繼青在國(guó)立劇場(chǎng)上演《牡丹亭》。劇評(píng)家戶坂康二在《每日新聞》和《演劇界》上大力贊美張繼青的表演,認(rèn)為她塑造的杜麗娘形象可與梅蘭芳 《貴妃醉酒》中塑造的楊貴妃相媲美。隨后,張繼青率領(lǐng)的昆劇訪日公演團(tuán)在東京演出13場(chǎng),在大阪、名古屋等地演出7場(chǎng),取得圓滿成功。曾經(jīng)有一位日本姑娘,在張繼青演出結(jié)束后,特地來(lái)到后臺(tái)感謝張繼青將女性的心態(tài)深刻細(xì)膩地完美表現(xiàn)出來(lái)。
2007年日本歌舞伎大師坂東玉三郎來(lái)到蘇州,聆聽(tīng)昆曲并與蘇州昆曲界人士接觸后,產(chǎn)生了合作《牡丹亭》的愿望。在雙方的努力下,2008年中日版《牡丹亭》開(kāi)始了積極籌備 。同年3月6日,由中國(guó)蘇州昆劇院和日本松竹電影公司聯(lián)合打造的《牡丹亭》,在日本京都南座劇院進(jìn)行首次公演,公演20場(chǎng),場(chǎng)場(chǎng)爆滿,每場(chǎng)演出結(jié)束后,全體觀眾都報(bào)以長(zhǎng)達(dá)25分鐘持續(xù)不斷的掌聲,以致平均每場(chǎng)演出的謝幕次數(shù)達(dá)到了4次。朝日新聞、讀賣新聞、《和樂(lè)》雜志、NHK電視臺(tái)、TBS電視臺(tái)等日本重要媒體都在顯著位置重點(diǎn)報(bào)道了中日版 《牡丹亭》的演出盛況。2009年,坂東玉三郎再次與蘇州昆劇院合作,在蘇州科技文化藝術(shù)中心上演了自己版本的《牡丹亭》,引來(lái)大量的日本粉絲。2015年9月,中國(guó)北方昆曲劇院在日本東京、橫濱以及長(zhǎng)野縣,為日本觀眾奉獻(xiàn)了3場(chǎng)昆曲經(jīng)典名作《牡丹亭》和《續(xù)琵琶》,幾乎每個(gè)會(huì)場(chǎng)都座無(wú)虛席,掌聲雷鳴。
比起美國(guó)華裔導(dǎo)演陳士爭(zhēng)和臺(tái)灣白先勇編導(dǎo)的《牡丹亭》,中日編排合作演出的《牡丹亭》,除了服裝樂(lè)器有所改進(jìn)之外,內(nèi)容上基本沿襲了國(guó)內(nèi)原有版本,變動(dòng)不大,之所以能引起日本觀眾的共鳴,其中的原因或許是因?yàn)橹腥諆蓢?guó)文化中本身就具有某些相通之處,日本觀眾在理解《牡丹亭》上,有著某些得天獨(dú)厚的有利條件。該文試從昆曲與日本能樂(lè)的相似性、《牡丹亭》的美學(xué)思想和日本人的“物哀”意識(shí)、兩方面來(lái)分析《牡丹亭》在日本演出成功的原因。
2 昆曲與能樂(lè)
昆曲是中國(guó)最古老的傳統(tǒng)戲曲劇種之一,有600余年歷史,素有“百戲之主”之美譽(yù)。能樂(lè)也有600多年歷史,它是一種以歌舞為中心的抒情劇,在日本戲劇中占有重要地位。昆曲靈動(dòng),能樂(lè)靜默,但兩者又有很多相似之處,這些相似之處應(yīng)該是日本觀眾能夠接受《牡丹亭》的知識(shí)基礎(chǔ)。首先,在表演形式上(1)兩者都是歌舞劇,重視樂(lè)歌在戲劇表現(xiàn)中的作用。昆曲是一出一套,能樂(lè)是一個(gè)腳本一小段;(2)兩者的主要人物上場(chǎng)方式也很相似,都要吟“上場(chǎng)詩(shī)”,要向觀眾作自我介紹,戲曲叫“自報(bào)家門”,能樂(lè)叫“通名”;(3)兩者在時(shí)空調(diào)度上都很自由,上天入地,或古或今,能通陰陽(yáng)兩界,演員在舞臺(tái)上走一圈,就可以表示場(chǎng)面的轉(zhuǎn)換,中國(guó)戲曲叫“走圓場(chǎng)”,能樂(lè)叫“道行”;(4)兩者的表演都是程式化、虛擬化的。能樂(lè)演員手持竹竿,頂上如果扎有一撮白毛,就表示他騎在馬上;如果扎的是黑毛,表示他趕的是牛。這和中國(guó)戲曲的做法極其相似[1]。
其次,在格律上,昆曲和能樂(lè)都非常講究節(jié)奏。比如開(kāi)場(chǎng)部分,昆曲的開(kāi)場(chǎng)大致使用“干吟”,歌唱部分利用曲牌體的長(zhǎng)短句,倚聲填詞,非常講究曲律;能樂(lè)的韻文由七五調(diào)構(gòu)成,即前半句七個(gè)音節(jié),后半句五個(gè)音節(jié),配角的上場(chǎng)詩(shī)規(guī)定是三句七五調(diào),第三句結(jié)尾必須少一個(gè)音節(jié),共三十五個(gè)音節(jié)。這些要求跟中國(guó)昆曲對(duì)曲詞的格律要求非常相似。
最后,演出時(shí)間長(zhǎng)短上差別不大。昆曲劇本雖然洋洋萬(wàn)言,冗長(zhǎng)不堪,但是實(shí)際演出時(shí)多是“折子戲”,或演一出,或連演兩出,像《牡丹亭》里的“驚夢(mèng)、尋夢(mèng)”“拾畫(huà)、叫畫(huà)”等,這樣一來(lái),昆曲在實(shí)際表演中一次演出的量,演出的時(shí)間長(zhǎng)度,其實(shí)和能樂(lè)差不多:一場(chǎng)或者兩場(chǎng)。能樂(lè)的一出戲也是十一二個(gè)樂(lè)歌段落。
3 《牡丹亭》的借景抒情與日本的“物哀”
《牡丹亭》是美的,它里面的人物美、景物美、曲調(diào)美。亭亭玉立的大家閨秀,玉樹(shù)臨風(fēng)的少年才俊,他們不經(jīng)意的一個(gè)顧盼、一個(gè)微翹的蘭花指都深藏著中國(guó)式的文化精神;一陣鑼鼓聲、一唱三嘆的唱詞都彰顯著濃郁的東方美學(xué),這種“只可意會(huì)不可言傳”的古典氣韻與日本的“物哀”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戲曲中彌漫的那種陰柔的優(yōu)雅、淡淡的哀愁讓日本觀眾沉迷其中,不能自已。
王國(guó)維曾說(shuō):“昔人論詩(shī),有景語(yǔ)情語(yǔ)之別,不知一切景語(yǔ)皆情語(yǔ)也。”《牡丹亭·驚夢(mèng)》中杜麗娘游后花園一段唱詞,即是通過(guò)大量情景描寫(xiě),委婉地表達(dá)了杜麗娘此時(shí)的傷感情懷。剛開(kāi)場(chǎng)的“裊晴絲吹來(lái)閑庭院,搖漾春如線”,就描述出人物生活的環(huán)境,庭院里春光如線,好像召喚著杜麗娘,她癡迷地望著窗外庭院,幻想著外面百花爭(zhēng)艷的世界。來(lái)到園里,看到早已開(kāi)遍的滿園春景,她悲嘆道“原來(lái)姹紫嫣紅開(kāi)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lè)事誰(shuí)家院!朝飛暮卷,云霞翠軒;雨絲風(fēng)片,煙波畫(huà)船——錦屏人忒看這韶光賤”!曲中用“云霞、翠軒、雨絲、煙波、畫(huà)船”等一系列自然意象來(lái)映襯杜麗娘孤獨(dú)與寂寞的心扉,特別是“錦屏人忒看的這韶光賤!”一語(yǔ)道破了杜麗娘內(nèi)心深處的隱秘,縱有“良辰美景”,但卻無(wú)“賞心樂(lè)事”,渲染出杜麗娘淡淡的哀愁。再美的園子只是看也無(wú)用,即使賞遍了十二亭臺(tái)也是白費(fèi),倒不如趁興回去,任滿懷心緒彌留在對(duì)美景的回憶中。她唱到“成對(duì)兒鶯燕啊。閑凝眄,生生燕語(yǔ)明如翦,嚦嚦鶯歌溜的圓。去罷。這園子委是觀之不足也。提他怎的!觀之不足由他繾,便賞遍了十二亭臺(tái)是枉然。到不如興盡回家閑過(guò)遣”,在懷春的少女面前,那些鶯鶯燕燕成對(duì)兒的在“歌”、在“語(yǔ)”,真讓人遐想連篇。清脆的鶯歌燕語(yǔ),圓潤(rùn)地簡(jiǎn)直像在空氣里滾,那是自由的歌啊!轉(zhuǎn)念想到自己不覺(jué)黯然,無(wú)趣悲涼。這種感物傷懷的情調(diào),和日本文化中的“物哀”美學(xué)極其相似。
“物哀”一詞最初是日本國(guó)學(xué)家本居宣長(zhǎng)提出的,他把日本文學(xué)的本質(zhì)歸納為“在于物哀”。“物哀”,指的是人的各種情感,看到一景一物,觸景生情,感物傷懷,或喜悅、或憤怒、或恐懼、或悲傷、或低回婉轉(zhuǎn)、或思戀憧憬[2]。日本文學(xué)作品中感物傷懷的“物哀”名句很多,像紫式部的“月華幽光羨登臨,紅塵悲愴我自知”“心跡未予外人閱,花枝一束故人香”。矢代幸雄曾用一句話概述過(guò)日本文化的精神,即“雪月花時(shí)最懷友”,就是用“雪、月、花”這簡(jiǎn)單的三個(gè)自然風(fēng)物,概括了山川草木、宇宙萬(wàn)物、大自然的一切以及人間所有美好的感情[3]。“物哀”已經(jīng)是日本人所根深蒂固的一種精神狀態(tài),它與其他日式美學(xué)意識(shí)雜糅后,也頻頻現(xiàn)身于當(dāng)下。被“物哀”傳統(tǒng)浸潤(rùn)的日本觀眾,聽(tīng)著悠長(zhǎng)纏綿的昆曲,賞著蜿蜒的水袖、婀娜的身段,雖對(duì)“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情節(jié)不能說(shuō)深懂其精髓,但也會(huì)沉醉其意境中,不覺(jué)點(diǎn)頭自嘆。
可以說(shuō),昆曲和能劇形式上的相似讓日本人在觀看《牡丹亭》時(shí)產(chǎn)生的熟悉感是他們接受《牡丹亭》的外在原因,劇中感物傷懷的唱詞、委婉細(xì)膩的表演讓具有“物哀”傳統(tǒng)的日本人感到精神上的共鳴。這也許是《牡丹亭》在日本受歡迎的兩個(gè)原因吧。
- 文化創(chuàng)新比較研究的其它文章
- 醫(yī)學(xué)生生活事件、社會(huì)支持與學(xué)習(xí)成績(jī)的關(guān)系
- 學(xué)生對(duì)《護(hù)理人際溝通與禮儀》教學(xué)模式主觀評(píng)價(jià)結(jié)果的分析
- 應(yīng)用型高校人才培養(yǎng)質(zhì)量保障體系的構(gòu)建
——基于PDCA理念的探索 - 應(yīng)用型本科院校專業(yè)評(píng)估探索與實(shí)踐
- 我國(guó)近年學(xué)前教育研究熱點(diǎn)與趨勢(shì)研究
——基于2015—2017年文獻(xiàn)的Citespace可視化分析 - 基于學(xué)分制體系下“技能型”人才培養(yǎng)路徑研究
——以廣東松山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市場(chǎng)營(yíng)銷專業(yè)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