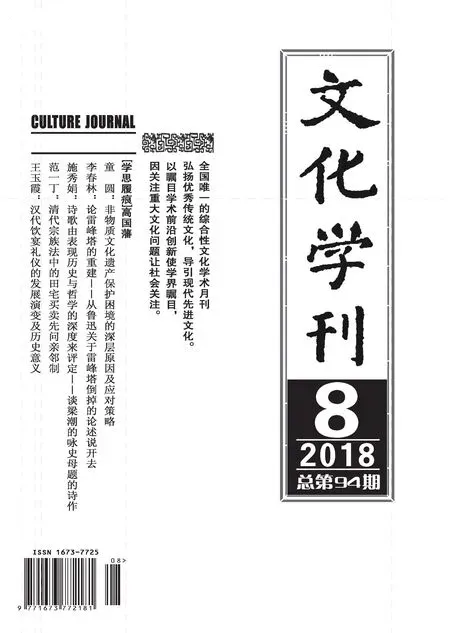新政治人類學維度下的“人性”光輝
鄭 要
(上海師范大學,上海 200234)
一、新政治人類學維度下的“人性”解讀
傳統政治人類學者董建輝曾說:“進入20世紀七八十年代后,政治人類學不得不證實一個現實,即人類學所研究的幾乎所有社會,都已融入世界大體系之中,而且大都集中在所謂的‘發展中國家’”。到目前為止,傳統政治人類學存在兩個問題:(1)界定及接受度仍比較模糊;(2)處于探索階段,學界對其內涵及邊界并未形成統一認識。這是傳統政治人類學發展中所面臨的主要困境。因此,新政治人類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應運而生,它由中國學者陶慶提出,在與政治學、公共管理學、政策科學、人類學等不同學科的交集融合的背景之下誕生,強調不同學科間的融合與交叉,強調跨學科的理論建構。“政治學科學化”與“人類學政治化”致力于研究權力關系在人類社會中的產生和運作,力求在處理政治權威與社會權力之間產生良性互動的內在關系,這就要求“管理學人性化”操作,反對僵硬的機械管理,轉為對人的價值的重視。“民族志寫文化”“政策學田野化”,同樣離開管理學知識也無法獨善其身。因此,這樣的一門具有多元理論基礎的新型學科以一種全新的視野進入了當下的政治和文化系統。
新政治人類學以政治哲學作為基礎,兼顧文化人類學之要義,以政治科學為改良方向,突破傳統政治人類學的以文化為基礎的探討,結合現實的社會管理,最終以公共管理為目標。而面對繁雜的管理學體系、汗牛充棟的管理學著作,要求人們在對新政治人類學“五化”統一的研究中,貫穿在政治學、人類學的發展過程中,各種理論都離不開一個核心概念——“人”,對人進行管理、管理中的人以及人如何去管理的研究等,是管理學始終探討且持續被學者多層面、多維度進行討論的問題。
(一)何為人性?
從古希臘開始,西方就有諸如畢達哥拉斯等哲學家曾涉及人性管理這一理論,更有米利都學派對其要點做出界定,更不用說亞里士多德、柏拉圖等各位先哲,從未停止過對“人”的價值的探討。文藝復興以來,“從普羅泰格拉‘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到笛卡爾發出‘我思故我在’的呼喊,而現代人性主義提出‘有意識的人是主體,主體是出于主體地位的東西,主體性即是主動性、創造性、能動性’。”這些思想和理論均是人類對現代社會中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與反思,他們都實然驗證了西方哲學對于人性的探討。而追溯到古代中國,孔子、孟子等的探討及立論也是從對“人性”的探討出發延伸而來,一直到當代社會,“人”如何實現其自身價值、回歸人的本質及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也始終是學者探究的主要話題之一。鮑桑葵曾在《關于國家的哲學理論》一書中提到:“國家的最終目的和個人的最終目的是一樣的,是實現最美好的生活”,而“最美好的生活,就是使我們的存在擴展到最大限度”。[1]誠然,在政治哲學研究范疇中,時代背景的不同使政治哲學家們關注的焦點也有顯著不同,但可以看出,人與國家的關系是西方政治哲學家始終未曾放棄的探討話題,始終貫穿西方政治學發展的邏輯要點是對“人”的價值的探討。
而綿延至今悠悠數載,歷經無數先哲與仁人志士,人們對于人性的認知至今也未能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何為人性?即人的一切屬性、人擁有的動物不曾有的屬性和人的最根本屬性,這三個關鍵詞有助于人們理解人性的涵蓋范疇,也能進一步理清人性與人的本質之間的關系,而本文對人性層面的探討不對人性與人的本質進行進一步區分,將其統一在對人性的探討之中。由此可以作出以下簡單界定:人性即在環境與人相關聯中表現出來的人的全部屬性。而管理學人性化即是遵循人的本質進行管理,根據人性的規律性特點進行統籌。
在系統科學的視角下考察人性,會趨向于將其理解為多要素在結構層次的復雜系統中復合而成的集合要素。在時間與空間的雙維度中去思考,這就使得人性系統展現出整體與穩定的特點。本文在相對穩定性特征與發展變化性特征的特點下進行綜合分析,用發展比較的眼光來研究人性的特征有助于接下來理解管理學人性化提出的必要性和意義。
人性的相對穩定性,從時間上來說,即指不同時期對人性的討論所圍繞的總層次、總要素無明顯差異;從空間上講,就是指不同國家地區所遵循的人性的觀念并無本質差異。在傳統的文化人類學中,人類學家認為人是一種文化聚合而成的動物體。卡西爾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將人類的人性與符號學相關聯;黑格爾強調理性,認為應在理性的基礎下討論人的本質。即使探討的內容不同,但其關于人性的討論具有歷史同一性。在當今現實社會中,無論隸屬哪個民族、集團、政黨,不管是個人,還是在集體中,關于人性的討論也不存在差異,都會思考其個體的諸多心理因素,即保持相對的穩定性。
(二)管理人性化中的“人性”解讀
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及組織環境的迅速變化,管理學想要改變被動適應狀況,就必須進行全面徹底地變革與創新,用人性化的管理風格推動政府行政管理,堅持公眾參與的視角,推動“人性化”管理的創新與發展。從另一個層面來說,即用政治科學引領政治哲學的發展,將傳統的政治人類學引入政策、公共管理層面。而在管理學人性化中,不能回避的問題是“人性假設”這一概念,“人性”是一極為宏大的概念,通過人性假設可更為細致地分析各管理理論中涉及的具體體現人性的觀點,以解析“人性”兩字到底如何滲透管理層面,又是如何被表達。
“整個歷史也無非是人類本性的不斷改變而己。”《馬恩全集》中的這句話深刻體現了人性的發展與變化的強烈特性。人性的復雜不僅體現在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的矛盾中,更是理性與感性的交鋒、屬靈還是屬欲的糾葛。但也正是這些交鋒的存在,使得人性演變有其內在的脈絡和動力,也逐漸建構其人類發展的內在情感邏輯。人性在每個人身上的體現不同,且在每個歷史時期所關注的焦點也有所不同,人是歷史發展的前提,又是歷史發展的產物,因此,站在發展的觀點上來看待人性,更有助于人們理解當代社會問題。我國東漢早期,王充在《論衡》的《本性篇》中列舉過人性的分類:“性善,性惡,性有善有惡,性無善惡,性善情惡,性情相應,察己順性。”直至今日,人們對人性的討論仍集中在以下幾方面:(1)人性本善或本惡;(2)何為人的本質或人的價值;(3)人性與情感的關系;(4)人性與集體(社會)的關系。也只有正確把握人性的基本屬性與時代內涵,才能正確認識以上四方面問題的根本內涵。
因此,要理解新政治人類學“五化”統一中的管理學人性化的重要地位和意義,首要的一點就是厘清“人性”這一綿延至今的詞匯,新政治人類學立足于人的實踐活動,強調人的價值回歸,反對僵化機械式管理,提倡多元性與多樣性,因此以下筆者將通過“人性”在管理學中的發展脈絡來闡述新政治人類學“五化”下的管理學人性化的根本要義所在。
二、新政治人類學的“人性”思想路徑
(一)滅人欲下的早期管理思想萌芽
在人性受到多方壓制的早期社會中,各方面條件極為不成熟,此時的管理只是滿足自給自足需要的單一實踐方法。隨著社會的發展,形成組織,這時管理思想便應運而生,如西方早期的埃及金字塔、漢謨拉比法典閃耀光輝、中央集權帝國從古羅馬帝國崛起。18世紀中期,《國富論》的誕生給管理思想學界帶來了不可忽視的曙光,其中,分工理論的產生是管理學的重要根基,推動了早期管理思想逐步成型。而在古中國,也有《孫子兵法》《戰國策》等著作,為管理統治提供了豐富的思想養料。
(二)人性部分解放——古典管理理論的閃光
19世紀前期,管理學中有極為重要的三大管理思想:泰勒的科學管理、法約爾的一般管理、韋伯的行政組織理論,這標志著古典管理理論的產生。這一時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日漸凸顯,勞資雙方矛盾日趨突出,因此,古典主義理論主要圍繞緩解勞資雙方矛盾、提高效率而產生,這也注定其著眼點不會過多考慮“人性”這一作用。到20世紀初,部分管理學家意識到單純考慮效率因素并不能完全促進生產,強制性原則有時反而對提高效率產生阻礙性效果,因此,一眾學者開始關注勞動者在生產活動與組織管理中的作用,行為科學產生,此時人際關系學派也初露頭角,這標志著“人”這一要素在此時被提上管理學的日程上來。麥格雷戈用“X/Y理論”引入管理學對人的討論,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對人在管理活動中的作用和重要性進行了論述。這些轉變促使管理人員對人的管理一改以往的全盤壓制手段,同時給予了被管理者更多空間,大大解放了人的個性與自我。
(三)新時代人性的完全解放
隨著人類學、社會學、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與應用,西方現代管理理論形成,并經歷了蓬勃發展的階段。1961年12月,美國管理學家哈羅德·孔茨使用“管理論理論叢林”來描述西方現代管理理論的主要特征,“管理理論已經發展成為盤根錯節、枝繁葉茂的‘熱帶叢林’”。[2]這顯示出西方現代管理理論多方向、多維度綜合體系的形成。
佩龍和葛爾力曾指出:“以市場為導向的公共行政或管理主義與民主政治價值之間存在著沖突,即自主性與民主責任、個人遠見與公民參與、秘密性與公開性、風險承擔與公共財貨的監護之間的沖突,的確是有道理的。”雖然現代管理理論“叢林”中極為重視人的作用,但如何應對管理與民主政治價值之間的沖突、如何解決個人與集體利益的矛盾仍是需要考慮的重大課題。在實際管理活動中,更為關注“人”這一要素,不僅要從管理方式開展,更重要的是理解人的本質與特點;不僅要追求效率,還要切身關注人的發展,實現人的最大潛能。但“人”這一要素始終是作為管理中的客體而存在,這一問題將是組織發展的最大障礙。特別是進入21世紀后,科技的迅猛發展、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更是削弱了人的作用,甚至“管理者”這一重要管理要素在某些領域也讓渡給了“機器”,這大大解放了人本身,卻也對在管理中如何加強人的地位這一問題提出了更為嚴峻的考驗。
三、回歸“人的價值”的現實意義
自古以來,有關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惡的理論研究致力于從不同的角度將人性歸納為一種特定的假設框架之內,卻忽視了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性。人的心靈世界是一個廣闊的領地,因此,人永遠不能被定義為某一種特定的類型,但人作為社會動物,其本質需求則是管理學可以把握的方向。管理學需要人性化,是指管理的過程需要考慮到不同人之間的差異,而并非限制和約束人的才能的發揮。
“韋伯認為理性是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征,并將理性區分為價值理性(也稱實質理性、規范理性、目的理性)與形式理性(也稱技術理性、工具理性、科學理性)。”[3]理性思維逐漸進入人們視野,并成為人們看待日常生活的最主要思維方式。而在現代性理性精神分化下,價值理性和技術理性的分界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轉向,“價值理性與形式理性的區分標志著作為現代性主題的理性精神的分化,它使現代性的研究在諸多哲學社會科學中出現了兩大傳統的分化,分別形成了科學主義(scientism)與人文主義(humanism)兩大思潮。”[4]在科學主義的指引下,人們趨向把人看作大自然的一部分,認為自然規律的觀察與探索可以用來研究控制人的行為。在科學主義中最具特性的方法是實證主義方法,人們通過實際調查與研究得出結論,而不再單純依賴于思維的延展性。而價值理性下的人文主義思潮,將人自身重新引入思索的本位中來,將人本身作為對自我、他者和自然探索的出發點,然后從中提取人自身的價值。
新政治人類學對于管理的理解是帶有人文關懷的,“管理是關于人的,管理理論與實踐的發展與對人性的認識緊密相連。”[5]人經歷了一系列的轉變,麥格雷戈將其界定為從“經紀人”最終過渡到“復雜人”的轉變。人有思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需求,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將人自我實現的需求作為人的終極需求,無論是政治,還是管理,都要以人為本,為人自我價值的實現提供幫助。
回到新政治人類學中,回歸“人的價值”,尋求美好生活的愿景是最終目標,而傳統管理模式下的考核和績效管理使人們如同機器一樣運轉,人們的所作所為是為了最后那一排排冰冷毫無意義的數字,這種現象的產生使得管理學人性化的提出尤為迫切。新政治人類學將人類學引向政策,引向管理,又不單單局限于管理,并將管理發展到人性化層面,使人類學與當代實際相結合,賦予人類學以新的生命,具有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回歸“人的價值”,即回歸到傳統政治哲學中的重視人的多元性,以“人”為主體視角,重視差異與多樣性,這并非阻礙政治的發展,而是推動了政黨、政治的個性化發展,摒棄了傳統的僵化的管理模式,加強民主的滿意度和參與感。人的全面發展、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人類社會的終點。因此,新政治學人類學中的管理學人性化給人們指明了一條道路,即如何通向美好愿景,如何有效提供實現其所必須具備的條件。
四、余論
對于新政治人類學而言,其是對傳統政治人類學的突破,更在時間和空間范圍上擺脫了傳統政治人類學的框架,新政治人類學所強調的多元學科融合,使得這門新型學科肩負起了更重大的使命和挑戰。新政治人類學站在文化整體的高度上俯視世間百態,研究人類早期社會的政治形態、權力結構,甚至可以追溯至人類社會誕生之前的黑猩猩時代,并且由于新政治人類學的學科交叉性質,致使研究者需要從研究的方法、本質、研究對象、研究的過程等方面對這門學科進行多方位闡釋,才能使讀者對這門學科的內涵形成一個系統的、多重維度的認識。
新政治人類學關注的是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面,是以整體性的視角從空間和時間上突破了傳統人類學的學科,其所肩負的使命是整個人類的社會價值。新政治人類學所關注的人性及實踐的真理性,是其區別于傳統政治人類學的重要突破。因此,在研究解讀新政治人類學中,不應將文化局限于人類習俗、地區特色等方面,這是對新政治人類學內涵界定的誤解,而應將文化放置于宏觀的整體之中,既包含地區的民族特色,同時也引入了權力、關系等因素的探討,這樣的內涵決定了新政治人類學視域的完整性,也解決了傳統政治人類學研究領域的狹窄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