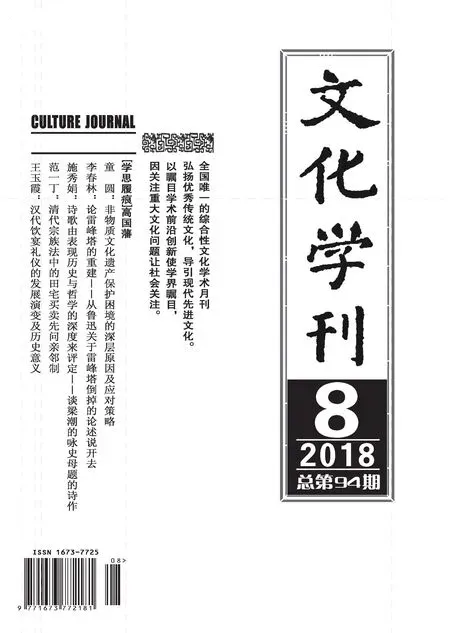魏晉玄學對儒學的繼承及發展
于冠琳
(西南大學含弘學院,重慶 400715)
在中國傳統文化長河中,儒家思想因其對中國古代小農經濟本質的充分適應而成為最有利于統治階級推行統治教化的思想[1],其傳承和發展在中國哲學源流中從未間斷過,在各個時代一脈相承,但都有其針對時代特點的不同表達形式,而在魏晉時期,儒學這一主流正統思想便在一個分支上特化成了糅合道家特質的玄學,并成為這一時期的代表思想。
一、玄學產生的時代背景和魏晉玄學家的儒學背景
從漢武帝始,儒學經董仲舒為適應統治階級需要而改造后成為了官方哲學,并在教化、選官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了充分實踐,牢固確立了其在思想領域的統治地位。但儒學在被統治階級使用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僵化,特別表現在名教思想上的僵化。魏晉時期戰亂頻繁,統治者不斷在名教的外衣下做出有悖倫常的事,傳統儒家的價值觀被當成了統治者掩飾自己對利益追求的工具。[2]
這時出現的玄學家大多具有世家大族的家庭背景,在小農經濟中屬于地主階級,為適應魏晉的門閥士族政治,在幼年時期必須接受良好的儒家思想教育,因此他們本身具備極高的儒學素養。幼年時期的熏陶和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玄學家的價值取向依然具有儒學內核,即作為士人(知識分子)對社會的強烈責任感和使命感。
結合以上兩個方面不難發現,玄學家內心所向往的積極入世為官、建立王道社會的理想與當時混亂的社會現狀和統治者的黑暗政治相去甚遠,但他們的價值觀又迫使他們對現實政治給予關注。為了在亂世中堅定自己的價值取向,不與統治者同流合污,同時又要保全自己和家族,他們出于對自身心靈寧靜和家族地位的考慮,委曲求全,選擇了用道家思想來豐富傳統儒家學說,因此,玄學的出現從根本上是為了維護儒家的正統地位。
二、玄學思想中對儒家的繼承和發展
(一)注經改革:進行理論創新
正始時期,玄學家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提出“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肯定了“意”的第一性,他認為可以將“言”與“意”適當地分開來看,從而使注經這一基于原有經典進行解釋的活動不僅僅局限于用儒家觀點來解讀儒家傳統思想,而給了注經者能夠與時俱進、充分發揮的可能性。“言意之辯”直接改革了注經方法,針對當時儒家經學僵化衰落的局面首先做出了理論上的革新,從中能看出王弼希望在亂世中用拓寬注經的方法來重振儒學,一改之前“注不破經”的學術瓶頸。
王弼的“言意之辯”為他自己和之后的玄學家利用道家觀點解釋儒家經典著作提供了支持與依據,使儒家學說在更廣泛的程度上接受、吸收、糅合其他學說的觀點,完善了整個儒學理論體系,從而維護了其思想主流地位。因此,玄學也成為了中國哲學史上承上啟下的環節,為其之后與佛學的融合及理學的興起奠定了基礎。
(二)玄學中的名教與自然
在道家與儒家的辯論中,道家常常用“自然”的觀點來反駁儒家的名教與禮法,但傳統觀點中對立的兩方在玄學中走向融合。傳統道家認為,“自然”代表宇宙原生,而“名教”是人為創造的,想要達到“任自然”和“逍遙”的境界就必須像掙脫束縛人的枷鎖一樣拋棄名教,回歸宇宙中的大道。但當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天賦皇權”學說深入人心后,玄學家們開始思考:宇宙原生的“天”產生了皇權,而“天”和人類社會連接的途徑也是皇權,而皇權正是名教、禮法的核心,因此正始時期的玄學家,如何晏、王弼等都認為名教生于自然。[3]而且老子所講的“萬物皆生于無”也是此想法的一個支撐,“萬物”中也包含禮法和名教。既然名教出于自然,那么“任其自然”就意味著對禮法和名教的認可,即遵從禮法、名教就可達到“無為而治”,從而用這種方法來使人們更好地遵從儒家禮法。
元康時期的向秀、郭象將名教與自然的關系又提升了一個層次,他們認為名教即自然,自然與名教完全合一。他們將儒家學說中的“天命”與“自然”相結合,認為“命之所有者,非為也,皆自然耳”,用自然的觀點來解釋“天命”,來表達自然和人類社會的秩序緊密結合的觀點,從而使自然社會化,即“儒化”。
(三)儒學在玄學家家族中的傳承
考察竹林七賢中阮籍、嵇康的家族以及他們的生平經歷不難發現,他們出身于官宦世家,因為在魏晉時期門閥士族政治背景下,只有世家大族的后代才有入朝為官和為人所知的機會。《晉書》中記載阮籍“本有濟世志”,少年時曾極為崇尚儒家經典,但當阮籍、嵇康等人轉而進入道學領域時,依舊在家族中遵守禮法,并且以儒家道德教育自己的子侄。如嵇康寫《家戒》來教育兒子嵇紹為人處世和做官的道理,他希望兒子有遠大抱負,能成為忠義道德的君子,而不希望他效仿自己;阮籍也曾在家中嚴厲地禁止子侄們效仿自己“放達灑脫”。[4]《世說新語》載“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從他們對于子侄的教育上就能看出竹林時期玄學家從內心還是非常信奉正統儒學的。實際上,竹林時期的玄學家反對的并不是儒學,而是當時黑暗社會政治中統治者的“假仁義道德”,他們的放浪形骸實質上是一種自保和保全家族的手段。唐長孺先生也曾指出:“嵇阮在原則上并不反對儒家所規定的倫理秩序,只是反對虛偽的名教,他們理想中真率自然之人格仍然與封建道德不可分割。”
三、玄學家的社會定位與自我認知
儒學在魏晉時期的傳承主要是通過政治的影響力。不管是在朝為官,還是拒絕做官,玄學家們都無法擺脫門閥士族政治的束縛:他們心中堅持的傳統儒家思想要求他們一定要重視家族,是故在烏煙瘴氣的亂世中保全家族成為了他們最大的行為約束。究其本質,是玄學家自身的貴族、地主階級屬性使得他們無法直接表達對傳統儒學的堅定信仰和對現實政治的批判。那些拒絕為統治者服務的玄學家努力在高壓政治下尋求自身和家族的保全,通過結合道家的學說來使自己獲得超越感和解放感;而那些在朝中做官的,依舊是為了在門閥士族政治下鞏固自己的家族地位,他們用道學觀點解釋儒家經典,一方面繼承和革新了傳統儒學,希望通過自己的學說來重塑符合傳統儒家價值觀的社會倫常秩序,另一方面也對統治者產生了“君主無為,門閥專政”的影響。
綜上所述,儒學在玄風勁吹的魏晉時期并沒有從哲學史中消失,玄學反而可以被看作傳統儒學的翻新和重鑄,在社會動蕩的魏晉時期保持了一份獨特的風骨。玄學家的階級屬性使他們形成了尊儒內核,而政治的壓迫又使儒學的傳承具有了玄學這樣一種獨特的表現形式,儒學得以曲折地向前發展,不斷豐富中華傳統文化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