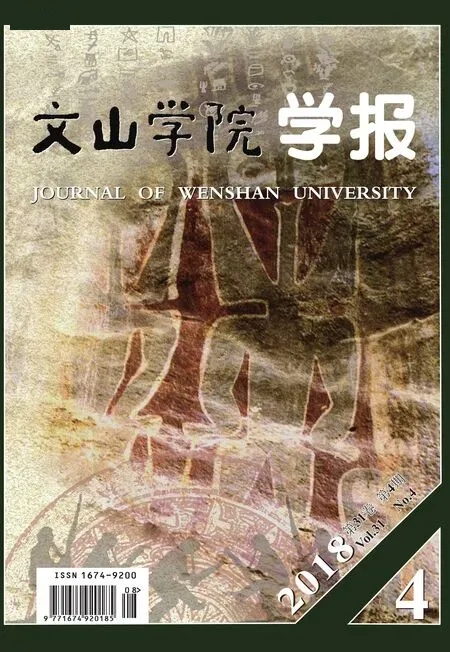壯族民間李應珍傳說敘事特征研究
(云南民族大學 民族文化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清光緒年間,法國以武力侵吞越南南部之后,又接連不斷向越南北部和我國廣西、云南侵犯;光緒十年(1884年),清政府被迫對法宣戰。在這場戰爭中,壯族人民為了保衛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積極參與了這次反侵略戰爭。在反抗法國侵略的斗爭中,涌現出了許許多多的能征善戰、智勇雙全的民族英雄;他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一直在壯族民間經久不息地流傳著。這些關于抗法戰爭的傳說,既塑造了抗法將領的英勇善戰的英雄形象,又反映了壯族人民反抗外國侵略的決心。
以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硯山縣為中心的壯族民間流傳著關于民族英雄李應珍在中法戰爭中的傳說。李應珍傳說講述了光緒年間中法戰爭爆發,皇帝被四處的告急奏折攪得驚恐萬狀,白發老人托夢給皇帝爺“十八子李去應征”;皇帝爺醒后立即下旨命云南各級官員找到“十八子李”應征,費盡波折,最后在開化府江那里城腳村找到了這個“十八子李去應征”。
李應珍早有奔赴疆場殺敵衛國之志,他帶著城腳村的81名青壯年告別眾鄉親到開化府待命。之后又以管帶之任帶領眾將士奔赴邊關,得白發老人相助,聯絡到了義軍,在良美之戰中奮力激戰,首戰告捷。又得白發老人相助,取得治“瘴氣”的泉水,使得戰士戰斗力倍增;李應珍率領各營管帶及戰士在極其激烈的響山之役中奮勇殺敵,大敗法軍。李應珍斬殺法軍駐響山據點的頭目德布林,同時也在戰斗中負了槍傷。響山之役,威震南疆。
李應珍傳說曾被收集整理為書面文學,由李安宏講述、那家佐搜集整理,見于《云南省文山州少數民族口傳非物質文化遺產叢書·壯族卷》及《文山壯族民間故事集》等。關于李應珍傳說的研究,在一些期刊論文中提及過有李應珍這么一個人,如龍永行的《評中法戰爭中的岑毓英》等。那家佐《李應珍的傳說》將李應珍的傳說由口頭文學轉化為書面文學,將李應珍傳說傳播到更遠的地方,可以說是為李應珍的傳說的傳承和傳播作了較大的貢獻。目前,關于李應珍傳說的研究還比較薄弱,在學界未見研究成果公布。
民間口頭文學是產生于民間,流傳于民間,發揚于民間的“原生態”文學樣式。李應珍傳說作為壯族民間口頭文學的一種表現形式,與壯族勞動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李應珍傳說以中法戰爭為主線,圍繞李應珍在戰爭中能征善戰、智勇雙全這一主題,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了民族英雄的英雄氣慨,也生動活潑地塑造了壯族人民心目中的英雄模型。李應珍傳說是壯族勞動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它由歷史事件嬗變為民間記憶,與壯族人民英雄信仰密切相關。李應珍傳說敘事特征主要表現在歷史事件的藝術化、離奇曲折的故事情節、濃烈的民族色彩、獨特的英雄形象、一定的傳播范圍等方面。
一、藝術化的歷史
李應珍(1847-1890年),字連山,又名李云道,壯族,今硯山縣江那鎮城腳村人,1884年中法戰爭時期任滇軍懷遠副前營管帶,率“開化民族軍”赴越南參戰。李應珍在宣光之戰、臨洮之戰、廣威之戰等戰役中勇擋前敵,屢著戰功。1886年封“廣鎮左營都司”。于1890年,率領民族軍駐守麻栗坡邊境,因槍傷復發逝于任上,后轉葬于硯山縣城腳村三臺坡山上,被誥封為昭勇將軍、授副將銜。關于李應珍的生平,在一些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到類似的記載,比如《硯山縣志》《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志》等。
可以肯定的是李應珍確有其人。“李應珍墓”位于硯山縣江那鎮城腳村三臺坡西北墓地,墓呈馬蹄形封土堆狀,周邊鑲砌著條石,坐西朝東,半圓開浮雕,墓碑通高1.75米,總寬0.52米,碑文楷書陰刻,保護完整。1985年,李應珍墓被硯山縣人民政府公布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華林先生在其《西南少數民族石刻歷史檔案的現狀與保護研究》一文中將李應珍墓碑列為西南少數民族較為典型的漢文墓碑之一,可見李應珍墓碑具有一定的研究及參考價值[1]。
在《中法戰爭調查資料實錄》中,云南省文山縣城張伯良(70歲)述:“覃修綱是壯族,和岑毓英有親戚關系,同是廣西西林縣那勞村人。他跟岑毓英“平回”有功,升到開廣鎮臺,帶有萬把人。他任開廣鎮臺時,是在同治年間,到了中法戰爭,他帶兵到越南去打洋鬼子,立了功,光緒皇賜給他一付黃袍馬褂。覃修綱有兩個得力的部將:一個是陸春,硯山人,后來當到協臺,署提督;一個是李云珍,做到什么官位不大清楚,李云珍打仗很勇敢,人稱他為鐵膽將軍。”[2]此處的李云珍應為李應珍,“云”與“應”諧音,當是記錄時堅持保持原貌、突出真實性的原則而按照述者發音記錄下來。根據云南省文山縣城張伯良所述可見,李應珍在民間是為人所熟知的。
由《岑毓英集》也可見關于李應珍的記載。光緒十一年(1885年)二月十五日,岑毓英在“收復緬旺清水清山兩縣暨臨洮大勝折”中云:“二月初一、二等日連接李應珍、張文擎等報:在象山旁村遇敵接戰,斬獲教匪數十,旋即竄匿象山,堅守不出……初七日,敵遽以大股并出臨洮,包抄山圍社、由義庯李應珍、韋云青各地營。覃修綱聞信,立督飭精銳三千人馳援。時李應珍營正被敵圍,槍炮如雨,李應珍嚴督兵勇堅伏不動,敵漸逼漸近,始扯動釘子火地雷,轟斃甚多。敵卻久復進,又俟其逼近,槍炮齊擊,敵復卻,更蕃疊戰。自初七日至初八日,援兵四集。李應珍率眾出營奮擊,斃敵百余名,身受槍傷,仍力前陣斬五畫一名。”[3]326臨洮之戰,李應珍雖受了槍傷,還斬殺了法軍五畫軍官,立下了顯赫戰功。據稱,法軍袖口鑲白邊表示軍銜,畫多則更大一級,比如七畫將軍總司令李威利、五畫校官副司令韋醫。可見,李應珍所斬殺的五畫是一名職位較高的法軍指揮官。
然而,在李應珍傳說中,李應珍一心想要拔除響山據點,無奈瘴氣使得部隊戰斗力大打折扣,后幸得白發老翁相助而戰勝了瘴氣,便積極御戰。響山據點法軍頭目德布林,調集部隊向李應珍部進攻,李應珍部用釘子火地雷擊退了敵軍的第一次進攻;敵軍用越南邊民作掩護展開了第二次進攻,經過李應珍部浴血奮戰,再次擊退敵軍。敵軍援兵不斷,李應珍部以死相抗,在戰斗最危急的時刻,越南邊民組織的義軍增援了李應珍,經過鏖戰,大敗法軍。戰斗最后,李應珍為救義軍首領受了槍傷,但砍下了法軍頭目德布林的腦袋。
光緒十一年(1885年)四月十八日,岑毓英在“除復邊外情形行抵文盤州布置防衛折”中云:“奏為陳復邊外情形,暨微臣行抵文盤州布置各營暫防要隘,以資鎮衛,恭折仰祈圣鑒事……仍令游擊張世榮、粱松生、粱禹福、李應珍、韋云青等分屯,以資鎮衛越民,免生他釁,即以慎固我防”;又在“保覃修綱片”中提到:“迨法圍臨洮李應珍、韋云青各營,該員親往援應,血戰日夜,因獲大捷”。[3]364由此可見,李應珍戰后任游擊無疑,且在臨洮之戰中得到了總兵覃修綱的援應,并大敗法軍。
然而,在民間傳說中,在戰事最為關鍵的時刻,前來援應李應珍的不是覃修綱,而是越南邊民組織的義軍,且義軍首領不知其名。李應珍在阻擊響山據點的法軍第二次進攻時,全力保護越南邊民,而后越南邊民出于感恩之情,組織起義軍在千鈞一發之時前來援助。這就體現出了當時軍民團結一致抗法,也折射了壯族民間傳說塑造“箭垛式”人物的藝術性。
虛構與實錄使得民間傳說與載于史冊的歷史區別開來,李應珍傳說既不完全是真實人物的傳記,又不是單純的歷史事件的記錄。“李應珍墓”及相關文獻記載相互印證了李應珍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人,李應珍參與了中法戰爭也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事件。流傳于壯族民間的李應珍傳說依據壯族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和一定的歷史記憶虛構了近于完美的英雄人物形象,凝聚了壯族人民的集體智慧。由李應珍參與中法戰爭這一歷史事件嬗變為散文體的民間口頭文學,在壯族民間口耳相傳,既有歷史性,又有幻想性,李應珍傳說可謂是壯族人民藝術化了的歷史敘事。
二、離奇曲折的故事情節
故事情節的傳奇性是民間傳說的一個顯著而重要的特征,人們往往就是以是否有傳奇意味為根據來區別歷史傳說和真實的歷史記錄。“所謂傳奇性,指故事情節在總體上符合現實生活邏輯的基礎上,又通過夸張、巧合、超現實的想象等虛構手段,構造奇情異事,使故事曲折離奇,高峰迭起,引人入勝。”[4]毫無疑問,傳奇的情節因素是傳說所必須具備的,沒有了傳奇性,也就喪失了它的獨特性。
“白發老翁”貫穿于李應珍傳說始終,表現出了李應珍傳說神秘莫測的神奇性。白發老翁從托夢給皇帝、再到指引李應珍聯絡義軍、再到派遣童男童女引導李應珍取得治療瘴氣的清泉、最后用治療瘴氣的清泉復活了李應珍,無不是在用神力幫助李應珍排除萬難,直接或間接地推動了故事情節的發展。
白發老翁的多次出現,使得李應珍傳說洋溢著一種神奇氣息。白發老翁賦予了英雄神秘力量,反映了壯族人民心目中的英雄能與神通話的特性,也凸顯了壯族人民對民族英雄的認同感和浪漫主義情懷。另外,李應珍傳說還通過夸張的修飾手法來表現出傳說的神奇性。比如李應珍從名不見經傳的一介平民一下子躍升為皇帝欽點的將軍、用來治療瘴氣的一罐清泉怎么也倒不完、李應珍死后被白發老翁復活并繼續抗擊外寇等等都極具離奇色彩。凡此種種,在我們平常生活中是不可能出現的。
壯族勞動人民將李應珍這一英雄人物的壯舉和人民群眾緊緊地結合在一起,突出描繪英雄人物李應珍,同時也表現群眾在斗爭中的重要作用。傳說中的離奇色彩,使得傳說更為生動活潑。除了離奇,李應珍傳說的故事情節單純卻富于變化,很有戲劇性,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給人們呈現了異彩紛呈的傳奇場景。
傳說主要用對比的表現手法來反映故事情節發展的曲折。各級官員慌忙尋找皇帝欽點的將軍和李應珍沉著應對相對比,表現了李應珍“應征”的一波三折;敵軍優勢變為劣勢與李應珍部由劣勢變為優勢相對比,反映了李應珍部戰斗的此起彼伏;浩然正氣的李應珍和貪生怕死的官僚對比,表達了英雄人物反對議和的艱難困苦。這些富于變化的故事情節,無不妙趣橫生,使得傳說具備了扣人心弦的極大魅力。
三、濃烈的民族色彩
壯族音韻溢彩的歌圩文化是壯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一個歷史悠久、酷愛唱歌的民族,壯族的民間歌謠,其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都十分豐富多彩,而且有著自己的民族特色”[5]。在壯族民間,劉三姐的傳說故事家喻戶曉,人們“以歌傳情”“以歌言志”,甚至“依歌擇偶”。對歌成為壯族民間一種特殊的表達和交流方式。
李應珍傳說中,李應珍便以歌言志:“邊關急,邊關急,七尺男兒理應征;說應征,就應征,壯家漢子要應征”。李應珍通過唱山歌來表達自己的一腔熱血,同時也是李應珍作為壯族人民的一員,是壯族人民酷愛唱歌、“以歌傳情”“以歌言志”的民族性格的一個縮影。李應珍用山歌委婉地表達了他早有抗敵壯志,表現出壯族人民謙和又剛柔相濟的民族性格。
李應珍應征后,他帶著81個城腳村的青壯年一起奔赴疆場,在響山之戰的激烈戰斗中,特意描繪了81壯士緊跟在李應珍身后的典型的戰斗場景。李應珍因反對議和,被軟禁了起來,他身邊的81壯士也被陸續調走,最后飲下毒御酒身亡。壯族人民在講述李應珍的傳說時,自覺或不自覺地多次提及壯家81壯士,反映了壯族人民積極投身于抵御外侮的斗爭中去的迫切愿望,同時也體現了壯族民族的凝聚力,也可以說是一種民族歸屬感和認同感的集中體現。
四、獨特的英雄形象
李應珍傳說用“白描”的方法來塑造人物形象。“傳說中的人物形象不注意外在的肖像描寫和內在的心理刻畫,而是用夸張的手法,從故事情節的開展和人物的行動來展示性格特征。而正面人物多半是理想化的,有的甚至是神化為具有超人力、超自然的本領,從而表現出人物精神的美好和高尚。”[6]壯族勞動人民用夸張的語言對李應珍參與中法戰爭這一歷史事件進行了口頭創作,集中塑造了具有典型特征的李應珍。人們將所有對英雄的美好的愿望和崇拜集中到李應珍一個人身上,來表達他們對民族英雄的景仰之情。
人們用“一邊唱山歌一邊拾糞的粗壯漢子”來展現李應珍地地道道的壯家漢子的風采;用“那個騎著黑色高頭大馬的漢子,就是李應珍了”來表現李應珍奔赴疆場的昂揚斗志;用“山坡上,身著紅袍的李將軍,捋著胡須仰天大笑”來反映李應珍在戰斗中勝券在握;用“騎著馬,揮著刀,他的戰袍上濺滿了污血,一個個洋鬼子的頭滾落于他馬下”來體現李應珍在戰斗中勇往直前。人們在講述李應珍的傳說時,沒有注意李應珍外在的肖像和內在的心理刻畫,而是以簡單的線條和離奇的故事情節來塑造他們心目中的李應珍。
壯族勞動人民賦予了李應珍諸多優良性格品質,幻想性地塑造了一個近于完美的“箭垛式”英雄形象。李應珍好比箭垛,而勞動人民豐富的想象力則有如一支支射向箭垛的飛箭。在民間傳說中,人們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在李應珍的基礎上增添一些有助于塑造其英雄形象的元素或事件。由此,李應珍被神化為壯族獨有的“戰神”般的存在,成為了壯族勞動人民精神家園的依托。
五、一定的傳播范圍
民間傳說總是圍繞一定的客觀實在物敘事,敘事風格也要受到歷史、受到客觀實在物的限制,這就使其流傳的范圍也會圍繞著客觀實在物進行。因此,其傳承范圍是相對固定的,受到傳說內容的限制。壯族人民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愛憎和好惡來塑造了大眾喜聞樂見的李應珍,并通過口耳相傳來進行傳播。壯族人民在歌頌自己的英雄時,難免受到語言和地域的限制。
日本學者柳田國男在談到傳說的特點時提到:“傳說有其中心點。……傳說的核心,必有紀念物。無論是樓臺廟宇、寺社庵觀,也無論是陵丘墓冢、宅門戶院,總有個靈光的圣址,信仰的靶子,也可謂之傳說的花壇發源的故地,成為一個中心。”[7]李應珍傳說以李應珍為中心,主要流傳于云南省文山州硯山縣,以硯山縣為中心向四周散布。馬關縣流傳有堵陣河的傳說,講述了堵陣河的來歷與李應珍密切相關,李應珍在堵陣河與法軍展開了激烈的戰斗。這即與李應珍參與中法戰爭的傳說相輝映。
眾所周知的口耳相傳游戲就明顯地反映了話語在傳播過程中的變異對話語一致性的影響。李應珍傳說以口耳相傳作為流傳方式,一傳十、十傳百,其故事情節在傳播過程中難免發生一些微小的變異。但是“萬變不離其宗”,畢竟李應珍被塑造為集體性的英雄人物,凝聚了所有壯族勞動人民關于英雄的整體概念。無論該傳說在民眾講述過程中如何添加自己的元素,其主體還是難以發生較大的變化。
概而言之,民族的居住地域和分布情況、民族的語言隔閡或方言差異、傳播過程中的變異性就使得李應珍傳說具有一定的傳播范圍。李應珍傳說的流傳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主要流傳于李應珍生活的地區,以硯山縣為中心點,逐步向四周擴散。
六、結語
壯族民間李應珍傳說是壯族勞動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它由中法戰爭的一些歷史事件糅合并嬗變為一種民間口頭敘事文學,經過壯族勞動人民不斷地傳承和傳播,有一定的教育功能和審美感受。李應珍傳說是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它通過全體壯族勞動人民的口頭創作,塑造了“箭垛式”的英雄人物。
從傳說的敘事內容來看,李應珍傳說以中法戰爭的一些歷史事件為基礎,匯聚了壯族勞動人民的奇特幻想,呈現了神奇而又仿佛真實的景致,歌頌了以李應珍為代表的壯族人民反抗外國侵略的決心。總而言之,歷史事件的藝術化、離奇曲折的故事情節、濃烈的民族色彩、獨特的英雄形象、一定的傳播范圍始終貫穿于李應珍傳說的敘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