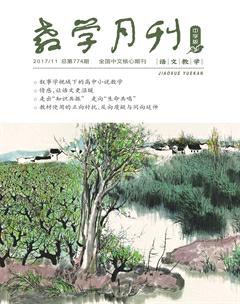走出“知識共振” 走向“生命共鳴”
2018-03-07 17:42:00鄭俊
教學月刊·中學版(語文教學)
2017年11期
鄭俊
摘要:學生對古詩詞產生“共鳴”是生命閱讀的基礎,而“共鳴”是因古詩詞所蘊含的詩人的情與思與學生內心某一刻的生命經驗具有某種普遍存在的相似性,因此古詩詞教學要真正實現“對接學生生命經驗”的目標,須走出“知識共振”的現象,走向“生命共鳴”的本色。
關鍵詞:古詩詞教學;共鳴;生命經驗
毋庸置疑,當前的高中古詩詞教學在“教材”“教學”等方面都存在著諸多問題:“量的不足”——各種版本的語文教材所選錄的古詩詞數量難以支撐學生生命發展所需的文化成本;“質的不足”——古詩詞教學仍停留在“寫什么、怎么寫的、為什么寫”的“淺讀、淺知”層面上,鮮有對接學生生命經驗層面的“深讀、深知”的實踐。盡管學者和教師深知這種淺嘗輒止的教學形式難以觸動學生生命經驗的發展,但是卻苦于當前古詩詞教學理念研究的破局之難,教學形式的積重難返,而不得不在這條難有“生命共鳴”的教學之路上愈行愈遠!
古詩詞教學雖然只是語文課程體系中很小的一部分,卻同樣承擔了語文學科絕大部分的課程目標。古詩詞教學如何與學生生命經驗對接的研究,至少應該成為當前屢受詬病的語文課程破局的關鍵一環,而破解這一生命棋局的重要一子便是“共鳴”,從“人的發展”的角度來說,沒有共鳴的古詩詞教學是無法實現生命經驗的對接的!
共鳴本指物理上的共振發聲現象,在文學的范疇是指描述思想或情感的一種狀態,是人與人在思想上有相同或相近的感受和理解,或情感上相互感染相互影響,或在心靈上的一種默契,它側重于“情感、思想、心靈相互感染而產生的媾和融通的情緒”。……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