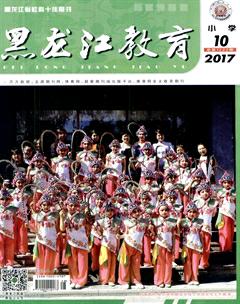遇見
郭聰
世間的一切都是遇見。就像冷遇見暖,有了雨;冬遇見春,有了歲月;人遇見人,有了生命。
我喜歡旅行,每次旅行最能打動我的不是風景,更不是繁華的城市和故作姿態的表象,而是人,是在路上遇見的那些喜歡或者不喜歡、認同或者不認同但平凡生活著的人。正是他們各不相同的人性,在那個與我航跡交錯的瞬間改變、點化并充盈著我的人生。
記得從林芝到拉薩的路上遇見許多磕長頭的人。以前曾經聽說藏族教徒磕長頭的事情,直到來到西藏,才有了更真實、更深刻的感受。藏族人民對佛的虔誠,是其他民族所無法比擬的。在他們心目中最能表達對佛誠意的舉動,就是獨一無二的磕長頭。他們會不遠千里,五體投地,用自己的身長丈量著、詮釋著對信念的追求。我為他們算了一筆賬:林芝到拉薩有400公里路程,他們就要磕10萬個長頭,才能丈量完這個距離。而每個磕長頭的動作設為1分鐘,則每小時磕60次,每天按凈磕10個小時算,是600次。那么,10萬個長頭,就得耗時170天左右,就是半年時間啊!
這半年時間中,不論酷暑嚴寒,還是風雨雷電,他們就這樣不受干擾、不受阻擋、不受任何誘惑地做著同一個動作。蓬頭垢面,就是他們的形象;衣衫襤褸,就是他們的旗幟;圣城拉薩,就是他們眼前的燈塔。而當你看他們的表情時,絲毫不見痛楚,也沒有特別的喜悅,只有平和,平和得就像是西藏的天空一塵不染。我沒有敢打擾任何一個磕長頭的人,因為他們讓我覺得圣潔和崇敬。我不停地思索,要做到這一點,需要何等的力量和毅力!我為之震撼,也為之動情!從此,每當我做事想放棄時,我就會想起這些人,想起他們教給我的虔誠,想起他們交給我的篤定,想起他們教給我的堅持!
許久以前,我就對南太行深處叫“郭亮村”的地方非常感興趣。喜歡“郭亮村”,源于它給我的那種與世隔絕、飄飄渺渺的感覺。這個村坐落在海拔1700米的懸崖之上,只有80多戶人家,300多口人。以前人們要下山,只能走一條“天梯”,就是在懸崖邊上走出的一條小路,特別險要,因此村子基本上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現在村里有了一條“掛壁公路”與外界相連。這條公路,最寬的地方只有四米,一邊是壁立千仞的峭壁,一邊是萬丈深淵,而且沒有護欄,一個急彎接一個急彎,全部在崖壁上。在這條路上行駛,你會真正體會什么叫心驚膽戰。而這條所謂的公路,其實就是村民硬生生鑿出來的洞。這個洞是不規則的拱形,依著絕壁的邊緣,蜿蜒伸展,而向外的一側,每隔一段的距離,就開一個口,通氣透光。它被譽為 “世界第九大奇跡”“世界最險要公路之一”。村里的老人跟我們介紹說,從1972年到1977年,村中13名壯勞力自發組成鑿洞突擊隊, 在沒有任何機械的情況下,用土法測繪,揮舞鐵錘、鋼釬,向絕壁上一錘一錘地鑿去,打禿了鋼釬12噸,打爛了8磅重的鐵錘4000個。當時上至70歲的老人,下至十幾歲的娃娃都輪流到隧道里清理石渣,這是現代版的“愚公移山”!
13位英雄已經所剩無幾。我們有幸遇見了其中的一位。聽說原來他會驕傲地為遠方的客人講述那段艱苦的歷史。現在他年齡大了,我們只能看到他滄桑的背影,但依然偉岸。不過村里的每戶人家都會深情地講述那段過往,他們真心地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自豪。從此,每當我遇到困難想要退縮時,我就會想起這條“掛壁公路”,想起村里的人,想起他們教給我的無畏!
在日喀則逛街時,貿然走進一家唐卡店,遇見了一位畫唐卡的畫師。我們進到屋里,他沒有看到我們,依然專心地畫他的唐卡。于是我們輕輕走到他的身后,想看看唐卡究竟是怎么畫的。這時,他才注意到我們。我們略帶歉意地實話實說,并不想買唐卡,只是好奇,想看看這么漂亮的畫是怎么畫出來的。他沒有介意我們的打擾,有些羞澀地用濃重的藏式普通話和我們聊了起來。我問:“畫一張唐卡大概要用多長時間?”他說:“手上的這一張要用一年,準備去參加北京的展覽。”畫一張畫要用一年,我很吃驚。看到我驚訝的表情,他說:“畫唐卡是個需要一定功底的事情,從打稿到幾遍上色,不能有一點失誤,需要控制內心,要有一個安詳寧靜的心態。真正的唐卡,即使是大紅大綠,你看到以后內心也是平靜的。”我問他:“畫唐卡累嗎?”他很平靜地說了兩個字“幸福”。沒有過多地打擾這位畫師,我們帶著思索離開了他的畫室。雖然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記得曾經看到過一個關于“人為什么老是感到不快樂”的科學研究,結果很意外:和幸福直接相關的不是財富、相貌、種族、婚姻……甚至不是你是否生活在和平的環境里,而是一個人保持專注的能力。越是能長時間專注一件事情的人,幸福指數越高。我想這位畫師的幸福就來自于對一件事情的專注!
在新疆葡萄溝里遇見了一位普通的賣葡萄的大叔,他的長相我已經記不清了,銘刻在心的是他的熱情與善良。在小學二年級的語文書中有一篇課文叫《葡萄溝》,里面描寫的葡萄溝景色優美,瓜果飄香。作為一名語文教師,來到新疆,就必須到那里去看看。我們去的季節正好是葡萄豐收的時候,幾乎每家門口都會有一個小攤在賣水果,尤其是葡萄的種類特別多。熱情的維吾爾族老鄉讓我們隨便嘗,喜歡哪種就買哪種。我們選了兩種葡萄,每樣要一斤(新疆是一公斤)。老鄉用蹩腳的普通話對我們說:“我們這里的葡萄特別好吃,多買點吧。”我們遺憾地說:“只有一家三口,晚上還要去甘肅,買多了吃不了該壞了。”老鄉聽我們是外地口音,就問我們是從哪里來的,我們說是從東北的哈爾濱來的。他一聽,做了個非常夸張的動作說:“好冷的地方呀!”我們笑著回答:“可不,冬天要零下二三十度呢。”他聽說我們來自哈爾濱,就往稱好的葡萄里多放了一串,還拿起旁邊的一個哈密瓜說:“這個也拿著。”我們愣住了,他見我們有些詫異,趕忙說:“不要錢,不要錢。哈爾濱來的不容易,哈密瓜好吃。”我們連忙說:“這怎么行,不能要。”他有些倔強地說:“一定要。”我們說,那就得給錢。他說:“不值錢,不要錢。”推脫了幾次,包車的司機說:“你們就拿著吧,不拿著他該不高興了,這兒的人就這樣的。”實在拗不過他,我們謝過之后,帶著沉甸甸的葡萄和哈密瓜離開了葡萄溝。說實話,葡萄溝的葡萄特別甜,哈密瓜也特別甜,但比它們更甜的是我們的心。人生沒有那么多的預設,生命的精彩就是不期而遇的美麗。異地他鄉,萍水相逢,撲面而來的是陌生人的熱情、真誠和溫暖人心的善良!
在泰國的芭堤雅遇見了三個年輕的音樂人。記得那天正好是正月十五,皓月當空,銀光遍灑,我們在將軍山的觀景臺上俯瞰整個芭堤雅。在觀景臺上這三個泰國青年,兩個人彈吉他,一個人敲著鼓,悠閑地唱著自己喜歡的歌。他們第一首唱的是泰國歌,第二首唱的是英文歌,我們隨著音樂的曲調,邊輕輕敲打著節拍邊欣賞著眼前的風景,無比愜意。第三首歌的前奏就非常熟悉,竟然是Beyond的《真的愛你》,只不過他們唱的是泰語版的。這個熟悉的旋律引起了在場10多個中國人的共鳴,于是變成了大合唱。三個青年看有人和他們一起唱特別開心,帶著燦爛的笑容,彈得更起勁兒了。整個觀景臺立刻成了歡樂的海洋,引得旁邊的幾個外國人也跟著一起手舞足蹈。那時那刻,異國他鄉,不分國籍,不論性別,大家彼此沒有芥蒂,都沉浸在快樂之中,這源于對音樂的熱愛。而那天又是一個特殊的日子,在正月十五這個日子里,當我們在異國同唱一首中國的歌曲時,每個人心中都升騰起一種莫名的情愫,是對國家的發自內心的熱愛。那個時候,我覺得這份熱愛比其他任何時候都更濃、更重!
堅持、無畏、專注、善良、熱愛……這些都是我在旅行中的“遇見”。我們總是在仰望和羨慕著別人的幸福,如果愿意回頭,我們會發現,自己同樣正被仰望和羨慕著。
生命是一段旅程,是一次又一次的“遇見”,遇見那個你最想成為的自己。當一切都經過了,一切都走過了,一切都熬過了,生命的底色里,便增了韌,添了柔。這時候,平和下來的生命,便可以沉靜到動不驚,擾不亂。
其實我更想說,每天都是一次新的旅行,“遇見”的每一個和我們走過一段的人都值得珍惜!
(作者單位:哈爾濱市香坊區教師進修學校)
編輯∕王劍慧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