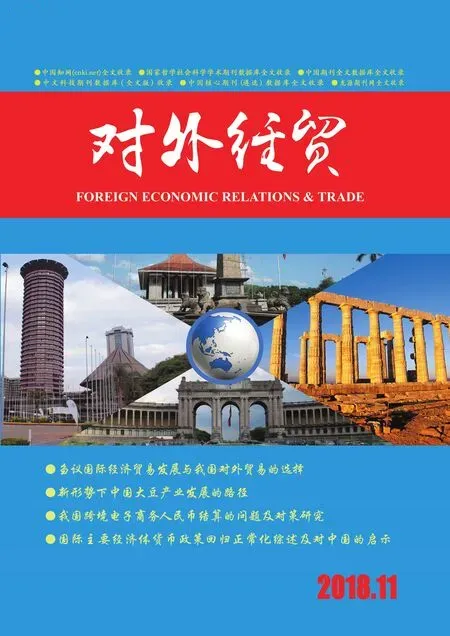數據本地化措施及其對貿易的影響
畢 婧 徐金妮 郜志雄
(寧波工程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浙江 寧波 315211)
當前,全球貿易經歷傳統貿易、全球價值鏈貿易(GVC),進入了數字貿易時代(OECD,2017),數據成為數字經濟的關鍵要素,被譽為“新時代的石油”。出于對國家安全和保護隱私權的考慮,許多國家對跨境數據流動進行規制,制定法律及政策措施對本地化數據的收集、處理、存儲及跨境流動進行監管。從一定角度看,數據本地化措施限制了跨境數據的流動,成為數字貿易的壁壘。因此,研究數據本地化措施的具體類型,分析其對貿易的影響,探討應對策略,對推進中國數字貿易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數據本地化措施及其類型
數據本地化是指數據來源國(地區)政府對在其關境范圍內產生、收集的數據的存儲、加工和使用進行監管,使之符合本國法律規定或政策要求。數據本地化通常分為個人信息保護和數據跨境流動兩個層面。數據本地化措施早于互聯網的出現,始于1961年。根據歐洲國際政治經濟研究中心(縮寫ECIPE)的研究報告,1961年至2016年期間,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與普及,全球范圍數據本地化措施的數量逐年增多,2000年全球本地化措施只有19項,2016年達到84項,涉及64個經濟體。目前,數據本地化措施主要分為三大類:有條件的跨境傳輸、本地存儲、禁止傳輸及本地加工要求。其中,有條件的跨境流動的措施要求在數據轉移到國外之前必須達到本國規定的特定條件,這類措施的數量較多,占42%;本地存儲的措施允許數據本身可以在國外處理,某些數據的副本必須留在國內,這類措施占25%;禁止傳輸和本土加工要求是對數據限制最嚴格的措施,這類措施要求該公司使用本地服務器進行數據的主要處理,在禁止傳輸的情況下,即使是數據副本也不能離開,占33%(Ferracane et al.,2018)。
二、不同經濟體及國際組織對數據本地化的相關規定
發展中經濟體對數據本地化的要求中,有共性也有差異(見表1)。如中國、俄羅斯都要求數據在境內存儲、加工,巴西、印度對與國家安全有關的數據也有同樣要求(陳詠梅和張姣,2017)。對于數據跨境流動,有的國家規定需要評估(如中國)和提前告知,印度、巴西對于訪問和處理沒有命令禁止。

表1 發展中經濟體對數據本地化的主要規定
發達經濟體的數據本地化規定中,美國提倡數據自由流動;歐盟則是在注重保護居民合法隱私權的基礎上,促進消除跨境數據流動的限制;澳大利亞對個人健康記錄跨境流動規定最為嚴苛,原則上禁止出境(特定例外情形除外);日本是在獲得本國認可的第三方取得數據主體同意的情況下可以進行數據傳輸(見表2)。

表2 典型發達國家對數據本地化的主要規定
國際組織原則上鼓勵數據的跨境流動,同時也有例外條款。《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的指導思想是逐步自由化,GATS下的義務以具體承諾為準,同時也為防止消費欺詐、個人隱私和數據保護等設置了例外條款;當前的當地儲存和加工數據等本地化規定有可能違反GATS第16條的具體承諾義務(彭岳,2018)。OECD的《關于隱私保護和跨境個人數據流動的指南》(2013)規定,成員國應采取合理、恰當步驟確保個人數據的跨境流動,避免以保護隱私和個人自由為由制定法律,同時也規定:可以根據本國的隱私法對特定類型的個人數據施加限制,或者是因其他國家沒有提供同等的保護而限制(李海英,2016)。此外,有較大影響的區域協定《環太平洋貿易伙伴關系協定》(TPP)第14章的目標是促進互聯網的開放和電子商務的跨境自由流動。該章第11條規定:當通過電子方式跨境傳輸信息是為涵蓋的人執行其業務時,締約方應允許此跨境傳輸,包括個人信息;為實現合法公共政策目標,締約方可以采取或維持與上述不符的措施,但該措施不能構成不合理歧視,或對貿易形成變相限制;也不得施加超出實現目標所需要的限制。
三、數據本地化措施對貿易的影響
(一)抑制全球數字貿易的發展
目前,全球服務貿易中有一半以上已經實現數字化,超過12%的跨境實物貿易通過數字化平臺實現。各國越來越依賴數字貿易的發展,數字連接產生了商品和服務之間新的互補性,國與國之間最低互聯網使用量增加10%,郵電部門出口增長3.2%。發達國家雙邊數字連通(Digital Connectivity)增長10%與出口增長5%相關。發展中國家數字連接的同等增長帶來0.12%的出口增長(López González & Ferencz,2018)。而數據本地化措施會提高國家間數據傳輸的貿易成本,增加貿易雙方的對接成本,限制貿易機會,形成數字貿易壁壘。鮑爾等(2017)的GTAP模型測算表明,數據本地化對巴西、中國、印尼、韓國和越南的商品出口的負面影響高于服務出口。此外,不同國家間對數據隱私的立場不同及數據本地化措施的差異會直接引起國家間貿易糾紛的發生,不利于貿易環境的穩定。
(二)限制經濟增長,間接影響貿易發展
受到數據本地化的影響,采取數據本地化措施的國家的GDP發展速度也會受到影響。在印度尼西亞,數據本地化法律使其GDP減少了0.7%,投資減少了2.3%(Bauer et al., 2014),歐洲的數據本地化使歐洲GDP損失約0.27%(ECIPE,2016)。這也將間接影響貿易的發展。
(三)不利于發展中經濟體中小微企業貿易競爭力的提高
云計算和大數據為政府、消費者和企業帶來了巨大利益,提高了生產效率和成本效益,推動了經濟增長。而數據本地化措施的實施卻違背了技術行業對于全球經濟規模效應的經濟邏輯(Mishra,2016),那些“被隔離”的供應商再也無法獲得全球云的好處,破壞當地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的發展和創新能力,不利于中小微企業高新技術的發展,降低了其貿易競爭力。
(四)有利于新興數字貿易相關產業的保護
數據本地化的實施一定程度上對國內信息技術及相關產業起著保護作用。一方面,數據本地化可以把只能提供跨境服務的外國企業排除出國內市場;另一方面,數據本地化增加合規成本,削弱外國企業的競爭優勢。例如,在美國新建一個數據中心的成本是4300萬美元,在智利是5120萬美元,在巴西是6090萬美元(黃寧,2017)。同時,云計算、3D打印等數字化相關新興產業都需要大量數據傳輸,數據本地化措施保護了本土的新興產業。
綜上所述,數據本地化有利有弊,各國政府應當處理好保護居民隱私、國家安全與數據跨境流動之間的關系,在為隱私、安全設立最低的安全線的基礎上,應鼓勵跨境數據合理流動,以推進與世界其他國家間的數字聯系,共享數字貿易發展的紅利。據波士頓咨詢公司預測,2035年中國整體數字經濟規模將近16萬億美元,數字經濟滲透率48%,就業達4.15億。對于中國來說,應適度保護好居民的數據隱私權,分類管理跨境數據,合理規劃跨境數據流動,逐步減少數據本地化限制,增強數字貿易的競爭力,推進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